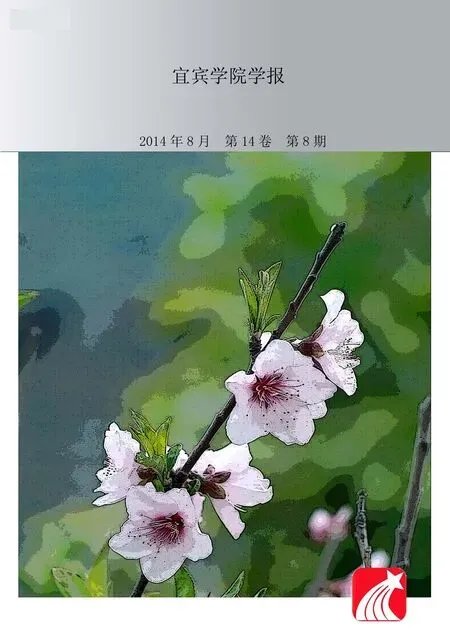從電影與文學的關系論《一九四二》之改編
高 玥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自從梅里愛、格里菲斯將一個個鮮活的虛構故事搬上銀幕,電影就開始積極地從文學藝術中尋找靈感。文學改編為電影創作打開了另一扇大門,也使電影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成為了人們關心和爭論的焦點。電影與文學是兩種表達方式與接受形式截然不同的藝術,但都在通過敘事反映人類的思想和情感。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始終相互影響,交織起千絲萬縷的聯系。對電影與文學關系的認識不僅影響著人們對待電影時的態度,也在影響著電影創作的發展。
一 電影與文學關系的歷史之辨
關于電影與文學的關系,理論界長久以來形成了兩派迥然相異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電影與文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偏激的觀點將電影劃歸到“大文學”的范疇當中,作為文學的一種。如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所認為:“沒有必要把電影看作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就它的虛構形式而言,它有與小說相同的意圖,就像小說與戲劇有相同的意圖一樣。”[1]較為客觀中庸者,如國內的電影學者張俊祥等則強調電影具有文學性,認為電影藝術的品質高低,很大程度上與電影的文學性有關;電影藝術的提升,離不開對電影文學性的重視和發揮。前者的觀點忽視了電影作為一門獨立的第七藝術的藝術特性,過于偏激;而后者用文學性來概括電影從文學中借鑒來的藝術特性也是不恰當的。
一方面,電影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是借鑒了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等多種藝術的部分藝術特性后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獨立的、統一的藝術。在電影最初的發展時期,這種融合還不夠協調穩定,但隨著電影藝術的成熟,它所借鑒的文學特性已經協調、融合于它的整體藝術特性之中,不再等同于原來存在于文學中的藝術特性。電影有了適合于自己的聲畫表現、蒙太奇思維及片長時限的獨特敘事方式,有了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和表達思想的角度。電影藝術的發展又反過來對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新的影響和啟發。用文學性來概括文學與電影之間相似的,可以相互借鑒的藝術特性是一種從文學本位出發的認識,這種認識忽視了電影藝術本身的敘事能力和洞察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若從文學本位出發,來探討文學性問題,則可發現,文學性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難以清楚完整定義的概念,不同的文學研究者會給出不同的答案,這樣的文學性與電影文學性的所指也是有差異的,用文學性來談電影的問題,容易使人產生對電影藝術特性的誤解,因此也是不合適的。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并不應該被過分夸大,電影與文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形式。如諾曼·梅勒所說:“電影與文學相去甚遠,比方說,就像窯洞繪畫與一首歌”[1]。而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則更加偏激,聲稱“電影和文學毫不相干;這兩種藝術形式的特性和本體通常是互相沖突的”[1]。我國文學歷史悠久,擁有著很高的地位,電影藝術在中國誕生的最初,就是通過對文學的改編,提高了自己的敘事功能,獲得發展。從“第三代”到“第五代”的電影人都非常重視文學對電影創作的借鑒,傾注大量的精力在文學改編電影的創作上,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限制了中國電影發展的更多機會。我國的專業劇本創作行業一直不受重視,造成現在國內的電影創作常常陷入缺乏好劇本的窘境,電影表現技術與藝術風格的發展也一直比較滯后。從西方電影藝術與技術的發展中,國內影人開始逐漸意識到電影藝術本身的各種可能性,從“第六代”開始積極地倡導電影的獨立發展,強調電影的“電影性”,將文學僅僅作為電影的素材來看待,反映在文學改編電影的創作中,則表現為導演放棄對小說原著的忠實。批評家主張將文學改編電影與小說原著看作為兩個獨立的文本,強調文學改編電影的作者是導演,與小說作者沒有必然聯系;強調電影的“電影性”糾正了國內電影過去對文學的依附,有利于對電影藝術本身展開深入地探索和開發。但從電影與文學的相似特性來看,擁有幾千年發展歷史,表現手法、流派多樣,人文內涵深厚的文學對與年輕的電影藝術來說,絕不僅僅只是素材。前蘇聯電影理論家波高熱娃說:“沒有對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巴爾扎克的作品的改編,那么電影的歷史是不堪設想的。”[2]文學敘事技巧對人的注意力、興趣、情緒和感知探索;敘事者觀察人、事的角度,思考的高度,對人類精神深刻細微的洞察力,都是作為同樣通過敘事來反映人類精神不同側面的電影藝術需要學習的。雖然電影是一種大眾消費藝術,但如果只表現娛樂而沒有深厚的人文積淀,那將與馬戲團演出沒有區別。
由上述辨析可以明確,電影既不屬于文學,但其發展也離不開文學。法國學者艾·菲茲利埃所說:“文學和電影的關系可以歸結為兩大問題:電影能夠為文學帶來什么?文學能夠為電影帶來什么?”[3]文學改編電影的過程最突出地體現了電影與文學的這種互動關系。馮小剛的《一九四二》是2012年國內文學改編電影的一部佳作。原作《溫故一九四二》是一部散文化的紀實文學,對于改編成電影有較大難度,但導演和編劇最終成功地將這部沒有任何劇情、人物,結構松散的紀實文學改編成了一部非常忠實于原著精神的影像化作品。以下筆者通過對這部影片改編得失的分析,對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做出考察。
二 文學與電影的忠實轉化
《溫故一九四二》是作者通過對經歷了1942年河南大災的許多人物的采訪及翻閱大量相關歷史資料后寫成的,主要內容是對1942年河南大災被埋沒的一段歷史現象的陳述及反思。作品用紀實風格的平實文字挖掘了那段關于“吃的問題”不再被憶起的歷史,并從民眾的角度進行反思,提出“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4]的問題。馮小剛被這部小說所挖掘出來的那段令人震驚卻被人埋沒、不愿提起、不為今人所知的歷史真實以及作者審視那段歷史的獨特角度與反思所打動。這部作品本身具有較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和人文價值內涵,因而在文學改編電影是否要強調忠實性的問題上,答案毋庸置疑。一方面,從觀眾的接受心理角度,讀過小說的人看電影往往是出于一種還原想象的心理欲求,而不是去看導演對原作解讀的一家之言;沒讀過小說的觀眾則多是想通過電影管窺原著的風貌,而不想被導演和編劇的篡改所誤導。另一方面,這恰恰是采用文學來改編電影的原因和意義所在。文學具有反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而電影則更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電影與文學始終存在著媒介上的互動關系:電影借助于文學改編,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題材和視角;而通過電影,文學的記錄和沉思也將得到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因此,對于優秀的文學作品,電影與文學之間的這種媒介轉換更強調忠實性。
喬治·布魯斯東說:“小說家和電影導演的意圖是相同的,都是讓人們去看見,但小說家讓讀者通過頭腦的想象來看,導演讓觀眾通過肉眼的視覺來看。而視覺形象所造成的視像與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兩者間的差異,就反映了小說和電影這兩者手段之間最根本的差異。”[5]歷史總是復雜多變而又匆匆過去的,相對于影像而言,文字更便于記錄歷史的復雜面貌;而電影作為造夢工廠,能夠實現許多我們在現實中已經不存在或無法實現的景象,因而它更能還原歷史。在《溫故一九四二》的改編中,編劇和導演選擇了通過畫面還原歷史現場,而沒有采用如小說中的現實主義的紀實回憶。小說可以通過人物的行動來講述故事,也可以展現人物的思維來表達思想,而電影則主要通過人物的行動來講故事。因此在還原歷史的改編中,需要將原小說中平白簡述的內容加以虛構擴展,轉化為具體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們的行動。小說中的深思則只能通過對人物的行動和臺詞的具有表現力的設計來暗示性地傳遞給觀眾。在《一九四二》的改編中,編劇虛構了范財主一家、平民瞎鹿一家以及信仰基督的小安等在那一段歷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形象,然后將小說中平鋪直敘的歷史現象提煉擴展為生動的故事情節,還原到了這些具體的人物身上。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對話,原小說中作者站在百姓角度審視這段歷史的感觀,通過畫面和故事的方式更直觀地傳遞給了觀眾。實現了文學向電影的成功跨度。
原作《溫故一九四二》主要挖掘了河南大災的歷史,卻并非僅僅挖掘和渲染那段被人們遺忘的歷史,而是將一九四二年作為整個歷史長河中的一片截下,從這一時間碎片中的歷史縱橫來觀照河南這次災難。因此,在電影敘事中,編劇首先確立了敘事人的全知視角,然后在原小說松散的內容中提出河南百姓逃荒與重慶中央執政兩條故事線索。第一條故事線索通過虛構歷史中的典型人物:范財主一家、平民瞎鹿一家以及信仰基督的小安等,將依據原作陳述的歷史現象提煉的故事情節,還原到了這些具體人物身上,用他們各自的命運把情節串到了起來。再將這一災民群體的歷史縮影丟到共同的逃荒路上,將他們的命運相互交織,結構成一個完整連貫的故事。在第二條故事線索中,編劇依據歷史資料還原了當時執政的歷史人物和國際國內的重大歷史事件,然后依據小說眾的虛構內容和第一條故事線的敘事擴展了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故事情節。在這兩條基本線索之下,作者將小說陳述中在這兩條線索間起關鍵作用的人物和事件:為救災奔走的白修德、主席李培基,阻礙救災的軍隊、官員以及利用救災侵略的日本人的故事等虛構擴展開來。至此,電影改編將文學作品中主要陳述的歷史現象以具體的人物關系和事件關聯成了一個有宏觀有微觀,背景宏闊而視角細微的整體故事文本,實現了文學向電影劇本的創造性轉換。
劇本是電影創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部,為整部作品的風格奠定了基礎。到影片的拍攝階段,導演為使電影畫面的敘事更加有力,更好地呈現歷史的真實感,電影中人物的衣著、道具都精心參考了歷史文物,演員挨餓表演以傳達更真切的感覺,龐大的群眾演員的調度形成了壯觀的歷史場面,飛機狂轟亂炸場面則采用近距離現場拍攝,畫面效果非常真實震撼。最終電影畫面的視覺沖擊力和音畫配合形成的震撼效果得到了充分體現。小說平淡描述的歷史現象以驚心動魄的真實場面生動地再現在觀眾眼前,觀眾更加直觀真切地感受了那段歷史的悲慘與沉痛。在后期的剪輯中,電影敘事將兩條故事線索交替關聯,營造了小說原作中宏闊的歷史視野。敘事進程中將第一條線作為主線,將范財主這個人物貫穿了整部影片,從而實現了作者在小說中所采用的平民角度看歷史的獨特視角。馮小剛全片以冷靜、克制的鏡頭風格主導,希望盡量將原作中打動他、引人深思的東西,客觀、完整地呈現給觀眾。最終影片達到了“看了原作需要去看電影,而看了電影則無需在去看原作”的成功效果。這樣就將一部并不適合電影表現的直陳而又瑣碎、思考多于故事的文學作品成功轉化為生動的電影形象,并達到了對原作內涵、風格的忠實傳遞的一部成功之作。
按照艾·菲茲利埃的思路,這部作品的改編中,文學給電影帶來了歷史材料,而電影則給文學帶來了現實的展示。文學可以有條理地記錄歷史、反思歷史,將對現實的記錄隨著時間慢慢轉化為歷史;而電影則通過文學將歷史還原為熒幕上的現實。杜阿麥爾說:“小說家是‘現在時’的歷史學家”。[6]文學對電影的這種不可代替的歷史文獻功能早在我國第一部文學改編電影作品《莊子試妻》中就已經表現出來,而電影創作者要想了解和表現過去,就必須求助于過去的文學,文學中對于過去的生活、情感、社會關系、情感表達方式、憂慮、禮儀和一般風俗等的形象記錄是歷史所無法達到的。此外,從媒介的角度來看,二者始終存在互動互補的關系:文學具有反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從而增強了電影的表現力;而電影的強大影響力則使文學中隨著時間而被人逐漸淡忘的沉思能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增強了文學的社會影響力。《一九四二》讓人們再次抬頭注意曾經被遺忘的那段歷史,也開始反思當下的社會問題。
三 文學改編電影的目標——超越
文學改編能夠忠實地傳達原作的廣闊內容、精神風貌和復雜內涵是優秀文學作品改編電影成功的標志,而文學改編電影的目的和意義則不僅僅于此。福樓拜早在他所生活的時代就意識到,文學改編的核心是“改編了的內容”。這個內容的改編指的是思想、認識、深度的突破。電影如果只是以另一種形式轉換了文學,那么也只能作為文學的副本而存在。優秀的文學改編電影,其目的則在于忠實基礎上的進行超越,超越已有的文學文本,達到一個從導演立場上的更高的高度或更寬闊的視野。這樣的電影改編作品就獲得了自己獨立的價值和生命,而不再作為原文學作品的影像化復制品。
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這部影片雖創造性的忠實了原文學作品中的內容、風貌,影像化的歷史再現非常具有沖擊力、渲染效果,讓觀眾的心靈通過電影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但在改編過程中,由于導演沒有更主動地去干預作品,盡管成功忠實地保持了原作反映歷史的客觀性與復雜性,但影片的敘事無主題和敘事動機可循。完全客觀地呈現一段不包含任何評價的歷史,這樣的客觀敘事中缺乏一種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樣能夠引發人的深思的力量。《一九四二》的劇本主要由劉震云本人依照他原本創作小說時的意圖和認識而改編,作家有他自己站的高度,也有他視野的局限,導演拍攝文學改編電影作品是站在作家的肩膀上看問題,其思考的起點和把握的高度應該更高于作家,而不應僅僅讓自己創作的電影完全忠實與作家的意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忠實了原作的哲學意蘊,但表現出來的卻是李安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間的更宏闊的視野。
《溫故一九四二》所能呈現的內容,能夠引發人深入思考的東西很多,從開篇對歷史的談論給人的啟發:歷史本是由人民而組成的,但歷史卻不是人民的歷史的提出。文章主體內容對“吃的問題”的表現,與現在這個豐衣足食卻糧食浪費極度嚴重的社會的關聯。再到文章中間部分論述的一種國家主義的觀念:“一塊陣地上死了一個逃亡的百姓,那這個征地還是中國的,死了一個兵那這塊陣地就不是中國的了”[4]。一塊土地先有了人民才有了國家,才有了軍隊,軍隊抗戰不是為了保衛國家的榮譽而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安危。但這種打著保家衛國旗號看似有理,而坑害百姓的觀念不光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我們現在社會上仍可窺見。結尾對“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后者”的問題的探討——當人民不被認可為人時,他們就要開始行使人的本能。
原小說可以進行更深入拓展的思考很多,然而導演并沒有從自己的角度深入下去,影片的改編除了忠實地呈現了文學敘事中的歷史和作者雜陳的討論,沒有從導演角度更深入追尋。最終導致影片中除了客觀地還原所呈現的悲慘情境和人情悲喜,沒有突出展現能夠引起觀眾深入回思的點。影像的語言本身就是含混而復雜的,因而更需要導演的引導與掌控。如喬治·布魯斯東所說:“攝影機不能充當托爾斯泰,也不能充當喬伊斯,它并不能很好地處理主要人物的蕪雜狀態,也不能對現實世界作全景式的關注。它也不能解剖思維在言語的復雜錯綜之中的隱秘生命。”[5]而馮小剛卻放棄了介入鏡頭的機會。《一九四二》將極度慘烈的歷史以克制不煽情的方式表達出來,并且帶有了一絲諷刺的幽默,這本是表現這樣的災難提出的一種獨特的方式,卻缺乏更深入的主題的引導,使這部本可以闡發更多引人深思的歷史大片,僅僅呈現為了一部還原歷史的記錄文獻。
結語
從這部作品改編的遺憾之處來看,電影與文學畢竟是各有優勢的兩種不同的藝術,文學為電影提供了豐富的視野和藝術借鑒,但電影不能成為文學的影像化附庸,電影是站在文學的肩膀上發展起來的,因此電影改編文學更需要的是超越。《一九四二》這部馮小剛醞釀了18年、籌備9個月、拍攝135天、制作8個月、耗資2.1億的電影,傾注了導演許多的心血,作為一部以與眾不同的角度,勇敢地回顧災難歷史的嚴肅大片,這在國內的商業電影中是少有的,這種勇氣和影片的歷史意義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但作為一部文學改編電影,我們還需思考,在表現人類精神世界的領域,電影要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超越文學。
參考文獻:
[1] [美]莫·貝哈.電影與文學[J].齊頌,桑重譯.世界電影,1989(6).
[2] [前蘇聯]波高熱娃.論改編的藝術[J].俞虹譯.世界電影,1983(2).
[3] [法]艾·菲茲利埃.文學和電影的關系[J].卜禾譯.世界電影,1984(2).
[4] 劉震云.溫故一九四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5] [美]喬治·布魯斯東.從小說到電影[M].高駿千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8):1-69.
[6] 孟中.文學改編:一次特殊的電影心理活動[J].電影藝術,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