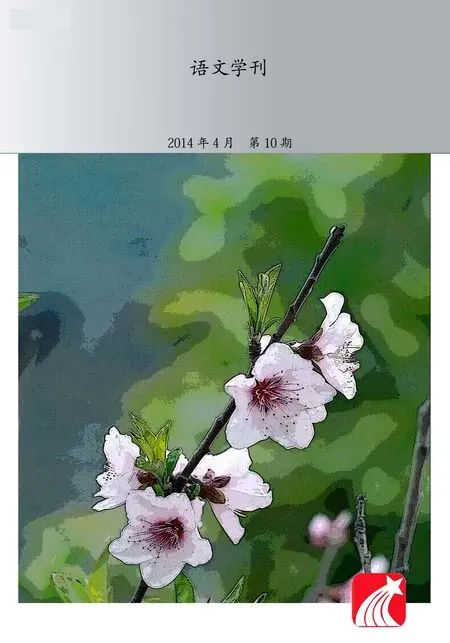民族化和全球化
——淺談全球化語境下西部文學的發(fā)展
○劉雪娥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眺望當今世界,經(jīng)濟全球化和技術一體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著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將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納入到世界大工廠的體系之中。如此迅猛而廣泛的經(jīng)濟大潮不僅影響著各國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影響著各國文化軟實力的發(fā)展,乃至文學的發(fā)展。在這樣一個經(jīng)濟方面全球逐步趨向統(tǒng)一的時代大潮下,曾以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地域文學,又該以怎樣的姿態(tài)去面對強勁的經(jīng)濟一體化進程?如何在宏大的全球化語境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亦或者說,西部文學是否會最終消解在全球化風起云涌的浪潮中,成為歷史記憶中多樣性的表征?面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西部文學應以怎樣的姿態(tài)在一體化進程中保持自我,發(fā)展自我,如何在風馳電掣的全球化中保持西部文學鮮明的民族性,不迷失,不趨同?
自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問題的討論一直熱度不減,相關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棟,卷帙浩繁。那何為“全球化”呢?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定論,但筆者比較認同何為在《“全球化”概念的語義闡釋》中的定義,他“從社會發(fā)展形式、時間、空間、人的實現(xiàn)方式、實踐過程、認知方式等六個維度進行了辮證闡釋,提出‘全球化’是一個‘多向度的綜合概念’的觀點,認為全球化是人類社會整體發(fā)展的一種全球多樣一體化形式,是人類社會化為全球性的過程,是對人類的閉關自守狀態(tài)的揚棄,是人類的本質(zhì)力量以新的方式的對象化過程,是主體與客體對全球性社會的雙向建構過程,是全球性社會的現(xiàn)實和理想從對立走向統(tǒng)一的過程”。
由此可見,盡管全球化具有世界性,但并不意味著徹底的,完全意義上的統(tǒng)一性,而是“多樣一體化”的既有多樣性,又有統(tǒng)一性的辯證統(tǒng)一。這就為民族性的存在留下了空間,也就是說,全球化并不否定和抹殺民族性,它與民族性的關系并不是要么你死,要么我亡的絕對對立,也不是歷史性的承接關系,即認為全球化是從多元走向一元的。相反,民族化和全球化是共時性的關系,民族化的發(fā)展是全球化發(fā)展的基礎,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化能夠促進全球化以生機勃勃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具有世界性的命題意義,也能使具有特色的民族性走向世界的廣闊舞臺。
因此,就西部文學這一具有民族性的地域文學而言,它在全球化語境之下的發(fā)展,也就不以抹殺其地域風情、民族特色為代價,而是在張揚和發(fā)展民族性的過程中,在多元文化的認同與吸納中,逐漸匯入全球多樣一體化的世界潮流,成為世界文化中獨立的奇葩。
縱觀西部文學的發(fā)展歷程,經(jīng)過許許多多西部文藝工作者不辭艱辛的耕耘,獲得了較大的發(fā)展,涌現(xiàn)出了一批以西部獨特自然景色為底色,書寫西部精神和人文底蘊的優(yōu)秀作家,如賈平凹,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對家鄉(xiāng)商州的風土人情進行深情的描繪,同時也將商州的發(fā)展放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召喚下進行審視和考察,在動態(tài)的發(fā)展中思考商州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成就了其獨具地域特色的“商州系列寫作”。還有阿來以反思民族文化的視角對藏族土司制度逐步瓦解的回望,張承志以堅守理想的態(tài)度對回族哲合忍耶為守護心靈圣地而前仆后繼誓死反抗精神的表現(xiàn),郭文斌以空靈飄逸而又略帶感傷的筆調(diào)對記憶中多情鄉(xiāng)土的詩性闡釋,董立勃在人道主義底色上,對現(xiàn)代性的平等、自由、尊嚴和人權意識的彰顯等等。正是這些作家在自身生命體驗之上對西部生存環(huán)境、生命遭際的深刻書寫,使西部獨特的文明形態(tài),包括自然環(huán)境、生產(chǎn)方式、社會進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樣性、混雜性、獨特性得以展現(xiàn),也使西部文學獨異于其他文學的美學特征和美學價值得以發(fā)現(xiàn)。在這些書寫中,西部文學不僅主動關注、參與、呼應著文學主潮的發(fā)展,與中國文學的整體趨向基本同步,而且也依據(jù)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因素,不斷抵近本土,發(fā)掘這一獨特文化形態(tài)的潛在資源。也就是說,西部文學的發(fā)展,一直都得益于西部文化獨特的民族性,這是西部文學得以自立自強的寶貴財富。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中,要使西部文學繼續(xù)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不僅需要我們以全球化的眼光重新審視西部文學發(fā)展存在的問題,在自省中開拓創(chuàng)新,而且要正確認識西部文學對傳統(tǒng)民族資源的利用和開掘,使西部文學以獨立的審美姿態(tài)參與全球多樣化審美形態(tài)的建構。
一、自省精神
人貴有自知之明,對本土文學的審視也一樣,要想使西部文學得以長足發(fā)展,就必須以客觀的自省精神認清文學發(fā)展的現(xiàn)狀,包括認清它存在與發(fā)展的優(yōu)勢資源,存在的問題,及至在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大的文學發(fā)展框架中它所處的地位和擁有的價值。西部文學發(fā)展至今,存在著一些影響西部文學進一步健康發(fā)展的問題,如話語建構的狹隘化、學術定位的模糊化、作品多精品少等等。因此,我們的自省就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對于“西部文學”內(nèi)涵的界定,我們知道,“西部”首先是地理的劃分,這個地理性的修飾詞限定了西部文學的地理范圍,盡管這種限定是相對的,但也有其界定性,使我們不會把如山東、天津、上海這些東部地區(qū)的作家創(chuàng)作歸于西部文學的范疇。同時,還得注意避免西部文學地域劃分的狹隘化,如在《簡明中國當代文學辭典》中,列有“西部文學”條,將其界定為“中國西北地區(qū)文學的統(tǒng)稱”,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將西部文學進行了自我縮軍,甚至有論者以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為例,認為“國內(nèi)的‘西部文學’之名也被‘西北文學’甚至還需要加上綴語的‘西北大部文學’冒領,這構成了國內(nèi)文學界中對‘西部文學’的后殖民理論想象的進一步狹隘化、邊緣化”。這或許是一種比較極端的看法,卻也有其合理性,在某種意義上警示我們?nèi)绾螢槲鞑课膶W定界。另外,更為重要的是,西部文學也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包含著諸如宗教底蘊、民族互融、文明形態(tài)、精神內(nèi)涵等諸多內(nèi)容。因此,必須客觀而準確地把握它的內(nèi)涵,既要避免概念界定的狹隘化,又要避免泛化的傾向,正確地為西部文學定位。
其次,不能固化對西部的認識,這里既有對西部作家的要求,又有對西部評論家的要求。就西部鄉(xiāng)土小說的創(chuàng)作來說,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涌現(xiàn)出了很多非常優(yōu)秀的作品,如賈平凹的《高老莊》、雪漠的《大漠祭》、陳忠實的《白鹿原》等,這些作品不僅是西部鄉(xiāng)土敘述中的精品,也是鄉(xiāng)土中國想象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板塊。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在西部鄉(xiāng)土小說敘述中存在著模式化傾向,敘述的場景往往都是“傳統(tǒng)文化積習深重,家庭血親關系穩(wěn)固,或是在現(xiàn)代文明和商品意識沖擊下發(fā)生經(jīng)濟和文化震蕩的西部村鎮(zhèn);而敘述的對象則是生于斯、長于斯的父老鄉(xiāng)親和他們的凡俗人生”。而且,由于西部長期的物質(zhì)貧困、生存條件的艱難,苦難化就成為作家敘述的主要內(nèi)容。如雪漠在《大漠祭》的前序中寫道:“我寫的不過是生之艱辛、愛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無奈而已。這無疑是些小事,但正是這些小事,構成了整個人生。我的無數(shù)農(nóng)民父老就是這樣活的,活得很艱辛,很無奈,也很坦然。”這樣的書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具有典型性,將西部農(nóng)民生存的痛苦體驗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也有局限性。因為時代在發(fā)展變化,地域文化也在發(fā)展變化,我們對其的認識不能停滯,不能僅僅停留在經(jīng)濟貧困等外顯的文化層次上,也不能停留在以奇特的地域風貌滿足讀者獵奇心理的表現(xiàn)層次上,更不能停留在由原始的惰性和凝重的習慣勢力造就的西部人愚昧麻木的生存境況的書寫上,而是要在動態(tài)發(fā)展中,試著去挖掘西部人的民族性格在時代變化中的新變化,表現(xiàn)文化的差異性和落差性,去尋找普世原則在西部生活的表現(xiàn),包括普遍的人性、理性與邏輯思維法則等,建構西部文學的普世價值,提升西部文學的思想性。當然,必須明確的是,追求西部文學的普世價值并不是要丟掉我們的民族之根,一味跟上世界的步伐,迎合世界的潮流,而是在我們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中探尋能夠影響乃至引導世界文化潮流的精華。
另外,文學評價是文學生產(chǎn)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評論家對作品評價的角度和立場也影響著西部文學以怎樣的面貌出現(xiàn)在廣大的讀者面前,因此西部文學評論家對西部文學的發(fā)展肩負著舉足輕重的責任。對于西部文學創(chuàng)作的美學風格,丁帆在《中國西部現(xiàn)代文學史》中概括為“三畫四彩”,即“呈現(xiàn)為外部審美要求的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的美學形態(tài),以及作為內(nèi)核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的美學基調(diào)”。這是對西部現(xiàn)代文學美學特征高度而準確的概括,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對我們對西部文學美學特征的研究具有指導性的意義。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概括性具有典型性和濃縮性,它在對事物的本質(zhì)特征做出概括的同時,也可能使事物的豐富性喪失,西部文學因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決定了它是一個豐富而多元的文學形態(tài),僅僅用簡單的概括難以將它的美學風貌一概而全。正如“新邊塞詩”代表詩人、著名散文家周濤也對“新邊塞詩”所做的反思,“對于‘詩美’,我不喜歡‘粗獷、豪放’的概念。美是豐富的,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強化某種東西只能損害文學。西部詩給人的錯覺與當時強調(diào)的表面現(xiàn)象有關,仿佛西部人就是能吃苦、耐勞。在這樣的‘豪放’中,人的深層的感情未能在‘新邊塞詩’中被發(fā)掘出來,發(fā)掘出來的內(nèi)心世界只是一個層面的,不夠豐富,詩人的美學追求應更深入地貼近自己的內(nèi)心感受”。從這樣的反思中,我們明顯可以感受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邊塞詩”因為過度強調(diào)其雄壯之美、陽剛之氣,而使“新邊塞詩”對美的描繪和闡釋有所局限,破壞了它的多樣性。而且,隨著時代與社會的更替和演進,許多文化因子也會加速裂變,文學元素的變化也就在所難免。因此,這就需要西部文學批評家不斷更新批評理論,與時俱進,嘗試用新的理論方法,從多角度、多方位對西部文學進行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解讀,挖掘西部文學中那些被遮蔽的話語,不斷為西部文學塑造有內(nèi)涵、有特色的新形象,擴大西部文學的影響力。
二、開拓意識
誠然,西部文學這些年來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這并不是我們故步自封、盲目自信的資本。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球化進程日益逼近,容不得絲毫的懈怠,怎樣不斷開拓和創(chuàng)新才是西部文學迎接全球化應有的姿態(tài)。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筆者認為西部文學應從對待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兩方面入手求得生存之地。
首先,“拿來”西方文化。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文學觀念的發(fā)展速度一直領先于我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始,我們就開始廣泛地向西方學習,借用其先進的思想文化觀念建構我們自己的現(xiàn)代文學觀。這些先進的文化觀念和文學觀念的引入,也確實為我們打開了新的思想天空,為我們反觀自身傳統(tǒng)提供了絕妙的參照,才使我們在對西方文化的借用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審視中形成了今天蔚為大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觀。井底之蛙止于井,天地大小限于井;天高海闊任鳥飛,乾坤無限覽無余。這就是對比,也是實實在在的差別,對西方文化持什么樣的態(tài)度,決定著我們的胸懷乃至視野是井中之天,還是域外之天。而且,沒有交流和互動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是一潭泛不起任何波瀾的死水,是終究要消亡的靜止的存在。只有多元文化之間的補充、質(zhì)疑、對話、競爭才能產(chǎn)生讓本土文化生機勃勃的引力,才是本土文學生命力之所在。因此,對待西方文化,我們依舊可以持有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既然已有車,何必閉門造車,拿來用之又何妨。不過,西方文化良莠不齊,魚目混雜,不能全盤吞吃,“要占有,要挑選”,對其要批判性的吸收和接納,即在辯證的認識中接受外來文化,增加知識容量,融會貫通,擴大視野,提升我們的思想深度,做有大氣魄、大胸懷、大視野的學者、作家。同時,要善于捕捉西方文化與民族文化碰撞的新火花,一種新的學術思想往往得益于這些新火花,它很有可能是本土文學新鮮血液滋生的契合點。
其次,要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偉大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每一個民族的職責是,保持自己心靈的永不熄滅的明燈,以作為世界光明的一個部分。熄滅任何一盞民族的燈,就意味著剝奪它在世界慶典里應有的位置”。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中,不能一味求同而不存異,只追求統(tǒng)一性而喪失民族性和多樣性,保持民族自我,永不熄滅民族之燈,才能在世界文學中占據(jù)一席之地。縱觀西部文學的發(fā)展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的發(fā)展受益于西部獨特的地域風情和多樣性的文化交融。神奇的天山、蒼茫的草原、無垠的大漠、烈風中的經(jīng)幡、烽火的殘垣、荒涼的戈壁等意象和景觀在西部文學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給人色彩濃烈、風格奇詭多樣的視覺效果,是西部文學賴以存在的背景底色。在這一背景之下,又有對西部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民族性格的關注,對西部普泛化的自然崇拜、隱秘的歷史、虔誠的宗教信仰的追尋。這都是其他地域文學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學資源。文化的多樣性則體現(xiàn)在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上,既有各少數(shù)民族游牧文化之間的沖撞與融合,游牧文化與內(nèi)地農(nóng)耕文化、現(xiàn)代都市文化的撞擊和融合,還有異質(zhì)文化的沖撞和融合,包括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與中華民族之間的交流,這種文化的匯流,形成了西部多元文化混合的特色。而這些都是西部文學得以憑借的文學資源,過去是,將來更是。無根之木會枯萎,無源之水會斷流,無基之房會坍塌,民族文化就是西部文學賴以發(fā)展的根本、源泉和地基,它是曾經(jīng)身處“邊緣”的西部文學實現(xiàn)“文化突圍”的珍貴財富,也將是西部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下謀求更好更快發(fā)展取之不盡的寶藏。因此,西部文學也只有深深扎根于此,接受多元混合文化的熏陶,探索西部人民的精神脈向,發(fā)現(xiàn)廣袤的西部與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聯(lián)系,才能在世界文化的版圖中為其找到恰當?shù)奈恢谩?/p>
縱觀當今世界局勢,全球化已經(jīng)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民族化與全球化的對話和交流在所難免。反思民族文化的優(yōu)劣性,繼承和堅守民族文化,挖掘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既是對全球化中多樣性建構的貢獻,也是對民族化中現(xiàn)代性建設的要求。因此,以對內(nèi)自省、對外開放的態(tài)度兼容并蓄世界各種優(yōu)秀文化,迎接不可避免的全球化進程,才是西部文學發(fā)展應有的姿態(tài)。
[1]丁帆.中國西部現(xiàn)代文學史[M].人民出版社,2004.
[2]雪漠.大漠祭[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3]何為.“全球化”概念的語義闡釋[J].西北人文科學評論,2009(10).
[4]田啟波.矛盾與解析:全球化的哲學反思[J].廣東社會科學,2003(06).
[5]黃祖橋.論全球化中的民族化[J].新視野,1999(03).
[6]王曉宏.關于普世價值的研究:問題與爭鳴[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2).
[7]曹永萍.普世價值民族化與民族價值普世化[D].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8]白浩.西部文學想象中的理論后殖民與主體重鑄[J].長江學術,2007(07).
[9]趙學勇.全球化時代的西部鄉(xiāng)土小說[J].唐都學刊,2003(01).
[10]賀云.淺談全球化語境下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J].理論與當代,2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