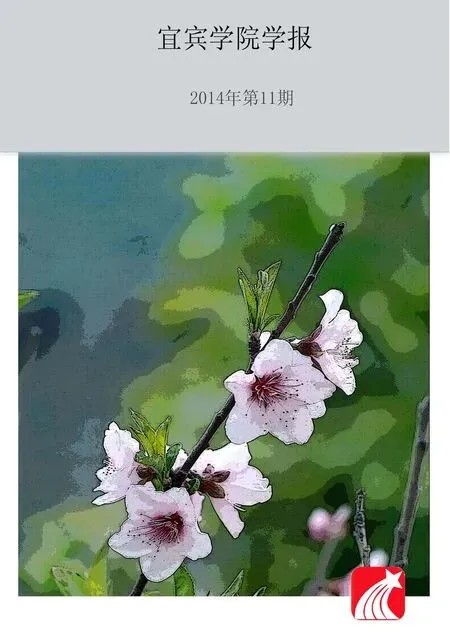中西自然宇宙觀之異同——朱利安《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觀》①讀書札記
岑詠芳
(法蘭西學院 漢學研究所,法國)
朱利安這篇讀書札記,發表于1984年他創辦的一份刊物《遠東遠西》(Extrême- orient,Extrême-Occient)第3期,117-125頁。記得當年,我曾去信唐師母講及此事,之后,師母回信表示高興,同時希望我能翻譯成中文給她看。可惜當時因能力及環境問題,雖然已開始了部分的翻譯工作,卻不得不停下來,如此一耽擱,倏忽不覺已三十載。今年有幸被邀參加宜賓舉辦之儒學論壇,適逢君毅師105歲壽辰紀念,謹藉此機會把這篇文章的翻譯續完,并整理成報告,聊表對老師、師母的致敬與懷念。當重拾舊篋,翻開書頁,字里行間,仍留下當年翻譯的筆跡;師母囑咐的信柬,亦赫然夾在書中,驚喜之余,不禁汗顏。這是我第一次來禮拜老師的家鄉,而提出的這篇論文報告,又恰好是關于法國學界第一次介紹老師的思想。
朱利安在1978-1981年間,曾擔任法國漢學中心香港分部主任。期間,他來新亞研究所聽徐復觀和牟宗三兩位先生的課,受徐先生的影響特深。1982年回到法國,出任巴黎第八大學教授,旋即創辦《遠東遠西》學刊。創刊詞標宗明義,以下所引,便是其宗旨概要:“西方對于理論的探索,越來越意識到不能再限于自身的傳統文化的領域里。然而,中國與西方之間,不能用一種簡單的比較方式,它是憑單獨的客觀存在的相似點為依據,只引來混淆與影響。如今這份刊物所選擇的方向,卻是從宏觀入手,因著‘相似性’而對‘相異性’的觀點予以重視,在面對未為人開發的場域,彼此文化,透過互相凝視的迂回進路,以思索其原創性的基調。”事實上,“迂回的進路”一直是朱利安透過對中國文化思想的探索,而引發對西方自家文化中那未思之境所持的方法,這可從他日后多年的各種著作中印證,從《勢》(La Propension des choses,1992)到《功效論》(Traitéde l’efficacité,1997);從《圣人無意》(Un sage est sans idée,1998)到《間距與之間》(L’écart et l’entre,2012),均溯游而上,迂回而進,從東方繞回西方,刻下思考的尺度,往往發人深省,精辟而具創見。
《遠東遠西》是一份年刊,每期以一固定題材為重心,從1982年開始至今已出版了32期,從無間斷。其范圍不單指向中國,并廣及日本、韓國,甚至東南亞。開始的兩期,分別以《中國詩學之比較與評論》(Essai de poétique chinoise et comparée),和《中國與革命觀:關于模式的問題》(L’idée révolutionnaire et la Chine:la question du modèle)為主題,嘗試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切入中西文化的共同點,讓其“互相凝視”,突顯兩者在文學,或在政治上的根本差異性。及至1984年第3期,則以《人與自然的關系》(Le rapport à la nature)為總題目,收入四篇文章,計有:程艾藍 (Anne CHENG)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國古代天地人三綱之概念》(De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univers:la conception de la triade Ciel- Terre- Homme à la fin de l’antiquité chinoise)、樂唯 (Jean LEVI)的《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之互相聯結:中國古代法家思想中之自然法與社會法》(Solidarité de l’ordre de la nature et de l’ordre de la société:“loi”naturelle et“loi”sociale dans la pensée légiste de la Chine ancienne)、朱利安的《作品與宇宙:模仿與發揮〈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之模擬觀念〉》(L’uvre et l’univers:imitation ou déploiement)、尚 德 蘭 (Chantal CHAN)的《情與景:在中國詩中體驗主觀與外界》(Emotion et paysage:subjectivité et extériorité au sein de l’expérience poétique de la Chine);書末是兩篇與自然觀念有關的讀書札記,一篇是朱利安撰寫的《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觀》(La conception du monde naturel,en Chine et en Occident,selon TANG Jun-yi),另一篇則是狄梅杰奧 (J-F Di MEGLIO)撰寫的《牟宗三所詮釋的“天命之謂性”》(La nature comme“destin émanant du Ciel”d’après MOU Zongsan)。前者是對唐先生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第五章,特別是第二至五節中所論述之中西自然觀的鉤玄撮要;后者則是對牟先生的《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七至九章中有關天命觀的提綱挈領。這是法國對當代兩位新儒家思想的首次觸及,雖然只是一讀書札記,且篇幅不長,但饒有意義,值得向中國讀者介紹。此外,兩位大師的哲理,透過法國兩位同樣受過精密的思想訓練,并充滿文化理想的年青學者的析讀,以另一種語境再皺折呈現,為中國讀者帶來新的閱讀方式,其意義又自深一層,但可惜這兩篇文章卻一直被忽略。
以下首先將這篇讀書札記的內容作重點介紹;接著,譯述朱利安的讀后感言;最后嘗試將他提出的一點意見予以補充。札記的全文中譯,則附在文章后面,以供讀者參考。
一 《唐君毅之中西自然觀》的幾個重點
唐先生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②第五章《中國先哲之自然宇宙觀》,原有八節。第一節,西方哲學科學中之自然宇宙觀。第二節,中國自然宇宙觀中,缺乏超越的必然律之觀念。第三節,中國自然宇宙觀中,“共相”非第一義之理。物之存在之根本之理為生理,此生理即物之性理。物之性表現于與他物感通之德量。性或生理,乃自由原則,生化原則,而非必然原則。第四節,中國自然宇宙觀,視物皆有虛而涵實,以形成生化歷程,故無純物質性之實體觀念,萬物無永相矛盾沖突之理,而有相感通以歸中和之理。第五節,中國宇宙觀中物質與能力,物質與空間,時間與空間不相對立,以位序說時空,而缺“無限之時間空間觀念”。第六節,中國自然宇宙觀,重明理象數合一而不相離。第七節,價值內在于自然萬物之宇宙觀。第八節,儒道陰陽法諸家之自然宇宙觀之比較。如上述所言,朱利安這篇讀書札記,是對第五章之第二至五節的綜合撮要。不過,在行文間,他以自己西方人的身份換作觀察者。
唐先生于書中清楚地說:“中國由易經以來,自然宇宙觀之特色,一為融質力于陰陽,二為由物質之位序以說時空,而無‘無物之無限時空’之觀念,而重觀當下之天地中萬物之相涵攝、相感通、相覆載。第三點則為數與理與象之合一。”札記分從內在律則到事物的真實性、從自然律則之生化原則到宇宙中的道德行為、交界中的時間與空間三個部分來處理,是對應第一及第二點,而未有把第三點納入。
(一)從內在律則到事物的真實性。這一部分所著重的,是唐先生提出的“條理秩序”以及事物的律則。對于“條理秩序”,朱利安翻譯為“連續順序的一致性”。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以“天命”為主導,天命非永恒不變,亦不會有終止。所以與西方的傳統思想,自然定律為絕對的必然,被視為外在于事物自身不一樣。中國古代自然律的構成,非由神之自外賦予或自上而下地超越地安置,而是內在于自然萬物的一種思考。以自然萬物有律則,內在于其運行變化中。中國自然觀的形成,始于事物內在的律則,并非如西方將現象的連接看成是一因果律。
(二)從自然律則之生化原則到宇宙中的道德行為。這一部分所著重的,則是唐先生根據易經思想,提出“感通”“虛與實”“中和”等觀念來說明現實物之事象感通,能涵攝他物,以形成生化歷程之義。因此,萬物之德(剛—柔、動—靜),亦唯由物與他物相感通時所見之功用上說,亦即皆由虛之涵實,實之涵虛而見。古希臘開始時對物理之思辨,是凡物本身不能自動,必待外力使之動,或物與物相沖突而后動。西方近代物理學之革命,打破物質為本身絕對實在之觀念,此時西方的科學便與中國思想的演繹相接近。
(三)交界中的時間與空間。這一部分所著重的,是唐先生根據易經思想,以“時序”與“位序”代替“時間”與“空間”來說明中國古代的宇宙觀。這兩個觀念互相依存,每一物占一定位置,其生起變化乃依于一定的時序。位變則時序變,時序變而位變,位與時序變而事物所感通的其他事物亦變,事物本身亦變。所謂空間,即是萬物賴以感通之場域;同樣,所謂時間,即是萬物相承而感通之際會。是以,在易經之思想中,是不存在西方物理學中之單純定位(Simple Location)之觀念(西方當代物理學即批評此觀念)。因為不以物限于決定的位上及時序上,便無須思考時空之無限。蓋感通之際,萬物皆超出其原先的位序,超出原先的有限時間空間,而見無限。因此,中國思想不言“有限”而言“交會”,不言“無限”而言“中和”。自是,中國人從不扣問人類或萬物之起源,亦不可能有進化論之理論結構。進化論之觀點有利于西洋人的處事精神,在意識上他們不斷地要求超越有限,在自然宇宙觀上則置萬物于力與力的沖突之緊張關系中,這構成了西方社會及其精神狀態的特色。與之相反的,是宇宙不斷自我調節的一種中和思想,這是中國寧靜的根源。
二 朱利安對《唐君毅之中西自然觀》的評述
帶著困惑來思考的東方哲者,仍然尋找生命調和的訣竅,他們將訣竅從西方帶到東方,但不會將自己深深贊賞的,合理的先人遺產輕以破壞。
——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
在當代中國哲學中,西方人只認識馮友蘭的著作。是因為當中國建立共產政制時,馮友蘭選擇留在北京,還因為他的《中國哲學史》很早就被翻譯成外語③。自此,我們對那些在1949年流亡到臺灣、香港等地的哲學家便甚少關注。他們為配合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在香港創立了新亞書院,目睹西方科技思想的入侵(造成概念統一化),這些哲學家理性地為當代中國文化尋求出路,為我們提供一個挑戰思考的模式。面對世界文明的苛求,他們不但沒有放棄寶貴的傳統,并且將其賦予時代意義。
唐君毅將中國的自然觀念,解釋為“自然界”,以別于西方從物理學著手的自然觀。他以懷特海(A.N.Whitehead),特別是《科學與近代世界》(La science et le monde moderne)一書為思考的起點。根據后者,“律則”一觀念,是一切科學可能形成的根源,“首先,如果對事之規律,特別是自然的規律,如果沒有直覺的、普遍的信念,便不能有活的科學。”但唐君毅明確地就此而突出一個與之相異的,并孕育了中國的自然觀的律則。他認為,必然性、決定論等觀念是中國沒有的,因此,中國的自然律則,恒被看作是一創生原則,它透過感通而呈現,事物由此而生化不斷。自此,我們知道中國思想是不能產生物理學。但正好,沿著懷特海的理論下去,唐君毅指出,與古典物理學全不相干的中國傳統自然觀,恰好與西方那源自相對論與量子論的當代物理學的革命有客觀的相似。無疑,這樣的比照是有點兒浮淺,例如對缺乏決定論的可能問題的思考不夠嚴密,而這樣的模擬,在今天肯定值得再作更精確的審思,例如,可以從IIya Prigogine和Isabelle Stengers在《新的組合——科學的蛻變》(La Nouvelle Alliance,Métamorphose de la science)一書中所探討開始。而對于西方人來說,余下的便是對以下這狀況的影響予以衡量:遠東思想怎樣不用將古典物理作解構,就能輕而易舉地進入類似的新科學里。
在唐先生和牟先生的這些論述中,對我們自身文化所予以的形象(自由與決定論的紛爭、西方哲人的精神風貌與中國智者相反等),我們大可不必全部認同。但他們借用西方的概念術語,以反思中國文化,其中所實施的方法是有意義的。反過來,西方人是否也可以借用中國文化的概念,來對自身文化的根源作一反思?
三 作者的幾點補充
(一)上文朱利安說,中國知識分子(指流亡到香港的當代新儒家)一方面痛苦地生存于近代中國的悲劇里,一方面則理性地為當代中國文化尋求出路,頗能道出唐先生等新儒家當時的憂患與使命。他寫這篇讀書札記時,一定不會忽略唐先生在述說此書的寫作緣起時,當中那一段沉痛的話語:“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余,不惜加以擯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于一旦。時或蒼茫問天,臨風隕涕。”而唐先生《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正成于顛沛流離之際,他說:“平日所讀書皆不在手邊,臨時又無參考之資。凡所論列,其材料皆不出乎常識與記憶。身居鬧市,長聞車馬之聲,亦不得從容構思。”但仍“勉自發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只因“分析中國哲學之智慧,以論中國文化之‘精神的價值’之著,而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尚付缺如。”
(二)對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朱利安在2004年答復訪問者的提問:他對牟先生以康德重讀儒家的方式有何看法時,便有如下比較:“我認為牟宗三的作品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比如把他和之前的馮友蘭相比,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完全是用西方的哲學范疇來理解和書寫中國思想史,沒有任何懷疑,而且還把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方式套用到中國哲學上。然而這部中國哲學史被翻譯為英文,形成學派。牟宗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對中文文本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而自30年代開始由英文入手,再由中文,進行了偉大的思想探索。”
(三)唐先生認為中西自然宇宙觀的主要分別,可從三方面了解:中國之自然律為內在,與西方之恒視自然律為超越相對;中國之自然律為萬物之性,而性則表現于其能隨境變化而有創造生起處,因而可謂之內在于物之自由原則、生化原則,此與西方之必然的自然律相對;又由中國思想之以物之性,表現于“與他物相感通之德量”,此與西方以物之本質為力之說相對。此三點乃是中國之自然宇宙觀之核心,而最重要者,由此而引申出“自然物之實中皆有虛”之觀念。故在中國之古代思想中,從無不可破壞的,永恒不變的原子論與原質論。而西方則要到近代物理學的革命,才知物質之可以化為力,而力又可消滅于“他物之攝受其力”之前。對于這一點,朱利安特別感到沖擊:“遠東思想怎樣不用將古典物理作解構,就能輕而易舉地進入類似的新科學里。”但同時,他認為唐先生對缺乏決定論的可能問題的思考,不夠嚴密,建議參考IIya Prigogine和 Isabelle Stengers在《新的組合——科學的蛻變》中的論述。
IIya Prigogine(1917-2003)是一位俄裔比利時籍的著名化學家和物理學家,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Isabelle Stengers(1949-)則是一位比利時哲學家。《新的組合——科學的蛻變》一書由二人共同撰寫,1979年由巴黎伽利瑪出版社首次發行。這本書其中一個核心論題,乃主張科學與文化是互相影響的。作者反對與科學分裂的哲學,或反對以科學應該受政治、經濟、哲學保護的那些偏執。書中有一段這樣的話:“蛻變不是分裂。我們發現自然就在物理范圍內,容許它自律變化。簡言之,我們的世界就是一個自然的世界,我們就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這本書的理論看來簡單,但在我們對宇宙物理的思考模式里,卻牽進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結語
朱利安并沒有上過唐先生的課,當他知道了新亞研究所,并持之有恒地來聆聽徐牟等先生講課時,唐先生已離世,所以他完全是透過先生的著作來認識先生的學問與人格。甫回法國,他即選擇《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萃取當中有關中西自然宇宙觀的部分,寫成札記,雖然不是一篇深入的論文,但為法國研究當代新儒家思想領域揭開了序幕。唐先生思想博大圓融,這本著作從不同領域,論述中西文化精神之異同,恢宏廣拓,單是自然宇宙觀一章,便架構森嚴,當然絕非一篇札記能說得透徹,但其中的核心觀念,以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札記均能掌握恰當,頗能道出書中神髓。可惜之后不見有再深一層的發揚與探討,殊覺遺憾,唯待來日。
注釋:
① 這篇文章的譯文附于文后。
② 本文參照的版本為該書于1953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的第一版。
③ 陳榮捷在他的《中國哲學數據選》(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第751頁中說:“‘馮友蘭無疑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最卓越的哲學家’成為了慣常所見的評價。”
附:
《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觀》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第五章(特別是第2-3-4-5節)
讀書札記
朱利安撰 (法文)
岑詠芳譯
從內在律則到事物的真實性
對中國自然觀的理解,應從中國文化精神處著手,而不能如西方般建基在科學的理論上。西方的傳統思想,受希臘之命運論(如必然的命運)和羅馬的司法制(如強制的法律)影響,自然定律為絕對的必然,被視為外在于事物自身,這種觀念在科學的表述中便已具體形成。然而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則以“天命”思想為主導,天命非永恒不變,亦不會有終止;既非不易亦非不止(靡常、不已);是以自然定律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便不具備絕對的必然性。再者,中國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沒有超越的基督教精神,亦不肯定與感性分離的知性世界的存在,就像辟薩各拉斯(Pythagore)、柏拉圖傳統中的數理或概念的世界。是以,中國古代自然律的構成,非由神之自外賦予或自上而下的超越的安置,而是內在于自然萬物的一種思考。在易經的宇宙道德觀甚或傳統的儒道思想中,便已具體形成一種觀念,一種以自然萬物有律則,內在于其運行的變化之中,且非由一必然的、純理智的前提所推出的一種觀念。依此說,所謂自然萬物的律則構成了他的“性”,甚至可以說“物之性”(“性”的概念),此性是透過萬物的運行變化,同時透過自身功用(作用)的發揮而顯現。在這運行的過程中,必有連續順序的內在一致性(即“條理秩序”)。
中國與西方傳統思想之間對于自然之概念,存在著一種觀念上的根本差異。在西方特有的理性分析的影響下,早已意識到片段性及感覺的不相連續,這種思想順理成章地將現象的連接看成是一因果律,按照習慣的簡單作用,或人心所立之法,因果律的存在必然是相對的和有條件的。與之大相徑庭,中國自然觀的形成,乃始于事物內在律則,以及此事物的自然創造性,由事物的變化過程中了解,一如連續順序的內在一致性,而為道德精神與藝術精神所肯定并證實。
從自然律則之生化原則到宇宙中的道德行為
中國的自然思想,乃避免假定一個如宇宙性(共相)的超越第一義,且不以邏輯作為思想的開端(因恐落入以理為自外安置于自然界事物之說);而自然的轉化,乃始于連續一致的直覺,在特殊事物中顯現,此為事物的本性。然而,此創生之理,使萬物之事像之有生起成為可能而必然,卻非使萬物之所生起為何形式。
中國古代思想中,沒有像印度或西方所發展的原子或原質論。那種不可被破壞、永恒不變的原子或原質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里是決然陌生的。中國傳統中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或如易經之八卦),皆純從物與他物相感通時所見之功用上說。是故,依中國原始五行八卦之思想,皆沒有重視事物之純粹物質之實體之思想,亦無一切原始物質性實體之概念。
西方所謂物質實體,自始即含于潛伏于感覺世界之下之實在之義。此外,古希臘開始對物理之思辨,是凡物本身不能自動,必待外力使之動,或物與物相沖突而后動。將其應用到近代的自然科學中,遂構成了物質之根本性為惰性,以及抵抗運動性。西方物理學的發展,便與中國的自覺意識越來越背道而馳。反過來說,西方近代物理學之革命,打破物質為本身絕對實在之實體之觀念(知物質之可化為力),即打破一種不動之純物質實體之觀念。此時,西方的科學便與中國思想的演繹相接近。事實上,在中國易經之思辨中,早由現實物之事象感通,以論物之能涵攝他物,而皆實中有虛,以形成生化歷程之義。
根據易經思想,一物之實質性和實在性,純由其有虛能涵攝,而與他物相感通以建立,而不依其自身以建立。例如,地從表面上看,是一堅固的物體,但依易教,地之品德是柔和的(地之德為坤為柔);相反的,在西方視之為無物體之實質的天,據易所言,其有貫入地中的功用,以引出地中之植物,所以其品德是剛健的(天之德為干為剛)。此表示一種“于地之堅固之實質中,識取虛涵性,而于天之運行作用及其與地感通中,認識其實在性”之態度。故八卦本身,初所代表之八物,皆為兩兩相對,相反相感以相生相成之八物。如天高地下,為相反相成,地之向天凸者,為山;天之向地凹者,為澤;自上而下者,曰水,自下而上者,曰火;自內向外者,曰雷,自外向內者,曰風。是以,萬物之德(剛—柔、動—靜),亦唯由物之感通而見,亦即皆由虛之涵實,實之涵虛而見。由是,宇宙萬物間,只有暫時不相感通以至相矛盾或沖突之事,而未有永相矛盾沖突,永不得中和之理。而由矛盾沖突歸到中和之道,是不由下往上翻,以求綜合;而在分別求變易其道路,擴大其所感通之物之范圍,成就并行不悖之生化歷程,以求再感通。宇宙因以得永恒存在。
交界中的時間與空間
根據中國虛與實(實中涵虛、虛中涵實)的觀念,物之所以為物,即在其攝受性與感通性。是以,西方傳統思想中,物質與能力、物質與空間之對立,是不見于中國思想中。西方哲人論物質,是聯系于感覺世界之概念與惰性之觀念,此皆未能明白指出物質一名之所以立之積極性。其所謂物質不過是純粹之“充實空間性”、純粹之“惰性”、純粹之“質料”、純粹之“外在性”“限制性”而已。然而,物應有積極之攝受性,此乃依于其有“虛”,而非其只是“實”。說到“能力”這一觀念,蓋物之能力乃見之于外而為實,而當為他物質所攝受時,則入于虛。是以,“力”“質”皆只是一抽象的觀念(假名)。自然界中之所有者,只是一不斷之生化歷程之開啟而收斂,收斂而開啟。此收斂彼開啟,亦可以說彼攝受此,而此感通于彼的這種生化歷程,交替的說法,就是中國傳統思想中一陰一陽更迭之“道”。
在西方思想中,因為以物質為占據空間,所以物質必然有限;同樣,物質中能力之表現為動,而動所經歷之時間也必然有限。在西方,時間、空間又恒被視之為二。然而在中國,不會以時空為二。因為“宇宙”一概念,包含了這兩個元素,宇宙就是“時空”“空時”,此乃中國人“宇宙”與“世界”的觀念。另一方面,亦不認為一物只限定于占據一特定的時空,所以亦不會有抽象的無限時空的觀念。
易教中,以“位”觀念代替“空間”觀念;以“序”觀念代替“時間”觀念。這兩個觀念互相依存,每一物占一定位置,其生起變化乃依于一定的時序。位變則時序變,時序變而位變,位與時序變而事物所感通的其他事物亦變,事物本身亦變。誠然,就個別物而言,其位與時序亦特定,自與他物不同。但若從自然萬物為一互相抑制、互相吸引、互相涵攝感通上看,則每一物不會限于一特定之位與一特定之時序。一物之場所,是其功用之發揮與效益之顯現之場所,但不會只限定于其所占的那一點時空上。例如,太陽所在之空間,并非限定于天的某一部位,而是遍于日光所照之下;草木之生長,非只生于其生長的時期,而是生于使草木生長的過去之所有的生化歷程之上,及其所開啟之未來的生化歷程之中。而所謂“空間”非他,乃是萬物賴以相與感通之場域;同樣,所謂“時間”非他,乃是萬物相承而感通之際會。西方物理學中之單純定位(Simple Location)之觀念(法譯按:被當代物理學所批評)在易經之思想中,是自始不存的:因為不以物限于決定的位上及時序上,便無須思考時空之無限。
中國古代思想之宇宙觀,乃自其當下體會的位置與時機(當下位時)而說:當下為古今四方上下之交會,亦即不同時間與不同方位的平衡點(中和)。因為不能抽象思考與其他事物互相依存的關系,中國人的精神與心思,即不須窮根究底,以肯定無限虛空之境;同樣,亦不須透過過去之歷史(宇宙的或人類的),以達到太初之無有一切的時間。是以,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時間空間之無限,便可只須從感通無盡,而生化無窮上說。蓋感通之際,萬物皆超出其原先的位序,超出原先的有限時間空間,而見無限。因此,中國思想不言“有限”而言“交會”,不言“無限”而言“中和”(此中和即無限)。
中國思想沒有自事物中分析出其所占之時空,將其客觀化為一抽象無限時空之態度。反之,中國先哲恒視事物與其在時空中的位序不相離。每當事物變滅而往,人們可以說其所居之時位,亦與之俱往。當此一事物再來,或同類事物依同理而新生,則可說事物與原居之時位之再來。是以,事物所占之時位,乃在變滅與再生(陰與陽)的循環中。由日月星辰之往復,四時草木之代榭,以見天地中和之氣之常在,生生之機之不息。中國人“天”之觀念,是周行不息、生化發育,而永無古代西方思想以天為層迭觀念(屈原之“九天”是一地理空間之結構;揚雄之九天,則是根據天之功用來分別)。自是,中國人從不扣問人類或萬物之起源,亦不可能有進化論之理論結構。進化論之觀點有利于西洋人的處事精神,在意識上他們不斷地要求超越有限,在自然宇宙觀上則置萬物于力與力的沖突之緊張關系中,這構成了西方社會及其精神狀態的特色。與之相反的,是宇宙不斷自我調節的一種中和思想,這是中國寧靜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