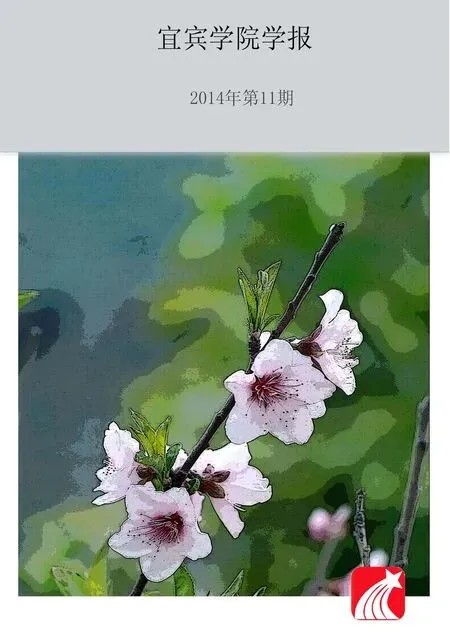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文心雕龍》視域中的《楚辭》
黃文彬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 桂林541006)
《文心雕龍》視域中的《楚辭》
黃文彬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 桂林541006)
《文心雕龍·通變》篇認為《楚辭》是文章“從質及訛”的轉折點,希望通過“宗經誥”與“變乎騷”,達到文章“通”與“變”的平衡。在這一大背景下,劉勰將《楚辭》列入“文之樞紐”,并在《辨騷》篇中提出了“倚經馭騷,酌奇存真,玩華保實”的寫作原則,把“文”之變納入可以指導的范圍內,《辨騷》篇的宗旨就是指導人們如何“驅辭力”和“窮文致”的。這一寫作原則與“正言體要,惡乎異端”的思想密切相關。《風骨》篇與《定勢》篇還從不同角度對《辨騷》篇的寫作原則進行了補充和豐富。實際上,劉勰就是借《楚辭》來述其運辭之道,這是他解《楚辭》的獨特之處。
《文心雕龍》;《楚辭》;《通變》;《辨騷》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寫道:“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1]1924《辨騷》篇又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1]134可見“騷”在劉勰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劉勰如此重視《楚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楚辭》是文章“從質及訛”的轉折點
《楚辭》的“奇文郁起”使文章之發展起了巨大的變化,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文心雕龍·通變》篇認為,從縱向的歷史看,《楚辭》是文章“從質及訛”的轉折點,改變了自經典產生以來文章發展的歷史軌跡。
《通變》篇云: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云》,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1]1084-1090
從中可以看出,劉勰認為《楚辭》是文章“從質及訛”的轉折點,《楚辭》之前的文章作品“序志述時,其揆一也”,原則都是一致的。楚以后則“從質及訛,彌近彌澹”,變化的原因是“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
南朝時期的另一位批評家鐘嶸在他的著作《詩品》中,亦批評了當時的文壇:“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2]64-69“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2]74鐘嶸與劉勰時代相近,都對當時的詩壇(文壇)不滿,認為當時的詩壇(文壇)創作有弊病,不同的是鐘嶸品評的是詩歌,劉勰談的則是所有的文章。可見當時的文壇的確出現了問題,以至于理論家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批評的意見,這些問題也是他們撰寫批評著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質及訛,彌近彌澹”的文壇狀況,實際上是文章發展中“變”與“通”的不平衡導致的結果;而“競今疏古”的文壇風氣,則是士人們過分求“變”,忽略了“通”的創作心理所致。劉勰提出“矯訛翻淺,還宗經誥”[1]1094,用經書的典雅、淳質之風來改變文壇“訛”“淺”的弊病,就是希望文壇再回到宗尚古人的作文之法上。但是,“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1]1079,經書有其常體,“文”之發展卻“日新其業”,經書之體顯然不能適應文章之變,且“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1]1106,劉勰顯然意識到了這些,所以又指出為文不僅要“資於故實”,還須“酌於新聲”,學會通變才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1]1081。實際上,劉勰在處理文章發展“通”與“變”的問題上,非常注重“通”與“變”的平衡,他努力使“變”不能壓過“通”,但是“變”之于文章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如何達到“通”與“變”的平衡就成了擺在眼前的難題,而《楚辭》則是劉勰解決文章發展“通變”矛盾的突破口。
二 劉勰對《楚辭》的評價
劉勰并沒有系統地注釋或解說《楚辭》,但是他對《楚辭》的評價,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楚辭》研究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龍·辨騷》篇追述了漢代人對《離騷》(亦可視為對《楚辭》)的評價: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昆侖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1]136-144
從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歸納出漢人對作品進行藝術分析和評價的三個突出特點:一是與政治倫理聯系密切,漢代統治者對《離騷》(亦可視為對《楚辭》)的喜好和評價成為影響人們對《離騷》看法的重要因素,政治直接介入到對文學作品的評價中;二是以經書為標準,無論是班固所謂的“非經義所載”,還是王逸的“依經立義”,漢宣帝的“皆合經術”以及揚雄的“體同《詩》雅”,都透露出漢人依經立義,以儒家詩論為標準來衡量一切作品價值的時代傾向,是儒家政教文學觀的體現;三是受到“知人論世”說的影響,如班固在評論《離騷》時,注意聯系屈原的品行談論其作品。而這三個特點實際上都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可見漢人對《離騷》和《楚辭》的評價是在以儒家思想文化為依托這一大背景下作出的。
面對前人的評價,劉勰認為“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1]144,于是提出了自己對《楚辭》的評價。他認為《楚辭》有“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四事“同於《風》《雅》”,[1]146又有“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四事“異乎經典”,[1]148并總論《楚辭》:“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旨,亦自鑄偉辭。”[1]152-155劉勰將其對《楚辭》的評價細化,但是他以“《風》《雅》”和“經典”為標準評價《楚辭》的內容并沒有超出漢人評價的范圍,而且劉勰以經評騷的方式恰恰是對漢儒以儒家經典作為衡量一切作品準的的治學觀念的繼承,與漢代人“依經立義”的觀點實相契合。
三 “文之樞紐”與《辨騷》篇的寫作原則
關于《辨騷》篇的歸屬問題,《文心雕龍》的研究者分歧很大。有人認為,《辨騷》篇雖屬“文之樞紐”,但不是“總論”;而更多的人認為,雖屬“文之樞紐”,但兼有文體論的性質。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未有定論。
要弄清楚這一問題,必須理清《辨騷》篇與“文之樞紐”其他各篇之間的內在聯系。除了劉勰在《序志》篇中言明:“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他在《原道》篇中的闡述亦頗能說明“文之樞紐”各篇之間的關系: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24-28
圣人根據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來進行著述,“創典”“述訓”“敷章”,他們“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道、圣、經典各逞其義,然后才“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這段話即是《原道》《征圣》《宗經》三篇貫通之意旨。而緯書“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1]124,倚《雅》《頌》,馭《楚辭》,“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1]164,可知《正緯》《辨騷》正是“彪炳辭義”之意。“《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文辭是“文之樞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圣、經、緯、騷就這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又,劉勰在《序志》篇中寫道: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1]1909-1913
這段文字對我們理解《文心雕龍》的宗旨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解釋了劉勰“乃始論文”的緣由。文章之用,五禮六典,君臣炳煥,軍國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是為《宗經》篇之意旨;“去圣久遠”,所以要《征圣》;“《周書》論辭”“尼父陳訓”也是《宗經》《征圣》;“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則可以說是《辨騷》,因為《辨騷》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寫作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段文字就是《征圣》《宗經》與《辨騷》三篇之間互相承接的理路。“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1]163-164則是《辨騷》篇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是《辨騷》篇作為“文之樞紐”地位樹立的一條作文準則,是劉勰對《楚辭》作用的一種界定。
關于作文,劉勰主張征圣宗經,他在《征圣》篇中寫道:“是以論文必征於圣,窺圣必宗於經。”[1]46在《宗經》篇又寫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1]56并指出:“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1]83-84同時,他也認為“然則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1]50,“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1]82,雖然是強調圣文之“雅麗” “銜華”,須以“佩實”為基礎;作文要“稟經以制式”,“富言”須“酌《雅》”而為,但是卻從另一面證明了圣人之文也須“銜華”和“富言”。所以他在《征圣》篇中說圣人(生知)“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1]53,指出圣人為文是“辭富山海”的,并不排斥文采,只是有一個前提,必須以雅、實為基礎。劉勰從圣人的角度肯定了文采、辭藻,這就為《辨騷》篇和之后關于文辭的內容提供了依據。
因為《楚辭》有四事“同于《風》《雅》”,四事“異乎經典”,可以作為辯證學習的典范,劉勰便以《楚辭》為載體把以上思考融合起來,于是就有了《辨騷》篇所謂的“倚經馭騷,酌奇存真,玩華保實”的“驅辭力、窮文致”之法。“倚《雅》《頌》”即是宗經,“馭楚篇”就是要“酌奇而不失其真”,存其“真實”,避免“楚艷漢侈,流弊不還”[1]85的文病,也就是要不詭、不誕、不淫,“玩華而不墜其實”就是“銜華而佩實”。因此,《辨騷》篇是《征圣》《宗經》篇“銜華佩實”“酌《雅》富言”思考的繼續。
《通變》篇云:“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1]1081“資於故實,酌於新聲”是劉勰“望今制奇,參古定法”[1]1106的“制奇”之法。而這一方法實即是《辨騷》篇寫作原則的另類表述,指導文章“通變”之法的就是《辨騷》篇樹立的原則。實際上,劉勰作《辨騷》篇,就是要從文章寫作原則上糾正《楚辭》以來不合于經典那一方面的文風,消除其不合理的影響。劉勰接受《楚辭》入“文之樞紐”即是接受了文章自《楚辭》以來之“變” “變乎騷”即是此意。“倚《雅》《頌》”“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與《通變》篇所謂的“矯訛翻淺,還宗經誥”一樣都是通,都是為了合于經典的規范,使“變”有所依。既“宗經誥”,又“變乎騷”,以此達到“通”與“變”的平衡,以期明文章發展的“通變之數”。
綜而述之,《辨騷》篇是對《征圣》《宗經》篇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它所樹立的指導人們如何“驅辭力” “窮文致”的寫作原則,是文士作文通達經書“六義”的途徑之一,亦是“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之需要,這也是《辨騷》篇“文之樞紐”地位的體現。它更多表現為一種指導如何“為文驅辭”的方法論的意義,而不是所謂的“文體論”的性質。這與《文心雕龍》全書的宗旨和性質也是相符的。[3]7-24在《通變》篇的結尾,劉勰希望后世作者為文驅辭要“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1]1102,“會通”與“適變”并舉,這與“倚經馭騷”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劉勰就是要把“文”之變納入可以指導的范圍內,防止再次出現“楚艷漢侈”的流弊。一如《征圣》篇所說:“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1]45
四 《辨騷》篇寫作原則與“正言體要,惡乎異端”的思想
《序志》篇在陳述了“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等“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背景后,鄭重引用了《周書》和孔子在《論語》中說的話:“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此處的“《周書》論辭”,即《尚書·周書·畢命》所謂:“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4]245“尼父陳訓”即《論語·為政》:“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5]2462異端指不合正道者。
在《征圣》篇中也有相似的征引:“《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美。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1]47-49“《易》稱”來自《周易·系辭下》:“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6]89“《書》云”即與《序志》篇的“《周書》論辭”一樣同為引用《尚書·畢命》的內容。《風骨》篇也引述了這句話:“《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1]1069
“體要”的要求接著也出現在了《詮賦》篇和《奏啟》篇中。《詮賦》篇云:
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1]307
《奏啟》篇云:
是以立范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御,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1]871
《詮賦》篇和《奏啟》篇的這兩段話共同透露出了劉勰“體要”觀的一些精髓,即“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為文寫作應表達要義,有一定的常規、法度,否則就會導致“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的弊病。《風骨》篇引述“辭尚體要,弗惟好異”,便直接言明“蓋防文濫也”,亦是此意。此外,劉勰在《神思》篇中還提到了藝術構思和寫作時經常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意翻空而易奇”[1]984“辭溺者傷亂”[1]1000,而“正言體要,惡乎異端”的要求恰恰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實際上,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引用《尚書》《周易》和孔子之言,就是想借用經書和圣人的地位,來表達他關于作文運辭必須符合“正言體要、惡乎異端”要求的思想。《楚辭》有四事“同于《風》《雅》”,是為正言;四事“異乎經典”,即是異端。因此,《辨騷》篇提出的“倚經馭騷,酌奇存真,玩華保實”的寫作原則,即是倚正言、去異端、存體要要求的體現。而這些思想的反復出現,歸結起來還是為了指導如何“驅辭力”。
五 “詩騷”傳統的形成與《風骨》篇對《辨騷》篇寫作原則的補充
“奇文郁起”的《楚辭》之所以被劉勰列為“文之樞紐”與《時序》篇所謂的“時運交移,質文代變”[1]1653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1]1664,“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馀影,於是乎在”[1]1677,“且《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故后進銳筆,怯於爭鋒”[1]1751,《楚辭》之艷說“籠罩雅頌”,“衣被詞人,非一代也”[1]162,其影響已大到與《詩經》“并據要害”,即與經典并馳,幾乎取得經書的地位。
《楚辭》之所以有這么重大的影響和這樣高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漢魏以來“詩騷”傳統的逐漸形成,“詩騷”或“風騷”并舉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多次這樣運用,如《章句》篇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1]1270《練字》篇云:“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1]1467《物色》篇云:“且《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亦是如此運用:“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7]1778同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論巨著的《詩品》也是“風騷”并舉,如:“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2]43鐘嶸更直接將《詩經》《楚辭》列為所品論詩人的源頭。
“詩騷”傳統的形成,再加上“愛奇之心,古今一也”[1]1475,受《楚辭》影響,當時人們為文寫作出現“尚奇”“尚艷”的傾向有其必然之勢。《楚辭》“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1]160,可謂風力遒勁,但自漢以來的文人“祖述《楚辭》”,多是學習《楚辭》之“奇辭”與“艷采”,劉勰自己也認為“屈宋以楚辭發采”[1]1770,于是便有了“楚艷漢侈”“相如好書,師范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1]1777,紀昀就曾在評論《辨騷》時說道:“辭賦之源出于《騷》,浮艷之根,亦濫觴于《騷》,‘辨’字極為分明。”[1]133因此,在文章的寫作中,就難免會出現“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等“無骨之征”[1]1055,面對這樣的情況,劉勰便聯系“風骨”談到了如何駕馭“奇辭”的問題。
《風骨》篇說:
若夫镕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1]1066-1069
劉勰以經典為本,要人們以經書為典范來學習寫作,再雜以子書和史書的寫作方法,并深入了解文學創作的發展變化情況,詳悉各種文章的體勢,然后便能“莩甲新意,雕畫奇辭”,這是劉勰在洞悉《楚辭》對后代文章的影響后,對如何掌握運用其所代表的“奇辭新意”提出的指導原則。
此外,《風骨》篇一開始就提出:“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1]1048《楚辭》上接《詩經》,四事“同於《風》《雅》”“氣往轢古”,忠怨之情溢于言表,但《辨騷》篇提出的“倚經馭騷,驅辭窮文”之法卻沒有談到作文之前應先樹文章之“骨”,《風骨》篇涉及到了這一問題,指出在“驅辭力”之前,首先還應練“骨”,“情與氣偕,辭共體并”[1]1073,否則又會導致與“楚艷漢侈,流弊不還”相似的“習華隨侈,流遁忘反”[1]1071的局面和弊病,這是劉勰關于如何“驅辭力”的又一條準則,亦可視為對《辨騷》篇寫作原則的補充。
六 執正以馭奇
在《定勢》篇中劉勰將其關于《楚辭》的思考進一步深化。《定勢》篇說:“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1]1117“模經”與“效《騷》”的指歸似乎相反,但是劉勰轉而指出:“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1]1120-1124奇正雖反,卻不對立,必須“兼解以俱通”;如果愛典惡華,愛經惡《騷》,就會導致“兼通之理偏”。重要的是“功在銓別”“隨勢各配”,要“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1]1125。
近代辭人和新學之銳們卻沒有“循體而成勢”,他們“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1]1134,“逐奇而失正”[1]1140,最后導致“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1]1140。面對這樣的情況,劉勰指出“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1]1140,“執正”即同于“倚《雅》《頌》”,“馭奇”則等于“馭楚篇”。模經“自入典雅之懿”,是為正與典雅,效《騷》“必歸艷逸之華”,是為奇與華艷,因此“執正以馭奇”也即是“倚經馭騷,酌奇存真”,是對《辨騷》篇思想的概括。劉勰還指出“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反之,若執典雅之經,馭華艷之《騷》,愛典而不惡華,則能“兼解以俱通”“兼通之理”不偏,這是他在《序志》篇中提出的“擘肌分理,唯務折衷”[1]1933思想的體現,也是劉勰遵循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種表現。《辨騷》篇所樹立的“倚經馭騷,酌奇存真,玩華保實”的寫作原則亦是這種“折衷”觀的體現,“唯務折衷”才能經騷相濟,正奇兼解,典雅與華艷兼通。“折衷”觀實際上也貫穿于《文心雕龍》的整個體系中,說其是《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亦不為過。
結語
《文心雕龍》以《楚辭》為載體述文章寫作之法與運辭之道,既是漢魏六朝時期業已形成的“詩騷”傳統巨大影響的體現,也代表著《楚辭》本身對文章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它的“奇”與“華”,為“文”之發展提供了“宗經”之外的另一種可能(當然,劉勰認為“文”必須以“宗經”為本);而《辨騷》篇樹立的寫作原則和其他篇章對這一原則的補充與豐富,不僅有助于解決當時的文壇弊病,而且對南朝至唐初綺靡浮艷文風的改進亦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1]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增訂本)[M].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王運熙著.文心雕龍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阮元校刻.尚書正義[M]//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5]阮元校刻.論語注疏[M]//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6]阮元校刻.周易正義[M]//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7]沈約撰.宋書:第六冊: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74.
〔責任編輯:王 露〕
ChuCiintheViewSystemof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
HUANG Wenbin
(CollegeofArts,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 541006,Guangxi,China)
Accroding to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Tongbian,ChuCi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literary writing from quality to novelty, with a desire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ong” and “change” in article writing through “Zong Jing and Gao” and “Change on Sao”.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Liu Xie elevatedChuCias the “Literary Pivot”, and put forward the writing principle inDiscriminationofLiSao, which placed emphasis on harnessingChuCi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Ya and Song, pondering over novelty without breaking its trueness, using flowery language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fact, putting the change of Wen into the scope of guidance for literary writing.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fDiscriminationofLiSaois to guide people how to use rhetorics creative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language.This principle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Using correct words to expound the point without pursuing heresy”.The article ofFengguandFixedTendencyalso complemented and enriched the writing principles proposed inDiscriminationofLiSaofrom different angles.In fact, Liu Xie usedChuCito state how to use rhetorics and give full play to language, which was the unique point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ChuCi.
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ChuCi;Tongbian;DiscriminationofLiSao
2014-09-10
黃文彬(1990-),男,江西贛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漢魏六朝文學與文論研究。
I207.22
:A
:1671-5365(2014)11-00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