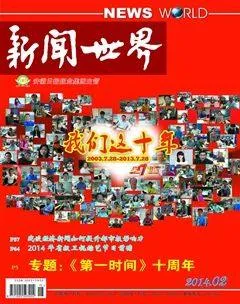電視民生新聞的公共轉向及其可能
汪成軍
【摘 要】經歷十年發展的電視民生新聞,在當下的困境恰如黎明前的黑暗,其本身正處于新一輪電視新聞改革的十字路口。在這個關鍵節點即將到來之前,一場電視民生新聞的變革已經在悄悄地鋪展開來,逐漸呈現出一種大眾性邁向公共性的轉型。
【關鍵詞】電視新聞 民生新聞 公共轉向
如果從2002年《南京零距離》的開播算起,電視民生新聞已經經歷了產生、發展和繁榮的十年歷程。十年來,電視民生新聞的發展正像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所寫到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①。一方面,電視民生新聞促進了電視新聞本體的回歸,標志著中國真正開始擁有了自己所謂的“本土化新聞”;而另一方面,其娛樂化、瑣碎化、低俗化、同質化傾向等問題長期為社會各界所廣泛詬病,甚至被視為一地雞毛式的低端產品。
回顧改革開放后中國電視改革的歷程,從1983年的“四級辦電視”,到1993年由《東方時空》開始的電視新聞浪潮,再到2003年由央視新聞頻道開播引領的新一輪電視新聞改革,中國電視改革近30多年來不僅呈現出十年一輪的“周期特征”②,而且有著“逢三變革”的歷史巧合③。基于此點,作為始于2003年之新聞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十年發展的電視民生新聞,在當下的困境也便如黎明前的黑暗,其本身正處于新一輪電視新聞改革的十字路口。實際上,在“逢三”這個關鍵節點即將到來之前,一場電視民生新聞的變革已經在悄悄地鋪展開來,逐漸呈現出一種大眾性邁向公共性的轉型。
電視民生新聞的公共性轉向
2006年之后,電視民生新聞的轉型與提升就成了其發展中的核心問題,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民生新聞欄目和省級地面頻道也開始積極醞釀理念和實踐上的變革。典型的如電視民生新聞的開創者《南京零距離》就以樹立和打造公益品牌作為轉型提升的突破口,在提高節目質量的同時,打造獨特的品牌形象,鍛造欄目的公信力,以品牌影響帶動節目收視。而南京另一檔名牌民生新聞欄目《直播南京》,則走上了一條主流新聞民生化、政經新聞貼近化路子,從國計民生出發,突出關系公共利益的政經新聞的地位,強化調查性和評論性報道,加大關注普通人生存狀態的情感類節目的比重。2010年,強勢民生新聞頻道湖北經視則旗幟鮮明地提出和實踐“大民生”的新聞理念,從“更廣闊的視域、更人文的視角、更宏觀的高度、更多樣的形態,關注并展現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④。在定位內涵上,“大民生”理念強調從瑣碎到公共關切,提高民生關注點,從關注一家一戶到關注一批人、一類人,同時主張電視民生新聞應當從迎合到引導,從宣泄到溝通,構建電視服務平臺,并提出民生新聞應該從展示苦情到展示生活中的感動,激發普通人的夢想和希望,完全突破了原有的“民生”理念,從理念上為電視民生新聞的發展賦予了新的生命力,也使湖北經視成為電視民生新聞轉型的一面旗幟。與此同時,以江蘇衛視《1860新聞眼》為代表,電視新聞界又開始了一場“公共新聞”的試驗探索,試圖吸取“公共新聞”的理念,實現電視民生新聞品質的提升。2004年,《1860新聞眼》正式打出了“公共新聞”牌,宣稱自己走出了一條比民生新聞更為寬廣的道路:“我們用公眾的眼睛關注國計,我們以人文的精神關注民生,我們創造公共新聞話語,我們搭建社會和諧的公共平臺”⑤,一時間“公共新聞”仿佛是苦海中的“諾亞方舟”,為電視民生新聞的進一步前行提供了一條光明大道。應該說,雖然由于社會體制等方面的原因,電視民生新聞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公共新聞”,但《1860新聞眼》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打造公共話語平臺,在新聞理念相對舊有的民生新聞理念下的確也不失為一種巨大的提升。
從《1860新聞眼》到湖北經視對電視民生新聞轉型的實踐,應該說,不管是主張電視民生新聞應該邁向公共新聞的新階段還是倡導以“大民生”的新聞理念實現電視民生新聞品質的提升,盡管實踐形式多種多樣,而學界所提供的實踐路徑也是不一而足,但是當我們將這些枝枝蔓蔓的東西拋卻在一邊,實際上所有的東西歸為一點就是其新聞理念上的公共轉向。電視民生新聞議題選擇上由市井生活向公共問題的轉向,所體現的實際上乃是定位主體由大眾向公眾的轉向,在更高的層面上則是電視民生新聞由大眾性向公共性的轉向。
邁向公共性,如何可能?
那么,電視民生新聞果真能夠承擔得起為公眾利益代言的重任嗎?或者說電視民生新聞何以能實現由大眾性向公共性的轉向,實現自身的主流化轉型呢?
誠然,電視民生新聞向來被認為在普通市民大眾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而通常這種影響也僅僅局限在市民的一般生活層面,電視民生新聞因此與公共利益、民主政治等嚴肅主題基本無關。作為一種大眾化的新聞產品,同都市報在很長時間里所面臨的情形類似,電視民生新聞在公共參與上的空間與可能基本上被忽視了。但是,反過來,也恰恰是同為大眾化傳媒的都市報在公共參與上的卓越表現,為電視民生新聞實現公共轉向提供了某種可能的路徑。無須費心回顧,都市報在一些民眾廣泛參與的公共實踐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典例,我們隨手便可拈來。譬如《南方都市報》之于“孫志剛事件”、《華商報》之于“黃碟事件”、《新京報》之于“寶馬撞人案”、《東方早報》之于“三鹿毒奶粉案”等等。“這正是中國社會和中國傳媒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趨勢,公民的政治參與從日常生活開始,都市報正在這樣一個交匯之處——它將國家政治與公民的日常生活連接在一起”⑥。既然如此,有著“電視晚報”之稱的電視民生新聞,理應有著經由日常生活通向公共政治的空間和可能。
對于大眾化媒介的政治功能,菲斯克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認為其具備一種特殊的“日常生活的政治”作用,“這意味著大眾文化在微觀政治的層面,而非宏觀政治的層面進行運作,而且它是循序漸進式的,而非激進式的。它關注的是發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環境、教室等結構當中,日復一日與不平等關系所進行的協商”⑦,而“此類微觀層面上的抵抗,一定會為宏觀層面上的政治行動創造出有利的社會條件,盡管這些抵抗行為本身并不是宏觀政治行為的充足理由”⑧。而吉登斯則將這種現代社會的新型政治形態命名為“生活形態政治”。在吉登斯看來,現代社會存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兩種不同形態的政治。與旨在打破制度性的不合理統治、力圖將個人和群體從不幸的生存狀況中解放出來的“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政治,其“在一種后傳統秩序中提出了有關‘我們應該怎樣生活這樣的問題倫理,并抗拒存在性問題的背景”,“試圖在全球化背景下創造能夠促進自我實現的道德上無可厚非的生活方式”⑨。概而論之,這種“日常生活的政治”旨在實現在個體多樣化的選擇中達成對政治目標的追求。
對于這種日常生活的政治,貝克將其命名為“亞政治”,并認為由于全球化和現代性具有同一性,這種以個人為主體、在日常生活層面展開的新型政治形態,在進入高速增長期的后發現代性國家也已經出現并顯示力量⑩。誠如貝克所言,“生活政治”在后發的現代性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民主進程的核心力量。生活政治在中國能夠獲得比解放政治更多的表達空間,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國媒介生態環境的特殊性決定的。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國家發展被認為是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而所有可能有礙于安定繁榮的主題都必須為其讓路,盡管“生活政治”仍然試圖通過對日常生活的介入來實現公共參與,達成政治目標,但是卻是一種溫和的改良主義實踐,與“解放政治”相比,不會從根本上危及社會的穩定。因此,當今中國,這種由大眾化媒介所實踐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正越來越頻繁地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動力。
中國大眾化媒介對日常生活的政治之實踐最集中地表現在都市報上,其“生活政治”的實踐表現在對重大社會事件的報道中。以“孫志剛事件”、“黃碟事件”、“寶馬撞人案”等典型實踐為例,通常情況下,這種新聞事件一定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層面獲得解讀,與其市民報紙的定位完全契合,這也是都市報最熱衷的報道主題。但是,如果還按照都市報傳統的做法,竭力突出其刺激性,靠制造噱頭來取得眼球效應,也就不可能達到什么政治上的作為。而恰恰相反,在這三個事件的報道中,都市報的超然之處就在于沒有囤于對日常生活事件的瑣碎式報道,而是從公眾的視角出發,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為切入點,揭示出隱藏在其背后的重大社會問題,開掘日常生活事件中的公共意義,引發公眾的參與和表達,從而實現從“日常生活”到“立法原則”的升華,達到影響公共政策的政治目標。實際上,這也是以都市報為代表的大眾性媒介關于“生活政治”的一般實踐路徑。
作為大眾化媒介中的典型一種,電視民生新聞和都市報有著難以割裂的緊密聯系,二者均立足城市,面向市場,以普通市民為受眾定位,報道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生存狀態,所以都市報本質上是一種新的晚報,又被稱為“市民新聞報”,而電視民生新聞則被稱為“電視晚報”,并且某種程度上都市報也正是電視民生新聞發展的先聲。所以,電視民生新聞同樣存在著實踐“生活政治”的無限可能。實際上,在對電視民生新聞轉型之路的探索中,也不乏類似“生活政治”這樣的成功實踐。2004年10月23日,江蘇衛視《1860新聞眼》播出了這樣一條現場新聞:一個男子騎著棗紅色的高頭大馬在鬧市的人行道上行進,卻被警察以違反相關法規為由加以阻攔,之后當事男子和警察、市容部門就馬能不能上馬路產生了爭執。如果新聞到此為止,那么它頂多是一則旨在獵奇的民生新聞。《1860新聞眼》卻由此發起了一場關于鬧市騎馬合不合法的大討論,最終導致觀眾紛紛加入其中,試圖尋找騎馬者合不合法的依據,而立法部門則開始了有無必要將之寫入法規的探討。《1860新聞眼》的這種實踐被認為是“民生新聞”實現向“公共新聞”提升的典范,而實際上拋開對“公共新聞”存在語境的爭議,這一實踐更大的意義其實在于,作為大眾化媒介的電視民生新聞由此找到了一種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為切入點,實現公共參與的政治作為之路徑。
由此觀之,不管是主張電視民生應該由“小民生”轉向“大民生”,還是認為電視民生新聞應該走向公共新聞的新階段,內在所體現的其實都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政治”之思想,這種“生活政治”以普通民眾瑣碎的日常生活事件開始,從公共利益的視角,著力開掘日常生活事件背后的政治意義,使普通的民生新聞上升為公共事件,從而實現從“閨房私話”(日常生活)到“立法原則”(政治意義)的升華⑾。這種“生活政治”的核心在于新聞議題設置上不再止于以大眾性評估日常生活事件的價值,而以公共性作為考量其新聞價值的首要標準,歸根到底實際上是電視民生新聞定位主體由大眾向公眾的轉變,而從根本上來說,只有實現了這種理念上的提升,才有可能使電視民生新聞真正完成邁向主流化的轉型。
參考文獻
①狄更斯:《雙城記》[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
②孫玉勝:《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M].三聯書店,2003:2
③胡智鋒、劉春:《會診中國電視——關于中國電視現狀及問題的對話》[J].《現代傳播》,2004(1)
④《大民生戰略:電視民生新聞創新的突破口——訪湖北廣電總臺電視經濟頻道總監張建紅》[J].《新聞前哨》,2010(11)
⑤張恩超,《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N].《南方周末》,2004-11-4
⑥孫瑋,《現代中國的大眾書寫——都市報的生成、發展與轉折》[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148
⑦⑧菲斯克 著,王曉玨、宋偉杰 譯:《理解大眾文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68、69、203
⑨吉登斯 著,趙旭東、方文 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三聯書店,1998:252
⑩烏爾里希·貝克 著,吳英姿、孫淑敏 譯:《風險社會》[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⑾江雪、小斌,《見證公民權利終于得到保護》[N].《華商報》,2003-1-5
(作者:安徽廣播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第一時間》記者)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