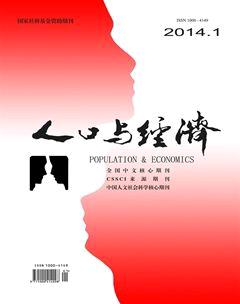主持人點評
黃榮清
今天,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區域人口城鎮化的問題。對于區域,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一個地理單元,或者指某一級行政管轄范圍,但這里說的區域,主要是從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經濟聯系上說的空間范圍。它在經濟上應該是完整的。所謂完整,是指“區域能夠獨立地生存和發展,具有比較完整的經濟結構。能夠獨立地組織與其他區域的經濟聯系”。“區域必須具備能夠組織和協調區內經濟互動和區際經濟聯系的能力,如果不具備這種能力,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區域,不能單獨組成一個區域。要具備組織和協調能力,不僅要能夠制定符合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且能夠刺激區域經濟持續高漲的各種政策法令,還要具備‘高級循環,也就是要具有金融銀行業、貿易批發業、現代服務業等所組成的循環系統。”一般來講,制定政策的權力機構和高級循環系統主要集中在較高等級的中心城市,因而,這種中心城市充當了區域經濟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因而,稱為同一區域,必須是內部各地域之間社會經濟聯系緊密,且有包含至少一個中心城市組成的核心。從上面的意義來說,長三角、珠三角被公認為“區域”,而京津冀的經濟聯系相對松散,別稱為同一區域就比較勉強,“西北地區”就可能不是上述意義上的同一區域。而只是一個地理范圍。
從以上幾個專家的闡述中,我們注意到人口城鎮化在各個區域的發展速度、發展水平是很不相同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珠三角、長三角區域有大量的人口遷入,人口集聚顯著,人口城鎮化速度較快,城鎮化程度較高。1982~2010年,全國各地遷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估計超過3000萬人,“眾多的人口涌入珠江三角洲約1.91萬平方公里的狹小空間,形成了高度的人口聚集,把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從1982年的550人/平方公里,推高到2260人/平方公里以上。根據2010年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都可以視為城鎮了”(李若建文)。1985~1990年間遷入長三角都市群地區的外省市人口為179.25萬人,1995~2000年間增長為679.09萬人,到2005~2010年又進一步增長到1816.07萬人。在1990年代,全國年均城市化速度為2.01%,長三角都市群地區則為3.11%,比全國快1.1個百分點;新世紀以來(2001~2010年),全國年均城市化速度為2.47%,長三角都市群地區則為3.53%,也比全國快1個百分點以上(王桂新、陸燕秋文,以下簡稱“王文”)。在京津冀區域。北京、天津一直是全國人口遷入率較高的地區,而河北則是凈遷出地區,“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人口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的時候。河北省的人口城鎮化水平尚未過半,甚至低于世界欠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45%)”(李建民文)。在西北各省區中,除新疆外,其他都是凈遷出地區。五省區城市化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但發展速度呈現出較大差異(郭志儀、顏詠華文,以下簡稱“郭文”)。
“人口遷移是人們用腳來‘投票。哪里經濟增長快,就業機會多,收入水平高,生活環境好,人們一般就選擇向哪里遷移,所以哪里遷入人口多,基本能反映出那里是優勢地區。”(王文)或者說,哪里的經濟發展快,哪里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哪那里的城市化速度就快,城市化水平就高,所以說到底,城市化需要靠經濟發展作支撐,當然,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也是互為促進的。
上面,我們看到了中國不同區域的人口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差距。現在我們的問題是這些發達區域的城市化歷程對相對落后的地區是否有示范效應,或者說這些“模式是否能復制?”(李若建文)。其實,從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個不同區域看,它們發展的路徑是有所不同的。珠三角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利用毗鄰港澳之便,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大量地引進外資,利用當時區內外廉價的勞動力,“大大小小的各類工廠如雨后春筍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成為被稱為世界工廠的發源地,一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高速地區,并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珠三角是依靠外來資本實現高速的工業化并推動了城市化。長三角是充分發揮了上海這一近代中國最大工商城市的活力,又依托中國最富裕地區江蘇、浙江兩省在經濟和人文方面的優勢,從而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區域(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長三角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等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國內生產總值之和)。京津冀區域中北京憑借首都的優勢,集全國人才最集中的力量,又有天津作為直轄市、老工商業城市作呼應,所以也成了中國重要的經濟區域。但北京、上海這樣的超級城市只有一個、毗鄰港澳這樣特殊條件的區域只有一塊,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中國的人口已跨入“老年型社會”,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農民工的供應已經不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所以說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等區域的發展只能作為其他區域發展的參考,不可能照樣復制。各個區域的人口城鎮化道路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客觀條件,揚長避短,發揮本地區的比較優勢,如此才能得到健康地發展。
一個區域人口城鎮化是否健康發展,衡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區域內部的協調性。一個區域城鎮化是否協調,表現在它的城市規模等級體系上,即不同規模城市的組成和它的地區分布。按照地理學家齊帕(G.K.zipf)的研究,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一個大的區域內,按城市的人口規模從大至小排列,則城市人口和它的規模順序呈冪函數形式分布,即接大、中、小城市呈有序增加。這種規模等級的有序性,反映了不同規模級別的城市各自的功能和它在區域中承擔的角色,是由生產的地域分工和市場范圍所決定的。小城市或集鎮,作為聯系廣闊農村的人口聚居地,它的功能主要是城鄉產品交換、農副產品簡單加工、對本地提供相對比較簡單的初級服務,所以,必定是數量較多和比較分散。中等城市提供較為高級的服務和規模較大的生產,市場范困擴大。而大城市、超大城市作為制定政策的權力機構和高級循環系統的所在地,提供高級的服務,它面向的對象為壘區域、全國甚至壘球。大城市、超大城市需要較多數量的中小城市來支撐,反過來,大城市、超大城市能通過向中小城市提供金融、技術、市場交易、人才培養等高級服務,提升中小城市的能力。某一等級規模城市的缺失或過剩,說明這個區域的發展不協調或不成熟。上海作為長三角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有些研究者把它和江蘇、浙江的關系,形象地稱為“前店后廠”,以上海為首,隨后有蘇州、南京、杭州、寧波等次大城市,無錫、常州、南通、紹興等大中城市以及為數眾多的中小城市,這些誠市共同組成了較為協調的城市體系。而從京津冀地區看,有2個千萬級規模的超大城市——北京和天津,卻缺少了50萬~10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從城市結構體系看,這種斷層的存在,表明京津冀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失衡,區域間經濟聯系不夠緊密,勞動的地域分工較亂。一方面,超大城市的發展沒有次大城市的支撐,而超大城市因為承擔了本來應該由次大城市承擔的角色和功能,造成其人口過于膨脹。而西北地區“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數量結構混亂,呈現出大小相間無序排列的特征”(郭文),這說明西北地區之間分工不細,市場范圍有限,地區之間經濟聯系不強等特點,使其不能構成統一的經濟“區域”。
區域人口城鎮化要高質量、協調和持續發展,需要解決區域內部統一市場的形成、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協調問題。一個較大的區域,往往包括幾個不同的地域行政單位,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如果每個單住都過分強調自己的利益,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以鄰為壑,形成市場壁壘,則市場的交易成本就會提高,各種生產要素得不到有效配置,從而導致資源浪費,其結果,不但區域整體會因之受損,各個局部區域的利益也會受損。如果合作達到協調,則各單住地域就會獲得共贏。有些學者在比較長三角和京津冀的發展時發現,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京津冀地區曾是我國城鎮化發展速度最快、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但現在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其重要原因是因為“京津冀地區的地方保護主義色彩濃厚,地方分割形成市場分割,阻礙了京津冀地區的一體化發展”(李建民文)。所以有人調侃為,上海像是太陽,它的輻射帶動了江浙的發展,而北京和天津像是“黑洞”,吸凈了河北的資源,導致了河北的發展無力。現在的局面是北京“人滿為患”,而河北“狼煙四起”。
區域內部的地域分工和角色定位是協調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區域內各個局部地域在分工中的角色,取決于各地域在區域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以廈該地域的發展水平,只有每個地域都明確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發揮出整體效益,否則就可能受損。筆者記得讀過一篇關于記載安徽貪官王懷忠的報告,說王懷忠在主政安徽阜陽期間,在阜陽修建了面積和上海機場大小相同的機場,王修建大機場的根據是因為“阜陽的人口比上海還多”,結果因為旅客少、航空班次少,機場雜草叢生,造成很大的浪費。從地域分工視角看,這是處于“下位”的地域盲目地和處于“上位”的中心地域攀比,想承擔但實際上又承擔不了中心地功能,結果只會造成資源浪費。但另一方面,當前的問題更多地出在處于“上位”的中心城市大包大攬,大城市、極大城市擔心資源流失,不愿轉移可以給次級城市完成的功能,因此,導致大城市、極大城市人口膨脹、環境問題突出、地域發展不均衡,這也是一種浪費。
[責任編輯 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