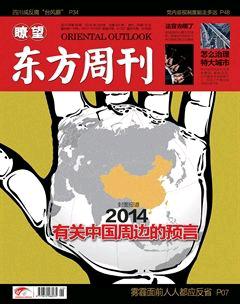2014中國周邊外交政策
戴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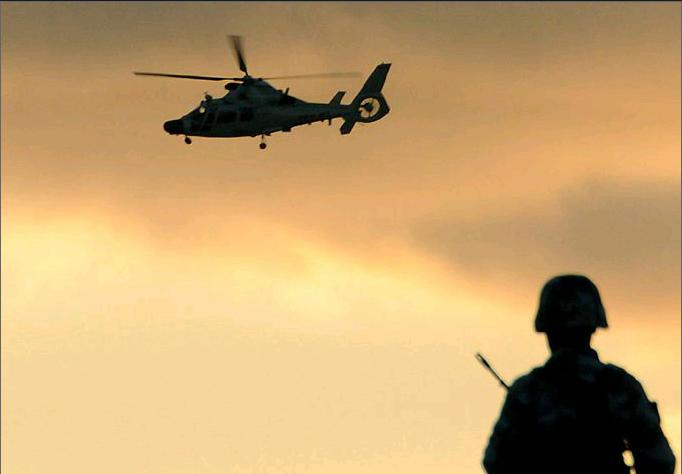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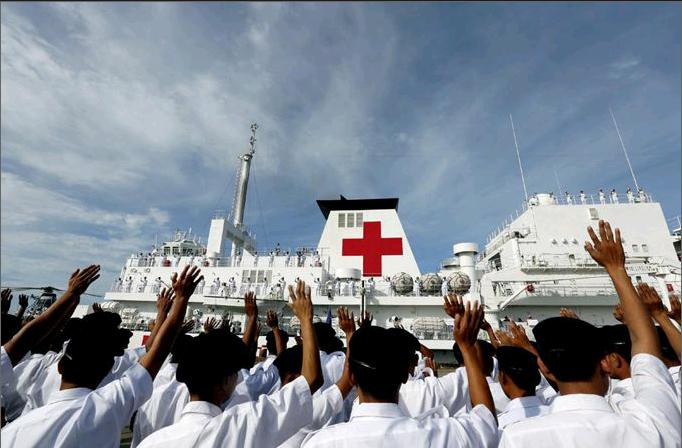
2013年10月24至25日,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政治局七常委悉數出席,這樣“高規格”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議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前所未有的高規格,體現的是超乎尋常的重視,傳遞出的信號也十分清晰---“周邊外交”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周方銀研究員的解讀是,這意味著“周邊外交將從大國外交的陰影中走出來, 并比過去具有更大的獨立性”。
在2014年以及未來一段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如何建立起一套與時俱進的“周邊外交政策”,為中國發展營造親和有利的周邊氛圍,將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大考驗。
本刊記者在2013年底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研究中心召集的“未來十年的中國周邊外交”研討會上,就此對話一批國內知名周邊外交學者。
周邊形勢嚴峻:東海與南海聯動、陸地與海洋內聯
關培鳳(武漢大學邊海研究院):
近年來,中國的邊海形勢日益嚴峻,對中國的周邊外交構成了巨大的考驗和挑戰。
東海,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僵持;在南海,中國同菲律賓等國的海洋權益爭端不斷加劇,而且中菲南沙爭端還因菲律賓的惡意擴大事態而沖破了以往的外交談判框架。
無論是在東海還是在南海,除了爭端當事國之外,都有非爭端當事國勢力介入。美國宣布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并以“航行自由”為幌子積極介入南海問題;日本也試圖介入南海爭端。
印度、越南有關公司簽署了在南海爭議海域共同開發海上油氣資源的合作協議,還與日本就從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這一“海上交通路線”的航行安全重要性進行了確認。
在陸上,中國與印度的領土爭端問題長期僵持不下,去年出現了中印“帳篷對峙”事件。
此外,陸地邊疆的安全問題較之往年更為突出。“東突”勢力在新疆的恐怖活動沒有停止;西藏的一些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此外,由于朝鮮半島問題持續升溫,我國東北邊疆的安全形勢也面臨考驗。
當前中國邊海形勢的特點是:第一,與周邊國家領土爭議明顯化、激烈化;第二,與中國存在領土或海上權益爭端的國家間正在相互靠近,使東海與南海聯動、陸地與海洋內聯的邊海形勢進一步演進;第三,域外大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與周邊鄰國邊海爭端的升級有直接聯系;第四,陸地邊疆的安全問題再次凸顯,且受到周邊國家安全形勢的影響。
由“弱勢中國”向“強勢中國”下的關系演變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有這么多鄰國、這么多遺留爭端的國家,這樣的特點構成獨特的周邊關系---鄰國情況復雜,與中國的關系變數多,近而不親者多;遺留爭端存在于領土、歷史、海域、人文等各領域,容易發酵;局勢隨中國興衰而動。
可以說,周邊外交的新挑戰是中國迅速崛起引起的多重反應之一,且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由“弱勢中國”下的關系向“強勢中國”下的關系演變。
此外,美國因素發生轉變。美國的戰略重點由改變中國轉向應對中國崛起與挑戰,保護美國的主導地位和利益。通過自身戰略調整,防止中國替代或者削減美國的存在與影響力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新戰略。
在幾乎所有的新變局中都有美國的影子,美國通過加大在中國周邊的投入,利用多層關系機制,企圖構建應對中國的網絡。
當前,重要的是準確把握周邊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形勢有沒有發生逆轉?這是一個大判斷。
我認為,盡管應對強勢中國是周邊國家的戰略性布局,但周邊沒有形成一個敵對包圍圈,具有多層含義,中國有巨大的運籌空間。
美國的限度:不破局
張蘊嶺:
把握中美關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國的主導戰略是構筑制約與平衡網,但挑動周邊國家對抗中國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是:不破局。
歷史上沒有過一個現存霸權國家與一個崛起大國之間有這么難分難解的利益關系,“不發生大的對抗”是雙方的戰略底線。中國對美“避免對抗,尋求合作”的大戰略沒有必要改變,中國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符合中國的利益,也得到美國積極回應。
日本把“應對強中國”作為主要戰略,這個戰略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利用中國因素推動國內改革,為政治右傾化、修改和平憲法造勢;二是與中國爭奪利益與影響力。
“合作又有疑慮”、“防華而非反華”是東盟與中國發展關系的戰略基線。應繼續深化中國東盟合作,“打造自貿區升級版”,加大對東盟國家的投入。
菲律賓在南海強硬是出于現實利益,利用外來勢力對抗中國增強的干預力和潛在控制力,但難以與中國直接對抗。南海涉及我國核心利益,但解決爭端的條件不成熟,強奪回島嶼和海域要付出巨大代價,要采取積極的維穩對策。
中印的領土爭端可控,要努力構建穩定基礎上的中印理解與合作關系。同時需要加大投入發展與南亞其他國家的關系,幫助他們發展,提出“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倡議,并推動構建中國-南亞(南盟)對話合作機制。
此外,上合組織是一個穩定器,要加大投入,提升合作水平,加強中俄的戰略協商。在安全合作的基礎上,加快推進經濟、人文合作,并把上合組織作為構建新型周邊關系的試驗田。
要有自信,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孤獨的大國”。
“擱置外交”仍然不可棄用
石源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綜合實力有所提升后,“擱置外交”依然是中國周邊外交中不可棄用的重要方策。在進行中國周邊外交頂層設計時,應全面考慮實施“擱置外交”的重要要素。
在及時處理好緊迫的外交問題的同時,也應該將那些可以“擱置”的外交爭端恰當地“擱置”起來,繞道而行,先從其他方面做起,尤其是從“共同開發”著手發展雙邊關系,等以后時機成熟時再來處理爭執問題。endprint
諸如領土、領海、界河的爭端,涉及國家重要利益,如中日釣魚島爭執、東海劃界問題爭執、南海爭執等等,在雙方分歧尖銳的情況下,企圖希望實現“單贏”目標,是不現實的,除非雙方采取戰爭辦法,決一死戰。即便仗打了,也未必能解決問題,如英阿馬島之戰,英國雖然取勝,馬島問題實際仍未解決,以后仍然需要雙方通過談判來尋找解決的方法。
最好的辦法是通過談判來緩解矛盾,尋求“擱置”。雙方采取克制的、不刺激對方的態度,將問題“擱置”。等待雙方關系全面改善,才能有可能心平氣和、互諒互讓地討論和解決問題。
中國在周邊外交實踐中,已經有中俄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中越解決陸地邊界以及北部灣劃界等成功案例。中印雙方同意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努力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但“擱置外交”同時是有原則的,在“擱置”若干外交爭端時,必須強調“主權在我”。“擱置外交”也是有選擇的,凡是涉及民族和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是不能“擱置”的。“擱置外交”還是積極進取和與時俱進的,應積極尋找、創造和抓住歷史機遇,推動爭端取得合理的解決。
未來要“更加奮發有為”
周方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周邊外交總體上將表現出更為強勁和具有可持續性的戰略進取精神。“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發揮出更大的主動性,一定程度上改變在某些問題上被動應對、隱忍待機的做法。
在具體的工作層面,做事的方法和態度會更加積極主動,工作會更加細致周到和具有針對性,對面臨的問題會作出更為及時有效的反應,在形勢的判斷方面也會表現出更強的前瞻性。
未來一個時期,是中國崛起的重要階段和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崛起面臨許多現實挑戰和困難的時期。在這樣一個階段,完全依賴“柔性”的手段,對所有問題都單純采取“溫和”的方式加以應對,不足以解決中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所有問題。
在若干強大的障礙與阻力面前,我們需保持更加高度的堅定性。在必須加以堅持的問題上,不應受“眾說紛紜”的拖累而產生“舉棋不定”的猶疑和行為上的“中途半端”。避免對外部世界傳遞出混淆不清的信息,這樣的信息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有意無意地加以曲解。
做“可親的大國”
任曉(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國儒家思想中對“大”與“小”之間的關系,作過精辟的闡明,濃縮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這12個字。“仁”意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時小國不應因大國仁厚而刁鉆油滑或得寸進尺。大國克制,小國識相,是理想的相處之道。
作為地區大國的中國,未來的課題,是中國如何成為一個“大而可親”的國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強大而令人畏懼的國家。
做可親的大國,首先是不要居高臨下,而是平等相待。其次,親是親切。親切是具體的,它不光體現在高層互訪中,更體現社會之間的紐帶和感情之中,比如外國青年來華留學就是一條重要的途徑。泰國詩琳通公主與中國很親近,就與她有在中國留學的經歷、培養起了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
第三,愿意傾聽。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很多時候可能是刺耳的聲音,也很重要。惡意的言論一定存在,但多數言論不屬于這種情況,不宜一概以“中國威脅論”來加以定性,或者拒絕與之接觸對話,而應作出具體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之后日本一直重視援助其他亞洲國家,幾十年來贏得了不少好感。在中日爭端問題上,對日方的批評一定要注意用事實說話,把握好分寸。
不容樂觀的中亞形勢威脅中國安全
趙華勝(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亞與中國特別是西北地區的安全有密切關系,中亞的風吹草動都會通過種種途徑傳導到新疆,對中國安全造成影響。
展望未來,對中亞安全形勢的擔心多于信心,不能過于樂觀。
其一,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呈擴張之勢。近年來,“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伊斯蘭解放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老牌恐怖主義組織繼續活動,同時新的極端主義組織陸續出現,如“吉爾吉斯斯坦社會”、“哈里發戰士”、“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圣戰”等。由于網絡等新興媒體的廣泛應用,境外宗教極端主義向中亞的滲透越來越容易,極端宗教思想的蔓延越來越難以控制。
其二,中亞一些國家將面臨國家領導人更新換代的考驗。
哈烏兩國都已到了認真考慮權力移交的階段,“阿拉伯之春” 對兩國也有很大觸動,但現在還看不到明確的安排,兩國總統的想法是一團迷霧,難以窺測。一旦這一時刻到來,國內外各種力量都會紛紛走出來,可能發生激烈沖突。
其三,中亞國家普遍存在貪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分化、通貨膨脹等社會矛盾。哈薩克斯坦等國因擁有油氣資源,國家財富迅速增長,但分配不盡合理,存在兩極分化現象。
此外,中亞缺水,控制水資源對國計民生有特別重大的影響。為爭奪水資源,一些中亞國家的關系緊張,有時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這些都可能是潛在的“火藥桶”。
此外,阿富汗局勢正面臨重大挑戰。
美國和北約將在2014年底前把十多萬軍隊中的大部分從阿富汗撤出,國家安全的職責將交由阿富汗政府承擔。這將是阿富汗的重大轉折,形勢是逐步穩定下來,還是會發生逆轉,目前沒有答案。
如果局勢惡化,將使中國西北周邊出現一個動蕩地帶,使西北周邊安全緩沖帶的安全系數將會降低。此外,它會給“東突”勢力提供新的活動空間和發展機會,使控制和打擊“東突”勢力變得更困難,并會對中國在阿富汗的投資、企業、人員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脅。
概而言之,未來大中亞地區處于高風險期,值得密切關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