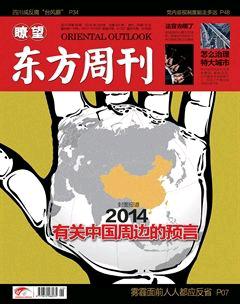蘇州:探路“城市養老”發現了什么
錢賀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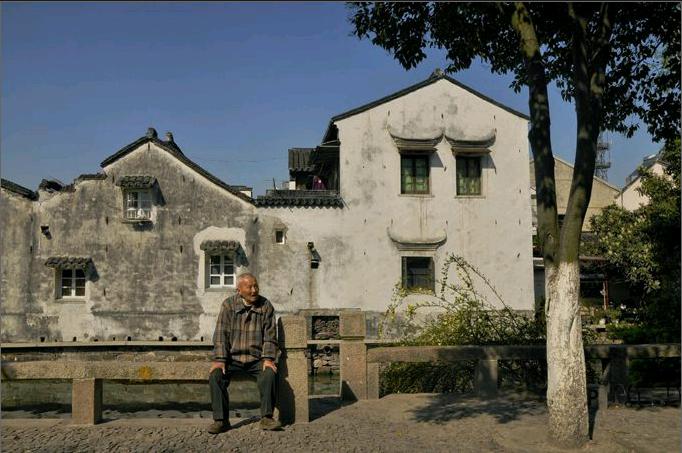

對于江蘇蘇州市區的老人而言,不少人的退休生活是這樣的:
每天到最近的日間照料中心吃飯、下棋、打牌;每月虛擬養老院的服務員會上門打理幾次生活,基本服務由政府埋單;倘若身體不好,失智失能,則搬到就近的民營養老護理院,這里有基礎的醫療與護理服務以及臨終關懷,自己每月支付2000元左右。
蘇州1982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比全國提前了18年,60歲以上老齡人數正以每年5萬?7萬的數字增加。
蘇州市民政局副局長鄭利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蘇州大約4個戶籍人口中就有1位老人,老齡化高于全省快于全國,社會撫養比也達到49.89%,即勞動力與非勞動力是1:1。蘇州的老齡化危機來得更早,所以作了不少探索,促進老齡產業發展。”
“十一五”以來,蘇州形成了“9064”養老服務格局,即90%居家養老,6%社區養老,4%機構養老。
外地人來蘇州考察最多的是居家養老的虛擬養老院,及機構養老中已具規模的民營養老護理院。僅姑蘇區的虛擬養老院就接待過600多批參觀者。
政府埋單居家養老
姑蘇區彩香二村的徐美英夫婦每月享受一次虛擬養老服務。
本刊記者拜訪時,虛擬養老服務員薛美珍正站在客廳的凳子上擦洗碗櫥。望一眼廚房,窗明幾凈,灶臺潔白锃亮。
81歲的徐美英站在櫥柜旁,叮囑高處的薛美珍小心。她的老伴吃完飯,到樓下的日間照料中心看下棋了。徐美英退休前是搪瓷廠的女工:“我有尿毒癥,現在家務活越來越力不從心,多虧了小薛。”
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工資基本都花在血透、吃藥上,看病是徐美英最大的開銷。欣慰的是,子女都在蘇州,工作再忙,周末還是會上門探望并補貼家用。
姑蘇區的虛擬養老院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為高齡、殘疾、五保等不同類型的退休老人提供無償服務。徐美英老伴年滿84歲,每個月可以享受一次免費服務,一些自理困難、符合條件的老人則可以享受更多次的無償服務。
老人若覺得還不夠,可以自己購買服務,每小時20元,低于30元的家政市場價。有一位華僑老人每月掏480元,讓薛美珍每周做三次飯,一次做兩天的,解決了一個月的吃飯問題。
姑蘇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副主任路忠對本刊記者說:“虛擬養老主要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務,有居家保潔、買菜做飯、陪同就醫、洗澡擦身、換季整理、水電維修、配餐上門,等等。”
“現在是基礎服務階段,下一階段有增值服務,比如醫療、飲食等等,免費服務也會逐步覆蓋更多老人。”鄭利江說。
薛美珍服務完畢會讓徐美英在服務單上簽字,并掃描門口的二維碼,記錄下她的來去時間。在服務員離開一小時后,居家樂服務中心的話務員會電話回訪,詢問老人的意見。每次服務前,話務員還會提前一天提醒老人。
薛美珍今年50歲,與所有居家樂服務員一樣是蘇州本地人,之前是彩香街道公益性的服務員,今年秋天將退休。她們就近就業,與老人們溝通談心也方便些。
路忠介紹,姑蘇居家樂虛擬養老院一線服務員有261名,所有人都經過崗位職業培訓,九成以上的員工持有“家政技能資格證書”和“養老護理員資格證書”雙證書。她們的身影遍布全姑蘇區17個街道158個社區居委會。
2003年,蘇州在全國首創社會化的居家養老服務,2007年建設運行虛擬養老院這一居家養老服務新模式。到2013年12月31日,虛擬養老院已覆蓋到8188戶老人家庭,11845位老人享受到這一服務。
虛擬養老院:看的多學的少
這些年國內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已近7000人次,然而真正學習的卻少之又少。
“雖然都叫居家樂、虛擬養老院等等,內涵卻大不一樣,只聽說無錫可能也要做。”鄭利江說,“這是我個人的分類提法,外地是技術主導型,蘇州是服務主導型”。
按鄭利江的分類,前一種是老人打電話說需求,基本什么服務都有,服務供應商在社會上,需要信息平臺整合資源;后一種不需老人打電話,是經過需求調查形成數據庫,有一支專門的隊伍為老人上門服務。
“外地的一指通、安康通等等太多了,摁個鍵,打個電話,提供服務。5年過去了,看看他們現在在干什么,我們這邊在干什么?”鄭利江認為技術主導型的模式沒有能力整合社會供應商。
這種“呼叫平臺”虛擬養老的模式,蘇州曾有失敗先例。路忠介紹說,15年前,蘇州金閶區推出的“一指通”服務,老人只要摁下隨身攜帶的電子鈴,即可聯通呼叫中心。工作人員詢問老人的需求,聯系社會服務。當時曾引發外界關注,服務過幾萬名老人,到2007年卻只剩下十幾戶了。
曾有北方某省會城市來姑蘇區考察后,還是建了“呼叫平臺”式的虛擬養老平臺。盡管他們受到上級領導的贊賞,鄭利江還是寫了封信給當地領導說“有問題”。
“技術主導型的模式,我感覺浪費了國家很多的錢為企業服務,而不是在為老人服務。市場經濟實際是訂單經濟,大企業規模訂單才能產業化發展。老人主動打電話,后期整合社會力量是不夠的,難以形成規模訂單,會做不下去。在中國有多少電話一打就能一步到位的事?”鄭利江說。
鄭利江與路忠都認為,外地不愿學習蘇州做法主要是培育養老服務的社會力量有困難,參與的人才太少,“這一模式太辛苦了,看的多學的少。”
據了解,姑蘇區虛擬養老院的服務員,每月稅后收入約2000元,這在蘇州已算比較低的收入,與社會上的家政鐘點工收入也有不小差距。盡管虛擬養老院每天都在招人,應聘者卻寥寥無幾。不少熟練的家政人員一聽說是伺候老人就不愿意來了,因為很累很臟,還時常溝通不暢。
唐麗禮說:“我們服務員很不容易,給老人清洗廚廁,修剪指甲,還要照顧老人情緒。”
虛擬養老院將老人們主動捐給機構的感謝費設成多種獎項,獎給那些吃苦耐勞、忍受委屈的優秀服務員,以資鼓勵。endprint
姑蘇區虛擬養老院幾年來培養了一支261人的家政隊伍。“我們招聘本地下崗或者家庭困難的婦女,雖然收入不高,但崗位穩定,管理規范。我們還繳納五險一金,按照現行的社保政策,50歲就可以退休,退休后有保障,所以還有一定的吸引力。”路忠說。
路忠認為,虛擬養老院是公益性機構,提高對老人的收費并不合適。我國的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應當超前規劃,真正扶持養老行業,如有可能應將其納入社會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提高從業人員的待遇與地位。
護理院的蘇州品牌
蘇州在護理院醫保定點上開了先河,這種醫養結合的民辦護理院也是外地參觀者的興趣所在。
位于北環西路的蘇州夕陽紅護理院,由四棟白色小樓構成。會議室與姑蘇區虛擬養老院一樣,掛滿了各種獎項與錦旗,座椅整整齊齊,已習慣了接待各地參觀者。
院長劉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前年去北京開會,外地好些衛生廳長問是不是老年人醫院,他們也有護理院是老年公寓,沒有護士。沒有民辦護理養老院的概念。”
夕陽紅護理院是一個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收納對象為失能失智的老人,功能是延續醫療康復,精神撫慰,延長老人壽命,減輕老人痛苦及臨終關懷。
本刊記者隨機走進幾間有家屬的護理房,老人們大多在曬太陽,護士正送去下午茶—熱茶與蛋糕。88歲的徐文芳患有糖尿病,因骨折入院,她66歲的女兒王筱敏正好前來探望,守在一旁。
“小姑娘們的服務態度很好,這里價格也便宜,我們看報紙知道的。”王筱敏比較滿意。“夏天是綠豆湯和水果!”旁邊的老奶奶突然大聲插話。
一位老人在這里住院,醫療、生活和護理每月開銷總共不到2000元。
收費由住院費用和自費構成。住院及醫療費用,一般退休職工走醫保卡報銷95%,個人承擔5%,約一兩百元;自費含伙食、生活護理和雜費,約1770元。
“蘇州一位老人一天87.15元的平均定額,醫保費用不算很高,但解決基本醫療沒有問題的。蘇州非公務員的退休工資約2000元。我們這樣的服務,對于減輕社會和家庭負擔很有幫助,要是請家政每月三四千元,還無法提供醫療護理。”劉軍說。
這個護理院有40多位醫生,大多是退休的老醫生,一般的疾病和搶救在這里都可以救治。但并非所有老人都可入住,只有失能或失智的才行。
上午,夕陽紅護理院剛剛送走人社局、衛生局、民政局、財政局的檢查人員。劉軍介紹,蘇州比較規范,衛生局查醫務人員資質、人員配比、醫療規范、藥房等等;民政局查生活護理,護理員(護工)資質、人員配比、上崗資質等等;人社局查收費及人員是否符合標準,防止浪費社保基金。人社部門還會免費上門培訓,直到護理人員拿到護理員證。
夕陽紅的護工,主要處理老人大小便、洗澡等等,其他的由140多位年輕的護士包辦,她們是衛校、大專、大學的畢業生,一人管兩個房間,5到6人,8小時輪崗三班制。
鄭利江說:“全市39家護理院基本都是民營的,1.2萬張床位,使用率超過八成。”
蘇州對民營護理院的政策扶持力度很大,財政每年都會拿出一筆錢給予建設、運行補貼。
建設補貼是一次性的,一張床位補貼5000至1萬元(新建1萬,改建5000)。而民營機構建一張床位,成本為六七萬元,如購買土地,至少20萬元。公立福利院由于標準較高,一般至少50萬元的成本。
運行補貼則是長期的,一張床200元/月,按實際入住病人算。正常運作時,水、電、氣、電話的收費標準都按民用計算。對于護理員也有特崗補貼,按月發放,第一年100元,第二年200元,8年后800元封頂。
鄭利江說:“蘇州的護理院占江蘇省六成以上,十年的運行,已形成了蘇州特色的民辦護理院品牌效應。吳江盛澤鎮又有兩個老板投資了5000萬元做護理院,他們的眼光比政府獨到,相信很有前景。”
只欠東風
“護理院的投資大,周期長,贏利點低。”做了七年護理院的劉軍說。
“我們收費是死的,不懂財務的人也能算出我們的收入,雖說有補貼,可投入是巨大的,社會需求大,我們2007年50張床,現在650張,一直沒停過。”劉軍掰著手指頭說。
蘇州的護理院支出最大的部分是人力資本,占到55%~60%。隨著最低工資的上調,五險一金基數、夜班費水漲船高。蘇州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530元/月。
夕陽紅護理院全員交五險一金,護士、護工月收入分別為4000、3000元左右。由于護工待遇不高,工作臟累苦乏,沒有社會地位,所以招聘極難。
第二塊開支是房租,夕陽紅護理院一年的租金是350萬~360萬,占支出的15%~20%。
劉軍說,現在是微利運行,蓄勢待發,需要的不再是補貼,而是國家給政策,只欠東風。
“比如一個瓶頸是,政府投資應有的功能沒有發揮出來,公立福利院建設動輒幾億元,其實未必要花這么多錢。政府應節省開支,用到該用的地方。”劉軍說。
在劉軍看來,公辦養老院本應面向三無老人、五保戶托底的,很多不符合條件的人卻占用和浪費了資源。比如夫妻公務員退休金最少1萬元,花3000元住在公辦福利院。如果將這部分人群釋放出來,會給民間養老機構巨大的市場空間。
蘇州的護理院往往會為同一個問題擔心:租用的大樓何時會搬。因為政府沒有相關規劃,一家護理院幾年之間搬了兩次,馬上又要搬家了。
“盡管蘇州養老已經做得蠻好,但這些反映出政府對養老還是不夠重視,還處于被動應對的姿態。”劉軍說。
蘇州政府最近的一次雪中送炭,讓劉軍看到了政府對待養老的誠意。
劉軍曾經最頭痛的是意外傷害,僅僅2013年就賠償了30萬元。“老人摔跤,我們先治療,摔一次認一次。好在政府剛剛幫我們購買了機構養老人身意外傷害險,政府出80%保費,我們20%。”
信任危機也是劉軍時常擔心的事。他怕投資人是外行,追求快速回報,一旦出現醫療事故,一經媒體曝光,整個行業將遭到抹黑。幾年前,一家護理院曾發生一起護士扇老人嘴巴的事件,被媒體曝光后,同行們郁悶了許久。
“我們的管理固然需要更加成熟,但這是個大家不愿涉足的行業,有待扶持,希望社會能夠寬容一些。”劉軍說。
為了讓家屬了解老人情況,夕陽紅護理院搜集意見本上的意見,每月召開工休座談會,并定期發問卷調查,家屬不常來的會主動打電話告知近況。夕陽紅護理院還設立了病人服務中心,專門處理投訴。
劉軍說:“投訴最多的是伙食,眾口難調。我們很需要民政部或行業來制定一個標準,每位家屬生活護理標準不同,缺乏標準,易引發醫患糾紛。”
2012年到北京開會時,劉軍發現全國的護理院不到50家,首都只有3家,還是區級醫院改的。蘇州在全國護理院最多,起步最早。作為探路者,蘇州面臨的難題,或許越來越多的城市也會遭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