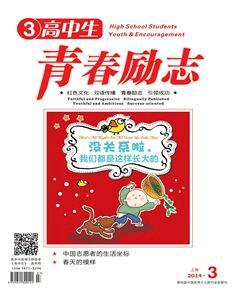天行者的夢想
2014-03-14 17:00:10孟祥云
高中生·青春勵志 2014年3期
關鍵詞:學生
孟祥云
一臺鳳凰琴,暮歸的老牛,界嶺的國旗,幾抹清瘦的背影,雪蓮的圣潔,人性的光輝……這是小說《天行者》呈現給我們的畫面。望著淺黃的稻田,再看看這些非洲饑民般的孩子,我心潮起伏。他們借宿在余校長家,二三十個人僅靠余校長微薄的工資和山里的天賜之物度過書聲瑯瑯的歲月。余校長那雙骨節粗大的手,他的妻子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孫四海和鄧有米吹奏的哀怨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些似乎是界嶺在漫長歲月中的見證。
“面對他們,我無地自容。”記者在采訪被清退的民辦教師后,感嘆民辦教師是中國教育的一部血淚史,他們一手握著鋤頭,一手拿著課本,在學生的心中種下燦爛的花海。
支教生夏雪,將青春的夢想留在了界嶺的山上,玻璃板下的抄詩本,記載了已成往事的青春年華。她說是界嶺的純粹,是界嶺紛紛而下的雪凈化了她的心靈。她帶著一沓作業本,坐上寶馬車離去,后來卻不幸離開了這個世界。她的離去令人傷感,也讓人久久緬懷。還有原本只想作秀的駱雨,在冰冷的教室里光著腳丫上課,引發了哮喘,最后不得不回省城休息,但他最后竟毅然決然地回到界嶺,因為他中了界嶺的“毒”,靈丹妙藥無法解的精神之“毒”。
偉岸的形象、堅定的目光是英雄定格在相框里的模樣,但我更想記下來自身邊的感動。我們可以純粹地活著,無關金錢名利,磊落地立于天地之間。
轉正對于民辦教師來說是夢境深處的希望之花。唯一的轉正名額,余校長將它讓給年輕的教師張英才。街上飄來縷縷肉香,余校長卻在昏暗的街角嚼著冰涼的紅芋。黃昏的放學路上,老師領著學生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涪陵窖里,家長們在忙碌,孫老師的茯苓是孩子們的書本費和伙食費。
學生是老師的孩子。
(作者系湖南常德市鼎城區一中淺草文學社成員,指導老師為虞曾麗)endprint
猜你喜歡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21年4期)2021-04-26 19:00:35
英語文摘(2020年9期)2020-11-26 08:10:12
甘肅教育(2020年6期)2020-09-11 07:45:16
甘肅教育(2020年22期)2020-04-13 08:10:54
甘肅教育(2020年20期)2020-04-13 08:04:42
當代陜西(2019年5期)2019-11-17 04:27:32
電影(2018年9期)2018-11-14 06:57:21
作文世界(小學版)(2018年4期)2018-10-16 17:13:34
快樂作文·低年級(2016年12期)2017-01-03 20:52:44
快樂作文·低年級(2016年6期)2016-06-24 18:5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