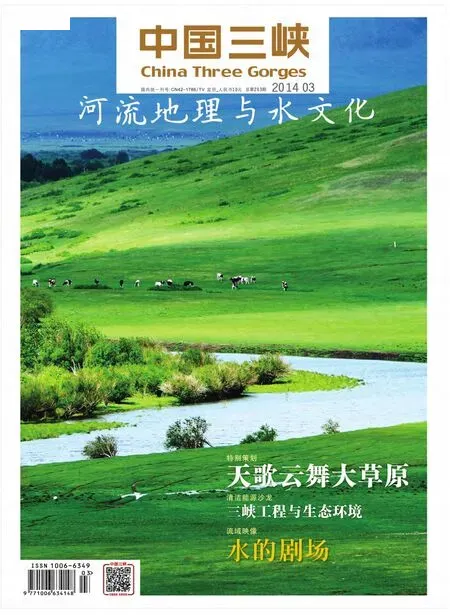癸未三峽記③
癸未三峽記③
文/于 堅 編輯/羅婧奇、吳冠宇
無論你走到我故鄉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會聽到人們談論這條河就像談到他們的神。
——于堅《河流》
遇到一個干瘦的老頭牽著一匹馬從山上下來,踏著碎磚走過,我心里動了一下,差點就問出“杜甫無恙”?
夔門是從西向東進入三峽的開始之處,“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杜甫)。平淡無奇的江岸在這里忽然崛起,聳起兩座南北對峙的垂直巖壁,北岸的赤甲山呈紅色,南岸的白鹽山呈灰白色。猶如巨大的鋼鐵之門剛剛緩緩拉開,“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蛟龍屈窟宅,愁畏日車翻”,“西南萬壑注,勁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杜甫)。偉大與光榮開始了,后面就是奇峰怪石層出不窮的三峽,猶如巨石組成的鴻門宴兩邊排列,遠處是變幻莫測的云霧和滾滾大江。只等著“天降大任”者前來赴湯蹈火,培養浩然之氣,天地雄心。夔門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座造物主在河流上創造的凱旋門,但它與羅馬的凱旋門不同,它不是結束而是混沌初開。
一個有心靈的人,從前只是在書本上理解“雄渾”、“大氣”、“混沌初開”這些形容詞的,來到這里,他立即就“胸含元氣,眼窮大荒”,覺悟到那是什么。一個詩人,由此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一個豪杰,由此會拋棄草莽,萌生逐鹿中原之志。昔日的詩人無不意識到長江對他們生命的意義。這河流流淌著的東西是書本上永遠找不到的,那種隱蔽著的東西可以啟發人的心智,令詩人在人群中出現,令詩人在詩人中成為偉大。去夔出峽是一種偉大的中國經驗,它曾經造就了許多偉大的詩人,李白去夔出峽,從此進天下,“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杜甫來到夔門,詩歌更多了悲壯沉郁,“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偉大的青銅之聲,過了千年,我這個剛剛誕生的讀者進入夔門穿過三峽的時候,依然像陸游感嘆的那樣“頃來目擊信有證”,被那語言的能指力量所震撼。
大壩蓄水后,水位上升,夔門就看不見了,“水面增寬,流速下降,峽感減弱”,水位上升30-40米,枯水季節水位更高,相當于十多層樓那么高。白帝城也要淹沒。夔門、白帝廟將成為庫區的群島之一。夔門旁邊就是夔州,現在叫做奉節,是四川省的一個縣城。公元766年,杜甫帶著家人來到這里,一住就是兩年。

左:2010年10月,航拍175米水位的三峽夔門。 攝影/劉曙松/CFP
在這里,中原詩人杜甫徹底成為一位長江詩人。“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州一系故園心”,長江詩人的意思就是像河流那樣成為了時間本身,“逝者如斯”,杜甫的詩歌是生長的,越來越重、越來越深、越來越寬闊深厚。“巨積水中央”、“神功接混茫”,他的詩歌進入了不滅的自然之道,像季節那樣循環,日日新。
奉節舊城已經拆除,新城建在山頂上,比白帝城還高。昔日,白帝城是夔州最高的地方,“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飄渺之高樓”(杜甫)。我明白了為什么是“白帝彩云間”,因為如果在江面的船上,白帝城就是在高山頂上,從江岸到達城中至少要爬一個小時。我們踩著瓦礫殘磚,沿著也許是杜甫曾經走過的石級,登上白帝廟,放眼望去,長江灰蒙蒙的,“峽圻云霾龍虎臥”,南岸停著許多黑乎乎的運煤船,山坡也是黑乎乎的,這是多年從事煤炭工業的結果。但“江濤萬古峽”,看見的還是杜甫看見過的那種地形,他在這里寫下的詩歌也仿佛是筆墨未干似的。
遇到一個干瘦的老頭牽著一匹馬從山上下來,踏著碎磚走過,我心里動了一下,差點就問出“杜甫無恙”?“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白帝廟是杜甫經常來的地方,建筑已經不是杜甫時代的,但“舊俗”使祠廟毀了又建,現在的白帝廟是明朝留下的,依然供奉著劉備、關羽、張飛和趙云。我以為這里面應該是供奉李白和杜甫,是他們的詩歌使白帝小城名垂千古,而不是這些正襟危坐的三國時代的政治家和將軍,但是沒有。文史館的人領我們去參觀,問我們看出什么異樣之處沒有?都看不出來,他笑道:文革時期,紅衛兵把劉備、關羽、張飛和趙云的頭都砸掉,只留下在一邊脅肩諂笑的侍候主子的小官人的頭,說他們是勞動人民,所以這些小人的頭都是原裝的,而劉備、關羽、張飛和趙云的頭則是文革后重塑的。

2002年,奉節依斗門。 攝影/顏長江/FOTOE
忽然想到,此時代的許多事情看起來都像是行為藝術。行為藝術玩的就是一招鮮,但河流不是一招鮮,它是存在,是我們的宿命。
到達忠縣的時候大年三十,也是一個水泥城。100年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博爾德·約翰·立德所見到的“最令人矚目的是眾多的廟宇和亭子”已經消失。我們原來以為可以在長江邊放炮仗進入癸未年,但縣城里也禁止放炮仗。天一黑街上就沒有什么人了,家家都關門看電視。沒有炮仗聲音的小縣城,安靜得令人孤獨感倍生,我們摸黑出城,去到郊外,在一個大橋上偷偷摸摸地放了一把,像是游擊隊炸橋似的。一個支炮,一個點火,另兩個放風望哨。寒風呼呼,隱約聽見爆竹聲音從大地的深處傳來,與我們的爆炸聲呼應著,那邊是鄉村,心里溫暖了許多。忽然想到,此時代的許多事情看起來都像是行為藝術。行為藝術玩的就是一招鮮,但河流不是一招鮮,它是存在,是我們的宿命。
大年初一前往石寶寨,去那里的陸路很不好找,在長江兩岸,人們習慣的交通是水路,上水或是下水,在岸上問路,經常是語焉不詳。我們好不容易問到了路,非常可疑,路順著長江邊,土路,泥濘,坑坑洼洼,一輛車也沒有。偶爾,“歲時伏臘走村翁”(杜甫),問問,都說這路就是去往石寶寨的。在泥坑里跌撞前行,慢得要命,經過一個一個美麗的村莊,風景看得很清楚,想起魏晉時代的人物,在馬上看風景都嫌快,要坐牛車看。雖然建筑雷同,但地勢、植物各有千秋。偶然還會出現一片青瓦,陌生,令人眼睛一亮。人們沉浸在新年的喜悅中,田野里再沒有人勞動,年豬已經煮熟,酒已經釀就。大家都閑下來,新衣裳已經穿得開始合體,或坐在房屋外面聊天、打牌、玩麻將,或站在公路兩邊曬太陽、嗑瓜子。昔日,春節儀式煩瑣,活動豐富,一個地方與一個地方不同,是中國社會祭祀祖先,敬畏神靈,交流感情、交流文化的重大節日。現在除了吃,就是看電視,每個地方都一樣。在土路上磨蹭了幾公里之后,忽然又找到了水泥路,原來這才是去石寶寨的正路。我們問的是去石寶寨怎么走,農民告訴的就是他們走的路。而去同一個地方,農民有農民的路,政府有政府的路。一上了政府的路,速度就快了,沒有什么車輛,汽車都停下來了,我們得以風馳電掣,剛昏昏欲睡,已經到了。
石寶寨名聲顯赫,重點保護,但在我看來,只是差強人意。也就是把一個十二層的樓宇依著突向江面的巨巖建造,木梁子都固定在石壁上,猶如腳手架,把外觀修成了廟宇的樣子,小聰明。古代建筑,精美偉大的多了,要不是已經拆得所剩無幾,石寶寨也不會“世無英雄,逐使豎子成名”。倒是這里的一個典故很有意思,巖石中有一個石頭叫做流米石,典故如下:“相傳,石穴有米出,可飯一僧。僧嫌孔小,鑿大,米絕。”在許多方面,人類今天不是正在干著“嫌孔小”的事情么?

左:重慶巫山,神女峰下青石鎮上的游客。 攝影/微光

重慶巫山縣青石村晨景。 攝影/顏長江/FOTOE
現代主義拒絕迷信死亡,對死亡的儀式毫不講究,一切從簡,死亡冷冷清清,文化系統里面沒有鬼城這種象征性的闡釋體系,死無定所。
鬼城豐都所在地叫做平都山,蘇東坡曾寫詩贊美:“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歲月閑”。遠遠看去,卻一點都不閑,很是熱鬧,山前人聲鼎沸,山頂修建了一個白色的巨人頭像,坐落在鬼城上面,非常搶眼,令周圍的一切都小掉。問當地人,那是什么?告曰:是開發商搞的旅游項目,修了一個鬼王的巨像。又悄悄地附我耳朵說:“那個老板前幾天出車禍了,膽子也太大,敢在鬼頭上動土。”
鬼城很有意思,進去的人無不戰戰兢兢、擔驚受怕的。過一個橋叫做奈何橋,橋有三座,其中一座是奈何橋,導游不出氣,看你走哪一座,走了不對的那一座,就是做過壞事。我恰恰走得不對,又叫我把一個鎳幣扔到一個水缸里去消災,落下去要正好進入缸底的一個洞口,扔了幾個,才進去了,松了口氣。又過一個門叫做鬼門關,男左女右,而且過門的時候不可碰到門檻,碰到門檻就成為“關門鬼”,我不記得是否碰到了門檻。又經過黃泉路,東地獄、西地獄什么的。
來到閻王殿,殿前有一個腳跟大小的鵝卵石叫做“考罪石”,你要單腳站在上面若干時間,并且正視大殿前面寫著“目光如電”的匾,如果站不住,就是心中有鬼。進了閻王殿,柱子上的對聯說的是“不涉階級從這里過行一步是一步,無非貴賤都向個中求悟此生非此生”,“善惡昭彰”、“黑白分明”。然后就到閻王面前,燒香點燭,搞得非常陰森,很有氛圍,和想象的閻王殿差不多。唯物主義者把這些視為迷信,有一個當代人的對聯說“三三兩兩,笑談鬼城牽強附會”。
其實這并非“迷信”兩個字那么簡單,在我看來,它是一種儀式,經歷了這個儀式,對人的心理會產生某種暗示作用,從而對人的行為有所規范、限制。這是一種中國化的民間的教育儀式,它的作用未必不如那些課堂里的一本正經的宣講。在虛擬的地獄場景中,人們身臨其境,我看出來很多人確實是臉色發白,沉默不語。戲劇性的是,在進入閻王殿之前,山上還有財神廟,可以保佑生育的百子殿什么的,在那里,熱鬧非常,燒香求卦的爭先恐后,香火彌漫,大殿被熏得黑漆漆的。最后卻來到閻王殿,那里安靜得出奇,雖然也是摩肩接踵,魚貫而入。

豐都鬼城展示的地獄。 攝影/微光
鬼城下面的豐都老城大部分已經拆為瓦礫堆,剩下的幾棟也已經搬空,這些建筑一看就是匆忙簡陋的那種,根本沒有好好搞,像是沒有完工的毛坯板。一邊是空曠的瓦礫堆和人去樓空的水泥房子,陰森森的。另一邊則是人氣沸騰、廟宇香煙的有著千年歷史的鬼城,穿長袍馬褂綾羅綢緞的鬼住在里面。古代文化對于死亡是有交代、有去處、有說法、有儀式的,所以死亡非常熱鬧。現代主義拒絕迷信死亡,對死亡的儀式毫不講究,一切從簡,死亡冷冷清清,文化系統里面沒有鬼城這種象征性的闡釋體系,死無定所。
有很多小販人賣冥錢、冥紙、土香什么的,隨便問問他們有沒有見過鬼,都笑著說小時候見過的。同樣的問題換個地方問,人家恐怕大驚失色。他們描述的鬼與根據《聊齋》改編的電視劇里面的那些形象差不多,蒲松齡創造的話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實在廣泛,其實哪里有鬼,鬼就是文化上關于死亡的一套話語系統。我在神秘主義、知識的有限性上相信鬼世界的存在,我確信并非一切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世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在到達他們復雜的計算之巔的時候,總是發現他們成為了神秘主義者,鬼神游走在科學的最深處,只是在科學以為一切難題都已經演算完畢,答案出現的時候,忽然露出一張鬼臉來,咧嘴一笑。
我看見了那兩條唐朝游過來的石魚,水靈靈的,我慢慢靠近,蹲下來,摸了摸,它體溫冰涼。
我一直喜歡黃山谷的書法,少年時期就一直看,有一本《黃山谷書墨竹賦等五種》,每年都要拿出來翻翻。到了長江邊的涪陵,在江水中間的石頭上看見他的字,才知道他晚年被貶到涪陵,“落木千山天遠大”,“出門一笑大江橫”,就住在白鶴梁對面的江岸,據說每天寫字,流下來的墨水把長江染黑一片,那一帶的鯉魚都是黑的,稱為墨鯉。在長江邊,他的書法越寫越寫越好,是長江使他覺悟了書道。他說:“晚入峽,見長年蕩漿,乃悟筆法”。白鶴梁,是長江中的一群黑色的石頭,每到春天和冬天的枯水季節,它就像一條巨鯨的脊背那樣露出來。它仿佛長江的靈魂,一現身,人們就要去祭祀膜拜,誠惶誠恐,看看大河之神在黑暗中又干了些什么。人們在上面刻字銘文,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民國、包括后來的地方官員,都在石頭上留下痕跡,渴望著他們的名字能夠依賴大河靈石而不朽。從唐代開始,白鶴梁就成為神話、傳奇。一個傳說是有道士于水落石出的時候在石頭上修煉,水漲,石頭消失,他羽化為白鶴飛去。人們還在石頭的一處刻了兩條魚,相信石魚出現的時候,就意味著豐年吉兆。后來科學界發現,這兩條石魚標示的水位與涪陵地區的0點水位很接近,成為一個水位的標準尺度,那些題刻也可以視為一個古代的水文歷史記錄,一座記載了1000多年以來長江上游枯水水位表的“水文站”。

2003年,白鶴梁上的石魚,重慶涪陵。 攝影/顏長江/FOTOE
庫區蓄水之后,水落石出就不存在了,白鶴梁將永沒水中。補救的辦法是,在石梁周圍建造一個玻璃罩子之類的東西,就可以隨時參觀了。但白鶴梁的神秘在于水落石出,它要整條大河在某一刻緩慢地落下去,才現真身,而且這大自然創造的偉大儀式通常每十年才出現一次,一個人就是一生住在涪陵守著,也就是幾次機會而已。這水落石出的神秘儀式令人感受到的是時間,是比人的歷史更長久的造物者的力量。我是幸運的人,癸未年的正月初三,白鶴梁再次水落石出,而且是最后一次,我是前往參觀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員。明天,這里就要封閉施工,開始建筑水下展廳了。
我們乘著小船渡過長江的一段,駛向距江岸100米的白鶴梁,石梁長約1600米,寬約15米,并不是整石,而是許多石塊組成的。那些石塊上刻著各種字體的漢字,被江水打磨之后,像是刻在鐵鼎上甲骨文。有的石頭被雕刻成魚,有的上面刻著白鶴。一位1963年在涪陵當專員的官員刻的文字對那些古代的題刻評論道:“盡管有唯心的觀點,貴在四代文。”題刻內容大多是贊頌山水,祭祀神靈,到此一游。黃庭堅題刻沒有單獨用一塊石頭,而是隨便題在另一幅石刻的一個角上,他題的是:“元符庚辰涪翁來”。果然不同凡響,什么也沒有說,卻字字珠璣,“來”已經足夠。已經是造化,在著,如此,還說什么呢。石梁很滑,長江簇擁著它,像是要把它推走,它不動。以動著的河流觀之,石頭一直在動。以不動的石頭觀之,河流是不動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孔子說的是川流,也是石頭。河流的靈魂是不動的,它現形于石頭。我看見了那兩條唐朝游過來的石魚,水靈靈的,我慢慢靠近,蹲下來,摸了摸,它體溫冰涼。

仿古的游輪穿行在長江三峽。 攝影/微光
那些食物的歷史和長江一樣古老,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來,他們當然不會在一個叫做重慶的地方舍棄古老而偉大的火鍋直奔麥當勞。
重慶是從宜昌開始的長達六百多公里的三峽大水庫的終點。我們到達重慶的時候是公元2003年的2月4日,舉國正在放假,大都會喜氣洋洋。過春節與國慶節、五一節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大紅大綠,大吃大喝,張燈結彩,紅旗飄飄,標語掛起。重慶是長江流域的一個現代主義之夢,未來中國的樣板之一。在出租汽車里,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聽著相聲,那相聲在嘲笑重慶人的椒鹽普通話。
古老的朝天門碼頭已經煥然一新,修得就像一艘水泥的航空母艦。三十年代的那個典型印象“霧都重慶”已經不大看得出來,高樓林立,大部分房間都裝著空調,數千年來在炎熱夏夜露宿街頭的風俗終結了。由于高樓林立,城市感覺上似乎已經沒有過去那么高峻,幾乎成了一個平臺。摩天高樓的縫隙中,偶爾可以瞥見長江,它正經歷著它最后的一個枯水季節。朝天門碼頭還可以看見原始的河床,江水在流動,一片巨大的沙灘裸露出來,它只是在冬天出現。許多市民領著孩子沿著水泥的臺階一直下到那河床上,在那里放風箏、玩沙。
解放碑因為有1949年解放重慶的紀念碑而聞名,這附近的街區是重慶市中心,已經率先進入現代行列,世界第一流的商業步行街、大商場、電梯、摩天大樓、玻璃幕墻和當代中國最時髦的紅男綠女。春節期間,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這里購物或者走一走,滿足一下。摩肩接踵,人頭密集,洪流滾滾,空氣令人窒息,它也許是世界上行人最密集的商業區了。二十多年前我在這個城市花20元錢買了一雙黃色的皮鞋,但這次我什么也沒有買,那些豪華的百貨商場與昆明也差不多。
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名模廣告、化妝品、各式各樣的世界名牌,從那些時髦的大櫥窗望進去,與在巴黎或者紐約的櫥窗所見者并無二致。但人們一開口,你聽到的就是古老的四川方言。解放碑的購物中心令我產生一種分裂的感覺,一方面是人們大大咧咧的舉止動作,滿街嘩響的生動清脆的四川方言,令我這個四川籍的外省人聽著親切,頗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感覺,因為雖然身在云南,但我父親一輩子都對我說的是四川話。對于我,這種語言來自我父親,來自沱江邊上一個叫做南津驛的小鎮,可以上溯到于氏家族族譜的開頭,上溯到古代的長江流域的巴人。另一方面,那些巨大的建筑物、玻璃、瓷磚、電梯似乎只是與英語或者普通話有關的某種生活。兩種完全格格不入的東西拼貼在一起,一方面是與時俱進、日新月異的產物,一方面是古老時間以不變應萬變的產物,是滿大街的“鄉音無改”。如果周圍的人都不說話,這里看上去似乎就是紐約、香港的步行街或者斯德哥爾摩的皇后大道。但他們一張口,又仿佛是歐洲最時髦的商業步行街的行人都忽然被換了舌頭,說起四川方言來,發音是從古老的長江流傳下來的那種,是適合于傳授榨菜與椒鹽麻辣臘味燒鹵的那種,是適合于李白蘇軾這樣的詩人吟風弄月、天馬行空的那種,或者潭邦五那樣的船老大在朝天門碼頭上喝五吆六的那種。

白帝城。重慶奉節。 攝影/王苗/CTPphoto/FOTOE
現代主義其實是一場英語領導的全球運動。在中國,它至少也是普通話領導的運動。四川方言無論怎么聽與現代主義的標準都是別扭的,它完全不適合彬彬有禮地站在麥當勞的柜臺前點炸雞腿、熱咖啡和漢堡包。在中國,普通話在四川最難推廣,一講普通話,四川人的舌頭就硬掉。我父親,四川資陽人,在政府里面工作一輩子,沒有學會一句普通話,而是逼著同事聽了一輩子他的四川話。所以,癸未立春這天的上午,在解放碑,在古老的四川話和日新月異的當代現實之間我有點感覺分裂,思維混亂。但轉過一個街口,就看見無數人在小吃街上埋頭猛吃麻辣燙,令人直咽口水的川味從一個接一個的小吃鋪子里漫溢到街道上,這就對了,重慶真相畢露。什么西裝領帶,站在黃線外面等候,左手使叉,右手拿刀……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家街邊一站、一蹲,一靠、褲子一擼,領帶撕開,埋頭猛喝,凝神細品,湯澤汁液什么的把瓷磚地面弄得滑膩非常,一不當心就要滑倒。這些現代主義的瓷磚地面可不是為重慶小吃的鹵澤湯水設計的。許多拎著竹篾扁擔,衣服襤褸的挑夫,在人群間穿來走去,尋找活計,大家也不會白眼看他,怪他有辱現代化的斯文。那些食物的歷史和長江一樣古老,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來,他們當然不會在一個叫做重慶的地方舍棄古老而偉大的火鍋直奔麥當勞。
我在一家旅館結束了長江之行,乘飛機返回昆明走之前,我走進昨天發現的一條即將拆除的舊街道,在這里,重慶的日常生活依然像榨菜那樣緩慢地腌制著,人們在街道邊上打撲克、敲麻將,補鞋匠靠在墻角落打盹,老人們坐在茶館里聊天、下棋,老媽媽提著蔬菜籃子悠悠地往家去,找到活計的挑夫滿頭是汗坐在石坎上休息。這生活現場令人想起李劼人的小說。我鉆進昨天吃過的那家小館子,再要了一碗肥腸粉,老板依然像二十年前那樣,朝著里面的伙計用鄉音吆喝一聲,“肥腸粉一碗……”。他把那個碗字唱得轉了一個彎,那一刻,我感覺到時間并沒有前進,就像永恒的長江。

重慶解放碑。 攝影/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