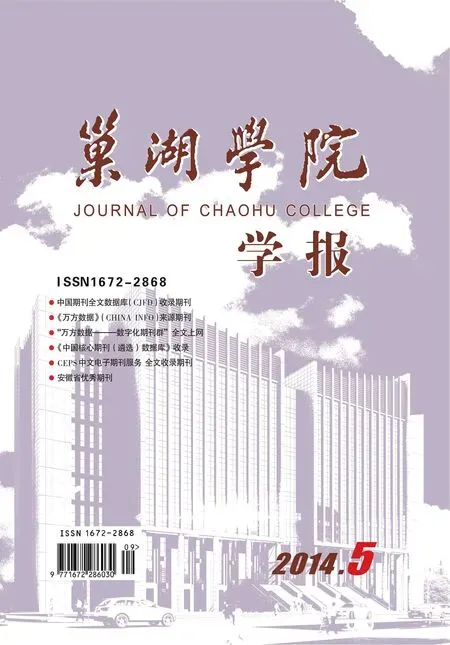民國時期知識界關(guān)于農(nóng)村文化的認(rèn)識及其規(guī)劃
——以《東方雜志》為中心
蔡勝
(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民國時期知識界關(guān)于農(nóng)村文化的認(rèn)識及其規(guī)劃
——以《東方雜志》為中心
蔡勝
(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民國時期,農(nóng)村文化匱乏,主要表現(xiàn)為文盲比率高和陋習(xí)盛行。時人主要從農(nóng)民的貧困和新式教育的不良來分析農(nóng)村文化匱乏的原因。以《東方雜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從教育內(nèi)容、教育對象、歸農(nóng)運動和移風(fēng)易俗等方面提出了相應(yīng)的對策。
民國時期;知識界;農(nóng)村文化;《東方雜志》
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獲得者西奧多·W·舒爾茨認(rèn)為人力資本是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增長的重要源泉,強(qiáng)調(diào)了生產(chǎn)力與農(nóng)民素質(zhì)的關(guān)系。[1]農(nóng)村教育是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關(guān)鍵得到當(dāng)代知識界的認(rèn)同。①林毅夫.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發(fā)展農(nóng)村教育、轉(zhuǎn)移農(nóng)村人口[J].職業(yè)技術(shù)教育,2004,(9):31-35;楊明.發(fā)展農(nóng)村教育是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關(guān)鍵[J].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4,(7):91-92.民國時期的知識界也認(rèn)識到了農(nóng)村文化改造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應(yīng)的對策,本文以《東方雜志》為中心,對民國時期知識界對農(nóng)村文化的認(rèn)識及其規(guī)劃進(jìn)行初步考察。
1 農(nóng)村文化匱乏
民國時期,農(nóng)村文化極端匱乏,主要表現(xiàn)為文盲比率高和陋習(xí)盛行。1930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jìn)會在定縣進(jìn)行了教育程度調(diào)查,詳見下表:

此次調(diào)查是在“教育發(fā)達(dá)”的定縣,而且調(diào)查對象包括了縣城居民,其他農(nóng)村文盲比率可能更高。占人口總數(shù)17%的“識字者”也僅僅為認(rèn)識一些漢字,僅有部分人能夠看報、記賬和寫信。金陵大學(xué)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系在1929—1933年的調(diào)查提供了類似的結(jié)果,男子中不識字者為69.3%,女子中不識字者為98.7%;華南不識字者為80.7%,華北不識字者為85.2%。[3]針對此種狀況,胡愈之感嘆道,“吾國內(nèi)地農(nóng)民,殆全系不識字者,其智識之蒙昧,尚未脫半開化時代。因此吾國一切文化事業(yè),與大多數(shù)之農(nóng)民階級,竟若全不相關(guān)。”[4]
民國時期鄉(xiāng)村陋習(xí)盛行,婚喪、迷信和賭博等陋習(xí)普遍存在于鄉(xiāng)村。“接了媳婦,窮了公婆”[5]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毛澤東在興國調(diào)查中就指出婚喪鋪張的情況。[6]農(nóng)村迷信活動盛行,特別是遇到水旱災(zāi)和流行疾病的兇年時期。賭博風(fēng)行,江蘇靖江的農(nóng)民,“一年之中,除耕作外,殆無時無日不浸潤沉醉于賭博中。”[7]各種陋習(xí)直接導(dǎo)致了農(nóng)家的負(fù)債。江蘇武進(jìn)的許多農(nóng)家就因為各種陋習(xí)而導(dǎo)致“蒙莫大之損失,遂舉債藉以彌補焉。”[8]
農(nóng)村教育的缺乏,文化的真空化和生活的空洞化,使得農(nóng)村的“靈魂”喪失,“中國的農(nóng)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jīng)陷入了現(xiàn)代化變革的深淵。”[9]
時人認(rèn)識到了農(nóng)村文化改造的必要性。行政院農(nóng)村復(fù)興委員會從農(nóng)業(yè)發(fā)展角度分析農(nóng)村文化的必要性,“吾國農(nóng)民素?zé)o教育,不識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以至固陋寡聞,目光短淺,對于農(nóng)業(yè)之新技術(shù)、新方法,不知應(yīng)用,農(nóng)業(yè)推廣,倍覺困難,數(shù)千年來,農(nóng)民之泥守古法,而未有改進(jìn)者,非無因也。”[10]楊開道在《東方雜志》上指出,“農(nóng)民缺乏知識,是我國農(nóng)村生活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農(nóng)民自身沒有能力去教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政府又對于農(nóng)村教育毫不注意,所以一百個農(nóng)民里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于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他們既然沒有受教育的機(jī)會,沒有充分的知識;所以總守著幾千百年傳下來的老法子,不知道怎么樣去增進(jì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去提倡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因為他們沒有知識,所以他們的生活雖然低下,也沒有法子去改良,他們雖然被旁的勢力或階級所壓迫,也沒有法子去抵抗。 ”[11]
2 民國時期知識界對農(nóng)村文化匱乏原因的認(rèn)識
農(nóng)村文化問題病根在何處?時人主要從兩個方面分析了農(nóng)村文化匱乏的原因。

一方面,農(nóng)民負(fù)擔(dān)不起新式教育高昂的費用。據(jù)時人調(diào)查,“受高級小學(xué)教育一年,至少須用費銀五十圓。受中學(xué)教育一年,至少須用費銀百六十圓至二百圓。受大學(xué)教育一年,至少須二百圓至三百圓。以今日全國人民之經(jīng)濟(jì)能力而論,年出五十圓至三百圓錢以買得受教育之機(jī)會者為數(shù)實少。此今日教育之所以只能為少數(shù)富人所獨有也。”[12]張思明指出,“科舉停止了,私塾取締了,盛行的學(xué)校,沒有資本的子弟休想作‘入幕之賓’。因是,大部分子弟求學(xué)的權(quán)利便被金錢的勢力所剝奪,而所賸余的少數(shù)能夠入學(xué)校的子弟,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至少握有相當(dāng)?shù)膬?yōu)勢。”[13]另一方面,農(nóng)民為了生存而辛苦勞作,不愿涉及新式教育。“教育如果不能幫助農(nóng)家解決饑寒的問題,在農(nóng)家看來,簡直是‘有損無益’的東西。”[14]“吾國都市城鎮(zhèn)間,小學(xué)尚多,而鄉(xiāng)村間幾致全無小學(xué),有時并私塾而無之。蓋生活程度日高,塾師之薪金,少于都市間人力車夫之工資,維持個人之生活已難。而農(nóng)人方面,救死且不遑,更何有于送子弟入學(xué)。故我國自興學(xué)以來,近三四十年,而農(nóng)民之不識字者,依然居十之八九。”[15]

鴉片戰(zhàn)爭以后,近代中國逐漸建立了一整套新式教育體系。新式農(nóng)村教育具有鮮明的城市化傾向,完全定位于工業(yè)化社會,舒新城指出,“我國現(xiàn)行之教育制度與方法,完全是工商業(yè)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而國內(nèi)的生產(chǎn)制度,仍以小農(nóng)為本位,社會生產(chǎn)制度未變,即欲絕塵而奔,完全采用工商業(yè)社會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應(yīng)有的結(jié)果。 ”[16]
教學(xué)內(nèi)容上,新式教育與農(nóng)村社會脫節(jié)。“小學(xué)畢業(yè)后,在社會辦事,每不能游刃有余。甚至如家庭社會常用之便條賬簿都不能作。”[17]教學(xué)內(nèi)容是適應(yīng)城市的需求而開設(shè),新式學(xué)校中所學(xué)的西學(xué)知識在鄉(xiāng)村中無用武之地,“知識分子所學(xué)的,所習(xí)慣的,又不能不在都市過活。”[18]“十里洋場的都市,對于大學(xué)生具有多大的誘惑力呵!但在事實上,他們也有非麕集于都市不可的苦衷,農(nóng)村的破落,使大學(xué)生的活動范圍日趨緊縮,只有都市,才是工商金融政治學(xué)校的機(jī)關(guān)的所在地,而這些機(jī)關(guān)又是吸收人才的尾閭。大學(xué)生的唯一目的,也只是在供給這些機(jī)關(guān)的需要。”[13]何思源稱之為“士大夫的都市化”。費孝通也指出新式教育對農(nóng)村人才的負(fù)面作用,“現(xiàn)在這種教育不但沒有做到實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化的任務(wù),反而發(fā)生了一種副作用,成了吸收鄉(xiāng)間人才外出的機(jī)構(gòu),有點像‘采礦’,損失了鄉(xiāng)土社會。 ”[19]
教學(xué)時間和教學(xué)方法上,新式教育與農(nóng)村社會并不契合。費孝通在《江村經(jīng)濟(jì)》中指出了這一問題,在教學(xué)時間上,“學(xué)期沒有按照村中農(nóng)事活動的日歷加以調(diào)整。村中上學(xué)的學(xué)生大多數(shù)是12歲的孩子,他們已到了需要開始實踐教育的年齡。在農(nóng)事活動的日歷中有兩段空閑的時間,即從1月至4月及7月至9月。但在這段時間里,學(xué)校卻停學(xué)放假。到了人們忙于蠶絲業(yè)或從事農(nóng)作的時候,學(xué)校卻開學(xué)上課了。”[20]在教學(xué)方法上,“學(xué)校的教育方式是‘集體’授課,即一課接著一課講授,很少考慮個人缺席的情況。由于經(jīng)常有人缺席,那些缺課的孩子再回來上課時,就跟不上班。結(jié)果是,學(xué)生對學(xué)習(xí)不感興趣,并造成了進(jìn)一步的缺課。 ”[20]
師資缺乏的現(xiàn)象非常嚴(yán)重。僅僅識字已經(jīng)不再是擔(dān)任教師的合格條件了,“農(nóng)村教育經(jīng)費的低落”導(dǎo)致鄉(xiāng)村師資更加缺乏。[21]據(jù)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1935年的調(diào)查,全國農(nóng)村每小學(xué)平均僅有教師2.4人。[22]
正是因為新式教育的種種問題,陶行知于1927年指出,“中國鄉(xiāng)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xiāng)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wù)農(nóng);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nóng)夫子弟變成書獃子。”[23]農(nóng)民對“進(jìn)不了城門,下不了地”的新式教育并不感興趣,對于農(nóng)民來說,“用腳投票”是他們對新式教育的最好評價。據(jù)1935年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在全國22個省961個縣的調(diào)查顯示,私塾在農(nóng)村教育機(jī)構(gòu)中仍占30.3%,新式教育并未被農(nóng)民普遍接受。[22]
雖然農(nóng)民們渴望通過教育來脫離農(nóng)村,而現(xiàn)實的貧困卻打擊著貧寒農(nóng)家的這一愿望,無力完成身份的轉(zhuǎn)換。而且新式農(nóng)村教育不合農(nóng)村需求,促使大部分農(nóng)民游離于教育之外;小部分受教育者卻逃離了農(nóng)村。農(nóng)村文化的真空由此形成。
3 民國時期知識界對農(nóng)村文化的規(guī)劃
農(nóng)村文化問題如此嚴(yán)重,國民政府的教育行政當(dāng)局又沒有切實的規(guī)劃和行為,“對于占有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nóng)民所急需之最低知識,則未聞有如何實際的規(guī)定,對于全國正在高唱復(fù)興農(nóng)村,草定農(nóng)村救濟(jì)方案的熱潮中,不聞提出若何撲滅農(nóng)村文盲運動的規(guī)程和意見,此實為不可理解之謎。”[24]政府的不作為促使知識界廣泛探討如何改造農(nóng)村文化。
此時學(xué)者們認(rèn)為必須從農(nóng)村教育入手,對農(nóng)村文化進(jìn)行改造。何思源認(rèn)為,過去教育的錯誤造成“政治組織之崩潰,社會秩序之紊亂,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之破產(chǎn)。”[18]吳覺農(nóng)也指出,“農(nóng)民生活改造的第一步,自非從教育著手不可。”[25]
在農(nóng)村文化改造的呼聲中,《東方雜志》論者對如何促使農(nóng)村文化改造進(jìn)行了規(guī)劃。

教育與生產(chǎn)的脫離是時人批評的主要方面,時人認(rèn)為,“我國目前之生產(chǎn)落后,經(jīng)濟(jì)破產(chǎn),完全或大部分都是由于過去教育之失敗,學(xué)校不能訓(xùn)練生產(chǎn)者,反而造成了許多消費者。”[26]30年代初,“生產(chǎn)教育”是“教育上最流行的口號。”[27]在農(nóng)村教育上,媒體更是重點宣傳“生產(chǎn)教育”。《東方雜志》“教育欄”編輯郭一岑認(rèn)為,生產(chǎn)教育有利于農(nóng)業(yè)發(fā)展,“用教育的方法去救濟(jì)瀕于破產(chǎn)的農(nóng)業(yè),因而增加生產(chǎn)的能率。”[28]時人將生產(chǎn)教育的重任托付給鄉(xiāng)村學(xué)校,一部分學(xué)者主張“先在鄉(xiāng)村設(shè)立一學(xué)校,然后以學(xué)校為中心去接近農(nóng)民,去訓(xùn)練農(nóng)民,去促進(jìn)全國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機(jī)能。”另一部分學(xué)者主張“先訓(xùn)練農(nóng)民然后由農(nóng)民自動的去產(chǎn)生學(xué)校,是由農(nóng)民的本身入手。這派受有丹麥農(nóng)村民眾教育思想的影響。”[27]吳覺農(nóng)認(rèn)為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育內(nèi)容應(yīng)切合生產(chǎn)教育,“各小學(xué)校中于三四年級的時候,應(yīng)授以農(nóng)業(yè)上和經(jīng)濟(jì)上各種重要的智識,而鄉(xiāng)間的動植物,土地,氣候,及鄉(xiāng)村生活,與人民頃刻是不相離的,應(yīng)該時時提示,不應(yīng)該死守著教本,去對付小學(xué)生。”[25]
《東方雜志》論者在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教育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公民教育。楊開道指出,“鄉(xiāng)村教育,不是偏重農(nóng)學(xué)一方的,也不是偏重普通教育一方的;是指二者并重的;沒有普通教育,不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沒有農(nóng)業(yè)教育,不能造成一個完全的‘農(nóng)人’。農(nóng)學(xué)知識為農(nóng)人所不能少,公民常識和健全人格,尤為農(nóng)人所不可缺。”[29]
生產(chǎn)教育和公民教育得到重視,反映的是時人對鄉(xiāng)村教育脫離生活的不滿。何思源進(jìn)而提出“求生教育”的概念,他指出,“教育不是為的讀書識字,乃是為的發(fā)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換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極言之,讀書識字之本身沒有用處,讀書識字能影響于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處。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第一發(fā)展生活能力,第二擴(kuò)大生活范圍。”[18]

科舉廢除后的新式教育是針對兒童的“正規(guī)教育”,成人文盲問題卻得不到解決。成人教育受到時人的重視,《東方雜志》論者認(rèn)為,“農(nóng)村教育不惟教育兒童,也要教育成人。”[11]
何思源認(rèn)為小學(xué)教師可以擔(dān)任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雙重任務(wù)。他指出,“這小學(xué)的教員白天教育兒童,是兒童的老師,他就此機(jī)會,先求認(rèn)識兒童的家庭。晚間擔(dān)任民眾夜校,教育成人,……成人教育的方法,不必先求識字,最好先講農(nóng)民應(yīng)由之衛(wèi)生常識,家庭常識,及社會經(jīng)濟(jì)上淺近常識,有常識須要識字時,再教識字。這是小學(xué)教員的教育責(zé)任。”[18]陳醉云對成人教育進(jìn)行了更為詳細(xì)的設(shè)計,他指出,“應(yīng)于各鄉(xiāng)區(qū)遍設(shè)農(nóng)民教育館,擔(dān)任社會教育與學(xué)校教育兩項職務(wù)。”[30]“關(guān)于社會教育部分,不限定時間,不限定地點,不限定對象為個人抑或集體,須隨時、隨地、隨人,活用指導(dǎo)的方法,總以解答農(nóng)民的疑難,改善農(nóng)民的生活為任務(wù)。關(guān)于學(xué)校教育部分,則為集體的講授,有預(yù)定的時間,有預(yù)定的地點。農(nóng)藝講座、科學(xué)講座、軍事講座,系周期性質(zhì)的有系統(tǒng)的公開講演,并附以相當(dāng)實習(xí),以適于農(nóng)民所最需要的為范圍。”[30]在教育方法上,“教授時雖用講義或課本,但以語言授受為主要手段。不必太拘拘于識字。 ”[30]

農(nóng)村文化的改造離不開人才,在時人的關(guān)注下,“很時髦的歸農(nóng)運動,現(xiàn)在我們中國已經(jīng)一天一天的熱鬧起來了。這‘歸農(nóng)’兩字的新名詞,時常在大的報章雜志里吐他的光芒,來引誘我們的注意。”[29]吳覺農(nóng)呼吁“有覺悟的青年男女”歸農(nóng),“我國并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還是酣睡著,深深地酣睡著,沒有指引的人們,沒有領(lǐng)袖的人物,誰能使他們蘇醒轉(zhuǎn)來呢?”[25]胡愈之認(rèn)為,“官立學(xué)校,不能使農(nóng)民均受其惠,為指導(dǎo)農(nóng)民計,各地有志青年,必當(dāng)投身田野,躬任講演教導(dǎo)之職,乃始有成效可睹也。”[4]發(fā)出“有志青年,有慕托爾斯泰之高風(fēng),‘去與農(nóng)民為伍’者乎,吾愿執(zhí)鞭以從之矣。”[4]的口號。
楊開道在《歸農(nóng)運動》一文中,詳細(xì)分析了歸農(nóng)運動的幾種途徑。(1)作鄉(xiāng)村領(lǐng)袖。“鄉(xiāng)村社會最缺乏的,就是有遠(yuǎn)大見識,有健全人格的領(lǐng)袖,去謀全社會的進(jìn)行和福利。……現(xiàn)在應(yīng)有相當(dāng)?shù)娜瞬湃ヮI(lǐng)袖鄉(xiāng)村社會,組織各種公共團(tuán)體,維持公共福利。鄉(xiāng)村有了鞏固的團(tuán)體,適當(dāng)?shù)闹笇?dǎo)者,各種農(nóng)業(yè)事務(wù)如農(nóng)業(yè)組合等,皆可以次第發(fā)展,農(nóng)村公共的教育,治安,衛(wèi)生,娛樂,亦能步步進(jìn)行,達(dá)到‘新’的鄉(xiāng)村一個地步。”[29](2)作鄉(xiāng)村教員。“教員是一種清苦的職業(yè),而鄉(xiāng)村的教員尤其清苦。但是鄉(xiāng)村教育確是一種救濟(jì)農(nóng)民振興農(nóng)業(yè)的主要辦法,所以一方面主持鄉(xiāng)村教育的人士不能不設(shè)法增加薪水,改良待遇,來減少鄉(xiāng)村教員的清苦;一方面作教員的人不能不認(rèn)清鄉(xiāng)村教育的重要,而耐心忍受這樣的情況,跑到鄉(xiāng)下去教育鄉(xiāng)村子弟。”[29](3)研究農(nóng)學(xué)。“我國教育不發(fā)達(dá),以農(nóng)業(yè)教育為尤甚。學(xué)生一方面因農(nóng)業(yè)教育不發(fā)達(dá),沒有適當(dāng)?shù)霓r(nóng)業(yè)教育機(jī)關(guān)去讀書;一方面因為農(nóng)學(xué)生的出路太狹,所以研究農(nóng)學(xué)的很少。……鄉(xiāng)村的領(lǐng)袖,鄉(xiāng)村的農(nóng)業(yè)教員和農(nóng)業(yè)指導(dǎo)員,各種農(nóng)業(yè)研究人員,推廣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實施農(nóng)業(yè)的人才,在現(xiàn)在的需求,已經(jīng)一天多似一天,將來農(nóng)業(yè)愈形發(fā)展,需用的人才自然愈加增多了。”[29](4)經(jīng)營農(nóng)業(yè)。“自己用科學(xué)的方法去經(jīng)營農(nóng)業(yè),直接的利益就是振興農(nóng)業(yè)。……間接的利益就是作農(nóng)民的模范,使農(nóng)民信服科學(xué)的勢力,拋棄其數(shù)千年相沿成習(xí)的舊法,來采用新法。”[29](5)從其他方面扶助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從而救濟(jì)農(nóng)民的困苦。金錢上扶助農(nóng)業(yè);文字上進(jìn)行宣傳,“使全國人民都知道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的重要,并且知道我國農(nóng)業(yè)的衰敗狀況和你們得困苦情形,及其扶助挽救的必要。……總之,無論甚么人,在甚么地位,只要他有扶助農(nóng)業(yè)和救濟(jì)農(nóng)民的熱心,都能間接振興全國農(nóng)業(yè)救濟(jì)全國農(nóng)民。”[29]

陳醉云認(rèn)為農(nóng)村中有惡劣的習(xí)俗,必須予以糾正。他指出,“鄉(xiāng)間的小茶館很多,每天上午,農(nóng)民常在茶館喝茶閑談,把可以工作的時間輕輕浪費。在喝茶的時候,同時又燒著卷煙,這又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等到下午,茶館中座位較為清閑,便有小部分人在那里斗牌賭錢。正業(yè)既漸荒廢,惡習(xí)即漸傳染,不久,便形成了流氓化與匪化。”[30]“政府應(yīng)嚴(yán)厲取締小茶館,而代以農(nóng)民教育館,使農(nóng)民于余間作正當(dāng)?shù)膴蕵罚苷?dāng)?shù)慕逃盵30]
杜亞泉在《農(nóng)村之娛樂》一文中,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對農(nóng)村舊有習(xí)俗進(jìn)行揚棄。他指出,舊有的演劇賽神等娛樂活動不可取締,但需要糾正其中弊端,首先要“無害于風(fēng)俗為要旨。演劇則當(dāng)取其足資觀感,而淫邪儇薄之戲曲,最宜切戒。”[31]其次要“力持儉約”,“舉行之次數(shù),亦當(dāng)限制。”[31]時間上以農(nóng)事蠶事忙完后進(jìn)行。各地廟會也不宜取締,“農(nóng)人既得就近購買其日用之所需,無遠(yuǎn)涉城市之苦,而又得稍資游樂,實為兩利。”[31]但對隨廟會而生的“局賭誨盜之事”,必須嚴(yán)為取締。杜亞泉認(rèn)為農(nóng)村娛樂“宜隨時勢之需要,寓教育于娛樂,使農(nóng)民略有相當(dāng)之智識,以應(yīng)外界只潮流,然新式娛樂,多有不適于農(nóng)村,或為農(nóng)村財力所不克舉辦者,故不可不斟酌損益,因地制宜,以期程度之相合。如講演會陳列所及影戲幻燈等,皆可參酌行之。 ”[31]
綜上可知,《東方雜志》所刊文章對農(nóng)村文化改造非常重視,提出了農(nóng)村教育必須與農(nóng)民需要相結(jié)合,不能簡單套用城市教育模式,應(yīng)注重農(nóng)村教育特點的理念。在娛樂方面,對舊有習(xí)俗要揚棄,新式娛樂要因地制宜。但論者側(cè)重于對新式教育和舊的習(xí)俗的改造,相對忽視了農(nóng)民的貧困問題,在貧困的環(huán)境下,農(nóng)民無力投資教育。在改造新式教育方面,僅僅將農(nóng)村教育預(yù)設(shè)于“三農(nóng)”,是安于農(nóng)村、安于農(nóng)業(yè)的教育。①黃紹緒在抗戰(zhàn)即將勝利之時,在《東方雜志》中指出了農(nóng)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平等問題。他指出,“農(nóng)業(yè)教育的目的,不是狹隘的職業(yè)教育。訓(xùn)練有能力的農(nóng)民,不過是農(nóng)業(yè)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農(nóng)民子女的教育,在原則上應(yīng)與城市人子弟的教育平等。就是說:農(nóng)民子女享受城市別種職業(yè)或生活教育的機(jī)會,當(dāng)與享受農(nóng)業(yè)教育的機(jī)會一樣。”見黃紹緒:《中國農(nóng)業(yè)之命運》,《東方雜志》第42卷第9號,第8頁。在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發(fā)展過程中,農(nóng)村教育應(yīng)該多樣化,進(jìn)而能使農(nóng)村人口轉(zhuǎn)移出去,成為非農(nóng)人口。優(yōu)秀人才進(jìn)入“三農(nóng)”領(lǐng)域也并不是鼓吹“歸農(nóng)運動”就可達(dá)到,生活環(huán)境和待遇等方面的完善,這些配套設(shè)施才是人才歸農(nóng)的關(guān)鍵點。民國時期知識界不僅僅在理論上對農(nóng)村文化進(jìn)行探討,而且積極付諸實踐。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首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在鄒平、定縣等地區(qū)以文化建設(shè)為主要內(nèi)容進(jìn)行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驗,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結(jié)果卻仍是“號稱鄉(xiāng)村運動而鄉(xiāng)村不動”。[32]可見,“三農(nóng)”問題是個問題綜合體,僅僅從一方面提出對策并不能最終加以解決。
[1](美)西奧多·W·舒爾茨著,梁小民譯.改造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6:150.
[2]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diào)查[M].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2005:249、182、234.
[3]喬啟明.中國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jì)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46:291.
[4]羅羅.農(nóng)民生活之改造[J].東方雜志,1921,(7):4、4、4.
[5]嚴(yán)仲達(dá).湖北西北的農(nóng)村[J].東方雜志,1927,(16):44.
[6]毛澤東.毛澤東農(nóng)村調(diào)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7.
[7]汪適天.靖江[J].東方雜志,1927,(16):122.
[8]蕭錚.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M].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中文資料中心,1977:46871.
[9]張鳴.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xiāng)村世界——由“新政”談起[J].浙江社會科學(xué),2003,(2):193.
[10]行政院農(nóng)村復(fù)興委員會.中國農(nóng)業(yè)之改進(jìn)[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4:13.
[11]楊開道.我國農(nóng)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J].東方雜志,1927,(16):5、8.
[12]周谷城.中國教育之歷史的使命[J].教育雜志,1929,(2):5.
[13]張思明.經(jīng)濟(jì)破產(chǎn)中之中國教育[J].東方雜志,1933,(18):教6、教9.
[14]古楳.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問題[M].上海:中華書局,1933:3.
[15]陳其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史[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0:181.
[16]舒新城.小學(xué)教育問題雜談[J].中華教育界,1924,(4):4.
[17]謬序賓.鄉(xiāng)村小學(xué)之缺點及其病原之補救法[J].中華教育界,1924,(4):2.
[18]何思源.士大夫教育之惡果及教育改造途徑——求生教育[J].東方雜志,1934,(6):教15、教14、教17、教18.
[19]費孝通.鄉(xiāng)土重建[N].費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59.
[20]費孝通.江村經(jīng)濟(jì)——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51、51.
[21]丘學(xué)訓(xùn).中國農(nóng)村教育的危機(jī)[J].教育雜志,1930,(2):6.
[22]實業(yè)部中央農(nóng)業(yè)試驗所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科.農(nóng)村教育調(diào)查[J].農(nóng)情報告,1936,(9):242、236.
[23]古楳.鄉(xiāng)村建設(shè)與鄉(xiāng)村教育之改造[J].東方雜志,1933,(22):教10.
[24]章光濤.復(fù)興農(nóng)村與農(nóng)村教育[J].東方雜志,1933,(18):教3.
[25]吳覺農(nóng).中國的農(nóng)民問題[J].東方雜志,1922,(16):18、20、18.
[26]常道直.生產(chǎn)教育之根本問題[J].東方雜志,1933,(16):教11.
[27]周予同.中國現(xiàn)代教育之史的檢討[J].東方雜志,1934,(6):教10、教11.
[28]郭一岑.生產(chǎn)教育的意義之估定[J].東方雜志,1933,(16):教2.
[29]楊開道.歸農(nóng)運動[J].東方雜志,1923,(14):26、17、26、26、27、27、28.
[30]陳醉云.復(fù)興農(nóng)村對策[J].東方雜志,1933,(13):115、116、116、120、120.
[31]高勞.農(nóng)村之娛樂[J].東方雜志,1917,(3):9、9、10、9.
[32]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M].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2006:368.
責(zé)任編輯:陳 鳳
K25
A
1672-2868(2014)05-0096-05
2014-06-02
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SK2013B249);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博士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XJ201126);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重點學(xué)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1003-09);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科學(xué)技術(shù)哲學(xué)重點學(xué)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01010803)。
蔡勝(1981-),男,安徽潛山人。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xiàn)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