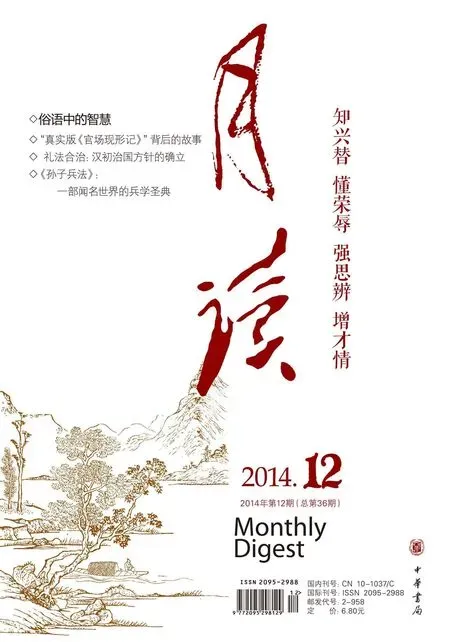“真實(shí)版《官場現(xiàn)形記》”背后的故事
◎ 思泉
“真實(shí)版《官場現(xiàn)形記》”背后的故事
◎ 思泉
一本書的重要價(jià)值
晚清官員張集馨的自敘年譜——《道咸宦海見聞錄》,是研究晚清政治、軍事以及經(jīng)濟(jì)、社會等領(lǐng)域的重要史料,甚至有人將它比作真實(shí)版的《官場現(xiàn)形記》。應(yīng)該說,這一評語是中肯的。近年來,專家學(xué)者在論述清代官場的腐敗現(xiàn)象時(shí),多次征引該書的史實(shí)。
36年的仕宦生涯,都被張集馨翔實(shí)記錄在書中。由于經(jīng)歷豐富,張集馨筆下,既有對晚清政局危機(jī)的洞見思考,又有對具體事件場景的刻畫描繪,加上其翰林出身,文筆流暢,指摘時(shí)弊一針見血,褒貶人物入木三分,特別是書中對于官場糜爛、吏治腐敗的敘述,歷來為人所重視。
但是,或許由于此書太過有名,相比之下,對于張集馨本人,人們反而較少關(guān)注。
一個人的宦海浮沉
道光九年(1829),30歲的張集馨以殿試二甲第22名的成績考中進(jìn)士,隨后被欽點(diǎn)翰林院庶吉士,踏上仕途。七年后,他又以武英殿纂修的身份補(bǔ)授山西朔平知府,至同治四年(1865)在陜西按察使任上被革職,歷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代理巡撫等職,時(shí)間跨越道光、咸豐、同治三朝,足跡遍及山西、福建、陜西等省。
首先,由于深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的教育,張集馨于逼仄之下仍堅(jiān)持有所作為。張集馨的日記難免有對自己的美化,但總的來說,他在晚清官場雖不能說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清官、好官,卻也已是為數(shù)不多的正面人物。不論是在山西治理蝗災(zāi)、辦理疑案,還是在陜西經(jīng)營糧道、清理虧空,以及隨軍作戰(zhàn)、平定叛亂,張集馨都表現(xiàn)出了很強(qiáng)的能力與謀略。尤其可貴的是,民本思想是張集馨從政的重要理念,如在擔(dān)任江西布政使時(shí),兩江總督曾國藩一再催其籌措軍餉,張集馨憤而寫道“余無催科之才,亦斷不肯為絕滅之事,寧可去官耳,不為不祥”,并諷刺曾國藩“直是玩視民瘼。平昔尚以理學(xué)自負(fù),試問讀圣賢書者,有如是之橫征暴斂,掊克民生,剝削元?dú)庹吆酢保?/p>
其次,現(xiàn)實(shí)的掣肘、同僚的傾軋又常使張集馨萌生深深的無力感,甚至萌生退意。也正是因?yàn)閲?yán)酷的官場生態(tài),張集馨在很多事情上往往不得不以妥協(xié)告終。如初到地方為官任朔平知府時(shí),山西按察使慶林曾為一起虧空案向他求情,張集馨直言:“只要有糧餉而士兵不鼓噪鬧事,我又何必深究!”令慶林聞之“甚喜”。代理福建布政使時(shí),張集馨曾對三名貪污犯詳參革職,但由于福建巡撫瑞瑸說情,張集馨又恰好調(diào)任江西布政使,便沒有嚴(yán)辦。
第三,對于已成俗習(xí)的官場陋規(guī)別敬(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別時(shí)致送的禮金),張集馨一樣隨波逐流。他還曾一筆筆算過賬,動輒上萬兩的沉重負(fù)擔(dān),顯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的,至于“年節(jié)應(yīng)酬,以及紅白事體,尚不在其內(nèi)”。張集馨筆下也不時(shí)有宦囊羞澀的記錄,如其出任陜西督糧道時(shí)的別敬就是舉債所籌。不過,羊毛出在羊身上,既有送,自然也有入。如擔(dān)任陜西督糧道僅一年,他不但將債務(wù)全部還清,還寄回老家一萬多兩銀子,難怪他亦自言糧道一缺“向來著名”,“陜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糧道為幸”。
盡管如此,應(yīng)當(dāng)說,張集馨對于官場往來仍有所節(jié)制,并不來者皆收。如任江西布政使時(shí),他自言“君子懷刑,余生性謹(jǐn)慎,凡作奸犯科之事,向不為也”,其筆下更不時(shí)有他人饋金而“卻之”的記錄,并自矜“自問數(shù)十年來,從未起婪贓念頭”。
最后,多年仕途的不如意,不能不使張集馨失意憤懣,特別是由此帶來的人情冷暖,更使他郁結(jié)于懷。咸豐四年(1854),張集馨在直隸布政使任上,因直隸總督桂良與欽差大臣勝保之間互相傾軋而成替罪羊,被參革職并隨勝保征戰(zhàn),其間又因腿傷到濟(jì)南療養(yǎng)。由于張集馨乃“業(yè)經(jīng)罷斥”之人,“省中司道府縣,無一人過問者”,此情此景,不禁使張集馨慨嘆“一貴一賤,交情立見”。
與失意憤懣相伴隨,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在張集馨身上越來越突顯。仕途官位的誘惑雖未能在他心中盡除,但現(xiàn)實(shí)的一再碰壁使他心生倦意,“從此戢影蓬廬,不與人間事”的想法日益強(qiáng)烈,而其最終革職賦閑,“優(yōu)游林下,蒔花種竹,飲酒賦詩”,也算是得償所愿吧。
晚年的張集馨曾一再感慨,“須發(fā)皓白,猶然捧檄,自恨無才,殊可恥也”,“余之偃蹇,不能奮飛,遂為豎子所侮,殊為可愧”!其實(shí),他的仕途曾經(jīng)擁有一個很好的開端:道光帝曾逐個召見翰林院人員,在眾多翰林中,張集馨引起他的格外注意。沒過幾天,軍機(jī)處傳令,皇帝還要再見張集馨。第二次談話后,道光帝特別叮囑張集馨勤讀慎行,言語之間對張集馨寄托了極大的期望與關(guān)懷。時(shí)隔一年,張集馨便由道光帝欽點(diǎn),破格出任朔平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集馨由四川按察使調(diào)任貴州布政使,進(jìn)京面圣時(shí),道光帝更是直接向他挑明:“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撫,汝不可自暴自棄。”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道光帝的提攜使他青云直上,道光帝的去世也仿佛使他的命運(yùn)從此定格。將近20年,張集馨在按察使、布政使任上反復(fù)輾轉(zhuǎn),始終未能再上一步。特別是道光帝“要汝作好督、撫”的叮囑、期盼與承諾,始終是張集馨揮之不去的負(fù)擔(dān)。
此外,不得不說的是,張集馨曾多次感嘆官場拉幫結(jié)派的惡習(xí),事實(shí)上,他本人既是派系斗爭的受害者,也曾是受益者。除去道光帝的垂青,張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還得到時(shí)任四川總督琦善的賞識,后琦善調(diào)任陜甘總督,又報(bào)請朝廷將其提任甘肅布政使。但好景不長,隨著道光帝的去世以及琦善在政治上的失勢,張集馨的仕途也日漸走向低谷,他自己也曾坦言:“人每謂余因公(指琦善)受累,余每謂賴公以傳也。”
當(dāng)然,張集馨仕途的跌宕,還有其他因素。一是其性格與官場風(fēng)氣的矛盾。由于家庭出身、經(jīng)歷特別是從小深受儒家教育的原因,張集馨性格溫和寬厚,遇事忍讓,甚至于被家人奴仆蒙蔽欺瞞,這一性格使得他在遍布傾軋的險(xiǎn)惡官場中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飽受同僚排擠構(gòu)陷。二是其能力與時(shí)代要求的沖突。應(yīng)當(dāng)說,經(jīng)過多年從政的歷練,與眾多顢頇無為的同僚相比,張集馨可稱得上一個“能吏”,但他畢竟又是文官,在戰(zhàn)亂不已的形勢背景下,朝廷首先需要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以湘系集團(tuán)為代表的軍事政治力量才是當(dāng)時(shí)政壇的主導(dǎo),從而,張集馨的乏人問津也就不可避免了,唯有其走鋼絲般的生存之道,至今仍令人無限感嘆。
一個時(shí)代的昏暗側(cè)影
讀懂張集馨的仕宦生涯,就必須了解他所處的時(shí)代。張集馨所處的時(shí)代,已是清代晚期。曾經(jīng)盛極一時(shí)的大清最終也未能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呈現(xiàn)出萬馬齊喑的衰頹氣象,特別是吏治的腐敗,不但在清代,放在整個中國歷史,恐怕也稱得上絕無僅有。
其一,貪贓納賄,暴斂橫征。張集馨曾總結(jié)甘肅吏治,“一言蔽之,有錢則好,無錢則不好耳”。這一結(jié)論無疑并不限于甘肅。如直隸總督桂良認(rèn)為“非錢不可”,“非納賄不能下委”,“否則此官不能做矣”,閩浙總督慶端甚至認(rèn)為“屬員多送紅包,才是看得起主人”。當(dāng)時(shí)竟有官員巧盡心機(jī),放出謠言,謊稱去任,騙取百姓納稅。

其三,酒色征逐,驕奢淫逸。張集馨筆下的晚清官場,隨處隨時(shí)都可見“酒酣耳熱,脫略形骸,歌唱?dú)g呼,村言俚語”等等性迷狂樂、縱情聲色的不堪場景。如陜西僅糧道官署就“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yīng)酬則無日無之”,甘肅則由于陜甘總督樂斌喜歡徹夜聽?wèi)蜓鐣绞鹑找贵细瑁岸諊?yán)寒,仆從忍凍,立于風(fēng)雪之中,徹夜伺候”。閩浙總督慶端更是“一經(jīng)入席,唯恐人之不醉,又唯恐己之不醉,不能觀人之大醉也”,其醉后“兩眼麻沙,雙趺彳亍,欲賭馬射,以示豪強(qiáng)”。可謂丑態(tài)百出。
其四,庸庸碌碌,顢頇無為。張集馨筆下,上到總督巡撫,下到縣官書幕,總能于寥寥數(shù)言,勾勒出其尸位素餐、庸碌無為的畫像。如說福建巡撫瑞瑸“庸碌無能,公事一概不管;耳聾頗甚,屬員回事,依阿可否……公事從不作主,一遵教令”,公堂木偶形象惟妙惟肖。這一切,沒有深切經(jīng)歷體驗(yàn),是寫不出來的。
張集馨的仕宦人生,他在官場中的應(yīng)對作為尤其是心路歷程,恰恰是晚清官員的“非典型樣本”,直觀而深刻地展現(xiàn)出了晚清官場生態(tài)的黑暗,既令人掩卷長嘆,又啟人深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