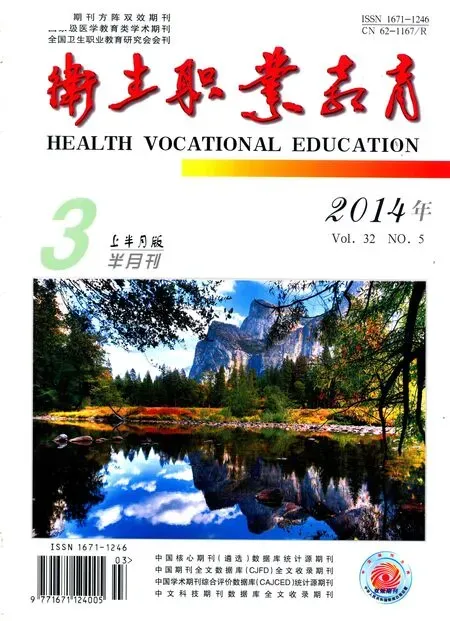對我國古代名醫優秀醫德的追溯
劉志哲,劉 靜
(隴東學院岐伯醫學院,甘肅 慶陽 745000)
對我國古代名醫優秀醫德的追溯
劉志哲,劉 靜
(隴東學院岐伯醫學院,甘肅 慶陽 745000)
我國古代眾多著名醫家的著作中都有大量醫德倫理的論述,本文試圖追溯它在醫德思想的創立、繼承、發展和促進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探討其對新時期醫德建設的作用。
古代名醫;醫德醫風;追溯
祖國醫學的魅力并不僅僅因為它神奇的療效和獨特的理論體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歷代中醫大家高尚的醫德。那些取得突出成就,對祖國醫藥學做出貢獻,豐富、發展和完善了我國醫藥學體系的醫藥學大家,無一不是德藝雙馨,他們用自己的言行舉止詮釋著“醫乃仁術”,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衛著醫道尊嚴。追溯這些著名醫家的從醫歷程,基本都具有以下特點。
1 濟世救人,厚德為先
自古以來,醫生行醫必須具有高尚的醫德。南宋《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說:“凡為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擁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正物,就是很好地掌握和運用治病的藥物和技術。古代稱醫術為仁術,認為醫學是一種活人救命的技術,其服務直接面對人。因此,醫生的職業道德——醫德就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浩瀚的中醫典籍里,有著極為豐富的有關醫德的論述以及古代醫家的許多嘉言懿行。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的《大醫精誠》中的“大”,不僅指出了祖國醫學的宏大廣博,更強調了醫者的高尚道德情操,寬廣的胸襟,至高、至遠、至深、至大的思想境界;“精”是指從醫者必須對醫術精益求精,一絲不茍;“誠”則強調醫者必須至誠至信地除疾滅病,為患者服務。他認為用精湛的醫技治病救人,使患者起死回生就是大醫。清代陳夢雷等編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中明確指出:“無恒德者,不可作醫。”“做人要有人格,看病要有醫德;貧莫貧于無才,賤莫賤于無志。缺此不可為良醫。”(《秦伯未醫文集》)這就是說,做醫生不僅要具有精良的技術,更要具備高尚的品德。明代醫家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指出:“醫道,古稱仙道也,原為活人。”因此,作為醫家,對人和生命必須無限熱愛,這種精神是醫學事業的準則,也是一個醫生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
2 博采眾長,業精于勤
祖國醫學博大精深、淵源流長,歷代典籍浩如煙海、汗牛充棟。“醫之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醫門法律·先哲格言》)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拜師羅知悌時,整天站在門外,風雨無阻,終于被收徒。“藥王”孫思邈直到白發暮年還手不釋卷,“一事長于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備急千金要方·序》)。這些都說明,“醫道精深,不可淺嘗輒止,而醫者責任重大,臨證不可不慎”(《名老中醫之路》)。“醫貴乎精,學貴乎博,識貴乎卓,心貴乎虛,業貴乎專,言貴乎顯,法貴乎活,方貴乎純,治貴乎巧,效貴乎捷。知乎此,則醫之能事畢矣。”(《醫門補要·自序》)明代名醫徐春圃說:“醫學貴精,不精則害人匪細(不淺)。”東漢張仲景年輕時師從張伯祖學醫,由于他勤奮好學,醫術“精于伯祖”。他生當戰亂頻繁、疾疫流行的東漢末年,生靈涂炭,死亡載道,他的家族二百多人,不到十年,就患病死去2/3。他目睹這種慘狀,于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潛心研究古典醫籍,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撰成《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創立“辨證論治”的綱領,成為中國醫籍的經典,他被后人尊為“醫圣”。唐代孫思邈,幼時多病,從少年時便酷愛醫學,直到白發蒼蒼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釋卷。他活了一百多歲,一生“博極醫源,精勤不倦”,在古稀之年,撰成《千金要方》三十卷。30年之后,年已百歲,不顧年邁,猶恐滄海遺珠,又繼續旁搜博采,精益求精,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與《千金要方》相輔相成,二書合稱《千金方》,是傳世不朽的醫學巨著,他被后人尊為“藥王”。又如明代李時珍,三代行醫,家學淵源,博學多才,熱愛醫學,他曾自我介紹說:“幼多羸疾……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漁獵群書,搜羅百氏。”他以學習為樂,讀書猶如吃甘蔗飴糖一樣美好,他發現歷代本草書訛誤和缺漏不少,因此下決心編寫一部新的本草著作。從34歲開始,“歲歷30稔,書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終于在60歲時編成了《本草綱目》這部舉世聞名的藥學巨著,郭沫若稱其為“醫中之圣,集中國藥學之大成”。有“高尚先生”之稱的金代醫家劉完素,生活在戰亂頻繁的時代,幼年家境貧寒,母親患病,由于家貧三延醫而不至,致使其母身亡,遂立志學醫,以濟世救人。劉完素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為救治疫病,一改“和劑局方”用方溫燥之弊,創立“六氣化火”論,終成寒涼派的開山鼻祖。清代溫病學家葉天士,出自名門醫家,天資聰穎,十余歲時醫術已很高明,以后10年中,他又拜師17人,直至成名后,仍然十分謙遜。當時有一個病家請他診治,他認為已不可救治了,囑咐家屬趕快料理后事。不料一年之后他見到這名患者還活著,且身體健康,他很慚愧,打聽到治病者是金山寺的一位和尚,第二天便到金山寺向那位和尚拜師求教,老老實實地學習,終于成為一代名醫。明代醫家繆希雍,父早歿,幼年孤苦。17歲患瘧疾,自閱醫書,遍檢方書而自己治療,遂至痊愈。遂立志從醫,搜求醫方,苦心研究藥道,博涉各種醫書,尤精本草之學,認為“神農本經,臂之六經,名醫增補別錄,譬之注疏,本經為經,別錄為緯”,于是鉆研其理。此外,繆氏生平好游走四方,曾游歷三吳,入閔,歷齊、魯、燕、趙等地,亦到過江西、湖北、湖南諸省。在周游之時,到處行醫,尋師訪友,采藥搜方。這些都說明,古人對醫術的要求是很高的,必須精求醫理,博采眾長,“捐眾賢之砂礫,掇群才之翠羽”(《外臺秘要·序》)。砂礫,是淘金時應丟棄的廢物;翠羽,是裝飾時宜挑選的精華。這就是說,向他人學習時不但要勤,而且要揚長避短,去粗取精。
縱觀我國歷代卓有成就的醫學家,無一不是在“精”字上下了一番苦功。他們畢生勤勤懇懇,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精益求精,最終取得了學術上的輝煌成就,贏得了后世的無限敬仰。
3 謙虛謹慎,尊重同行
東漢時代的“醫圣”張仲景,曾“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遂“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著成了融理、法、方、藥為一體,奠定了臨床醫學理論體系堅實基礎的《傷寒雜病論》。他嚴厲抨擊醫德敗壞者“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并指出“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古今從醫人員中,總有一些“無行之徒,專一夸己之長,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問疾疴,唯毀前醫之過,以駭患者”(《萬病回春·云林暇筆》)。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行為是很不道德的。作為一名醫生,應當時時處處謙虛謹慎,尊重同行。明代著名外科學家陳實功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說:“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輕侮傲慢。為人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自無謗怨,信和為貴也。”(《外科正宗·醫家十要》)孫思邈也告誡說:“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并說,有的人“偶然治瘥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
4 不畏權貴,棄官從醫
自古以來,棄官從醫,為民治病的醫家不勝枚舉。明末清初的費尚棄官從醫,定居孟河,開始了孟河費氏的醫學事業。唐代孫思邈,多次拒絕隋唐兩代朝廷的聘請,長期在民間行醫,一生“博極醫源,精勤不倦”,撰成傳世不朽的醫學巨著《千金方》。東漢醫學家張仲景,本為官吏,建安年間,他目睹民間瘟疫橫行,白骨露野的慘狀,為解除百姓疾苦,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留神醫藥,精究方術”,著成《傷寒雜病淪》,被歷代醫家推崇為“醫方之祖”,在世界醫學領域享有很高的聲譽。東漢杰出的醫學家華佗,醫理精明,經驗豐富醫好了曹操的“頭風眩”病。曹操想調他進京做官,給他豐厚的俸祿,但他一心想為百姓解除病痛,幾次拒絕去朝廷做官,更不愿為曹操做侍醫,竟慘遭殺害。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高尚品德一直為后人傳頌。
5 對待患者,皆如至親
醫乃仁術,濟世為懷,病家延請,有求必應,治病救人,認真負責,這是我國歷代名醫的優良傳統。醫生對患者要無微不至地關心、體貼和愛護,視他們如親人。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定神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在孫思邈所言中,我們感受到他視患者如至親的接診態度。元代名醫朱丹溪醫術十分高明,每天都有不少人請他看病,他“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有一次,天下著大雨,有一病家來請他,他的仆人為了照顧他的健康,向病家解釋要求免于出診。他得知后,教導仆人,患者度日如年,痛苦不堪,當醫生的怎能自圖安逸。說罷,拎起藥箱就出診了。這是多么高尚的醫德,多么令人景仰的修為。醫生遇危重患者,要積極搶救。例如戰國時的名醫扁鵲(秦越人),是一位民間醫生,周游列國,一日,路過虢國,遇虢太子突然發病,昏迷半日不醒,眾醫束手無策,虢君請扁鵲入視,扁鵲通過詳細認真的檢查,對虢君說:“若太子者,所謂‘尸蹶’者也,太子未死也。”遂使他的學生外施針灸、砭石,內服湯藥,經過搶救,太子終于轉危為安。為醫者,術可暫行一世,德則流芳千古。
6 心存濟世,不唯名利
扶貧濟困,施醫贈藥,是我國歷代名醫的優良傳統。例如三國時的名醫董奉,是一位醫術精湛,醫德高尚的民間醫生,他為人治病,不收診金,凡重病患者,治愈后,在其房前屋后種植杏樹5棵,輕病者種1棵,作為酬謝。數年之后,種杏十萬余棵,郁然成林。杏熟易谷,用以救濟貧苦患者。后世有“杏林春暖”,“譽滿杏林”,傳為醫林佳話。唐代名醫沈應善,精醫術,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時,則購儲藥物,在其宅旁構筑一舍,收留患者,醫藥費和伙食費一概不收。對待患者,來者不拒,其舍命名為“來安堂”(取既來之,則安之之意)。又如清代名醫張明征,曾供職太醫院,后回籍行醫,曾在途中遇一貧苦無告者患痢甚劇,視之惻然,令仆負至其家,服藥調治,月余痊愈,仍給資遣其回家,臨走時亦不問他的姓名和住址,時人稱頌其“視天下猶一家,救路人若骨肉”。清代醫家徐大椿著《醫學源流論》,他的醫學研究和臨床實踐在當時有很高的聲譽,他對沒錢就診的患者,不僅免費診治,而且經常無償送藥,這種精神深受后人的敬重。傳統中醫最反對見利忘義,“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孫思邈語),“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傷寒論·原序》);而提倡“不計其功,不謀其利”(《古今醫鑒》)。清代葉天士被譽為“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其立德也”(《臨證指南醫案·華序》)。有人在評價明代醫學家陳實功時說:“不張言災禍以傷人之心,不虛高氣岸以難人之請,不多言夸嚴以勾人之賄,不厚求拜謝以殖己之私。”(《外科正宗》)因此,不唯名利是良好醫德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純良不可信也。”(《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術是仁術,學醫的目的是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為了發財致富。金元時期的李東垣晚年收羅天益為徒,第一次見面第一句話就問他:“汝來學覓錢醫人乎?學傳道醫人乎?”意為你來學醫,目的是賺錢圖利,還是傳道濟世?羅天益毫不猶豫地回答:“亦傳道耳。”李東垣遂欣然收其為弟子。此后10年,羅天益既學到了李東垣良好的醫德,又得到了其醫術真傳,成為一代名醫,著有《衛生寶鑒》二十四卷。可見我國古代名醫對學生的學醫動機、道德品質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7 寬厚仁和,傾誠無忌
古代醫術,講究待人和善,以誠相見,急人所急。“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于情;篤于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醫門法律·問病論》)因此,行醫看病也好,配方制藥也好,必須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講求實事求是,“中無城府……與人交,傾誠無所忌諱;赴人之急,不計利害”(《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決不能弄虛作假,唯利是圖,自欺欺人。但是,卻總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有腹無藏墨,詭言神授;目不識丁,假托秘傳。此欺詐之流也。”“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辯相欺,或危言相恐。此欺詐之流也。”(《醫宗必讀·不失人情論》)在這方面,以誠信聞名于世的同仁堂有兩句著名堂訓,即“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很值得廣大醫務工作者及醫藥生產廠家自勉。
8 尊敬師長,虛心求教
我國歷代名醫多數出身于師傳,如扁鵲拜長桑君為師,倉公(淳于意)拜公乘陽慶為師,張仲景拜張伯祖為師等,他們都尊敬師長,虛心向老師學習,終于“盡得其傳”,甚至成就超過了他們的老師。金元時期的李東垣,家資富有,熱愛醫學,聞張元素有醫名,乃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得其傳,后來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朱丹溪,偶然在武林(今杭州)獲悉醫學大家羅知悌擅長醫學,往返十余次,“日拱立于其門,大風雨不易”,使羅氏深受感動,遂將全部醫術傳授給他,后來他也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清代葉天士,虛心好學,聞某人擅長治某病,即前往拜訪求教,先后共拜訪名師17位,他汲取各家之長,后來成為名家,尤其對溫病學貢獻最大,成為清代四大溫病學家之一。
如果說張仲景以他的《傷寒雜病論》創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和體系,那么孫思邈則以他的《大醫精誠》《治病略例》等論篇創立了祖國醫學醫德思想的原則和體系,而繆希雍的“祝醫五則”即是這個原則和體系從醫德方面對醫生提出的具體要求。古代醫家在和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提倡并具有高尚的醫德,對中華民族的繁衍和興盛做出了貢獻,取得了輝煌成就,這不僅源于祖國醫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也源于古代醫家的高尚醫德。高尚的醫德贏得了后人對我國古代醫學的信賴和稱頌,成為祖國醫學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G416
A
1671-1246(2014)05-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