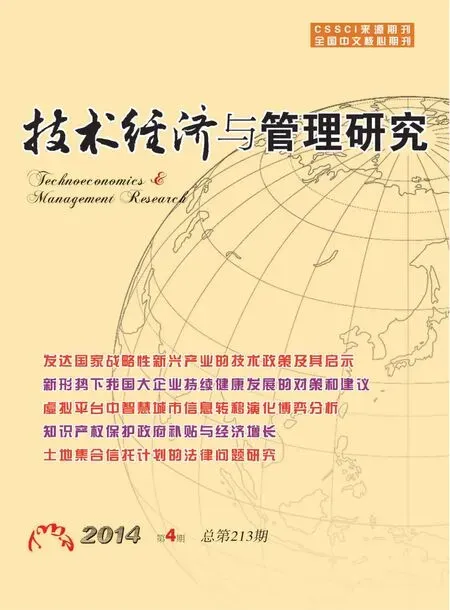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與經濟增長
張書琴,張 望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6; 2.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3.江蘇農業現代化研究基地,江蘇 南京 210095)
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與經濟增長
張書琴1,張 望2,3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6; 2.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3.江蘇農業現代化研究基地,江蘇 南京 210095)
文章構建了三部分模型,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確定的,根據本國自主創新的程度而異;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有助于放大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或減緩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政府補貼與經濟增長休戚相關,政府補貼份額越高,越有利于經濟增長;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放大或消弭政府補貼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技術應用成本與經濟增長呈現反向關系,技術應用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經濟增長,較高的政府補貼份額會減緩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放大或減緩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知識產權;產權保護;政府補貼;產業經濟
一、引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二戰至今,西方發達國家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逐漸拉大了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南北經濟差距加劇。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西方發達國家較為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不僅塑造了較為有利的創新環境,而且培育了國民崇尚創新的傳統,如1787年的《美國憲法》就賦予了作家和發明家在保護期內享有專有的和排他性權利,這一政策促使美國國民向來尊重知識產權,崇尚創新,也為日后美國的崛起和技術的繁榮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政府積極支持各種軍用、民用研究項目,新技術、新能源不斷涌現,經濟增長速度大大加快,如韓國政府為了促進本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推出了“10萬戶太陽能屋頂計劃”、“地方發展補貼計劃”等政府補貼項目,極大地增強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
2008年金融海嘯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依附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自主創新才是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出路。目前,我國正處于模仿性移植向自主創新轉型的關鍵時期,但我國無論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程度還是自主創新的發展狀況都面臨嚴峻挑戰。為了扭轉這一局面,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科研部門的投入,R&D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不斷攀升,但總體而言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并不突出,且各區域之間的差異較大。因此,現實的經濟發展為我們提出了一個艱巨的課題:根據國外的發展經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政府補貼是鼓勵企業創新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利器,那么我國在建設自主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如何設定具體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及政府補貼份額。在以往的理論分析中,鮮有將二者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分析二者在長期經濟增長與自主創新國家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關系,文章正是從這一角度展開分析。
二、文獻綜述
探索經濟增長的源泉,一直是宏觀經濟學近年來的熱點,前期的學者將增長的源泉歸咎為自然資源、資本、科學技術等方面(亞當·斯密,1776;Harrod,Domar,1939、1946;Solow,1956、1957)。此后,大量學者將自然資源引入新古典增長模型,研究發現只要達到一定技術條件,人口增長率為正,即便遭遇自然資源瓶頸,仍然能夠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Stiglitz,1974;Solow,1974;Dasgupta,Heal,1974、1979)。至此,學術界便確定了技術水平是經濟增長決定力量的主流觀點。
縱觀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與技術水平的差距是在擴大,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實施技術模仿(引進)戰略本身需要承擔一定的成本,而這一成本的大小將直接決定區域間能否實現經濟收斂,即經濟收斂是有一定條件的。技術模仿成本的大小是由技術選擇所決定的(潘士遠,2008)。Lin(1999,2001)技術選擇說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向發達國家經濟收斂,應該以促進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為目標,而不是以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為目標。發達國家所研發成功的世界前沿技術,是與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相適應的,并不一定適合發展中國家(Basu&Weil,1998;Acemoglu&Zilibotti,2001)。在現實中,諸多南方國家為了實現經濟收斂,甚至經濟趕超的目的,人為地盲目追求世界前沿技術,往往卻事倍功半。潘士遠(2008)研究發現,技術模仿的成本取決于技術選擇,發展中國家可以選擇適宜的技術,實現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收斂;若總是追逐世界前沿技術,致使模仿成本過高而日益拉大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林毅夫等(2004)通過對1970-1992年間41個國家的跨國宏觀數據分析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目標,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大力支持下,發展了許多與世界前沿技術相關的技術與產業,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技術選擇對經濟增長率與TFP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更是橫亙在諸多發展中國家面前的一道障礙,因為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大小將直接決定發展中國家可供模仿和學習的技術集合。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一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于不同的經濟主體的不同作用。Falvey等(2004)通過對8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于低收入水平國家和高收入水平國家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但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卻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日益嚴格,可供中等收入水平國際選擇的技術模仿集卻在縮小。韓玉雄與李懷祖(2004)通過寡頭競爭模型分析發現,在世界工廠模式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降低經濟增長率與工資福利水平。Mondal and Gupta (2009)通過內生化創新行為,分析發現在均衡增長率下,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激勵北方國家進行技術創新。二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形式及條件。Park(1997)通過對1960-1990年跨國數據分析發現,知識產權制度并不能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是通過促進諸如R&D資本與物質資本等要素積累而間接促進經濟增長。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在于知識產權對于經濟增長的增長效應并不是無條件的,必須滿足一定的基本條件。張亞斌與易先忠(2006)通過三部門模型分析發現,南北技術差距必須在一定的臨界值范圍之內,否則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難以達到南方國家向北方國家收斂的目的。王林與顧江(2009)以85個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知識產權的增長效應取決于一國技術與世界前沿技術的差距。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Chen等(2005)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行為,但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應該根據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而定。劉勇與周宏(2008)根據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關于技術外部性的假定使得其研究結論備受質疑,內生增長理論不僅使技術內生化、動態化,而且詮釋了經濟增長的真正源頭。由于技術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外溢性成為其突出特征,享受技術外溢好處成為廣大發展國家發揮后發優勢,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捷徑。馬歇爾(1898)在其經典著作《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由于集聚經濟帶來的技術外部性,使得從事相關聯行業的人能從中獲益,“方法上最重要的改良,經過試驗階段之后,很難成為長久保守秘密”。這一觀點得到Tor(2000)實證分析的證實,研究發現在政府出資的研究項目中,由于技術溢出的存在,受到政府資助的企業與沒有受到政府資助的企業在技術上并無實質區別。技術外溢無處不在,即便嚴格的專利保護制度也無法完全隔絕這一情況的發生,Mansfield(198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60%的專利產品在4年之內出現大量仿制品。在這一觀點雖然歷史性地刻畫了技術外部性的存在意義,但并沒有深入研究這一外部性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庇古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拓展性分析,將外部性作為影響企業技術投入影響因素之一納入模型分析,研究發現:由于外部經濟的存在,廠商的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存在差異,若沒有政府干預,競爭性廠商不會選擇取得社會最優量的技術投入水平,進而分散化經濟的競爭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Romer(1986)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D'Aspremont and Jacquemin(1988)建立了一個存在技術溢出的雙寡頭模型,結果表明,由于存在技術溢出,競爭型研發模式存在研發投入不足現象,合作型研發采取了研發投入外部成本內部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外部效應而導致R&D投資不足的問題,但仍然低于社會福利最大化時的最優研發數量。霍沛軍、陳繼祥、宣國良(2002)研究發現,每個企業都試圖通過減少給予另一個企業的信息來增加自己的利潤,但最終每個企業的利潤都降低,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也隨之降低。家庭和企業都可能成為技術外部性的受益者,但由于正外部性無法通過市場得到有效補償,個人將減少對技術研發的投資,這成為加大政府補貼額度的重要原因。因此,依靠適當的政府補貼能消除個體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的差異,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與提高社會福利(Romer,1986;Lucas,1988;Pradhan,1996)。加大政府補貼額度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補貼能增強企業技術創新動力與投資者信心,加快企業技術升級改造。Arrow(1962)通過比較壟斷與完全競爭情況下的創新活動,可以看出,單靠市場為個人提供創新激勵,整個社會的創新投入是不足的,因此政府要加強技術創新補貼,增強創新激勵。這一研究成果開創了政府補貼與企業技術創新激勵的先河。后續的大量學者證實了這一結論,Martin(1995)認為,政府創新補貼比專利保護制度與合作研發能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創新激勵,在研發競爭的壓力下紛紛采用新技術,生產新產品。Marryann(2006)研究發現,政府補貼研究項目,有助于增強投資者信心,有利于未來企業吸引到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技術創新中來。張春輝、陳繼祥(2011)運用演化博弈理論分析R&D補貼對企業創新模式的影響,發現當R&D補貼標準提高將導致企業選擇顛覆性創新模式的可能性增大,選擇漸進性創新模式的可能性減小。這些理論分析的結論得到了國內外大量實證分析結論的支持。Xulia(2008)以西班牙制造業企業為例,研究發現小企業由于受到自身規模、技術、資金的局限,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無力開展技術研發活動,政府補貼具有較大的示范與激勵效應,激勵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且不存在擠出效應。Eui(2010)分析了政府補貼對韓國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效應,發現政府補貼能降低企業的創新風險或融資成本。鄭緒濤(2009)以1995-2006年中國醫藥制造業16個行業的數據分析發現,R&D折舊、稅收優惠與政府的R&D投入都會對私人R&D活動產生激勵效應。王俊(2010)運用我國28個行業大中型企業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表明,R&D補貼對企業R&D投入存在明顯的正向激勵作用,但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卻具有不確定性。韓民春、樊琦(2010)通過自主創新評價指數、皮爾遜相關系數分析了R&D補貼與我國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研究表明R&D補貼政策對我國汽車產業自主創新具有顯著正向激勵作用。
通過先前諸多學者研究成果的梳理,我們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既是技術進步前行過程中難以逾越的一座大山,又是技術進步過程中必須具備的制度環境,而政府補貼政策的推行將有助于“潤滑”二者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這是因為,政府補貼的實行,一方面有助于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開展,保護創新者的熱情與積極性;另一方面有助于經濟主體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取新技術,加快科研成果與生產力的結合。文章接下來的部分將以如下的線索展開分析:第三部分構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各個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選擇;第四部分求解一般均衡解,以及通過比較靜態分析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出相關結論;第五部分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三、理論模型
在整個經濟中存在著無數個同質的個體,經濟中每個個體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為了分析方便,不考慮人口增長,假定經濟由連續同質的家庭組成,每個家庭具有無限壽命。經濟中人力資本(H)的供給缺乏彈性,人力資本可以有兩種用途:HY部分直接從事最終產品的生產;HN部分直接進入R&D部門從事技術創新。R&D部門運用投入的人力資本(HN)和已擁有的知識資本存量在知識產權法的保護下(φ)進行技術創新,即研究開發出新的產品種類或新的產品設計方案(N),然后將新研究開發出來的設計方案注冊為永久專利,并出售給下游的中間產品生產商。中間產品部門,在區間[0,N]上存在著無數個同質的中間產品生產商,第i個代表性中間產品生產商通過金融市場籌集與政府補貼創辦企業所需的啟動資金(Ω),隨之以此購買新的中間產品設計方案(N)生產新的中間產品(xi),然后將新生產的中間產品出售給最終產品生產商。在最終產品部門,存在著無數個同質的最終產品生產商,代表性生產商使用其購買來的中間產品(xi)和雇傭的人力資本(HY)生產最終產品,其產量用Y來表示。
1.最終產品部門
最終產品部門由無數個同質企業構成,為了簡化分析,我們用一個超大型的企業代替。廠商投入人力資本和中間產品來進行生產,假定人力資本與中間產品投入規模報酬不變,人力資本的供給缺乏彈性,最終產品部門的總量生產函數如下:

其中,Y表示最終產品部門的產出;A表示生產力參數;N表示中間產品的種類數,N越大意味著技術水平越高;xi表示第i種中間產品數量。
假設勞動力市場和最終產品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最終產品的市場價格為1,廠商可以通過在產品市場上購買中間產品(xi)和在勞動力市場上雇傭人力資本(HY),則最終產品生產商的利潤函數為:

其中,wHY表示投入到最終產品部門的人力資本報酬率;Pxi表示第i種中間產品價格。
由式(2),根據最優化一階條件及廠商利潤為0的條件可得:

我們假定xi=x,(3)式可改寫為:

2.中間產品部門
假定中間產品市場是壟斷競爭的,在中間產品部門,在區間[0,N]上分布著無數個中間產品生產商,每個廠商只生產一種中間產品,而且這些中間產品之間是不完全替代的。由于各中間產品生產商提供的產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各廠商擁有有限的壟斷勢力,因而市場中允許經濟利潤的存在。當R&D部門開發出一種新的產品設計方案后,中間產品生產商通過購買這種產品的專利開始這一新產品品種的獨家生產,享受由此帶來的壟斷利潤。根據Barro(1995)假定,中間產品市場是壟斷競爭的。任一新的產品設計方案被R&D部門開發出來后,一單位任一類型的中間產品xi(i∈[0,N])的生產正好消耗一單位最終產品投入,即生產函數為:

由于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中間產品生產商可以根據新技術的應用成本選購最終產品投入決定最優的中間產品供給數量,從而實現自身的利潤最大化。這里,我們假定新技術的應用成本為生產成本的μ倍,即中間產品生產商運用某一新技術生產一單位任一類型的中間產品xi(i∈[0,N])要消耗μ單位(μ>1)最終產品均為新技術的應用成本,則中間產品生產商的利潤函數為:

根據公式(5)和(7)可以得到中間產品生產商的壟斷定價為:

再根據公式(5)和(8)可得中間產品的需求量為:

將式(9)代入式(7)可得中間產品生產商的最大化利潤水平為:

一個中間產品生產商引進一項新的中間產品或設計方案的收益(Vt)等于它生產這種中間產品所能獲得的壟斷利潤的貼現值,即:


其中,φ表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
公式(12)表明當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與利率相等時,資本市場便處于均衡狀態。
3.R&D部門
我們的模型遵循Mondal&Gupta(2006),張亞斌、易先忠(2006)的假定,研發部門所能開發的新設計方案的數量取決于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資本存量。研發部門的總量生產函數為:

其中r表示市場利率。
根據資本市場無套利原則可知:
式(13)中,N為技術知識增量;δ為研發部門的生產率參數;HN為研發部門的人力資本數量。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知識資本存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內已擁有的技術知識資本存量φN+λ(1-φ)N,φ表示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φ表示由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利導致技術外溢的程度,λ表示舊技術對新技術進步的貢獻。這一部分知識資本存量的獲取是依靠國內企業自主研發以及對國內先進企業的技術模仿。二是對國外先進技術的模仿(1-φ)B(H)(N*-N),B(H)表示學習能力;N*-N表示國外已經研發成功而目前國內尚沒有掌握的新技術,這可以理解為國外相對于國內的技術優勢。這一部分知識資本存量的大小與技術溢出的程度直接相關。特別是當φ=1時,由于知識產權保護空前嚴格,技術溢出完全不可能,技術進步完全靠自主研發,靠模仿國外先進技術所得的知識資本存量為0;當φ=0時,由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利,技術知識完全溢出,國家的技術進步完全依靠對國外的技術模仿,靠模仿國外先進技術所得的知識資本存量為B (H)(N*-N)。
假設研發部門人力資本報酬為WHN,中間產品的專利價格為PN,則研發部門的總收入為:

本模型遵循Barro(1995)的假定,研發部門是充分競爭的,因此經濟利潤為0,即TR=TC。由公式(14)、(15)可以得到研發部門人力資本報酬率為:

由于研發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因此研發部門一項專利的價格應該與中間產品生產商所能獲得的壟斷利潤的貼現值相等,即:

4.家庭
我們假定經濟中的代表性家庭是具有無限壽命的Ramsey家庭,其通過優化選擇最終產品的消費數量來最大化其一生效用。效用函數為:

其中,C、ρ、σ分別表示居民的個人消費,時間偏好率,相對風險規避系數。居民消費的約束條件可表示為:

由上述約束條件,我們可以解得消費增長率的一般表達式為:

5.新產品的引入與政府補貼
Mckinnon(1973)認為,完善而發達的金融市場是學習和實踐新技術的充要條件。由于實踐新技術,開創新領域必然要面臨一定的資本門檻,而資本門檻的高低將直接決定科研成果商業化的速度。這里我們假定創辦一家中間產品生產企業所需的最基本的資本投入為Ω,表達式如下:

式中,Ω0表示中間產品生產的啟動成本,包括購買產品專利、廠房、材料和雇傭人力資本等。由式(21)可知,,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品種類越高,引進新產品所面臨的資本門檻越低。這主要是因為,若一地區的品種種類較多,本行業的生產技術基礎較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創業者的搜尋成本,從而降低了新進入者的資本門檻。
假定引入新產品的新進入企業需要通過外部融資與獲取政府補貼來創辦企業和組織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國內金融市場的效率如何,將直接決定引入新產品的難易程度。在一些地區,金融市場效率低下,這直接反映在貸款利率(i)明顯高于存款利率(r)(King& Levine,1993)。因此,由于外部融資而必須支付的利息費用的貼現值為:

這里我們假定i=φr,φ>1。φ表示金融市場效率系數,其值越大,金融市場效率越低。則公式(22)可以改寫為:

由于中間產品市場是壟斷競爭的,當φ(1-t)Ω0N-γ>V時,創業者將沒有進入投資實業的沖動;當φ(1-t) Ω0N-γ<V 時,由于受到利潤激勵,將有無數的創業者涌入這一行業。但金融市場在一定時期內所能提供的資金量是有限的,從而這一情況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創業者愿意引入新產品的均衡條件是:

由公式(24)可知:

將公式(25)代入公式(12),可得:

四、均衡分析
1.經濟的最優路徑
假定人力資本在經濟體系中可以自由流動,當最終產品部門和研發部門人力資本報酬率相等時,人力資本分布處于均衡狀態,即當WHY=WHN時,人力資本停止流動。
由公式(4)、(16)、(17),可得:

聯立公式(13)和(26)可得:

將式(28)代入(13)可得:

在均衡狀態中總消費、總產出與技術具有相同的增長率:

2.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
由公式(31)可得:


由式(32)可知,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確定的,的符號與1-λ-B(H)(M-1)的大小直接相關,即知識產權保護保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自主創新的程度與技術進步的方式休戚相關。即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低時,知識產權保護越嚴格,越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主要是因為,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低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保障R&D部門收益與提高人力資本報酬率,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投入到R&D部門,從而提高R&D部門產出,為經濟起飛提供技術支持。同時,由式(21)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產品種類N越大,創辦實業的資本門檻越低,新的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速率越快,經濟增長加速。,即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高時,知識產權保護越嚴格,越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是因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雖然有助于保障科研工作者及R&D部門收益,但由式(13)可知,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日益嚴格,后進國家或地區能夠從先進國家或地區那里獲得的技術外溢以及可選擇的模仿集(N*-N)減少,這減少后進國家的知識資本儲備數量與縮小了其能夠進行自主研發與自主創新的領域,直接導致R&D部門新產品開發速度下降,收益減少;由于產品種類N較少,新進入企業能從其他企業那里獲取的技術外溢效應及技術信息較少,這增加了新進入企業從R&D部門那里購買專利及創辦實業所需資本(Ω0),資本門檻陡增,極大的削弱了企業家的創業熱情,科研成果的市場化、商業化速率下降,經濟增速放緩。


命題1: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低時,知識產權保護越嚴格,越有利于經濟增長,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大會進一步放大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高時,知識產權保護越嚴格,越不利于經濟增長,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會減緩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3.政府補貼與經濟增長
由式(31)可得:

由式(34)可知,政府補貼份額越大,越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主要是因為,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降低了企業家將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所面臨的資本門檻,各大企業競相購買R&D部門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此成為運用該專利技術生產相應中間產品的唯一生產商,獲取壟斷利潤。在利潤的驅使下使得各大企業競相購買專利技術,從而對原創科研成果的需求空前增加,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的周期明顯縮短,R&D部門產出的速率與數量都大大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將加快。


命題2:政府補貼與經濟增長息息相關,政府補貼份額越高,越有利于經濟增長;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低時,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進一步放大政府補貼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高時,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消弭政府補貼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
4.技術應用成本與經濟增長
由公式(31)可得:

由公式(36)可知,技術應用成本與經濟增長呈現反向關系,即技術應用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經濟增長。這主要是因為,新技術、新產品的引入成本不僅取決于該專利技術價格的高低,更取決于對該項技術消化、吸收以及將其運用于生產過程之中等技術應用成本的高低。在專利價格一定的情況下,技術應用成本越高,將各項技術引入經濟所需的資金也越多,這一方面對企業的外部融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業運營的風險,稀釋了企業的利潤,使得對該項技術的需求者較少,該項技術往往被束之高閣,難以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
由(36)可得:

由式(37)可以看出,政府補貼份額越高,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越小,也就是說,較高的政府補貼份額會減緩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因為,高企的技術應用成本往往令大量的企業家望而卻步,而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可以減輕企業購買專利的費用及技術應用成本,降低了企業的運營風險,保障了企業的利潤水平,縮短了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周期。同時,由于新科研成果的市場化、商業化價值較快地得到實現,這有效提高了R&D部門收益及科研工作者的報酬率,使得R&D部門能夠正常運轉,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由(36)可得:

命題3:技術應用成本與經濟增長呈現反向關系,技術應用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經濟增長,較高的政府補貼份額會減緩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經濟中存在著自主創新,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進一步放大技術應用成本的負面效應;當經濟中缺乏自主創新,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減緩技術應用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縱觀命題1、命題2和命題3,由于各國自主創新程度與技術應用成本的差異,相同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與政府補貼份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高時,經濟增長依賴于寬松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來促進技術外溢及技術信息的流動以加強本國知識資本的積累,以及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來降低新進入企業創業過程中所遭遇的資本門檻與技術應用成本,加速R&D部門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進程;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低時,經濟增長依賴于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來保障R&D部門收益和人力資本報酬率,以及政府補貼份額的增加來加快R&D部門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進程,加速生產率提高。于是,我們可以得到命題4。
命題4: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較高時,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寬松,政府補貼份額越高,技術應用成本越低,越有利于經濟增長;當經濟中自主創新程度越低時,知識產權保護越嚴格,政府補貼份額越高,技術應用成本越低,越有利于經濟增長。
五、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1.根據自主創新的程度與技術應用成本的大小確定機動靈活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由于自主創新程度的差異,相同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同的效果,因為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與技術發展水平所需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是不同的,相同的資源稟賦及技術進步方式也會在不同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下有所區別。另一方面,在將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的進程中,各企業不僅會遭遇資本門檻,而且高企的技術應用成本也是阻礙這一進程不能忽略的因素,因為其直接決定企業家將該項技術運用于生產,引入經濟意愿的強弱,因而它不僅關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實施效果,更直接關系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與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戰略的實施。所以,我們在設定各個區域具體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時,應綜合考慮各區域在自主創新的程度與技術應用成本的大小方面的差異。
2.建立完善而統一的政府補貼體系,不僅加大對原創技術創新研究的支持力度,而且重視對技術應用研究的扶持力度
在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加大政府對技術創新的補貼份額對于保障R&D部門收益及科研工作者收益與加快新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進程意義深遠,因此加大政府對技術創新的補貼份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條件。二戰后,新技術、新產品層出不窮,究其原因除了日趨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扶持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各項政府研究基金都加大了對原創技術、基礎理論研究的扶持力度,這必將激勵R&D部門的研發熱情,加快技術進步。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技術應用方面的研發,因為技術成本成為決定該項技術運用前景及可獲取壟斷利潤多寡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技術成本越高,越難以運用于企業的生產過程中,往往會被束之高閣,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這也將危及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的步伐,政府加強對這一方面研究的扶持力度也是有效規避這一弊端的重要舉措。
3.加快金融市場建設,搭建企業融資平臺,加快R&D成果市場化、商業化進程
雖然政府補貼能有效降低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所面臨的資本門檻,但是隨著技術更新速度的加快,尤其是自主創新活躍的地區,政府能夠提供的資金畢竟有限,企業能否順利將新技術、新產品引入經濟更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外部融資能力的強弱。外部融資能力的強弱與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發展尚顯稚嫩,融資渠道不暢通,一方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閑散資金;另一方面大量好的項目因為資金匱乏而擱淺。因此,政府在加強對技術創新補貼的同時,應該搭建企業融資平臺,拓寬融資渠道,廣納社會閑散資金,降低金融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制約,縮短新科研成果市場化、商業化周期。
[1]韓玉雄,李懷祖.論世界工廠模式下知識產權保護對工資水平及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個簡單的技術擴散模型 [J].中國軟科學,2004(7):53-57.
[2]劉勇,周宏.知識產權保護和經濟增長: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 [J].財經問題研究,2008(6):17-21.
[3]王俊.R&D補貼對企業R&D投入及創新產出影響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0(9):1368-1374.
[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5]張春輝,陳繼祥.兩種創新補貼對創新模式選擇影響的比較分析 [J].科學學研究,2011(8):9-16.
[6]Acemoglu D,Aghion P,Zilibotti F.Distance to frontier,selection,and economic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 No.9066,2002.
[7]Eui Young Lee,Beom Cheol Cin.The effect of risk-sharing government subsidy on corporate R&D investmne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Korea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0,6:881-890.
[8]Ginarte,Park.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1997,26(3):283-301.
[9]Lin J,G.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5):426-431.
[10]Lin J.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R].https://www.bus.umich.edu/KresgeLibrary/Collections/W-ork-ingp-apers/wdi/wp409.pdf.
[11]Martin,S..R&D Joint Ventures and Tacit Product Market Collusion[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1.
[12]Maryann P.Feldman,Maryellen R.Kelley.The exant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spillovers:Government R&D policy,economic incentives and private firm behavior [J].Research Policy,2006,35:1509-1521.
[13]Mckinnon R.Monetar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e,1973.
[14]Mondal,Debasis,Gupta,Manash Ranjan.Endogenous imit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a North-South model: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9,31.
[15]Paul M.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16]R.F.Harrod.Essayin Dynamic Theory[J].The Economic Journal,1939,49(193):14-33.
[17]Robert M.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
[18]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19]Robert E.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20]Rod Falvey,Neil Foster and David Greenaway.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R].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conomic Policy,Research Paper 2004:12.
[21]Solow.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29-45.
[22]Tor Jakob Klette,Jarle moen,Zvi Griliches.Do subsidies to commercial R&D reduce market failures?Microeconometric evaluation studies[J].Research Policy,2000,29:471-495.
[23]Xulia,Consuelo.Do public subsidies stimulate private R&D spending?[J].Research Policy,2008,37:371-389.
(責任編輯:FZ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conomic Growth
ZHANG Shu-qin1,ZHANG Wang2,3
(1.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Jiangsu 210016,China;2.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3.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three-sector model,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imposing on economic growth.As the findings show,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xerts ambiguou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in accord with the extent of self-innovation.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contributes to lessen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r highlighting the positive effect the stri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impos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much to do with economic growth,the higher the ratio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s,the more rapi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The stri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lessen or highlight the positive effect government subsidies imposing on the economic growth.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cost exhibits adverse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rowth,the higher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cost is,the lower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The higher rat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will make up for the adverse effect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cost imposing on economic growth.The stri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ll lessen or highlight the negative effect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cost imposing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perty protection;Goverment subsidies;Industrial economic
F415.2
A
1004-292X(2014)04-0062-010
2014-12-31
張書琴(1979-),女,湖南安仁人,博士,主要從事經濟法與經濟刑法研究;
張 望(1981-),男,湖南安仁人,博士,主要從事產業演化與知識產權保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