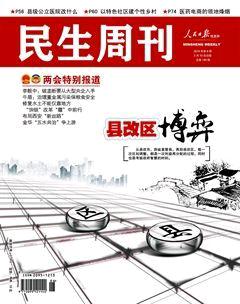全國人大代表、農工黨湖南省委專職副主委蔣秋桃:第三方監督遏制過度醫療
鄭智雄
“吃藥能好的小病,就不要打針;打針能好的病,就不要輸液。”如此簡單的醫學常識,在實際的醫療診治過程中卻難以得到有效貫徹。
作為醫療亂象的“過度醫療”,不僅造成公共醫療資源浪費,同時也會損害患者的身體健康。這一弊病的形成原因,除了患者面對疾病時的恐慌心理外,還有醫院、醫生等醫療主體的利益驅動。
“過度醫療”已然成患。針對這一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農工黨湖南省委專職副主委蔣秋桃建議,建立醫療行為第三方監督等制度遏制過度醫療。
患者的觀念誤區
“即便是感冒、拉肚子等小疾小患,患者及家屬也都希望盡快把病治好,于是就會不憑處方濫買濫用處方藥。”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蔣秋桃表示,這一現象非常普遍,屬于日常治療中的認識誤區。
這種認識誤區導致一些患者認為,能立竿見影的就是好藥,能迅速控制癥狀的就是好醫生,甚至認為,只有三甲醫院、大城市的醫院、著名醫院、專家門診才能看好病。
追求好藥、好醫生以及盲目追求高端醫療,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在蔣秋桃看來,盲目追求療效快是不正確的。
談及盲目醫療的后果時,她表示出自己的擔憂,片面追求治療的速效,容易導致抗生素類、激素類藥物的濫用。動輒選用昂貴的儀器設備進行檢查,選擇進口藥、高價藥,勢必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此外,如果一些普通、常見病或慢性病都傾向于選擇高端醫療,將使得大型醫院人滿為患、不堪重負。
蔣秋桃說,還有一種怪現象是一些患者“偏愛”住院。很多不需要住院的患者,都要求住院治療;已經達到出院條件的患者要求延長住院時間。盲目追求住院治療,會造成本就不寬裕的醫院床位更加緊張。
針對這種現象,蔣秋桃分析認為,心理上恐懼疾病的誤區,導致部分患者認為住院就等于進了“保險箱”;除此之外,還有貪便宜的想法作祟,為享受醫保政策而住院。
在關注醫療資源以及服務質量的同時,蔣秋桃還將觀察的視角延伸到更遠。她建議,應盡快建立患者心理輔導體系。
“應盡快建立社區、街道、鄉鎮和醫院三位一體的患者心理咨詢、輔導體系。”她對《民生周刊》記者說,除了使患者不出社區、街道、鄉鎮就可以接受身體健康檢查和咨詢外,更要通過宣傳、心理輔導逐步提高人們對疾病和健康的心理承受能力。
第三方監督
除人們追求健康長壽的需求變得強烈外,導致各種“過度醫療”現象的原因還有市場機制作用下,醫院追求業績效益。
有輿論指出,一些醫院和醫生“過度醫療”源于利益驅動。某些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違背臨床醫學規范和倫理準則,不思考如何為患者真正實現診治效果,只是一味耗費醫療資源獲取自身利益。
“破除以藥補醫,理順醫藥價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談到,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制。
蔣秋桃建議,要盡快建立第三方監督制度。按照她的設想,通過這個監督制度的約束,最終能夠實現“小病小醫,大病大醫,量力而行,適可而止”。
具體而言,就是遏制“小病大查、小病大醫、亂開大處方”等過度醫療行為,防止醫療保險費用不必要的浪費。此外,還要引導公眾、醫務人員、醫療機構樹立正確的治病就醫理念。
這個監督機制將如何開展工作?對此,蔣秋桃有具體的思路。“由第三方監督機構定期對醫生的處方、手術治療方案以及醫院對病人的檢查流程等,進行科學公正的監督和評審。”她說。
她建議,為確保監督的問題能夠落實,對經監督機構評審認為不合理的處方、治療方案和病案檢查進行曝光。對出現問題頻率較高的醫院給予公開警告,醫保費管理機關在收到被警告醫院的相關信息時,應立即拒絕支付醫保費。
在加強監管的同時,還應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建設。蔣秋桃談到,對符合醫療標準的基層醫療機構,應該允許其具有比大型醫院更高的醫保報銷比例,從而以經濟手段引導普通患者主動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近治療。
引入競爭機制,也是破解“過度醫療”的一個方面。“盡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精神,讓民營、個體醫療機構進入醫保體系,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政策。”蔣秋桃說。
此外,她還建議,應加強基層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隊伍建設,暢通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人員交流渠道;盡快出臺醫生多點執業具體操作細則,尤其要鼓勵省級以上醫院的醫生到最需要醫療資源的市、縣、鄉、鎮執業,改變醫生與單一醫院的所屬關系,逐步實現醫院與醫生之間的合作關系。
“安樂死”立法論證
改變患者就醫觀念,加強對醫療行業約束與監管,對于破除“過度醫療”的弊病是從制度設計上較為可行的辦法。不過,對于臨終治療這個“過度醫療”的特殊情形,恐難以奏效。
在蔣秋桃看來,“安樂死”觀念的推廣,將有利于解決這一問題。不過,在“安樂死”選擇中,始終存在著理性與情感、觀念之間的矛盾。
“在傳統道德觀念和患者家屬情感因素影響下,‘安樂死’仍難以被大眾所接受。”她談到,對于多數癌癥晚期患者及其他一些絕癥患者,生命的最后階段十分痛苦,患者本人可能會要求‘安樂死’,而不少家屬認為,只有傾盡全力治療才是對罹患絕癥親人的尊重和愛,很難做出選擇。
在蔣秋桃看來,通過立法推行自愿“安樂死”,既有利于減少過度醫療行為,也為社會節省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
她建議,要參照國外經驗,在我國進行“安樂死”立法探討,通過全民參與討論并取得半數以上認同以后,可考慮立法推行自愿“安樂死”。
“在考慮情感和道德因素時,或許我們應該反思:為了延續痛苦,并為極為有限的生命而耗費大量的醫療資源,以及患者家屬的財力、人力的行為是否理性。”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