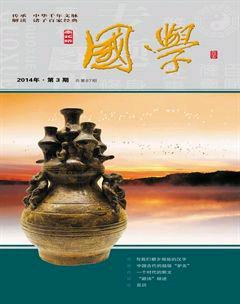一個時代的斯文
顧文豪

清華百年校慶舉辦了一個超級隆重豪華的典禮,這所名校什么時候建成“世界一流”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
在我看來,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或許就可以稱得上“世界一流”,至少是離“世界一流”很近。在歷數清華燦若群星的人物時,有一個人無論如何是繞不過去的。他就是服務清華近四十年、執掌清華和西南聯大十七年的梅貽琦先生。
梅貽琦被稱為“清華永遠的校長”,但在大陸,他的一生行為并不被太多人了解,這或許是和他晚年的選擇有關——他不像蔡元培這位資深的同盟會員,抗戰時在香港辭世,國共兩黨領袖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近日,我閱讀了黃延復和鐘秀斌合著的《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才對梅貽琦的生平和思想有所了解,知道梅先生除了那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還給中國教育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也能解開我曾有過的一點疑問。以前我看錢鍾書、曹禺、吳晗、韋君宜、趙儷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傳記和自傳時,很好奇為什么這些大家都出自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要知道,1925年清華才從預備留美學堂改成大學。清華大學短時間內能躋身全國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貽琦先生的貢獻是分不開的。梅貽琦在清華學堂改大學的第二年即1926年任教務長,在1931年至1937年清華的黃金時期任校長,抗戰八年他作為西南聯大事實上的校長(另,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堅持弦歌不輟、斯文不斷。
梅貽琦是一個職業教育家,他是一個最沒有“大師范兒”的大師,寡言少語而內心堅毅,初與人相交并無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沒有什么鮮明的領導才能,連他常說的“大概、或許、也許是”也被師生善意地調笑。但正是他辦事公道、生活儉樸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學規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離的品德和辦事風格,才使清華和西南聯大的師生敬服,從而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
梅貽琦比蔡元培小二十一歲,比梁啟超小十六歲,和胡適、蔣夢麟是同齡人。與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傳奇色彩,是一個純粹的教育家,一個純粹的大學校長。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學術地位——現在某些大學的校長在科研項目上“有權者通吃”的狀況在當時恐怕是丑聞,他也很少就政治、經濟等公共事務發言,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辦好清華這件事情上,心無旁騖,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這才是他的最偉大之處,這也是清華的最大幸運。
我以為,之所以說梅貽琦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維護“斯文”——尊重文化和學術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際上的恩怨則在其次。梅氏的辦學理念概言之為三句話:通才教育,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這三句話,可與至今尚立在清華園內一塊石碑上鐫刻的陳寅恪悼王國維的一段話參看。陳氏在悼文中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若無梅貽琦維護“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錢,是辦不好一所大學的。
1962年梅貽琦在臺灣地區病逝,葬在新竹清華的校園內,他的同道蔣夢麟先生為之撰寫的碑文稱其“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于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于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后生學子楷模”,不為過譽。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園”花木成林,成為校園一景,正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
在百年盛典的清華校園里,冠蓋如云,繁花似錦,不知道會有幾個人想起梅貽琦。能否問一句: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
鏈接
梅貽琦巧對寶塔詩
抗戰初期的一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行來到冰心家。閑談中,冰心當場創作了一首寶塔詩。這是女詩人一生創作的唯一一首諧趣詩。詩曰: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校長看罷不知何意。冰心作了解釋。原來,這是冰心丈夫吳文藻先生的笑話集錦。“馬”是說小孩子們把點心薩其馬簡稱為“馬”,一次,冰心讓吳文藻上街買薩其馬,吳文藻到點心鋪里說要買“馬”,結果鬧了笑話。“香丁”是指有一天冰心在樹下觀賞丁香花,吳文藻從書房來到丁香樹下,應酬性地問妻子:“這是什么花?”冰心答:“丁香花。”吳文藻點頭說:“噢,是香丁花。”惹得眾人大笑。“羽毛紗”是說一次,冰心讓吳文藻為岳父買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吳文藻到了布店說要買多羽毛紗。店員聽不懂,電話打到冰心家里,才知道吳文藻又鬧了個大笑話。“傻姑爺”因此得名。最后一句則是冰心同梅校長開了玩笑——吳文藻這個書呆子是清華大學培養出來的。
梅校長一聽也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校長先生以進為退,當場續詩兩句。梅校長的詩是這樣的: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