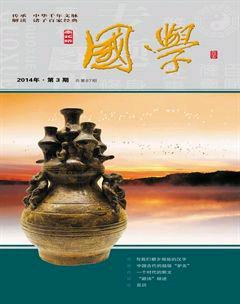吐峪溝石窟寺遺址
佚名
?笤 漢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標志
吐峪溝石窟寺遺址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這里的每一個石窟寺都是一系列精美建筑、雕塑、繪畫藝術的有機組合,是我國佛教藝術的珍貴實例。
吐峪溝石窟寺從窟制上看主要有三種:縱券頂窟、中心柱窟和方形佛壇窟。其中縱券頂式石窟,造型近同吐魯番地區常見的居民屋宇,窟分前后室,所謂后室,只是一處十分狹窄的小洞,是僧人坐禪用的“洞天”,稱為禪窟;方形窟地面往往有佛壇;中心柱窟,用佛教的觀念,也可以稱之為“禮拜窟”。巨大的塔柱,將洞窟一分為二,前后形若兩室。甬道可供僧侶、信徒回旋禮拜。他們虔心奉佛,入窟后右旋而行,繞塔瞻仰佛像,領會本生壁畫,接受佛教知識教育,聆聽法師教海,以求得到佛法的真諦,獲得靈魂的洗禮。佛像是中心柱窟主要的題材,幾乎畫滿窟中各壁,在方形窟中也有以千佛布列四壁的,千佛的造像在鼻眼上往往不提白粉,不做凸凹暈染,僅以線描畫出具有漢人五官特征的形象。窟甬道頂上有由忍冬、磷紋、團花等紋飾帶組成的仿漢式木構建筑,中土漢風的影響顯而易見。
石窟寺內壁中央大多繪佛教本生故事畫,尚能辨認的壁畫內容多為內地漢人所熟悉的如“肩提婆利忍辱截割手足”“摩鉗太子求法赴火”“慈力王施血飲五夜叉”“薩那太子舍身飼虎”和“毗楞竭梨王身釘千釘”“尸毗王割肉貿鴿”等,與龜茲莫高窟的單幅畫有較大的不同,且每幅壁畫旁都配有漢文。窟制、佛像、壁畫的特點顯示出吐峪溝石窟寺濃厚的漢文化影響。在唐以前,吐峪溝石窟寺所在的高昌古國就“國有八城,皆有華人”,是漢文化與西域文化第一個交匯之地,也是漢文化深入西北最西的地方。西域文化通過高昌傳人內地,內地文化又通過高昌傳向外域,而兩者初步結合便產生了高昌特色的文化。
另據唐代文獻《西州圖經》記載,吐峪溝石窟群中的丁谷窟除“有寺一所”外,還有“禪院一所”。這里的”禪院“應該是指唐代中期后,在佛教中興起的“禪宗”的宗教活動場所。“禪宗”是漢傳佛教的主流,其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大降低了民眾參佛的門檻,初起在廣東、湖南、江西等地,但勢力很快地在全國擴展,“禪院”的出現證實了西州境內很早就已經受到內地禪宗佛教的影響。
?笤 石窟寺榮衰的幕后主角:高昌政權
據考證,吐峪溝石窟寺的主要興建時間在公元443至460年之間,這段時期的高昌正處在北涼政權的統治之下,作為石窟寺的主要贊助人,高昌北涼政權的興衰成為石窟寺榮枯的幕后主角。北涼政權在統治河西時期,已在高昌設郡進行統治。至沮渠蒙遜之子沮渠無諱、安周時,高昌變成了北涼政權的統治中心。
北涼統治高昌的前后十八年,對高昌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吐峪溝石窟寺遺址是當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與衰微都與高昌北涼政權的存亡關系至密。發現于高昌故城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曾記載:“按十六國春秋,蒙遜時代,即尊弘事佛,禮接曇無讖。又于涼州南百里崖中,大造法象。茂虔尤軎文學,張溟、闞細之徒,并為顯官。故安周已挹其余風,雖身處窮域、尚能造像勒碑,恢宏釋教。”這段文字肯定了一個事實,即北涼王沮渠安周信奉佛教,曾在“百里崖中,大造法象”,吐峪溝成為沮渠皇室的造像集中地。
北涼滅亡后,到麴氏高昌時,皇室對佛教的重視只增不減。吐峪溝出土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記載了高昌王麴文泰與玄奘的一段故事:高昌王麴文泰篤信佛法,聽聞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經要路過高昌國,非常激動,他盛情款待了這位慕名巳久的高僧。為了把玄奘留在高昌,麴文泰用盡了辦法,甚至想出了嫁女兒的主意,想讓玄奘成為北涼的乘龍快婿。玄奘不得巳只好用絕食來表明取經的決心,麴文泰無奈只好放棄。基于這段往事才有了后來《西游記》演繹的西涼國皇室欲為唐僧招親的故事。
在玄奘臨行前,麴文泰準備了充裕的金銀與華服,訓練了一批小沙彌輔佐玄奘西行。臨別之時,二入鄭重約定,玄奘取經歸來仍要經過高昌。由此可見鞠氏對于佛教的重視。十七年后,玄奘從印度學成歸國,仍取道北路,翻雪山,涉流沙,履行與麴文泰的約定。他不知道,就在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麴文泰自恃距唐遙遠,中間又有大漠阻隔,勾結西突厥,阻隔西域與中原的交通,公然與唐王朝為敵。唐太宗派遣吏部尚書侯君集,于貞觀十四年率師數萬攻滅高昌王國,麴文泰身死,唐以其地改設為西州。佛教也就此失去了高昌政府的支持。
唐代的吐峪溝石窟繼承了高昌政權建造的佛窟規模,并有修繕。在敦煌遺書《西州圖經》中有這樣的記載:西州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高梁橫跨、綠蔭紛紛、香火繚繞、梵唄齊鳴,這其中猶以土谷窟寺最為聞名。如此數百年的經營和繁盛使吐峪溝石窟榮登東疆第一寶窟之位。至公元15世紀時伊斯蘭教越過蔥嶺進入佛教藝術興盛的南疆,取代佛教成為西域地區的主要宗教后,吐峪溝石窟遭才被廢棄。
?笤 屢遭破壞和劫掠
吐峪溝石窟在唐代以后毀壞嚴重,依現存遺址的情況,已很難找尋繁盛時期的“梵唄齊鳴”的景象,這除了宗教興替外,還因為地震以及海外探險隊的盜掠。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吐魯番地區就被歐洲及日本的各種文化探險隊、考察團頻繁光顧,先后有俄日英等國探瞼隊深入拜城、庫車、吐魯番等地,先是進行測量、繪圖、拍攝和考古發掘,然后瘋狂盜運。對吐峪溝考察次數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德國人勒柯克和格倫威德爾,從1902年到1914年,他們曾先后四次到吐魯番。勒柯克1905年第一次來到吐峪溝就剝割了這里最精美的壁畫,并找到了溝東一間密室(后稱“手稿窟”),拿走了滿滿兩麻袋文書和許多“驚人的刺繡品”。1907年,袼倫威德爾再次來這里進行測繪、拍攝和盜墓。洗劫之后,吐峪溝石窟變得更加千瘡百孔,一片殘破。
另外是地震等天災的襲擊,據歷史文獻記載,吐魯番地區屬地震常發區,而且震級多在六級以上,每一次強烈地震的發生,都會帶給位于峭壁上的石窟以毀滅性的災難。特別是1916年左右的一次大地震,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東西被蓋在地底下。
目前,對吐峪溝石窟寺發掘的已告一段落,專家表示:未來吐峪溝石窟寺的發掘將對整新疆石窟寺遺址的發掘及保護、管理起到示范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