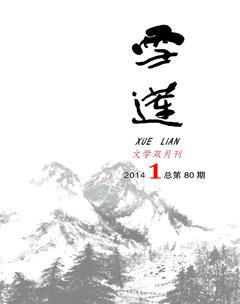煎餅果子
樓下賣煎餅果子的老李半個月沒來了,我有些擔心他。
我覺得就算是要換地方,老李也該告訴我一聲,畢竟我和他是有交情的。
這交情被我笑稱為是“果子交情”,一切都要從老李八年前開始在我們小區門口擺攤說起,我所在的小區在老城區,是以前政府大院的一部分,這里居住著許多上了年紀的文化人,其中不少都在機關單位工作過,除此之外便是這些人的子女,年輕人一人一個樣,比較不安,比較時尚。
我自己其實也屬于子女一輩,但由于年齡大了,反倒是和老住戶們交往多些,天氣好的日子里,伴著大爺大媽晨練的步伐,我收拾下樓,來到小區門口買早點。
遇見老李的那天正巧是冬至,老天爺總會賣給老祖宗一個面子,每逢節氣沒有不變天的,這樣令我們對于天地心懷敬畏,敬畏可以令人活得更加踏實。那天風吹人格外冷,晨練的老人家們大都選擇了休息,因此小區門口的小吃攤顯得特別冷清。
老李的煎餅車不是新的,但看上去很干凈,他自己一身藍色大褂,系著白圍裙,身上鼓鼓囊囊的,應該是穿著厚棉襖,遠遠看去給人忠厚老實的感覺,而他也確實如此。
從“老師,來一套?”到“陳老師,老樣子?”只用了半年,這半年里他的生意漸漸好了起來,他為人低調和善,與周圍攤販關系處得好,看見我們小區保安沒吃早飯,他就會招呼人家來一套免費的。
保安小劉吃他的免費煎餅最多,于是便破例允許他晚上把煎餅車停在小區里,這樣一來,他可以安心地從早干到晚,一般到了早晨十點左右,油條豆漿火燒湯包的小販就會撤去,他們給老李點點頭,老李報以一個憨實的笑容,接下來就是老李一個人的時光了。
原本我也沒特別關注老李,直到有一次我發現他坐在椅子上,捧著一本《讀者》在看,心里忽然就有些莫名的感動,他看書的姿勢很別致,身子斜著,雙手像抱小孩子那樣讓雜志對著陽光,他的眼睛可能有些老花,因為他并非湊到紙上去,而是腦袋在向后梗著,倘若他手中捧的不是書,那這副樣子還真有些像鐵匠欣賞自己剛剛打造出的兵器。
我問他,老李呀,你也愛看《讀者》啊,他說是啊,看了好些年了,煎餅果子時忙時閑的,沒事就翻翻。
于是我對他的經歷開始感興趣,并非我心存歧視,誠然這些城市最底層的奉獻者真實可愛,但他們中大多數沒有接受過教育也是事實,這或許便是他們生活艱辛的一個原因。老李卻是個例外,在得知他喜歡讀書以后,我就覺得他的身體里是充滿了力量的,甚至覺得小劉吃他的那些煎餅都不值一提,畢竟老李在這之中多少運用了生存智慧,他現在可以舒服地坐在小區門口,這就是智慧。
老李給我大致講了講他的故事,早年在田里干活,字是跟一位鄉村教師學的,最早的幾本書也是那個老師給的,言語中聽得出他對那位鄉村教師的感激之情,后來生養了一個兒子,家里有些吃緊,他便進城務工,什么活都干過,什么苦都嘗過,最風光的時候帶著干活的弟兄到最好的洗浴中心,最慘淡的時候被欠了一年的血汗錢,啥也沒撈回來。
后來也挺巧的,跟著合租屋的一對夫婦學會了做煎餅,老李說甭提多簡單了,做四五個就徹底會了,賣一個月就是煎餅大師,說到這兒我和他都笑了起來,再往后那對夫婦回鄉不干了,就把煎餅車留給了他,老李算了算成本還有平日花銷,心說賣好了肯定有得賺,于是一干就是三年。
我問他孩子多大了,他抹了抹鼻子,笑著說十七了,學習不太好,自己本來想把他高中供出來,可孩子自己說不學了,也就只好隨他的意思,現在家里的田是孩子在種。
我點了點頭,本來想跟他說說自己的兒子,話到嘴邊卻又收了回去,我怕我不經意間吐露的小事在他聽來會傷及自尊,這種有話不能說的感覺令我憋屈,感覺自己心里和憨厚真誠的他并沒有太多隔膜,相反我很喜歡聽他說話,但是某種來自于社會本身的距離感使我終究不能與他盡意。
他每次喊我陳老師,我則叫他老李,老李是大家叫的,我其實想叫他一聲李哥,想想還是算了,他多半會尷尬,我不應令他尷尬。
老李一如既往地賣著煎餅果子,看《讀者》,偶爾和我聊聊瑣碎,他的日子過得很平常,我的也是,往往說不多,兩個人就悶著看看周圍打發時間,有次我在小劉那兒取信的時候被他看到,他忍不住問我怎么時不時就會收到信,我便如實告訴他有些是稿費,有些是審稿意見,他這才知道我是個作家,拍了自己腦門一下,說自己真是糊涂,都不問問我是做什么工作的,聽他這樣講,我心里有點堵,其實分明是我避開不提罷了。
那天,我拿稿費請老李在附近的排檔吃了烤肉,喝了啤酒,老李說他不沾酒,我說不信,硬要他喝,喝了半瓶,他的眼睛就淚汪汪的,說陳老師你對我真好,你大作家,你城里人,你你你,你是大好人,大大好人,沒人對我這么好……
他越說我越難過,自己也眼淚汪汪的,不知道為什么,我難得喝醉一次,醉了以后給兒子打電話,讓他把家里攢的雜志拿來,能拿多少拿多少,《讀者》就不用了。后來就看到兒子叫了同院的兩個小伙子,提了扎好的雜志來大排檔,怎么也有三百多本。
這小子跑到我面前興奮地說,爸,終于舍得賣了啊?接著看了看老李,一臉疑惑地問我,爸,賣煎餅果子的也收廢紙啊?
我有些生氣地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說,沒有禮貌,這是你李伯,咱們把這些書送到你李伯家去。聽到這兒,原本迷迷糊糊的老李仿佛瞬間酒都醒了,連忙說,這這這,這怎么行。在我的執意要求下,老李終于同意收下書,但是說什么也不要我們搬,最后我拗不過他,只好看著他把成摞的書在煎餅推車上扎好,一步步推了回去。
他無論如何都不要我們送,我猜他可能介意我們看到他的住所,也就沒有堅持,但是留下了他的手機號。這一年是老李攤煎餅的第六年,我認識他的第四年。
后來幾年我和老李的交情越來越深,他回家歸來都會給我帶些鄉間特產,我除了給他雜志,偶爾也會送他些家里用不到的東西,這件事后來讓我陷入了深深的內疚與反省之中,我意識到老李給我的東西雖然土里土氣,但都是他能拿出的最珍貴最真誠的禮物,而我給他的卻并非是最好的,就比如家里安了天然氣灶,以前的電灶用不到了,我就洗一洗送給他,即便我從來沒有施舍的意思,但看上去就是那么回事。
有時我真想和老李互換身份,我感覺那樣我可能會安心許多日子,不必再為困擾著我的問題糾結,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和他說起來,他先是愣了愣,隨即笑著說,我可用不慣你家坐著屙屎的馬桶,我跟著笑了,笑得有些無奈。
認識老李的第八年,我準備認真送他一件禮物。
我為此想了很久,跟妻子商量了許多次,最后決定幫他換一輛嶄新的小吃車,妻子說現在有專門賣這種車子的公司,既好看又干凈,我覺得這應該是幫助的性質,而并非施舍,于是說那就送這個吧。
我準備好了買小吃車的錢,心里既興奮又忐忑,我怕這樣做會讓老李受驚,特別是怕他反應過度,要給我回一份大禮,如果真那樣,我會良心不安的。
我試著問了問老李的生日,他笑著說鄉下人過什么生日咧,我說你娘把你帶到這花花世界上,就值得紀念,為了咱娘,咱也要過生日啊你說是不是,他想了想,喃喃說以前還真沒過過呢,都記不清了,大概是臘月吧,應該是臘月,日子就不知道了。
我盤算著一進臘月就把小吃車買給他,眼看著還有四個月就到了,老李消失了。
老李消失以后我找過他,先是不停打電話,一直都是關機,接著是問小劉,然后問別的小吃攤販,后來日子越來越近,我就干脆滿城打聽,朋友們聽說我在找一個攤煎餅的,都笑我嘴饞,我沒有跟他們解釋,我解釋不清楚。
我著急找他是為了趕在臘月前把禮物買了送給他,可是一直到臘月過去了,他也沒有出現,因為過年了,他知道他肯定要回家過年的,那就只能等開春了。沒想到,是我太樂觀太粗心,老李消失這么久,我只猜他是回家了,卻沒想過他會出事。
開春的時候,我每天早起去看老李回來了沒有,直到有一天,老李的煎餅車終于出現了,我興奮地跑上前去,卻發現那里沒有老李,而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叼著一根煙,正斜眼看著我。
“來幾個?要腸不要?”他說。
我著急了,連忙問:“老李呢,這車是老李的呀!老李呢?!”
聽到我的聲音,周圍的小販都看過來,我感覺到他們的目光有些異樣。
年輕人的痞氣收斂了一些,問我道:“你認識我爹?”
“啊?哦哦,是!你爹呢?!”
“死了。”
我這才知道,老李有糖尿病,有一次他下午賣煎餅的時候碰上這一帶的城管,他和他們很熟,就好像他和小劉的那種熟,可是這次他們很嚴肅,說上面派了任務下來,要抓幾個典型,老李明白了,他們是看老李跑不動,拿他去充數的,于是老李就去了,車子被扣下,人被要求拘留一天,就是這一天,老李低血糖發作,先是休克,由于沒人發現,耽誤了搶救時間,后來沒能撐得住,死在了三平米不到的格子里。
城管的人于心有愧,找來了老李的兒子,處理了后事,把煎餅車還給了他,原本他沒想出來賣煎餅,可是年翻過去以后就感覺家里錢不夠花,這才根據老李以前告訴他的,重新回到了我們小區門口。
我愣了好久,可能有十多分鐘,他已經不想搭理我了,我這才慢慢地說了些我和老李的交情,最后說了我準備送老李的禮物。
他不可思議地看著我,似乎不相信我會那樣做,我說你放心,下午我就去買,當然如果你不想要的話,我可以送你別的東西,他眨了眨眼晴說,那你還是送我輛摩托車吧。
我說好。
他笑著說,來,叔,我給你攤套煎餅果子。
我說好。
面糊旋轉開來,他打了兩個雞蛋,打第二個的時候笑著看了看我,那眼神是在告訴我這雞蛋是專門為我加的,翻面,刷醬,撒上蔥花和香菜,他的動作比老李大好多,看上去利索,其實有些不細致,接著他放了兩根油條在中間,最后是火腿腸,疊起來,裝袋,遞到我面前。
我點了點頭,機械地摸出三塊錢放在錢盒里,我感覺我的精神是恍惚的,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問題,直到他把錢塞回我口袋,對我說了些什么,我慢慢往回走的時候,我都沒意識到是哪里出了問題。
后來,回到家,一口咬下煎餅果子,我這才反應過來,其實哪里都沒有出問題,我不過是想起了八年前的冬至,我第一次買煎餅時,老李給我說的話,他說:
“老師要夾薄脆還是油條啊?薄脆啊,好咧,老師會吃啊,煎餅果子簡單,里外一合就成了,面子和果子的關系最重要了,面子軟,果子脆最好吃,你說是不是啊?”
我又咬了一口煎餅果子,如同嚼蠟。
是啊,李哥,你說的是啊。
【責任編輯 柳小霞】
【作者簡介】陳文歆,男,90后,現就讀于山東大學,西寧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