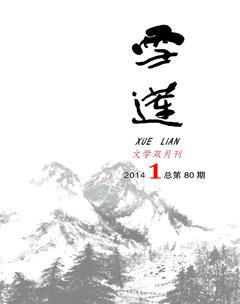鄉(xiāng)間鳥(niǎo)鳴
鳩 鳴
兒時(shí)的心常常被村頭、田邊、屋后一些鳥(niǎo)的聲音所牽動(dòng),砍柴正忙,忽聞一聲“天作怪”,舉起的柴刀就停在半空,而去細(xì)細(xì)辨聽(tīng)那親切有趣的鳥(niǎo)語(yǔ)。
“天作怪”是斑鳩的鳴叫,斑鳩羽毛灰白,皮膚黑灰,天欲降雨時(shí)它使勁地叫“天作怪”,而雨后天晴之際它又發(fā)出“燒大火”之音。在偏僻的大山中,鳩語(yǔ)就是最古老的天氣預(yù)報(bào)。在鄉(xiāng)下生活了二十余載,我從未想到這自然的天籟曾引起過(guò)墨客騷人們的興趣。
近日從周作人《關(guān)于禽言》一文中得知,這簡(jiǎn)單的鳩語(yǔ)還有諸多耐人尋味的典故。譬如,無(wú)悶居士所著《廣新聞》中就有關(guān)于“家家好”的文字:“客某游中峰,時(shí)值抗旱,望雨甚切,忽有小鳥(niǎo)數(shù)十,黑質(zhì)白章,啄如鳧,鳴曰家家叫化,音了如人語(yǔ)。山中人嘩曰,此旱怪也,竟奮槍捕殺數(shù)頭。天雨,明日此鳥(niǎo)仍鳴,聽(tīng)之變?yōu)榧壹液谩⒓壹液靡印!惫适鹿倘簧鷦?dòng),但我希望它不是真的。因?yàn)闊o(wú)論從形體毛色或聲韻節(jié)奏看,我認(rèn)為周作人把“家家好”認(rèn)作斑鳩的聲音是頗有道理的。斑鳩因鳴“家家叫化”而遭捕殺,不得不改鳴“家家好”,想來(lái)真叫人悲愴。周作人說(shuō),他那寧紹鄉(xiāng)間的斑鳩叫聲與“家家好”很是相似,“鳴聲有兩種,有雨前曰渴殺鶘,或略長(zhǎng)則曰渴殺者鶘,雨后曰掛掛紅燈。”這“渴殺者鶘”、“掛掛紅燈”的鳥(niǎo)語(yǔ),閉上眼睛一想真是很詩(shī)意,只可惜它在雨前雨后的叫法不同,又讓人聯(lián)想起“鳩逐婦”的傳說(shuō)。宋時(shí)陸佃在《埠雅》中說(shuō),此鳥(niǎo)“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yǔ)曰‘天將雨。鳩逐歸也”。這里說(shuō)的是自私的雄鳩,天陰將雨時(shí),為免淋漓之苦,便鳴叫著將雌鳩趕出巢去,全不管她在外面冒著多大的風(fēng)險(xiǎn);而當(dāng)天氣晴朗時(shí)又將她喚回來(lái),以滿足個(gè)人的歡愉。歐陽(yáng)修在《鳴鳩》詩(shī)中將雄鳩無(wú)情而輕浮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鳩呼歸婦鳴且喜,婦不亟歸呼不已。”這樣想著,那“掛掛紅燈”的聲音不免讓人感到虛偽甚至惡心了。
“鳩逐婦”,真有其事嗎?近人陸廷燦在《南村隨筆》中持相反之說(shuō):“明秦人趙統(tǒng)伯辯鳩逐婦云,乃感天地之雨陽(yáng)而動(dòng)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斑鳩用夫婦相離來(lái)感動(dòng)天地,以求降雨滋潤(rùn)萬(wàn)物,這不能不是一種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善舉。
普通鳩語(yǔ)融納了種種人情與世態(tài),這是少年單純的我不曾想到也無(wú)法破譯的,那時(shí)我心中的鳩語(yǔ)不過(guò)是一種天氣預(yù)報(bào)而已。
鵑 啼
“哥哥……等我……”暮春時(shí)節(jié),山谷里可聞一種凄切而酷似人語(yǔ)的鳥(niǎo)聲。
“那是包谷鳥(niǎo)在叫呢!”母親說(shuō)包谷鳥(niǎo)是冤死的少年所化。山里人無(wú)不知曉這個(gè)故事:兩兄弟,一為前母所生,一為后母所生,兩個(gè)甚為和氣。但后母別有心腸,欲將老大驅(qū)逐出門。某日她將兩人喚至膝前,讓每人背一袋包谷種上山去播,囑咐兩人各種一塊地,待苞谷長(zhǎng)出后才能回家,先長(zhǎng)出的先回,不許相等。原來(lái)后母給老大的種子是煮熟了的,以為如此老大便永不得歸。誰(shuí)知途中老大見(jiàn)弟弟幼小,主動(dòng)相助,無(wú)意中將種子調(diào)換,于是老大包谷苗全部出土,老二一株未生。老二見(jiàn)老大欲回家去,焦急不安:“哥哥……等我……”老大怎不想等等弟弟,只是母命難違。老大獨(dú)個(gè)回家后,后母知事不妙,速去山上尋找老二,可是再也不能見(jiàn)到他了,只見(jiàn)地上剛拉的一堆虎糞旁有老二的衣物。后母與老大守著虎糞悲不欲生,頃刻間天陰風(fēng)起,虎糞化作一只鳥(niǎo)飛上高樹(shù),哀哀直叫:“哥哥……等我……”往后,每當(dāng)播種包谷之際,山里人便會(huì)聽(tīng)見(jiàn)這種鳥(niǎo)叫。
這顯然是一個(gè)勸善的故事,母親講時(shí)很是動(dòng)情,好像真有那事發(fā)生過(guò),所以我每次聽(tīng)到這“哥哥等我”的聲音,心里就有一種悲涼的感覺(jué),仿佛人世間許多殘酷事實(shí)就在眼前。
啃過(guò)許多書后,我才知道家鄉(xiāng)所說(shuō)的“包谷鳥(niǎo)”是個(gè)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那鳥(niǎo)的學(xué)名叫杜鵑,它還有眾多有趣的別名,如杜宇、子規(guī)、子歸、思?xì)w、布谷、勃谷、撥谷、周燕等等,這些名字大都出自墨客騷人之口,都很雅氣。杜鵑又有好些種類,古人所說(shuō)的杜鵑專指四聲杜鵑,也就是農(nóng)人們所說(shuō)的包谷鳥(niǎo)。此鳥(niǎo)形象并不美,灰不溜秋,大口嘴扁,且有一種霸道的生活習(xí)慣——它自己不筑巢,而產(chǎn)卵于別的鳥(niǎo)巢中,由別的鳥(niǎo)來(lái)?yè)?dān)負(fù)它們孵育后代的任務(wù),之后這巢就被它長(zhǎng)期霸占……梁實(shí)秋先生在《鳥(niǎo)》一文中也描述過(guò)杜鵑的這種品性,他說(shuō)當(dāng)他這樣給朋友描述時(shí),朋友“對(duì)于這豪橫無(wú)情的鳥(niǎo),再也不能幻出什么詩(shī)意來(lái)”。這是可信的,但我覺(jué)得它的叫聲倒很獨(dú)特,四音一節(jié),似含人間情感,令人生出許多的聯(lián)想,于是就有人破譯它的“語(yǔ)言”了,古往今來(lái),人們所認(rèn)可的只是那句“不如歸去”,其來(lái)歷基本上是《蜀王本紀(jì)》、《十三州志》、《華陽(yáng)國(guó)志》、《成都記》、《環(huán)宇記》等書上的一些記載。《蜀王本紀(jì)》云:“杜宇為望帝,淫其臣鰲靈妻,乃禪位亡去。時(shí)子鵑鳴,故蜀人見(jiàn)鵑鳴而思望帝。”又因杜鵑啼聲凄惻,常常徹夜,而喙部又有紅斑,故“子規(guī)啼血”、“血漬草木”的說(shuō)法便深入人心,人們認(rèn)為杜鵑一直要啼叫到嘴巴流血為止,并把它的聲音擬為“不如歸去”。又說(shuō),杜鵑花其色殷紅,即為杜鵑啼血漬成,所謂“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鵑開(kāi)”便是。自漢以下,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范仲俺、梅堯臣、楊萬(wàn)里等許多文人都根據(jù)杜宇的傳說(shuō),或?qū)Χ霹N寄于深切同情,或?qū)⑵渥鳛椤笆窕辍薄ⅰ暗刍辍奔右愿柙仯袀诖耍允惆l(fā)人生悲情。
眾多文人為杜鵑啼血和那聲聲“不如歸去”動(dòng)情,想來(lái)甚是可笑。在我看來(lái),杜宇雖自立為王號(hào)稱望帝,但他與宰相稚氣私通,不得已讓位于宰相,造成了自己出奔并隱居山中的境遇,從帝王角度看,這也算得上一場(chǎng)悲劇了,但在平民百姓眼中恐怕只是一個(gè)偷情悲劇而已。這種杜鵑形象恐怕還是文人們糾結(jié)于“愛(ài)江山還是愛(ài)美人”的是非判斷,糾結(jié)于選擇象征權(quán)勢(shì)與榮華富貴的官位名位還是選擇真實(shí)的人情人性的表現(xiàn)。這種假托于“帝魂”而實(shí)為文人心靈深處痛苦掙扎的哀怨之聲,因與普通百姓生活相距甚遠(yuǎn)而不能深入他們的心靈,唯有文人自己知曉。幼時(shí)的我就不曾知道杜鵑還是什么“帝魂”所化的怨鳥(niǎo),只知鄉(xiāng)間凄慘叫著“哥哥等我”的聲音是一種真真切切的人間哀鳴。
鸮 哭
鸮,雅稱鵂鹠,俗稱貓頭鷹。我興趣俗,故喜喚貓頭鷹,而不喜喚鵂鹠之名。單看它的腦袋和眼睛,你真會(huì)把它當(dāng)作一只貓的,但它的翅膀及尾巴又與山鷹難辨難分。貓頭鷹還有一個(gè)古怪的特征:白日視覺(jué)不敏,夜間卻明察秋毫,連跳蚤頭虱都能抓到。
“貓頭鷹叫,必將死人”。山里人認(rèn)為它叫的時(shí)候是在喊“快哭,快哭”,或“挖窟,挖窟”。居在鄉(xiāng)間時(shí),每聞此鳥(niǎo)鳴叫我的心里便發(fā)怵,唯恐有災(zāi)難降臨自己或鄉(xiāng)鄰頭上,村人亡故,會(huì)立刻想到此前某日于某山頭聽(tīng)見(jiàn)過(guò)貓頭鷹的聲音。有時(shí)尚未及往這方面去想,已有人先道了個(gè)明白。
把貓頭鷹的語(yǔ)言摹擬得如此恐怖,并非鄉(xiāng)人獨(dú)創(chuàng),周作人在《關(guān)于禽言》中說(shuō),“《越諺》所舉十條除鳩燕外,唯姑惡鳥(niǎo)之如惡、貓頭鷹之掘洼系常聞的禽言。”國(guó)外亦有許多相似說(shuō)法,譬如英國(guó)著名戲劇家莎士比亞在《愛(ài)的徒勞》一劇中,把它擬為“哆喂——哆呵!”日本矢野蜂人則擬為“噢、噢、噢、噢,天何生我呵!”并說(shuō)它“好像把人之將死的聲音永遠(yuǎn)固化了一樣。”對(duì)貓頭鷹語(yǔ)言的詮釋,緣何在不同國(guó)度竟有如此驚人的一致?我想這大概是因?yàn)槿祟惖囊粋€(gè)普遍弊習(xí),即把與自己聲音相近的生命當(dāng)作怪物,似乎自己有的“別人”就不該有。恐懼的語(yǔ)言必出于恐懼的心靈,按照人類的經(jīng)驗(yàn)來(lái)判斷鳥(niǎo)類,貓頭鷹如何不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兇鳥(niǎo)呢?古人認(rèn)為它是難產(chǎn)死去的嬰兒所化,“好食人爪甲”,“好與嬰兒作祟”。民間許多地方都有不許把嬰孩的衣服放在檐外過(guò)夜的習(xí)俗,唯恐被這怪物抓去了“魂氣”,或被它滴上血而成為日后“收魂”的標(biāo)記。兒時(shí),我們幾個(gè)弟妹每至傍晚,祖母或母親便催:“把你們曬在外面的衣服收進(jìn)屋來(lái)。”
貓頭鷹既已成為兇鳥(niǎo),它還能與人共天么?《太平廣記》云:“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niǎo),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灸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這里記載的都是貓頭鷹遭殺戳的事實(shí)。其實(shí)貓頭鷹不屬兇鳥(niǎo)之列,現(xiàn)代生物學(xué)家證實(shí)它是一種益鳥(niǎo),作為山鼠的天敵,一只貓頭鷹每年通過(guò)捕鼠可減少1000公斤糧食的損失。貓頭鷹之“兇”,無(wú)非是它的聲音難聽(tīng)了點(diǎn),可正是難聽(tīng)的聲音招惹了捕殺之禍,這與斑鳩當(dāng)初的悲劇有些類似,斑鳩因鳴“家家叫化”而遭捕殺,改鳴“家家好”方得安生,可與斑鳩相比,貓頭鷹顯得有些頑固,它始終不愿意改變自己的聲音。
望著樹(shù)杈上的貓頭鷹,我想它大概也是一種既聰明又很有個(gè)性的生命,它或許還懂得,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叫,才能叫得真實(shí)自然,才能保持一種生命的本色,任何的誤解和偏見(jiàn)都將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而消失。
【責(zé)任編輯 柳小霞】
【作者簡(jiǎn)介】馬小寧,某軍工企業(yè)政宣干部,系中國(guó)散文學(xué)會(huì)會(huì)員、多家報(bào)紙?zhí)丶s通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