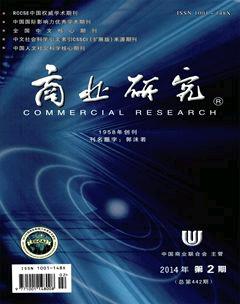要素偏向的技術進步、替代彈性與勞動收入份額
李博文 孫樹強
摘要:本文運用替代彈性不變的生產函數,分析了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是資本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負向影響;資本增進型技術是勞動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正向影響,但1995年以來資本增進型技術是逐漸下降的。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共同作用產生了我們觀察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動趨勢。在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所產生的影響中,勞動增進型技術解釋了其中的64%,占主導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的下降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作用次之。
關鍵詞:勞動收入份額;替代彈性;要素偏向型技術
中圖分類號:F22233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逐漸降低成為學術界和社會上討論的比較多的話題。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會對經濟和人們的生活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意味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回報產生變化,這樣就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對社會經濟狀況產生一系列影響,如消費和儲蓄等。例如,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認為要素間收入差距會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重要影響[1];又如Kuijis(2006)認為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對消費率的降低產生了重要影響。圖1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1978-2005)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收入份額比較穩定,大約在60%左右。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之間,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約11個百分點②。勞動收入份額的逐漸降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勞動收入份額的基本穩定不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特征事實(Stylized Facts)。但90年代以來的一些國家的實際數據表明,這個特征事實在中期和短期來看并不成立。Blanchard (1997) 計算歐洲一些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時發現,該值至少在中期內不是一個常數,他發現自20世紀80 年代開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四個國家的資本收入份額呈現增長趨勢[2]。Bentolila和Saint-Paul (2003)計算了13個OECD 國家從1970 年到1993 年的勞動收入份額,發現除了英國比較穩定外,各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情況各不相同[3]。
圖1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①
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原因,已經有很多文獻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從結構轉型和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結構轉型帶來的影響比較大;在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中,工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貢獻最大[4]。黃先海和徐圣(2009)利用要素偏向技術進步的思想,分析了我國制造業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認為勞動節約型技術是兩個部門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5]。羅長遠和張軍(2009)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以正相關性同時變化,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6]。李稻葵等(2009)從宏觀角度考察了勞動收入占比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跨國面板數據發現二者之間存在“U”型關系,認為中國還處在這一曲線的下行區間上[7]。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由于符合“Kaldor事實”中的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來看穩定不變這一事實,使得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因為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要素的收入份額就是其產出彈性。另外,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替代彈性為1也是C-D生產函數的重要性質。但是C-D生產函數也存在重要缺陷:一是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1被很多經驗研究所否定,例如Klump等(2007)利用美國1953-1998年數據估計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發現明顯小于1③[8];二是C-D函數不能解釋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三是C-D生產函數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影響要素之間的邊際產出比例的變化,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是中性的(Neutral),但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Klump等(2008)度量了歐元區1970-2005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技術進步總體上偏向資本[9];Sato和Morita(2009)研究了美國和日本的1960-2004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這兩個國家的技術進步也是總體上偏向資本的[10]。國內對于技術偏向和資本勞動替代性的研究文獻還比較少,一個例外是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的工作,他們利用1978-2005年資本、勞動以及要素收入份額的數據,經過研究得出,我國的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明顯小于1[11]。這表明,從總體上看我國資本和勞動之間是互補的關系。
Acemoglu(2003)證明,在長期來看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是唯一的技術進步方式,但是在短期來看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同時存在。如果勞動和資本的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勞動收入份額會上升。但資本數量的增加會引起技術的變化,如果技術是偏向資本的,那么資本收入份額會上升。勞動收入份額如何變化取決于人均資本水平和技術的要素偏向性[12]。本文根據這一思想,利用替代彈性不變(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生產函數,從總體上來分析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在CES生產函數條件下,同時存在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如果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大于1,那么資本和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也是資本和勞動偏向的;但如果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就是資本偏向的。勞動收入份額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水平。如果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和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使得勞動收入份額降低。
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了我國CES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為0736,也就是說在生產中,資本和勞動是互補的。同時,他們給出了1978-2005年的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水平,顯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較快,但資本增進型技術卻從1995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所以,從1995年以來,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都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只有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利用反事實分析方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我們得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起了主要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水平下降的作用次之,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擬合現實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模型顯示,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從5709%下降到467%,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實際數據顯示勞動收入份額降低了108個百分點,從5909%下降到4821%。如果把人均資本水平固定在1995年水平,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取現實數據,那么勞動收入份額會降低約21個百分點,所以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共同負向作用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21個百分點。在這下降的21個百分點中,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了64%。
本研究接下來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二部分給出基本模型并解釋勞動收入份額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根據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的數據進行反事實分析,分析資本增進型和勞動增進行技術進步以及人均資本的增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給出本文的結論。
二、模型
假設經濟中的生產函數為替代彈性不變的形式(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摘要:本文運用替代彈性不變的生產函數,分析了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是資本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負向影響;資本增進型技術是勞動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正向影響,但1995年以來資本增進型技術是逐漸下降的。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共同作用產生了我們觀察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動趨勢。在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所產生的影響中,勞動增進型技術解釋了其中的64%,占主導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的下降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作用次之。
關鍵詞:勞動收入份額;替代彈性;要素偏向型技術
中圖分類號:F22233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逐漸降低成為學術界和社會上討論的比較多的話題。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會對經濟和人們的生活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意味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回報產生變化,這樣就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對社會經濟狀況產生一系列影響,如消費和儲蓄等。例如,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認為要素間收入差距會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重要影響[1];又如Kuijis(2006)認為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對消費率的降低產生了重要影響。圖1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1978-2005)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收入份額比較穩定,大約在60%左右。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之間,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約11個百分點②。勞動收入份額的逐漸降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勞動收入份額的基本穩定不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特征事實(Stylized Facts)。但90年代以來的一些國家的實際數據表明,這個特征事實在中期和短期來看并不成立。Blanchard (1997) 計算歐洲一些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時發現,該值至少在中期內不是一個常數,他發現自20世紀80 年代開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四個國家的資本收入份額呈現增長趨勢[2]。Bentolila和Saint-Paul (2003)計算了13個OECD 國家從1970 年到1993 年的勞動收入份額,發現除了英國比較穩定外,各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情況各不相同[3]。
圖1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①
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原因,已經有很多文獻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從結構轉型和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結構轉型帶來的影響比較大;在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中,工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貢獻最大[4]。黃先海和徐圣(2009)利用要素偏向技術進步的思想,分析了我國制造業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認為勞動節約型技術是兩個部門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5]。羅長遠和張軍(2009)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以正相關性同時變化,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6]。李稻葵等(2009)從宏觀角度考察了勞動收入占比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跨國面板數據發現二者之間存在“U”型關系,認為中國還處在這一曲線的下行區間上[7]。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由于符合“Kaldor事實”中的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來看穩定不變這一事實,使得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因為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要素的收入份額就是其產出彈性。另外,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替代彈性為1也是C-D生產函數的重要性質。但是C-D生產函數也存在重要缺陷:一是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1被很多經驗研究所否定,例如Klump等(2007)利用美國1953-1998年數據估計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發現明顯小于1③[8];二是C-D函數不能解釋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三是C-D生產函數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影響要素之間的邊際產出比例的變化,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是中性的(Neutral),但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Klump等(2008)度量了歐元區1970-2005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技術進步總體上偏向資本[9];Sato和Morita(2009)研究了美國和日本的1960-2004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這兩個國家的技術進步也是總體上偏向資本的[10]。國內對于技術偏向和資本勞動替代性的研究文獻還比較少,一個例外是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的工作,他們利用1978-2005年資本、勞動以及要素收入份額的數據,經過研究得出,我國的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明顯小于1[11]。這表明,從總體上看我國資本和勞動之間是互補的關系。
Acemoglu(2003)證明,在長期來看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是唯一的技術進步方式,但是在短期來看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同時存在。如果勞動和資本的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勞動收入份額會上升。但資本數量的增加會引起技術的變化,如果技術是偏向資本的,那么資本收入份額會上升。勞動收入份額如何變化取決于人均資本水平和技術的要素偏向性[12]。本文根據這一思想,利用替代彈性不變(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生產函數,從總體上來分析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在CES生產函數條件下,同時存在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如果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大于1,那么資本和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也是資本和勞動偏向的;但如果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就是資本偏向的。勞動收入份額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水平。如果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和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使得勞動收入份額降低。
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了我國CES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為0736,也就是說在生產中,資本和勞動是互補的。同時,他們給出了1978-2005年的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水平,顯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較快,但資本增進型技術卻從1995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所以,從1995年以來,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都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只有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利用反事實分析方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我們得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起了主要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水平下降的作用次之,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擬合現實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模型顯示,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從5709%下降到467%,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實際數據顯示勞動收入份額降低了108個百分點,從5909%下降到4821%。如果把人均資本水平固定在1995年水平,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取現實數據,那么勞動收入份額會降低約21個百分點,所以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共同負向作用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21個百分點。在這下降的21個百分點中,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了64%。
本研究接下來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二部分給出基本模型并解釋勞動收入份額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根據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的數據進行反事實分析,分析資本增進型和勞動增進行技術進步以及人均資本的增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給出本文的結論。
二、模型
假設經濟中的生產函數為替代彈性不變的形式(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摘要:本文運用替代彈性不變的生產函數,分析了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是資本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負向影響;資本增進型技術是勞動偏向的,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正向影響,但1995年以來資本增進型技術是逐漸下降的。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共同作用產生了我們觀察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動趨勢。在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所產生的影響中,勞動增進型技術解釋了其中的64%,占主導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的下降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作用次之。
關鍵詞:勞動收入份額;替代彈性;要素偏向型技術
中圖分類號:F22233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逐漸降低成為學術界和社會上討論的比較多的話題。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會對經濟和人們的生活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意味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回報產生變化,這樣就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對社會經濟狀況產生一系列影響,如消費和儲蓄等。例如,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認為要素間收入差距會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重要影響[1];又如Kuijis(2006)認為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對消費率的降低產生了重要影響。圖1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1978-2005)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收入份額比較穩定,大約在60%左右。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之間,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約11個百分點②。勞動收入份額的逐漸降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勞動收入份額的基本穩定不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特征事實(Stylized Facts)。但90年代以來的一些國家的實際數據表明,這個特征事實在中期和短期來看并不成立。Blanchard (1997) 計算歐洲一些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時發現,該值至少在中期內不是一個常數,他發現自20世紀80 年代開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四個國家的資本收入份額呈現增長趨勢[2]。Bentolila和Saint-Paul (2003)計算了13個OECD 國家從1970 年到1993 年的勞動收入份額,發現除了英國比較穩定外,各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情況各不相同[3]。
圖1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①
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原因,已經有很多文獻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從結構轉型和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結構轉型帶來的影響比較大;在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中,工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貢獻最大[4]。黃先海和徐圣(2009)利用要素偏向技術進步的思想,分析了我國制造業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趨勢,認為勞動節約型技術是兩個部門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5]。羅長遠和張軍(2009)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以正相關性同時變化,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6]。李稻葵等(2009)從宏觀角度考察了勞動收入占比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跨國面板數據發現二者之間存在“U”型關系,認為中國還處在這一曲線的下行區間上[7]。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由于符合“Kaldor事實”中的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來看穩定不變這一事實,使得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因為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要素的收入份額就是其產出彈性。另外,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替代彈性為1也是C-D生產函數的重要性質。但是C-D生產函數也存在重要缺陷:一是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1被很多經驗研究所否定,例如Klump等(2007)利用美國1953-1998年數據估計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發現明顯小于1③[8];二是C-D函數不能解釋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三是C-D生產函數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影響要素之間的邊際產出比例的變化,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是中性的(Neutral),但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Klump等(2008)度量了歐元區1970-2005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技術進步總體上偏向資本[9];Sato和Morita(2009)研究了美國和日本的1960-2004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發現這兩個國家的技術進步也是總體上偏向資本的[10]。國內對于技術偏向和資本勞動替代性的研究文獻還比較少,一個例外是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的工作,他們利用1978-2005年資本、勞動以及要素收入份額的數據,經過研究得出,我國的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明顯小于1[11]。這表明,從總體上看我國資本和勞動之間是互補的關系。
Acemoglu(2003)證明,在長期來看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是唯一的技術進步方式,但是在短期來看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同時存在。如果勞動和資本的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勞動收入份額會上升。但資本數量的增加會引起技術的變化,如果技術是偏向資本的,那么資本收入份額會上升。勞動收入份額如何變化取決于人均資本水平和技術的要素偏向性[12]。本文根據這一思想,利用替代彈性不變(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生產函數,從總體上來分析我國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在CES生產函數條件下,同時存在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如果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大于1,那么資本和勞動增進性技術進步也是資本和勞動偏向的;但如果替代彈性小于1,勞動增進型技術就是資本偏向的。勞動收入份額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以及人均資本水平。如果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那么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和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使得勞動收入份額降低。
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了我國CES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為0736,也就是說在生產中,資本和勞動是互補的。同時,他們給出了1978-2005年的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水平,顯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較快,但資本增進型技術卻從1995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所以,從1995年以來,勞動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都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只有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利用反事實分析方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我們得出: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對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起了主要作用,資本增進型技術水平下降的作用次之,人均資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擬合現實的勞動收入份額數據。模型顯示,1995-2005年勞動收入份額從5709%下降到467%,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實際數據顯示勞動收入份額降低了108個百分點,從5909%下降到4821%。如果把人均資本水平固定在1995年水平,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取現實數據,那么勞動收入份額會降低約21個百分點,所以資本和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共同負向作用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21個百分點。在這下降的21個百分點中,勞動增進型技術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了64%。
本研究接下來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二部分給出基本模型并解釋勞動收入份額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根據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估計的數據進行反事實分析,分析資本增進型和勞動增進行技術進步以及人均資本的增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給出本文的結論。
二、模型
假設經濟中的生產函數為替代彈性不變的形式(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