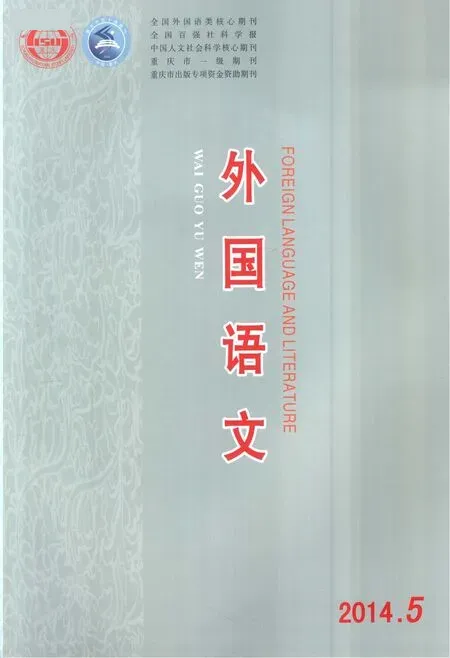凡塵洗盡即梵澄——翻譯大家徐梵澄的翻譯與思考
陳歷明
(華僑大學(xué) 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福建泉州 362021)
1.概述
梵澄先生1909年10月26日生于湖南長(zhǎng)沙,原名琥,譜名詩(shī)荃,字季海,梵澄為其筆名,晚年始用徐梵澄為通名。他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著名的精神哲學(xué)家、翻譯家和印度學(xué)專(zhuān)家,同時(shí)也是一位詩(shī)人、書(shū)畫(huà)家、藝術(shù)鑒賞家和評(píng)論家。徐先生幼承嚴(yán)格的家塾教育,先后就學(xué)于長(zhǎng)沙雅禮中學(xué)、武漢中山大學(xué)歷史社會(huì)學(xué)系(1926年)以及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西洋文學(xué)系(1928年),其間因機(jī)緣游于魯迅門(mén)下,受誨頗深。1929年至1932年留學(xué)德國(guó)柏林大學(xué)與海德堡大學(xué),攻讀藝術(shù)史專(zhuān)業(yè),研究美術(shù)史,練習(xí)木刻藝術(shù),曾多次代魯迅購(gòu)買(mǎi)文學(xué)和版畫(huà)作品,并創(chuàng)作一幅中年魯迅像,被譽(yù)為“中國(guó)新興版畫(huà)創(chuàng)作第一人”。1932年8月,因先父病重回國(guó)盡孝,后寄寓上海。隨后在魯迅的提議與幫助下最早系統(tǒng)地翻譯并出版尼采的著作,成為系統(tǒng)翻譯并研究尼采的第一人。抗戰(zhàn)期間,他先任教于中央藝專(zhuān),后任中央圖書(shū)館編纂,兼任中央大學(xué)教授。自1945年受?chē)?guó)民政府教育部委派,作為中印文化交流使者,赴印度任泰戈?duì)枃?guó)際大學(xué)教授(5年),講授“歐陽(yáng)竟無(wú)佛學(xué)思想”等,同時(shí)研究古印度宗教哲學(xué),1950年入貝納尼斯習(xí)梵文,譯出印度教經(jīng)典《薄伽梵歌》等梵文典籍。次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羅頻多學(xué)院,任該學(xué)院國(guó)際教育中心研究院華文部主任(27年),潛心翻譯、著述、講學(xué),專(zhuān)治精神哲學(xué),重研法相唯識(shí)之學(xué),有宏富著譯問(wèn)世。及至1978年末取道香港,只身皓首歸國(guó),歷33年!其間有大量有關(guān)印度宗教哲學(xué)譯、著面世,因被海外譽(yù)為“現(xiàn)代玄奘”。歸國(guó)后經(jīng)任繼愈先生推薦,入中國(guó)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員,兼中國(guó)佛教協(xié)會(huì)特約研究員,中國(guó)魯迅研究會(huì)顧問(wèn)。其間又有極具分量的學(xué)術(shù)譯著面世,由此迎來(lái)自己學(xué)術(shù)生涯的第二次高峰。
徐先生精通8種古今語(yǔ)言,會(huì)通中國(guó)、印度、西方三大文化,嘗試以“精神哲學(xué)”為契點(diǎn)重新闡釋古典,形成了獨(dú)特的學(xué)術(shù)體系,其學(xué)術(shù)成就涵蓋甚廣,且卓然成家;但他甘于寂寞,卓爾不群,從不張揚(yáng),視名利如浮云,只是竟日為學(xué)不輟,筆耕不止,焚膏繼晷,抱定古代士人“為往圣繼絕學(xué)”的宗旨,不聲不響地做著“接續(xù)”精神傳統(tǒng)的探索,直至生命的終點(diǎn)。梵澄先生于2000年3月6日寂于北京,享年91歲。
著名學(xué)者劉小楓(2002:51)認(rèn)為,梵澄先生的學(xué)術(shù)成就多端,大要有四:翻譯西方現(xiàn)代大哲尼采(完整的譯作有四部),翻譯印度古今哲學(xué)要籍,用英文譯述中國(guó)古代學(xué)術(shù),以及詮釋古學(xué)經(jīng)典的撰述。翻閱《徐梵澄文集》共十六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年出版)可知,其所言不虛,其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gè)方面:
其一,系統(tǒng)地翻譯出版尼采著作,譯成《尼采自傳》(1935)、《蘇魯支語(yǔ)錄》(1935/1992)、《朝霞》(1935)、《快樂(lè)的知識(shí)》(1939)等。
其二,系統(tǒng)地翻譯印度吠陀—吠檀多哲學(xué)之古今經(jīng)典,如《五十奧義書(shū)》(1984)、《薄伽梵歌》(1957)、《行云使者》(1957),阿羅頻多之《神圣人生論》(1984)、《薄伽梵歌論》(1957/2003)、《社會(huì)進(jìn)化論》(1960)、《瑜伽論》(1959/2005)、《佛教述略》(1939)、《神母道論》(1972)、《安慧<三十唯識(shí)>疏釋》(1987)等。
其三,用英文譯述中國(guó)古代學(xué)術(shù)精華,介紹給印度和西方,有《小學(xué)菁華》(1976)、《孔學(xué)古微》(1960)、《周子通書(shū)》(1978)、《肇論》(1987)、《唯識(shí)菁華》(1990)、《易大傳——新儒家入門(mén)》(1995)等。
其四,以精神哲學(xué)重釋中國(guó)古典思想,如《玄理參同》(1973)、《老子臆解》、《陸王學(xué)述》、《周天集》(1991)等。
圍繞南向通道沿線(xiàn)地區(qū)、珠江—西江地區(qū)、桂廣高鐵沿線(xiàn)等地區(qū)尋找面向越南、老撾及東南亞的往返貨源,大力發(fā)展過(guò)境貿(mào)易。在欽州、憑祥綜合保稅區(qū)培育一批具有東南亞、中西亞客源的離岸貿(mào)易公司,發(fā)展面向這些地區(qū)的轉(zhuǎn)口貿(mào)易、離岸貿(mào)易、國(guó)際中轉(zhuǎn)集拼與其他配套增值服務(wù),為欽州港增添補(bǔ)給貨源,逐步將現(xiàn)有的喂給港發(fā)展為銜接“一帶”與“一路”沿線(xiàn)地區(qū)的區(qū)域性母港。
雖其學(xué)術(shù)撰著本已不菲,但其翻譯成就實(shí)在了得,其刊行的主要譯著就有32部(含譯述,尚不包括佚失和待出版的另6部譯著)。
概言之,梵澄先生輝煌的翻譯事業(yè)在幾個(gè)領(lǐng)域可謂開(kāi)風(fēng)氣之先。他是我國(guó)系統(tǒng)翻譯尼采著作的第一人,也是我國(guó)最早的尼采研究專(zhuān)家。特別是他首次全譯的《蘇魯支語(yǔ)錄》(現(xiàn)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shuō)》),商務(wù)印書(shū)館仍然在再版,面世七十多年來(lái)還是無(wú)人超越。鄭振鐸曾如是贊許道:“這部譯文是梵澄先生從德文本譯出的,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fēng)是那樣的相同,我們似不必再多加贊美”(鄭振鐸,1936/1992:2)。此外,我國(guó)著名的尼采研究專(zhuān)家、尼采著作的翻譯者周?chē)?guó)平先生的話(huà)也可佐證:“梵澄、高寒二位先生曾譯尼采作品多種,盡管在譯文風(fēng)格上帶有時(shí)代特點(diǎn),文言氣較重,但是在譯文的準(zhǔn)確和傳神方面,我一向是佩服的”(周?chē)?guó)平,1987)。
他更是把印度古代精神哲學(xué)典籍《奧義書(shū)》系統(tǒng)譯介到中國(guó)的第一人。他深知中國(guó)文化的印度淵源,曾如此諄諄告誡后學(xué):“印度是個(gè)大國(guó),中國(guó)也是一個(gè)大國(guó),印度可以不懂中國(guó),中國(guó)不能不懂印度”(詹志芳,2000:78-80)。早在南印度任教時(shí),他就遍識(shí)《奧義書(shū)》百余種,擇其要者50種,陸續(xù)譯成中文,終于1984年由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1995年修訂版,計(jì)1133頁(yè))。本籍在歐洲早有多譯本問(wèn)世,對(duì)歐洲的宗教、哲學(xué)影響甚巨。由此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xiāo),印度因此重新認(rèn)識(shí)自己的這一寶典,并為“詩(shī)圣”泰戈?duì)枴ⅰ罢苁ァ卑⒘_頻多等所借重。上世紀(jì)20年代的日本也不甘落后,不吝人力物力,譯出全集:“東方則日本嘗聚梵文學(xué)者二十七人,譯成《奧義書(shū)全集》都百十六種,分為九卷。1922-1924東京出版”(徐梵澄,1995:12)。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著實(shí)不可估量。對(duì)此,我國(guó)先賢亦了然于胸,早在20世紀(jì)初,章太炎就發(fā)愿譯介《奧義書(shū)》,并邀魯迅、周作人同學(xué)梵文,然因?qū)W習(xí)未竟而擱淺(孫波,2000:64)。但梵澄先生幾十年后竟然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前輩的未竟夙愿!
特別值得一提還有另一本當(dāng)代印度哲學(xué)巨著《神圣人生論》的翻譯。譯者自陳,“全書(shū)譯成于1952年。初校于1956年,二校于1964年,三校于1979年,數(shù)月后全書(shū)細(xì)較重抄,至1981年七月初始畢。全書(shū)約85萬(wàn)字”(徐梵澄,2006b:133)。最終于1984年商務(wù)印書(shū)館出版。本書(shū)是當(dāng)代印度著名哲學(xué)家阿羅頻多的代表作,博采眾家之長(zhǎng)而卓然成思,“內(nèi)容集印度韋檀多(Vedanta)之大成,所據(jù)皆《黎俱韋陀》及諸《奧義書(shū)》。數(shù)千年精神哲學(xué)之菁華皆攝。以‘超心思’為主旨,以人生轉(zhuǎn)化為極歸。于商羯羅之幻有論及大乘空宗破斥彌多,其視法相唯識(shí)等蓋蔑如也。于柏拉圖之哲學(xué)多所采納,于達(dá)爾文之進(jìn)化論則服之無(wú)斁。立論在思辨哲學(xué)以上,于因明不廢而已。雖時(shí)言上帝,然與西方神學(xué)相遠(yuǎn)。其宇宙觀(guān)往往與我國(guó)大易之旨相合。稽于復(fù)性及變化氣質(zhì)之義,轉(zhuǎn)與宋五子及陸、王為近”(徐梵澄,2006b:134)。筆者谫陋,無(wú)力窺其宏旨,好在有譯者上述精到的比勘會(huì)通,足為研究者醒目。
對(duì)梵澄先生的這兩本煌煌譯著,學(xué)界識(shí)貨的和暫時(shí)不太識(shí)貨的都有宏論。其深厚的學(xué)養(yǎng)和獻(xiàn)身學(xué)術(shù)的堅(jiān)韌意志贏得了學(xué)界由衷的敬佩:著名印度學(xué)家金克木指出,《五十奧義書(shū)》和現(xiàn)代印度最有影響的宗教哲學(xué)家阿羅頻多的《神圣人生論》兩部巨著譯本,“兩書(shū)一古一今,相隔兩千多年,但是一脈相通”;“現(xiàn)在徐梵澄同志用漢語(yǔ)古文體從印度古雅語(yǔ)梵文譯出《奧義書(shū)》,又不用佛經(jīng)舊體,每篇還加《引言》和注,真是不容易。沒(méi)有幾十年的功力,沒(méi)有對(duì)中國(guó)、德國(guó)、印度的古典語(yǔ)言和哲學(xué)切實(shí)鉆研體會(huì),那是辦不到的。當(dāng)年我不過(guò)是有點(diǎn)直覺(jué)感受,等到略微在大門(mén)口張望了一下之后,就以為理想的翻譯,佛教經(jīng)論似的翻譯,現(xiàn)在不可能,至少是我辦不到。稍稍嘗試一下,也自認(rèn)翻譯失敗。因此我對(duì)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金克木,1987:57-62)。他譯的這些印度哲學(xué)典籍,詞義古奧,取精用弘,文采斐然,多為學(xué)者所稱(chēng)道。著名學(xué)者劉小楓則自承讀過(guò)《神圣人生論》,“當(dāng)然沒(méi)有讀明白,《五十奧義書(shū)》則不敢開(kāi)卷”(劉小楓,2002:52)。除了某種謙虛,恐怕也是當(dāng)時(shí)的實(shí)情。
2.翻譯思想
徐先生不僅在翻譯實(shí)踐上功勛卓著,而且翻譯思想也是獨(dú)樹(shù)一幟,盡管他并沒(méi)有系統(tǒng)的翻譯理論專(zhuān)著。他曾自謙說(shuō),“我自己的文字不多,主要都在序跋里了。”(孫波,2001:2)正如他的哲學(xué)思想一樣,其翻譯思考也主要體現(xiàn)在其譯著的序跋中,而且主要是結(jié)合自己的翻譯實(shí)踐,從語(yǔ)文學(xué)和文化學(xué)幾個(gè)方面來(lái)進(jìn)行的。
概而言之,他創(chuàng)造性地借鑒歷史上已有成功先例,針對(duì)不同的時(shí)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文體,量體裁衣,決不定于一尊,而是分別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思考:
其一曰“譯述”與直譯。對(duì)于像《奧義書(shū)》、《薄伽梵歌》等古代印度宗教哲學(xué)典籍,它們屬于鴻篇巨制,然成書(shū)時(shí)間長(zhǎng),多個(gè)時(shí)代多有增刪,且作者不一而足,內(nèi)容較為蕪雜,且無(wú)定本,因而很有必要進(jìn)行多種版本的比勘會(huì)通、削繁就簡(jiǎn),以去蕪取精,前后一貫,自然不便照本宣科一一迻譯;但對(duì)于其宏富的要義,則堅(jiān)持直譯,以去訛求真。先生因說(shuō):“此書(shū)中文譯本,成于1953年。原意在‘述’而非‘譯’。于是有合并之篇,有新編之節(jié),有移置之句,有潤(rùn)色之文。其存而未出者,凡六章。當(dāng)時(shí)以為此諸章內(nèi)容,與吾華現(xiàn)代思想相距過(guò)遠(yuǎn),出之適成捍格,反累高明。故留之以俟來(lái)哲。姑求出其邃意弘旨,無(wú)損無(wú)訛。自第十三章之后,漸次逐字直譯,直至全書(shū)之末。然非純?nèi)g本,故簽署曰‘述’”(徐梵澄,2003:1)。他在《奧義書(shū)》“譯者序”中精到地詳述了該書(shū)的要旨,及其在印度哲學(xué)史、宗教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對(duì)世界的影響:“獨(dú)此《奧義》諸《書(shū)》,義理弘富,屬于內(nèi)學(xué),為后世諸宗各派之祖,乃有可供思考參同而契會(huì)者,信宇宙人生之真理有在于是。而啟此一樞紐,則上窺下視,莫不通暢條達(dá),而印度文化之綱領(lǐng)得焉。此所謂立乎其大者也。”(徐梵澄,1995:4)
鑒于中印語(yǔ)言思維迥異,字、詞、句、篇必須適當(dāng)調(diào)整;而梵文典籍字少義豐,訓(xùn)釋難定,先生認(rèn)為現(xiàn)代漢語(yǔ)難當(dāng)此任,因而必須出之以典雅見(jiàn)長(zhǎng)的古文。這畢竟不是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而是專(zhuān)業(yè)性很強(qiáng)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自然毋須看重市場(chǎng):“竊謂此種著作,五印奉為寶典,吾國(guó)久已宜知。文化價(jià)值難量,象寄菁英稍見(jiàn),其可以隸之《雜藏》,博我書(shū)林。原其文辭簡(jiǎn)古,時(shí)有晦澀,與后世經(jīng)典梵文不同。貝葉傳鈔,歷世不歇,訛多衍文,見(jiàn)嘗可見(jiàn)。且字少義豐,訓(xùn)釋靡定;舉凡文法,修辭,思想方式,在在與漢文相異,此處義庸或不渝,而精圓概難乎臻至也。顧吾國(guó)籀譯天竺古典,權(quán)輿適自西元,名相可因,知聞已夙,傳承有自,非如歐西近世始鑿混沌。既歷史負(fù)荷如此,自宜出以文言,使前后相望,流風(fēng)一貫,紹先昆而不匱,開(kāi)后學(xué)以無(wú)慚,初不必求售一時(shí),取重當(dāng)世。自惟較之內(nèi)典之詰屈聱牙者,尚遠(yuǎn)過(guò)明朗通暢。以其本非甚深?yuàn)W義,亦必不肯故為深?yuàn)W之辭也”(徐梵澄,1995:13)。
讓譯作從語(yǔ)言到風(fēng)格盡量切近原作是他的一貫堅(jiān)持。先生在譯作《尼采自傳》序中,將翻譯比之摹畫(huà),認(rèn)為“好的字畫(huà)是不能摹寫(xiě)的,無(wú)論怎樣精審,傳神,最高度下真跡一等,何況以一種絕不相侔的文字,翻譯一異國(guó)偉大底哲人的思想,內(nèi)心,和生活的記錄?原著文辭之滂沛,意態(tài)之豐饒,往往使譯者嘆息。然為求不負(fù)著者和讀者起見(jiàn),竭力保存原作的風(fēng)姿;所以句子每每倒裝,或冗長(zhǎng),或晦澀。又凡遇原文字句太激昂的地方,直達(dá)反有傷本意,則稍與曲折一點(diǎn),這是譯者自知的錯(cuò)過(guò)”(徐梵澄,2006a:5)。盡力保持原作的句式,以盡力再現(xiàn)原作的風(fēng)格。這使人聯(lián)想到他的老師魯迅先生的翻譯原則:“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dāng)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fēng)姿”(魯迅,2005:364-5)。但并不偏廢接受者,在直譯有傷原意之處,則稍作曲折變通,以方便目標(biāo)讀者。直譯是他堅(jiān)持的原則,因?yàn)榉g的主要目的就是輸入外國(guó)的學(xué)術(shù)、文化,只有通過(guò)直譯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表征為文辭、義理之風(fēng)姿:“抑此圣典(即《薄伽梵歌》),歌也。歌必可唱詠諷誦,于華文以古詩(shī)體譯之也宜。抑此歌,圣典也。譯詞當(dāng)不失其莊敬,出義須還之于梵文也無(wú)失。敬不失禮,而文義可復(fù),庶幾近之矣”(徐梵澄,2006e:189)。
其二曰“精、妙、明、圓”。梵澄先生針對(duì)不同的文本類(lèi)型、譯者趣旨、時(shí)代特征以及目標(biāo)讀者等因素,相應(yīng)依據(jù)不同的翻譯準(zhǔn)則,而非千篇一律,泥古不化。如果說(shuō)對(duì)于《奧義書(shū)》、《薄伽梵歌》等由于年代作者難定,特別是《奧義書(shū)》,“作者非一人,歷時(shí)非一世,書(shū)數(shù)亦不定。于今匯為總集者,或百零八書(shū),或百二十書(shū),要其自古所推重者,不過(guò)十余種”(徐梵澄,1995:7),各個(gè)年代因時(shí)有添加附會(huì),文本時(shí)有蕪雜重復(fù),或勾連失矩之處,加之篇幅所限等問(wèn)題,譯者因之不得不有所選擇有所整合,而有“譯”有“述”的話(huà)(但對(duì)其中選定的精義部分,則是執(zhí)“信”而無(wú)鶩),那么對(duì)當(dāng)代哲學(xué)家的系統(tǒng)著述,譯者的翻譯原則與訴求就必須改弦更張,取“精”而舍“述”。
先生對(duì)嚴(yán)復(fù)的“信達(dá)雅”翻譯原則在翻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經(jīng)典著作中的功用有著同情之理解,對(duì)其歷史性又不乏辯證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見(jiàn)解。就印度當(dāng)代大哲阿羅頻多的《玄理參同》,梵澄先生指出,“這仍是義理之文,譯時(shí)自求其精密,美妙,明白,圓到。雖在另一文字里,意在于還他一個(gè)本來(lái)面目‘信,達(dá),雅’三字,昔嚴(yán)幾道樹(shù)為翻譯工作的指南。西學(xué)入華之初期,故應(yīng)懸此為圭臬。近世觀(guān)感已頗改變了:因?yàn)椴弧拧瘎t不成其為翻譯,是偽制;‘達(dá)’則獨(dú)覺(jué)有間隔,距離;‘雅’則屬于辭氣,形式,而出自譯者,是外加,原作可能是‘雅’或‘不雅’。然則僅從本文著想,而出之能精、妙、明、圓,不算是苛求了”(徐梵澄,2001:169-70)。
梵澄先生在《玄理參同》(見(jiàn)《徐梵澄文集·一》此類(lèi)元典的翻譯中,還有一個(gè)現(xiàn)象非常值得關(guān)注,那就是在每一個(gè)段落后附上自己的闡釋。除了“精妙明圓”地迻譯原作外,譯者考慮到文本的深?yuàn)W義理,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思考,于正文后輔以“疏釋”,參稽印、中、西古今學(xué)理,或紹介、或縷析、或引申、或考會(huì),每每倍于原文,往往卓見(jiàn)迭出,不遜原文,兩兩相參,比勘會(huì)通而相得益彰。此種策略可謂傳承有自,昔嚴(yán)復(fù)在翻譯《天演論》等西學(xué)典籍時(shí),段落后大多附有“案語(yǔ)”,進(jìn)行一般性介紹、評(píng)點(diǎn)、附會(huì)或引申,開(kāi)一代風(fēng)氣之先。不過(guò),梵澄先生的疏釋?zhuān)谏疃群蛷V度方面都是嚴(yán)復(fù)的“案語(yǔ)”所差堪比擬的,它們?nèi)诤狭俗g者深刻的稽考會(huì)勘,不乏別于原作者的獨(dú)立思考,且多所發(fā)明,幾乎可以獨(dú)立成篇。此時(shí),譯者已不止乎譯,然亦非喧賓奪主,而是一身二任,既為忠實(shí)的譯者,也是與原作者行跨越時(shí)空平等對(duì)話(huà)的作者。這與梵澄先生的國(guó)學(xué)力作《老子臆解》頗有類(lèi)似:“文字既有揀擇,句讀稍異尋常,義理遂可批判。未肯全襲舊說(shuō),間亦稍出新裁,根據(jù)不豐,只名臆解”(這其中自有作者的謙辭);“要之,求以至簡(jiǎn)潔之文字,解明書(shū)中之義理,恰如其分,適可而止”(徐梵澄,1988:1-2)。而“詮解古典思想文本,同樣是一種翻譯”(劉小楓,2002:52),這種“疏釋”與“臆解”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區(qū)別在于前者不外語(yǔ)際翻譯,后者可歸入語(yǔ)內(nèi)翻譯。
其三曰創(chuàng)譯。在翻譯印度經(jīng)典《行云使者》(Kalidasa)這種文學(xué)性很強(qiáng)的神話(huà)詩(shī)歌時(shí),鑒于梵漢音、律、義、象以及結(jié)構(gòu)迥異,直譯無(wú)法再現(xiàn)原作的美學(xué)意旨,因此,譯者采用的既“不是直譯,也不是意譯,而是創(chuàng)譯”(郁龍余,2010:139),即“取原文之義自作為詩(shī)”(徐梵澄,2006c:35):
顧終以華梵語(yǔ)文傳統(tǒng)不同,詩(shī)詞結(jié)構(gòu)懸隔,凡言外之意,義內(nèi)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長(zhǎng),風(fēng)神之秀,多無(wú)可譯述;故當(dāng)時(shí)盡取原著滅裂之,投入镕爐,重加鍛鑄,去其粗雜,存其精純,以為寧失之減,不失之增,必不得已乃略加點(diǎn)綴潤(rùn)色,而刪削之處不少,迄今亦未盡以為允當(dāng)也,姑存古體詩(shī)百二十首如此。用呈示吟壇方家,倘加欣玩。抑思明達(dá)自知,凡詩(shī)皆不可譯,如或勘以原作,亦必知其何以甚有出入者矣。(徐梵澄,2006d:31)
譯者的這種選擇,并非率性而為,而是有多方面的考慮:
夫拼音系統(tǒng)文字之互譯,尚有可易為力者,而乃出之以事象系統(tǒng)之華文,其相去不啻天壤,是猶之梵澄取原文之義自作為詩(shī),與迦里達(dá)薩幾若無(wú)與,然亦有不昧迦里達(dá)薩之光華燦發(fā)者,誠(chéng)不敢厚誣異域之高才。竊愿今后之治梵學(xué)及善白話(huà)詩(shī)者,再?gòu)亩g之,別鑄偉詞,后來(lái)居上。一作而傳數(shù)譯,亦經(jīng)典文學(xué)常例,不必謂誰(shuí)本之誰(shuí)。(徐梵澄,2006c:35)
盡管梵澄先生也認(rèn)為“凡詩(shī)皆不可譯”——雪萊(Shelley,1993:756)所言“譯詩(shī)之徒勞”的余響——但并不是說(shuō)不要譯,只是需要?jiǎng)?chuàng)造性地“取原文之義”而“別鑄偉詞”,舍此別無(wú)他法。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詩(shī)歌的確不可譯,“這是巴比倫通天塔遭受天罰的負(fù)累”,因?yàn)樵?shī)歌的“聲音和思想相關(guān),也與其再現(xiàn)的對(duì)象相關(guān),……詩(shī)人的語(yǔ)言總是牽涉著聲音中某種一致與和諧的重現(xiàn),舍此,詩(shī)也就不成其為詩(shī)了”(Shelley,1993:756)。但另一方面,詩(shī)又必須譯,否則,作為文學(xué)精華的世界詩(shī)歌文化就難以傳承,世界文明也就不可能像現(xiàn)在這樣發(fā)展。只是在迥異的目標(biāo)語(yǔ)言中,原詩(shī)的聲音、詞句、韻律、意象大多必須“重加鍛鑄”,方能再造詩(shī)境。卓立于印度文壇的梵文詩(shī)之巨制《行云使者》“全詩(shī)百二十首,每首四行,每行十七音,稱(chēng) Mandākrāntā,義譯可謂‘緩轉(zhuǎn)格’”,由于“此無(wú)從出之于華文者”(徐梵澄,2006f:26),梵澄先生以七言古體詩(shī)出之,譯詩(shī)風(fēng)格古樸,語(yǔ)言雅訓(xùn),詩(shī)意盎然。這也是先生自己美學(xué)訴求使然,他比較自重的《蓬屋詩(shī)存》就是五、七言古體或近體,其深厚的古典文學(xué)功底和創(chuàng)作才華尤為魯迅先生所器重。
此外,梵澄先生還提到過(guò)譯文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這也是自古至今永遠(yuǎn)的話(huà)題,很難有定論。大概世界上也沒(méi)有一個(gè)十全十美的譯本,正如沒(méi)有一個(gè)完人一樣。他認(rèn)為:“一個(gè)譯本無(wú)疵可指,處處精確,仍然可能是壞譯本,不堪讀。正如為人,‘非之無(wú)舉也,刺之無(wú)刺也’,仍往往是‘鄉(xiāng)愿’,不是‘圣人’。這仿佛是一有機(jī)底活事物,不是電子機(jī)器能操縱的”(徐梵澄,1992:3)。這自然也是適用于包括先生自己在內(nèi)的任何一位譯者的,因此,只要不是濫譯,對(duì)于任何一個(gè)嚴(yán)肅的譯者,無(wú)論是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理解都是很有必要的。
3.結(jié)語(yǔ)
但是先生卻是寂寞的,無(wú)論生前還是身后。誠(chéng)如劉小楓(2002:51)其時(shí)所言,“梵澄逝去才兩年,學(xué)界好像已經(jīng)不記得他曾經(jīng)死了,一如先生在世時(shí)學(xué)界似乎不記得他還活著。”現(xiàn)在十年過(guò)去了,情況并無(wú)多大的改觀(guān)。質(zhì)言之,先生的寂寞其一可能源于其學(xué)問(wèn)的高深,這個(gè)時(shí)代無(wú)有能真正與之對(duì)話(huà)者,這才有“看來(lái)我的學(xué)問(wèn)是沒(méi)人繼承了”(孫波,2009:454)的嘆息;其二可能在于他特立獨(dú)行的個(gè)性與人格。如果說(shuō)早年還頗有些狂狷,那么中年去國(guó),皓首還鄉(xiāng),已經(jīng)讓他極為內(nèi)斂中和,虛空清靜,一心向?qū)W而無(wú)旁騖。這從他晚年回國(guó)后向就職社科院宗教所所長(zhǎng)任繼愈先生提出的三點(diǎn)要求中可見(jiàn)一斑:“第一,不參加政治學(xué)習(xí);第二,不帶研究生;第三,不接受任何采訪(fǎng)。任先生一概應(yīng)允”(孫波,2009:301)。這也與他數(shù)十年如一日潛心為學(xué)的精神是一致的,即“努力做,趕緊做,其他一概不管”(姚錫佩,2000:71)。由于沒(méi)有及門(mén)弟子,身前身后都顯得甚為寂寞。
作為魯迅先生的私塾弟子,原本很可以坐收名利,但先生從來(lái)不屑為之。他有幸親炙魯迅的教導(dǎo),但以自己的勤奮和修為走出了一條與先師不同的學(xué)術(shù)通衢。他曾坦承,“我的性格乖張,是自知的,從來(lái)不喜依草附木,因老師而得名。自己的成就如何,自己是明白的,浪得浮名,至屬無(wú)謂。尤其在創(chuàng)作方面,獨(dú)立不倚,也算保持了知識(shí)上的誠(chéng)實(shí)”(徐梵澄,2001:192)。獨(dú)守其在為人上的“獨(dú)善其身”和為學(xué)上的“兼濟(jì)天下”之高貴品格,脫盡凡塵,令人肅然起敬,難怪劉小楓先生對(duì)他的為人為學(xué)欽佩不已,尊其為“大師”與“圣人”:“梵澄之為學(xué)術(shù)大師,并非因?yàn)樗?jīng)是魯迅的學(xué)生”;“兼及中西印三大文明學(xué)術(shù)的中國(guó)學(xué)人屈指可數(shù),有的不過(guò)浮泛涉獵、蜻蜓點(diǎn)水。梵澄在每一領(lǐng)域都涉獵頗深,不屬此列;何況先生勞作累累,有目共睹,絕非像某些傳說(shuō)中的大師”(劉小楓,2002:51)。
徐梵澄先生一生生活簡(jiǎn)樸,只是孜孜矻矻于艱深的學(xué)術(shù)研究。他不計(jì)名利,不參加評(píng)獎(jiǎng),所以“成果不無(wú),獎(jiǎng)未有獲”(孫波,2009:410),甚至謝絕央視等媒體的采訪(fǎng)宣傳或以自己為題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但他待人誠(chéng)懇,襟懷宏闊,有赤子之心。“他的人格力量和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按目前我們的認(rèn)知水平,無(wú)論怎樣評(píng)價(jià),都不會(huì)過(guò)高”(郁龍余,2010:137)。如果說(shuō)先生生前為人為學(xué)甘于寂寞是先生真正淡泊名利的人格訴求,我們必須尊重;如果先生仙逝后再讓其深厚學(xué)識(shí)繼續(xù)寂寞則是學(xué)術(shù)界的失職,我們是否理當(dāng)反思?1990年,20年前曾經(jīng)在印度擔(dān)任徐梵澄助手的美國(guó)姑娘瑪麗斯(Maris L.Whitaker),寫(xiě)信告訴徐梵澄的鄰居說(shuō):“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我希望人們都能夠與徐先生這樣的人生活一段時(shí)間,這樣他們就能認(rèn)識(shí)到許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孫波,2009:256)。然斯人已逝,徒留悵懷。
梵澄先生人如其學(xué),學(xué)如其人,可謂高山仰止。他不為塵世所囿所擾,脫盡鉛華,以出世為入世,以入世求出世,從而臻于一種“梵我一如”的至澄境界,那當(dāng)是“凡塵洗盡即梵澄”吧。
[1]Shelley,Percy Bysshe.A Defense of Poetry[M].M.H.Abrams,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 London:W.W.Norton& Company,1993.
[2]金克木.讀徐譯《五十奧義書(shū)》[J].讀書(shū),1987(9).
[3]劉小楓.圣人的虛靜[J].讀書(shū),2002(3).
[4]魯迅.“題未定”草[M].《魯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5]孫波.徐梵澄傳[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9.
[6]孫波.編者的話(huà)[M].徐梵澄集.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1.
[7]孫波.徐梵澄先生學(xué)術(shù)思想管窺[J].魯迅研究月刊,2000(5).
[8]徐梵澄.“跋舊作版畫(huà)”[M].徐梵澄集,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1.
[9]徐梵澄.《玄理參同》序[M].徐梵澄集,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1.
[10]徐梵澄.徐梵澄文集(1~16卷)[M].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
[11]徐梵澄.《尼采自傳》序[M].徐梵澄文集(4).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a.
[12]徐梵澄.《神圣人生論》出版書(shū)議[M].徐梵澄文集(4).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b.
[13]徐梵澄.《行云使者》跋[M].徐梵澄文集(4).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c.
[14]徐梵澄.《行云使者》譯者序[M].徐梵澄文集(4).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d.
[15]徐梵澄.《薄伽梵歌》佛協(xié)版譯者序[M].徐梵澄文集(4).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e.
[16]徐梵澄.原作格調(diào)[M].徐梵澄文集(7).孫波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f.
[17]徐梵澄.序[M].老子臆解.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8.
[18]徐梵澄.譯者序[M].五十奧義書(shū).徐梵澄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5.
[19]徐梵澄.綴言[M].尼采.蘇魯支語(yǔ)錄.徐梵澄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2.
[20]徐梵澄.《薄伽梵歌論》前言[M].阿羅頻多.薄伽梵歌論.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3.
[21]姚錫佩.梵澄先生給予我的教益[J].魯迅研究月刊,2000(5).
[22]郁龍余.徐梵澄的印度文學(xué)哲學(xué)經(jīng)典漢譯[J].南亞研究,2010(1).
[23]詹志芳.瑣憶徐梵澄先生[J].魯迅研究月刊,2000(5).
[24]鄭振鐸.序言[M].尼采.蘇魯支語(yǔ)錄.徐梵澄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36/1992.
[25]周?chē)?guó)平.翻譯尼采作品有感[J].出版工作,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