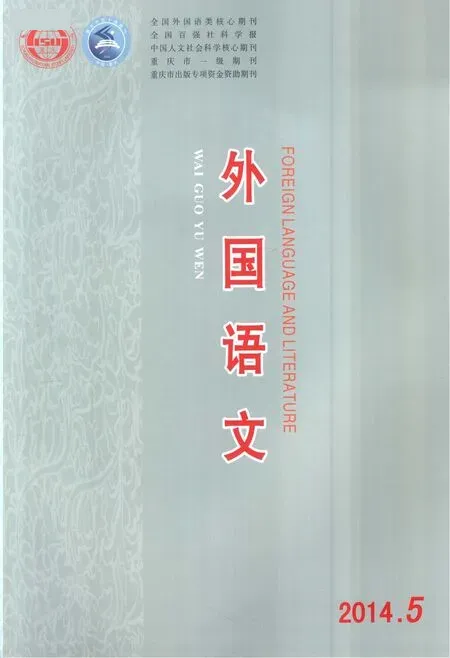二語習得石化研究:概念、成因與方法——簡評《第二語言習得石化研究》①
譚 春
(四川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重慶 400031)
1.引言
二語/外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語言會“石化”(fossilize)這一概念由Larry Selinker于1972年在Interlanguage(《中介語》)一文中提出。從那時起到現在近40年的時間里,“語言石化”(fossilization)始終都是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國內外學界從不同的理論視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對這一概念的本質、特點、成因、表現形式等方面展開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在眾多的研究者中,Selinker的學生Han Zhaohong可以說是集大成者。在其1998年博士論文的基礎上,Han于2004年出版了Fossilization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成人第二語言習得中的石化》)一書,對二語習得領域在過去30多年里的石化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評價,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見解和建議。作為該書的后續,Han Zhaohong和Terence Odlin于2006年合編出版的Studies of Fossilization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二語言習得石化研究》)一書反映了二語習得領域關于石化研究的新近發展動態,對語言學習中涉及到“石化”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更深入、更詳盡的探討。
2.主要論點
全書共收錄了10位二語習得領域領軍人物關于石化討論的論文,各自獨立成章,外加一篇Larry Selinker寫的卷尾語,論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語言石化的概念、成因及研究方法等方面。
2.1 石化的概念
關于“石化”這一概念的合理性,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學者們歷來都持有不同見解。Han Zhaohong和Terence Odlin在導言部分指出,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各研究者對“石化”的定義、本質、適用范圍等方面理解上的差異,以及研究過程中所采用方法的不同。在二語習得領域,研究者們所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學習者的二語/外語能力能否達到像其母語一樣的水平?圍繞這一問題,Han&Odlin列出了兩種對立的觀點:(1)二語/外語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學得的,大多數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都可以取得成功;(2)二語/外語的方方面面并不都是可以學得的,從總體上看,學習者的語言學習以失敗居多。兩位作者總結指出,在語言石化研究過程中,不管是以成功為導向(success-oriented)還是以失敗為導向(failure-oriented),成功或失敗都只是局部的(local),學習者的整個中介語系統不會發生石化,石化的只是一些語言子系統(linguistic sub-systems)或一些特殊的構式,而語言系統的其他方面仍可能繼續發展。換言之,不論語言學習/習得最后結果是什么樣子的,在這過程中確實會出現語言石化現象。書中其他幾位作者如Donna Lardiere對Patty的跟蹤研究(第三章),Terence Odlin,Rosa Alonso Alonso和 Cristina Alonso-Vázquez關于母語、二語、三語之間關系的探討(第五章),Usha Lakshmanan(第六章)對兒童二語習得與石化之間關系的研究等都認可語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會出現語言石化的觀點,認為“石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
作為石化概念的締造者,Selinker當然不會對石化的概念產生質疑。他在卷尾語部分介紹了自己對“語言石化”產生興趣的源起,石化概念的演化以及該領域研究的核心問題。Selinker認為,語言石化在語言學習中不可避免。無論語言石化研究如何發展,其關鍵還是(母語)遷移和中介語之間的關系問題,而遷移主要發生在目標語的核心語法層面。據此,Selinker提出了“關注其他形式假設”(Attention to Other Form Hypothesis):將語言學習者的注意力從核心語法形式(core grammatical forms)轉移到非核心的次要形式(non-core peripheral forms)有助于學習者自動習得核心語法形式,從而可以預防并避免潛在的語言石化出現。(p.208)
但是并非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語言石化”是一種正確的說法,本書中收錄的Constancio K.Nakuma和David Birdsong兩人的文章對石化的概念進行了質疑。Nakuma在第二章“語言石化與二語磨蝕研究:難以回答的簡單問題”里將語言石化和語言磨蝕(language attrition)放在一起進行了討論,對二語習得把石化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合理性提出了懷疑。在回顧前人研究的基礎上,Nakuma認為語言石化與磨蝕都是二語習得界學者們為研究二語學習者/使用者的學習行為和學習結果而“構造”的概念。(p.21)事實上,它們都只是“假設”(assumption/hypotheses)而不是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所以不可能用實證的方法(如歷時研究)加以量化驗證或展示。這也是為什么二語習得石化研究中缺少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的原因。在Nakuma看來,要解決這一難題不能一味地依賴所謂的實證研究,“假設驗證”(hypothesis testing)或許是一條途徑。文章最后總結出全文探討的六個“難以回答的簡單問題”。這些問題對大多數二語習得研究者和教師們來說并不陌生,有些問題具有啟發意義,值得大家進一步思考。
同樣,David Birdsong在第九章“為什么不談石化”對“石化”概念本體提出了質疑。Birdsong指出,二語習得領域所進行的石化研究是一項不無風險的活動(p.173),因為“石化”這一術語既可以用作“解釋物”(explanans)來說明語言習得的過程(process),又可以用作“被解釋的對象”(explanandun)來表示習得結果(product)。有時“石化”指的是那些永久的、固定不變的因素,有時卻是指那些始終處于變化之中的不穩定因素。Birdsong認為這種混亂狀況的出現源于研究者們大多以學習者的學習失敗為出發點,以非本族語者水平(non-nativelikeness)為參考標準。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研究者們應該把重心轉移到學習者的潛勢(learner’s potential)上來,看他們學習的最終成就能達到什么樣的本族語者水平(nativelikeness)。在他看來,這一方向的轉變雖然也可能有著風險,但它對二語習得石化研究不無啟發意義。基于此,Birdsong提出了“普遍可學假設”(Universal Learnability Hypothesis),聲稱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什么都有學得/習得的可能。也就是說,語言學習者在二語/外語學習過程中有可能學會語言的方方面面,不會出現語言的石化。
與前面兩種涇渭分明的觀點不同,Diane Larsen-Freeman對石化的概念沒有明確的肯定或否定,不過她提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會出現“穩定”(stabilization)狀態一說,認為這一術語或許比“石化”(fossilization)更能清楚的說明問題。在本書的第10章“二語習得與石化問題:沒有終點,也沒有狀態”,Larsen-Freeman針對二語習得領域在“石化”的定義、描寫和解釋三個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分析了為什么石化研究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仍能在二語習得領域長盛不衰的原因。她提出語言習得研究不應該糾纏于學習者最終的習得狀態。事實上,語言是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的,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終點(end)”,“石化”只是語言動態變化過程中相對較穩定的狀態。她認為這一觀念的轉變,不僅對石化研究具有啟發性作用,對語言教學也不無參考價值。
2.2 石化的成因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及其相關領域對于石化形成原因的解釋也有著比較明顯的差別。縱觀石化研究的歷史,Selinker(1972)的“心理論”、Lenneberg(1967)和Lamendella(1977)等的“生物論”、Schumann(1978)的“文化遷移模式”以及Vigil和Oller(1976)的“相互作用論”等都曾為二語習得石化研究做出過巨大貢獻,為其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研究的不斷發展創新,目前,涌現出了一批新的解釋模式。本書中Brian MacWhinney(第七章)和Elaine Tarone(第八章)等人對語言石化出現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見解和解釋。
MacWhinney在“石化的涌現性”一文中就一些導致二語習得石化出現的年齡相關因素進行了討論。他認為,相對于“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而言,學習者的“到達年齡”(Age of Arrival)可以從神經學、心理學、生理學及社會學等層面說明其局部語言停滯發展的原因,對二語習得石化更具解釋力。MacWhinney在此基礎上,批判性介紹了學界用來解釋語言習得石化的10種假設。作者指出,這些假設雖然從生物學和心理學等角度對石化的成因進行了說明,但是除了“固化”(entrenchment)和“母語遷移”(L1 transfer)兩種假設能夠較好地闡明AoA與學習者語言石化之間的關系外,其他幾種假設的作用微乎其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沒能考慮到成人二語習得中學習者主體和學習者之間因素的影響。為彌補這一不足,MacWhinney提出了兩個新的假設:社會分層假設(Social Stratification Hypothesis)和補償策略假設(Compensatory Strategies Hypothesis),把社會因素納入到了影響成人二語習得最終結果的范圍之內。
Elaine Tarone的“語言石化,社會環境與語言游戲”可以看作是對MacWhineey文章的“補充”。她在該章節中探討了社會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在引起和消解語言石化方面的作用。Tarone認為語言石化的出現,至少部分情況是這樣的,是隨著二語學習者年齡不斷增長而變得日益復雜的社會和社會心理交互網絡作用下的結果(p.170)。這種復雜性可以用Larsen-Freeman(1997)提出的關于語言習得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來解釋,把中介語看作是促使語言停滯或發展的平衡力量的產物。如果使得語言停滯發展的力量占據上風,則會產生社會心理障礙,進而導致石化。相反,如果促使語言發展的力量取得優勢,則學習者的中介語可以繼續發展,從而消解甚至阻止石化的出現。基于此,Tarone通過大量的實例分析來說明語言游戲(language play)或許能夠促使中介語繼續發展,達到消解甚至阻止石化出現的效果。Tarone同時也承認,這一假設還有待歷時的、實證的研究來檢測、驗證。
2.3 石化的研究方法
正是由于研究者們在研究出發點、理論視角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了二語習得石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千差萬別。本書中第三、四、五、六章的相關內容對該領域里常用的一些方法的有效性進行了討論。
Donna Lardiere的“特定第二語言語法最終習得狀態的確立”是其1998年實證研究的延續。在相隔18個月的時間里,Lardiere利用“是/否判斷”和“5分評級”兩項語法判斷任務(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ask)對其受試主體Patty(一位已在英語國家居住了近23年的華裔女性)的英語動詞和副詞配置關系知識進行了測試。結果表明,Patty的英語語法知識在某些方面,如詞語的曲折形態變化,與本族語人相去甚遠。但在另一些方面,如動詞提升的制約因素(verb-raising constraint),基本上與英語本族語人相差無幾。Lardiere認為Patty表現出的這些差異和其漢語母語語法關系并不是十分緊密,真正的原因在于Patty在目標語(英語)的句法特征上面已處于停滯發展狀態。Lardiere進一步聲稱,這一歷時研究結果表明,語言學習者在語言某一領域的石化并不能排除其在另外一些領域的繼續發展。(p.41)因此,沒有理由斷定石化會出現在整個語言系統。Lardiere還指出,在研究學習者二語/外語石化時,語法判斷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針對這一方法,Han Zhaohong在第四章“語言石化:語法判斷法能否作為一種可靠的證據來源?”專門進行了討論,探討使用語法判斷法來研究二語習得石化的可行性。在回顧前人研究對語法判斷法或否定或肯定的基礎上,Han結合自己利用語法判斷法進行的長達七年的歷時研究,指出自然產出語料和語法判斷語料在本源上無實質性區別。這兩種方法收集到的語料從歷時和共時角度來看都具有“廣泛的一致性”(p.74)和互補性,因此語法判斷法可以作為二語習得石化研究語料收集的一種有效手段。
Usha Lakshmanan在“兒童二語習得與石化之謎”一文里從動詞的曲折形態和普遍語法中的限制因素兩方面說明了如何利用Foster-Cohen(2001)的“滑窗假設”(Sliding Window Hypothesis)來解釋二語習得石化的內部機制。該假設有兩大主張:(1)一語習得和二語習得不是截然分開的;(2)研究學習者的發展模式應采用跨年齡(cross-age)的方式。在此基礎上,Lakshmanan從語言磨蝕和再習得兩個方面重新分析了Hansen(1980,1983)所收集的關于兩名英語為母語的兒童學習印地語/烏爾都語的中介語語料。結果表明這兩名兒童在句子否定的詞序判斷和使用上受母語影響,達不到二語本族語者水平。Lakshmanan認為兒童二語習得和成人二語習得在發展路徑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最終兒童在習得目的語結構上比成人更成功。她總結指出在二語習得研究領域,學者們對于學習者最終的二語能力總是偏向于參照單語目標語者的水平。她建議,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在研究中應該選取那些從一出生就同時習得并一直使用兩種語言的目標語者作為參照。
Terence Odlin、Rosa Alonso Alonso和 Cristina Alonso-Vázquez圍繞兩個問題:(1)在關于語言遷移與石化的問題上,二語和三語習得之間有什么相同之處?(2)在研究學習者時態及相關動詞類別習得時,什么樣的方法是最合適的?(p.83)采用篇章改錯(passage correction)的方法對母語或雙語為西班牙語的成人英語學習者(西班牙語是加西利亞人的二語,英語則是他們的三語)和英語本族語者的現在完成時態的習得使用情況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與二語習得一樣,成人語言學習者先前所掌握的語言會影響他們對目標語的判斷,三語學習者會把母語及二語中的一些語法特征遷移到目標語上,最終導致三語石化的出現。Odlin及其合作者們在研究中發現英語本族語者對現在完成時態的錯誤使用持一種相當容忍的態度,與兩組英語為非本族語的受試者“幾乎沒什么差別”(p.93)。Odlin等據此指出,在語言遷移及石化的研究過程中,不管是方法上還是理論上(如什么是“本族語者水平”)都存在有大量問題需要解決。
3.評價與思考
“石化之謎”(fossilization puzzle)是二語習得舞臺上一個長盛不衰、歷久彌新的經典主題。多年來,它吸引了無數專家、學者從各種角度對其進行分析、闡釋和論證,但各自的著述相對較為零散。作為《成人二語習得中的石化》姊妹篇,《第二語言習得石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零散的研究進行了匯總,收納了該領域一些著名學者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一些持批評和否定態度的作品。這一方面反映了石化領域的研究前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該書兼收并蓄,求同存異的嚴謹與科學的態度。
正如兩位編者在導言里所描述的,本書兼顧到了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平衡。在11篇文章中,Han&Odlin所寫的導言,Larsen-Freeman的結語和Selinker的卷尾語等三篇文章是對二語習得石化研究的綜述,從宏觀層面上勾勒出了這一領域的架構。Nakuma、MacWhinney、Tarone 和 Birdsong 等人的四篇文章從方法、描述和解釋等方面對石化研究進行了理論層面的探討。Lardiere、Han、Odlin、Alonso&Alonso-Vásquez以及Lakshmanan等的四篇文章則是各自實證研究的結果報告。
全書涉及論題廣泛,基本上涵蓋了本領域研究者們所關心的核心問題,體現了二語習得石化研究在過去30多年里的最新發展和成果。隨著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以及該領域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不斷融合,筆者認為該書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給我們留下了有待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1)石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書中關于理論的探討大都還是圍繞著傳統的石化研究理論展開,比如石化形成的社會、文化、生理、心理、認知、情感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毋庸置疑,這些研究對推動石化研究理論的發展功不可沒,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它們大都建立在以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為理論基礎的框架之上,因而對語言習得以及習得中語言石化的闡釋帶有先天的理論上的局限和貧乏。這或許就是為什么二語習得石化研究發展了幾十年都沒能形成一種統一、有效的解釋機制和原理的原因。隨著近幾十年語言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里認知語言學、應用認知語言學、認知神經語言學等學科與二語習得研究聯系的日益密切,國內外不少學者嘗試著將這些前沿學科理論知識用來解釋語言習得中的各種現象。所以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先前的理論解釋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些分歧和爭議甚至不足,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這些新近學科的相關理論來分析解釋語言石化的產生機理,從而構建一種更有說服力和詮釋力的石化研究框架?
(2)石化研究的對象層次。《第二語言習得石化研究》中的幾篇實證性研究報告對習得過程中可能引起石化的因素以及可能石化的語言現象進行了驗證,為石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大都還只停留在普遍語法句法理論指導下的語法層面上,語言的其它方面基本沒有涉及。那么我們需要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語言石化是否僅僅出現在詞匯語法這一層次?語言學習過程中石化是否會在其他如語音、詞匯、句法、語篇等層面上出現?更進一步,從語言的認知及認知神經科學視角出發,石化是否會出現在大腦中的概念結構層面?語言的石化是否只是概念層面固化的外在表征?
(3)石化研究的實用性質。眾所周知,在二語習得領域,不管是理論的探索還是實證的驗證,其最終價值體現在它們對實際課堂教學中語言學習的指導作用。但本書基本上沒有涉及語言石化與語言課堂教學之間的關系,給讀者一種為了研究而研究的感覺。這恰好反映了當前石化研究的尷尬境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石化研究已經有了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但它的實用價值在實際語言課堂教學中未能體現和發揮出來。尤其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對于語言課堂教學活動中的教師和學生這兩大主體來說,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運用石化研究的成果來改善和提高語言教與學的效果與質量?
總之,《第二語言習得石化研究》既反映了該領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留下了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如果能夠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無疑會對語言學習的本質以及如何有效解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提供更科學、更有說服力的解決辦法。可以斷定,只要有人類的存在,就會有語言石化的出現,也會有更多的專家學者投身到該領域的研究。我們希望,未來的研究者們不僅能夠從理論上提出更有解釋力和說服力的機制和原理,更能夠結合語言教與學的實際,從實踐上將研究成果轉化為語言學習的推動力。
[1]Ellis,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Gullberg,M.& P.Indefrey(eds.).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Malden,MA.:Blackwell,2006.
[3] Han,Zhaohong.Fossilization:Five Central Issu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4,14(2):212-242.
[4]Han,Zhaohong.Fossilization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2004.
[5]Holme,R.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M].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ian,2009.
[6]Robinson,P.& N.C.Ellis(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NY:Routledge,2008.
[7] Selinker,L.Interlanguag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1972,10(3):209-231.
[8]Selinker,L.Rediscovering Inter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