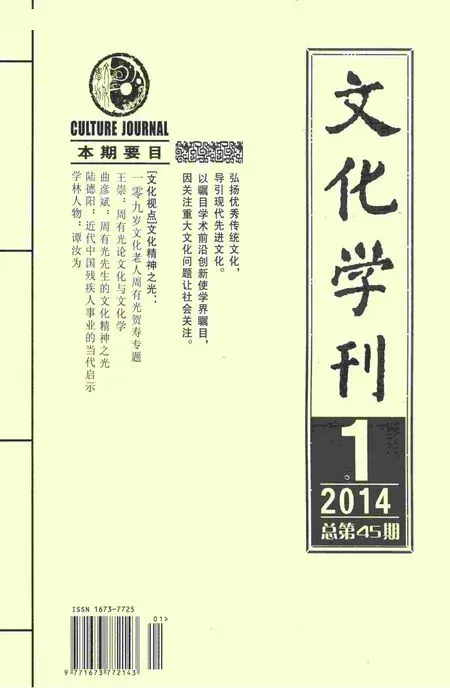百歲思想家周有光的中國夢
劉 鋒
2013年1月13日,周有光先生108歲了。如此高齡,身居斗室,卻有著白里透紅的臉龐,慈眉善目的笑容,縱橫四方的暢談,娓娓道來的百科故事,孩童般的純真夢想,達觀開放的閱世智慧,不能不讓國人高山仰止。
閱讀周先生的人生,便可與他一起做著求真、開放、民主、自由、共同發展的中國夢。這中國夢的歷史根基在于兩點:(1)親身經歷。周先生歷經晚清、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歷史時期,耳聞目睹了滄桑中國的百年變化;(2)讀透歷史。周先生縱覽了人類歷史的演進軌跡,把理想社會與現實社會,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梳理得清清楚楚。
周先生在百歲前后還廣泛閱讀各類文章、典籍,并堅持寫作,在其著述的《朝聞道集》《拾貝集》等作品中,讀者常常能發現令人眼前一亮的思想觀點。例如,在《胡適與陳獨秀的分道揚鑣》一文中,周先生十分贊同邵建先生的研究觀點,認為胡適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類似于“改革開放”的思想—— “哪有帝國主義”論與“國際的中國”論。也就是說,早在90年前,胡適就說過中國應該放棄革命對抗的思維,不要動不動就用“帝國主義”這樣的概念定性與中國交往的國家。中國需要與世界各國多交往,要融入世界,爭取世界機遇,做世界的中國。事實證明胡適的判斷是對的。只可惜,在實踐中,中國人常常不加分析地說,有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充滿仇視,妄圖顛覆中國,從而拒絕與它們交往,其實,這是革命對抗思維在起作用,其后果是失去了本應有的國際發展機遇。周先生依據歷史事實,對胡適的判斷加以肯定,顯示出了一個學者尊重史實的學術精神。
新中國最初的歷史教科書中,原來稱“太平天國革命”,是共產黨革命的榜樣,對民眾進行廣泛宣傳。后來《辭海》中進行了糾正,即把“太平天國革命”改成“太平天國運動”。周先生對這一行為進行了肯定。“革命”改成“運動”,雖然只是一個詞語的改動,但也說明了現在的歷史記載開始逐漸回歸它應有的真實。太平天國運動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它也有專制、落后、空想、推歷史倒車的弊端。以前的正史把它說成美輪美奐的革命運動,實在是不符合歷史原貌。在閱讀、寫作中尊重史實,冷靜客觀,敢說真話,周先生都為今天的知識人立下了鏡子。
在《微言大義和托古改制》一文中,周先生通過研究清末“公羊學派”的倡導者“常州學派”的學說,發現中國人凡是推行改革,都要在古代傳統中找到論據,“托古改制”,才能獲得國人的支持。言外之意在于,中國人有著保守的文化基因,對于創新、改革帶來的自然變化、歷史潮流有著“天然”的反抗心理。周先生又說古人之所以搞“微言大義”,轉彎抹角地委婉批評、褒貶古人,原因在于古代人缺少言論自由。古代人缺少言論自由,在今日的中國雖有一定限度的言論自由,但真正地落實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合法的自由不被落實,中國人的才能、智慧就會被壓制,中國人的前行之路就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坎坷。在《郭秉文和東南大學》 《經濟學的沉浮》《心理學的沉浮》《老舍之死》等文章中,周先生就如實地記錄了這種人的自由遭到踐踏所造成的種種悲劇。
中國夢的夢想成真,離不開國際現代文化的養分供給。在談到端午節的時代意義、阿富汗的落后、日本變西方、不丹王國的民主化、東亞“四小龍”的崛起、北歐五小國的崛起等話題時,周先生強調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并認為“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雙文化”并存,狹隘的民族主義,夜郎自大的文化先進論則不符合世界潮流,而“全人類共創、共有、共享的國際現代文化”則符合世界潮流,用國際先進的制度文化改進本國的傳統文化,也是歷史的潮流。
作為今日中國的“雙文化”人,應該知道人類文化發展的步驟。這方面,周先生給出了自己的歸納:在經濟方面,人類遵從農業化——工業化——信息化的演變路線;在政治方面,人類遵從神權——君權——民權的演變路線;在思維方面,人類遵從神學——玄學——科學的演變路線。歷史的演變路線,即歷史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有了這種認識,就需要遵守歷史的交通規則,就需要有世界觀點和地球村村民意識,就需要“從本國看本國改為從世界看本國,從本國看世界改為從世界看世界”,就需要“走進世界,做一個21世紀的世界公民”。
在一系列思考蘇聯歷史興亡的文章中,周先生在字里行間透露出對社會主義的反思,革命密碼的破解,以及人文精神的向往。蘇聯大廈轟然倒地,當地人待之以“沒有哭泣的葬禮”,曾經的“偉大、光明、正確、永遠勝利”都不見了,繼任的俄羅斯又難以與歐美所引領的現代國際文化所對接,其中蘊含的歷史經驗、教訓需要深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中國人消化吸收。
蘇聯為什么滅亡?這是一個老問題了。但是,它卻需要世人反復地去思考、引以為戒,才能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蘇聯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那套制度設計違背了歷史的演變路線。具體說來,周先生給出了許多數據詳細的清單。從經濟上看,計劃經濟造成的指標僵硬、特權揮霍財富、民眾貧窮化,農業集體化導致地主、富農被消滅,民眾大饑荒,“剝削率高出資本主義”,使民眾對所謂的社會主義失去了信任;從政治上看,深入制度骨髓的專制、特權、殘暴把這個政權一步步推向滅亡,再加上“大清洗”所造成的人人自危局面,以及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被監禁、被流放和被強迫遷移等社會悲劇的蔓延,都說明這個政權不得人心;從文化上看,這個制度禁錮思想,控制新聞,偽造歷史,摧殘科學,說著騙人的鬼話,最后暴露在世人面前,丟掉了最后的顏面,被民眾拋棄也就沒有可哭泣的必要了。
蘇聯滅亡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被世人所拋棄,但是,人人享受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主義理想沒有被世人拋棄。只是這理想離中國人太遙遠,而現實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統領世界潮流。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先建設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確實有道理。但是,據周先生的觀察,“馬克思去世太早,只看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一戰’前)的前半,沒有看到后半,更沒有看到中級階段 (兩戰間)和高級階段(‘二戰’后);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全貌,因此《資本論》只可能是哲學推理,不可能是科學實證”。所以,蘇聯人、中國人曾經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都有偏差,對馬克思的經典解讀也有謬誤,蘇聯拋棄資本主義規律的制度模式失敗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也照搬“蘇聯模式”,走了許多的彎路。改革開放后,中國人選擇融入資本主義歷史潮流,才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中國人仍不忘記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周先生說:“社會主義是理想,資本主義是現實。”現實不能令人滿意,但這就是現實,躲不過,只能在國際通行規則、國家憲法規則的范圍內爭取做到最好。理想很誘人,又必需,因為它提供精神支柱和歷史方向,但是它卻高遠,難實現,只能引領人類一步步艱難地靠近。
蘇聯不在了,但革命的基因卻沒有消亡,反而還在特定的時期演變成詭異的惡魔破壞社會。當然,正義的革命也會促使新社會的重建。在《南斯拉夫解體》《紅色高棉始末》 《柬埔寨開審紅色高棉》《懲越戰爭和中越心結》《何謂顏色革命》等文章中,周先生試圖破解革命的密碼——狹隘的民族主義、權力集中、高壓統治、宗教信仰分歧、語言文字不同、盲目建設理想社會、殘殺生命、外交手段、群眾政黨享權手段與民主潮流等。革命的正義性評價標準在于,它符合歷史潮流,能合法地滿足民眾的權利需要。流血的革命,代價太大,所以,今天中國人呼喚改革。但是,真正的改革不到來,革命就可能應運而生。這是中國人需要警惕的,也是周先生不愿意看到的。
在這樣一個改革口號滿天飛的時代,中國人應該相信哪些改革呼聲呢?周先生在《信仰問答》中給出了自己的兩大信仰坐標:一是直覺信仰,如宗教信仰;二是哲理信仰,如主義信仰,主義信仰屬于經驗知識的信仰。宗教與主義都不容許懷疑,而屬于實證知識的科學卻歡迎懷疑。所以,在驗證改革口號真假的時候,借助科學可以擦亮眼睛。借助科學,也不妨礙中國人堅持各自的信仰。只是當信仰與科學在實踐中產生矛盾時,最好能夠借助科學來解決矛盾;當不同信仰之間產生矛盾時,最好也能借助科學來解決矛盾。因為,科學允許獨立思考,符合人性自由發展的需要,符合人文精神價值需要。一句話,中國人需要信仰,因為信仰帶來美好生活的方向指引,更需要科學,因為科學帶給人自由、理性、創造、創新,以及符合歷史潮流的現代化生活方式。
閱讀周先生的文章摘錄、習得、人生,可以獲悉他心目中的中國夢。這是一個求真、開放、民主、自由、共同發展的中國夢,也是一個“雙文化”和諧共存、共融背景下,勇做21世紀世界公民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