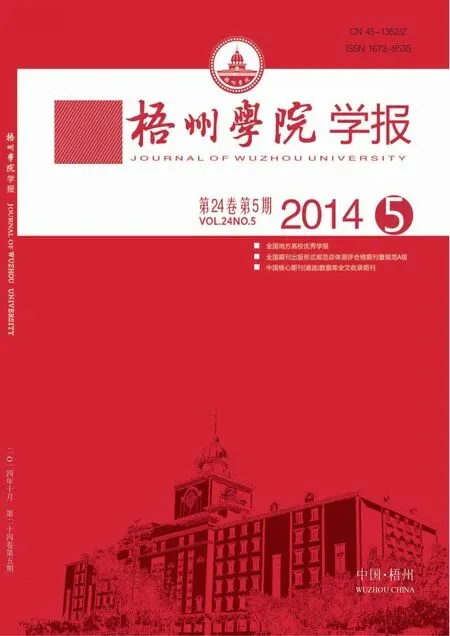關(guān)于馬克思、恩格斯典型論的一些思考
林瑩秋
(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基礎(chǔ)部,廣西南寧 530023)
關(guān)于馬克思、恩格斯典型論的一些思考
林瑩秋
(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基礎(chǔ)部,廣西南寧 530023)
馬克思、恩格斯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duì)于文藝學(xué)進(jìn)行了全面科學(xué)的論述,其中,典型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藝術(shù)哲學(xué)體系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文章從典型的本質(zhì)、典型共性與個(gè)性的關(guān)系、典型環(huán)境與典型人物的關(guān)系三個(gè)方面,對(duì)馬克思、恩格斯典型論進(jìn)行了梳理和思考。
典型論;本質(zhì);共性與共性;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
典型問(wèn)題是老生常談而又糾纏不清的問(wèn)題。自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理論誕生之后,它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條基本原則和科學(xué)方法論,已為大家認(rèn)可和接受,并在實(shí)踐創(chuàng)作中驗(yàn)證了其真理的價(jià)值,推動(dòng)作家創(chuàng)作出無(wú)數(shù)流傳不朽的藝術(shù)典型。但在近幾年,受到各種各樣文學(xué)思潮的影響,文藝界、理論界出現(xiàn)了一些否定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和文藝?yán)碚摰穆曇簦湫屠碚撘脖划?dāng)做傳統(tǒng)的東西加以指責(zé)和否定,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上,淡化典型、淡化人物、淡化情節(jié)的現(xiàn)象十分盛行,一些虛化、荒誕、無(wú)意識(shí)的文學(xué)作品肆意泛濫,使得作家創(chuàng)作和讀者的閱讀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因此,需要重新去思考和梳理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本質(zhì)與特性,否則,將不利于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
一、典型的本質(zhì)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guān)于典型的理論,特別是恩格斯在1888年給《城市姑娘》的作者哈克奈斯的信,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在美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闡述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典型觀。一直以來(lái),人們對(duì)馬克思、恩格斯關(guān)于典型的論述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態(tài)度,并將其看做是構(gòu)成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思想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典型問(wèn)題的核心在于典型的本質(zhì)、典型的共性。在馬克思主義以前,西方美學(xué)家普遍把典型的共性看作是抽象人性的反映,它受一定的宗教、道德、文化等社會(huì)因素的影響,在環(huán)境的變化和社會(huì)的變遷中,對(duì)人的性格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而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學(xué)地揭示了典型的本質(zhì),在典型環(huán)境的發(fā)展史上科學(xué)地說(shuō)明典型共性的內(nèi)容,明確指出典型的共性是人物的社會(huì)階級(jí)本質(zhì)。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人不是抽象的“類(lèi)”而是“現(xiàn)實(shí)中的個(gè)人”,其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1]18在階級(jí)社會(huì)中,由于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所造成了社會(huì)分工的不同和階級(jí)的差異,使得階級(jí)關(guān)系成為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最主要也是最本質(zhì)的關(guān)系。“某一階級(jí)的個(gè)人所造成的、受他們反對(duì)另一階級(jí)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總是構(gòu)成這樣一種集體,而個(gè)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gè)人隸屬于這個(gè)集體,只是由于他們正處于本階級(jí)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于這個(gè)集體;他們不是作為個(gè)人而是作為階級(jí)的成員處于這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中的。”[1]82-83因此,“他們的個(gè)性是受非常具體的階級(jí)關(guān)系制約和決定的。”[1]84但是,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概而論地認(rèn)為典型是階級(jí)的代表,而是具體指出典型是階級(jí)的一定傾向的代表,典型的階級(jí)本質(zhì)決不等于抽象概括出來(lái)的整齊劃一的所謂階級(jí)性。因?yàn)殡A級(jí)決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受到其外部和內(nèi)部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階級(jí)是一個(gè)充滿不同思想傾向的矛盾統(tǒng)一體,同樣的階級(jí)、階層也各有不同的特點(diǎn)。而且,不同階級(jí)的思想還能互相影響,因?yàn)楝F(xiàn)實(shí)的個(gè)人生活于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當(dāng)中,他與社會(huì)其他階級(jí)的個(gè)人發(fā)生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在社會(huì)交往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而,在現(xiàn)實(shí)的個(gè)人身上往往不僅表現(xiàn)出本階級(jí)、本階層的特點(diǎn),而且還表現(xiàn)出社會(huì)其他階級(jí)的痕跡。所以,典型的階級(jí)本質(zhì)就不僅取決于其所處的階級(jí)地位、物質(zhì)生活方式,同時(shí)還包括由復(fù)雜的社會(huì)生活造成的思想特質(zhì)。這樣,典型只能是階級(jí)的一定傾向的代表。
因此,一個(gè)階級(jí)可以而且必然會(huì)有各種不同的典型,而決非是一個(gè)階級(jí)只能有一個(gè)典型。典型的共性不是只有概括某一階級(jí)的階級(jí)特征,它只能是包括而不是等于階級(jí)性。典型的共性除概括某一階級(jí)的階級(jí)特性之外,還可對(duì)本階級(jí)屬性以及背叛自身階級(jí)的叛逆性進(jìn)行概括,如《紅樓夢(mèng)》中的賈寶玉,還可概括某一時(shí)代人們普遍的特性,如魯迅筆下的阿Q,也可能概括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特定民族心理,如抗金英雄岳飛,這就使典型具有豐富和多樣的形態(tài)。但有的人肆意歪曲馬克思、恩格斯關(guān)于典型是階級(jí)一定傾向的代表的論述,認(rèn)為劃分典型性就是階級(jí)性。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上就出現(xiàn)了工人形象必然是先進(jìn)的,農(nóng)民形象是自私的,知識(shí)分子形象是保守的,黨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是完美的,鑄造出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子,給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上帶來(lái)了嚴(yán)重的危害。
二、典型共性與個(gè)性的關(guān)系
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西方的典型理論,特別是黑格爾關(guān)于典型共性與個(gè)性相統(tǒng)一的辨證思想,尤其強(qiáng)調(diào)要通過(guò)個(gè)性去表現(xiàn)共性。恩格斯精辟地概括到:“每個(gè)人都是典型,但同時(shí)又是一定的單個(gè)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shuō)的,是一個(gè)‘這個(gè)’,而且應(yīng)當(dāng)是如此。”[2]36黑格爾在他的《美學(xué)》里,對(duì)于典型問(wèn)題作了詳盡精辟的論述。他認(rèn)為典型人物是普遍性和特別性、共性和個(gè)性的辨證統(tǒng)一體,并進(jìn)一步論述人物與環(huán)境的相互依存的辨證關(guān)系,典型人物須置身于環(huán)境的矛盾斗爭(zhēng)中才顯示出他的性格等等。這些結(jié)論顯然是很有見(jiàn)地的。但是,黑格爾把他的典型理論建立在了客觀唯心主義基礎(chǔ)上,所以還未能科學(xué)地闡明典型的真正實(shí)質(zhì)和它的精義。而馬克思、恩格斯擯棄了黑格爾“主體性格”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的唯心主義觀念,認(rèn)為人不是抽象的“類(lèi)”,而是“現(xiàn)實(shí)中的人”,“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3]因此,典型的本質(zhì)首先是階級(jí)的、時(shí)代的、歷史的,而且是通過(guò)鮮明的、獨(dú)特的個(gè)性顯示出來(lái)的。
據(jù)此,文學(xué)作品所塑造的典型首先就是具有鮮明的個(gè)性,因?yàn)楣残允窃⒂趥€(gè)性之中,只有通過(guò)個(gè)性才能表現(xiàn)共性。馬克思就十分贊賞莎士比亞戲劇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亞化”。恩格斯還具體指出,“一個(gè)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xiàn)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現(xiàn)在他怎么做”,要“把各個(gè)人物用更加對(duì)立的方式彼此區(qū)別得更加鮮明些。”[4]98他們都極力反對(duì)把人物作為表達(dá)觀念的工具這一“席勒式”“理想化”的錯(cuò)誤創(chuàng)作傾向,說(shuō)他把人物作為“時(shí)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恩格斯也批評(píng)敏·考茨基把自己主人公作為抽象原則的化身,使人物的個(gè)性“消融到原則里去了”,還呼吁“不應(yīng)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4]100誠(chéng)然,他們都很強(qiáng)調(diào)人物典型的個(gè)性化。哈姆萊特、安娜·卡列尼娜、葛朗臺(tái)、賈寶玉、阿Q等等,他們之所以成為不朽的典型,首先是他們具有鮮明而獨(dú)特的性格,如果把他們特殊的個(gè)性都去掉,那就無(wú)所謂其自身,也就不成為典型了。
但是,又必須指出的,當(dāng)我們?cè)谖膶W(xué)理論上批判典型的共性與階級(jí)性劃等號(hào),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上批判公式化、概念化的錯(cuò)誤傾向的時(shí)候,有人從相反方面提出典型問(wèn)題基本上是個(gè)性化的問(wèn)題,說(shuō)作家能創(chuàng)造出具有鮮明的、個(gè)性化的人物形象,就不用擔(dān)心其沒(méi)有典型性了。僅有鮮明的個(gè)性就一定有典型性嗎?其實(shí),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反對(duì)脫離人物的社會(huì)階級(jí)本質(zhì),單純追求藝術(shù)效果而去描摹人物表面?zhèn)€性的拙劣個(gè)性化的錯(cuò)誤創(chuàng)作傾向。因?yàn)椋x開(kāi)時(shí)代的、社會(huì)的、階級(jí)的生活土壤,任何人物個(gè)性越強(qiáng)烈越鮮明,就越顯示出它缺乏典型意義,這是馬克思早就批判過(guò)的那種“拙劣的個(gè)性化”傾向的翻版[5]。
其實(shí),藝術(shù)典型塑造成敗的關(guān)鍵,主要由作家的認(rèn)識(shí)能力、思想水平、藝術(shù)技巧決定的,是由作家認(rèn)識(shí)生活的深、廣程度決定的,是由生活本身所含有的思想內(nèi)涵、生活容量和社會(huì)意義所決定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作家寫(xiě)什么,作家對(duì)題材的選擇和提煉,對(duì)作品的內(nèi)容和他所創(chuàng)造的典型的程度,具有不可忽視的制約作用。我們反對(duì)“題材決定論”,但不能連題材對(duì)作品主題的制約作用也一同否定,作家應(yīng)當(dāng)選取最有意義的題材,塑造出典型化程度更高的藝術(shù)形象,題材和對(duì)象本身,對(duì)創(chuàng)作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在“題材多樣化”的口號(hào)下,如果一個(gè)作家忽視了社會(huì)的重大事件而專(zhuān)注于一些只為吸引讀者眼球的題材,把雜七雜八的東西都寫(xiě)進(jìn)作品中去,又怎能塑造出典型形象去反映生活本質(zhì)呢?
三、典型環(huán)境與典型人物的關(guān)系
談到典型,就一定會(huì)想起恩格斯的名言:“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意思是,除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外,還要真實(shí)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6]683對(duì)于這里所提到的“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理論界向來(lái)有諸多的解釋。首先,何謂“典型環(huán)境”?有人認(rèn)為“典型環(huán)境是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的總和”,“是一定時(shí)代的生活關(guān)系和發(fā)展趨勢(shì)”,“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真實(shí)”等等,總的說(shuō)典型環(huán)境就是文藝作品之外的客觀存在的諸樣條件。這樣說(shuō)法離開(kāi)了作為具有審美意義的文藝作品去談客觀環(huán)境,畢竟是無(wú)法揭示文藝作品中典型環(huán)境的真正意義。“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的總和”也好,“一定時(shí)代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發(fā)展趨勢(shì)”也好,“一個(gè)時(shí)代的真實(shí)”也好,說(shuō)的都是指與文藝作品無(wú)關(guān)的純客觀的那種社會(huì)環(huán)境。當(dāng)然,顯示一定歷史時(shí)代的階級(jí)關(guān)系和表現(xiàn)其本質(zhì)現(xiàn)象的客觀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只能是一個(gè)。但是,同一個(gè)時(shí)期眾多的文藝作品就只描寫(xiě)一個(gè)環(huán)境嗎?顯然是不符合創(chuàng)作實(shí)際的。客觀的那個(gè)環(huán)境畢竟是個(gè)大千世界,一部文藝作品也不能寫(xiě)盡那個(gè)包羅宏觀的、微觀的、社會(huì)的、自然的一切事物的浩瀚環(huán)境。文藝創(chuàng)作是審美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是作家再現(xiàn)生活和表現(xiàn)感情的統(tǒng)一體,它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審美意識(shí),作家在創(chuàng)造典型環(huán)境時(shí)必將客觀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加以提煉、概括而鑄造成具有典型意義的個(gè)別形態(tài)的具體環(huán)境,沒(méi)有作家的提煉概括加工,文藝作品的典型環(huán)境是不可能塑造出來(lái)的。所以,典型環(huán)境自然涂上作家主觀的審美色彩,文藝作品只能通過(guò)客觀環(huán)境的某一局部描寫(xiě)并以獨(dú)特的、具體的形態(tài)去體現(xiàn)社會(huì)大環(huán)境的本質(zhì)特征,因此,文藝作品塑造的典型環(huán)境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由于題材不同,描寫(xiě)角度的差異,創(chuàng)造出的環(huán)境肯定也不同。至于是否具有典型性,則看其能否以鮮明的、獨(dú)特的形態(tài)體現(xiàn)出那種時(shí)代大環(huán)境的本質(zhì)了。可見(jiàn),典型環(huán)境就是作品中人物所處的,以個(gè)別形態(tài)體現(xiàn)了那個(gè)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生活本質(zhì)特征和發(fā)展趨勢(shì)的具體環(huán)境,而不是那個(gè)純客觀環(huán)境。
至于典型人物,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那是指寓一定代表性于獨(dú)特個(gè)性的人物形象,正如恩格斯所說(shuō)的“每個(gè)人都是典型,但同時(shí)又是一定的單個(gè)人”。[2]384這里,典型人物的代表性并不從數(shù)量的多寡而定,而是看其究竟有無(wú)概括了時(shí)代的某些本質(zhì)特征,或是否概括了即使是少數(shù)卻能體現(xiàn)事物發(fā)展趨勢(shì)的東西。高爾基《母親》中的尼洛芙娜和巴維爾形象在俄國(guó)20世紀(jì)初期顯然不能代表俄國(guó)工人階級(jí)的多數(shù),但是他們確實(shí)體現(xiàn)了廣大工人群眾和工人階級(jí)先進(jìn)分子在斗爭(zhēng)中成長(zhǎng)和發(fā)展的歷史趨勢(shì),所以他們都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至此,又很自然地使人想起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兩者的關(guān)系來(lái)。恩格斯給哈克奈斯的信,批評(píng)她的小說(shuō)《城市姑娘》曾說(shuō)過(guò):“你的人物……是夠典型的;但是環(huán)繞著這些人物并促使他們行動(dòng)的環(huán)境,也許就不是那樣典型了。”[6]683很明顯,典型人物和典型環(huán)境顯然是共處對(duì)立統(tǒng)一體中矛盾的兩個(gè)方面,既是互相依存,又各有獨(dú)立性。可能有這種情形:人物典型或較典型,但環(huán)境不典型或不夠典型;或情況相反。典型作為反映生活的一種方式或形式,總是要揭示出某種程度的真理,而人物對(duì)真理的認(rèn)識(shí)又總是相對(duì)的,所以,典型也還有程度高低強(qiáng)弱之分。從古今中外大量創(chuàng)作實(shí)踐來(lái)看,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是相鋪相成、互為條件的,總不可能有人物十分典型而環(huán)境不典型或環(huán)境十分典型而人物不典型的作品。恩格斯在評(píng)論《城市姑娘》時(shí)運(yùn)用辨證法的觀點(diǎn)指出,作品的人物在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來(lái)說(shuō),“是夠典型的”,這里說(shuō)是在那具體環(huán)境中人物的獨(dú)特個(gè)性蘊(yùn)含著一定的代表性,“夠”上這基本的“典型”條件,并不是說(shuō)其典型性“夠”充分了;他又指出,作品描寫(xiě)的環(huán)境“就不是那樣典型了”,也可以說(shuō),從時(shí)代的、更大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范圍來(lái)看人物,“就不是那樣典型了”。在這里所說(shuō)的,人物“夠典型”僅僅是“夠”條件罷了,人物典型性的不充分強(qiáng)化不了環(huán)境的典型性,環(huán)境的不典型又影響和削弱了人物的典型意義。不具有典型性的環(huán)境可能產(chǎn)生典型人物,但這典型人物是不充分的,充其量只夠格而已。我們絕不能這樣理解:《城市姑娘》人物夠充分典型,而環(huán)境就不典型。
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學(xué)說(shuō),是批判地吸收和繼承了西方典型理論的精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科學(xué)的典型觀。這種典型觀是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科學(xué)總結(jié),用辯證唯物觀點(diǎn)解決了典型本質(zhì)、典型的共性與個(gè)性、典型環(huán)境與典型人物等一系列問(wèn)題。總之,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觀是充滿了深刻的、生動(dòng)活潑的內(nèi)容,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文藝?yán)碚摻萄惺?馬恩列斯論文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4.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I025
A
1673-8535(2014)05-0071-04
林瑩秋(1980-),女,廣西陸川人,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基礎(chǔ)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xué)。
(責(zé)任編輯:覃華巧)
2014-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