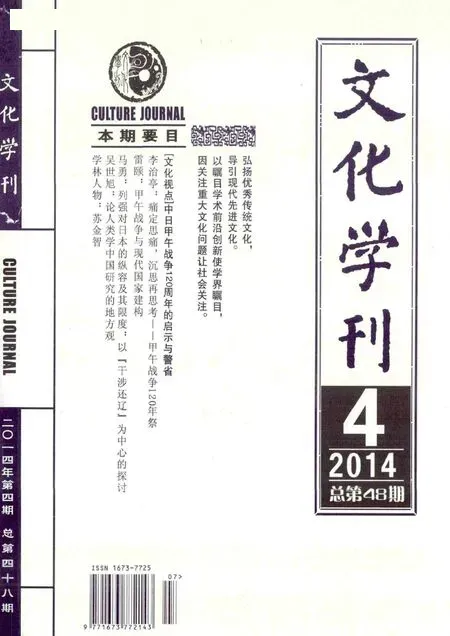論人類學中國研究的地方觀
吳世旭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和國家與社會理論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前者以可靠的田野作業為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而詳實的經驗素材,后者則以精到的見解豐富了理論探討的可能性。盡管如此,但它們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地方(place)這個基本概念缺乏足夠的理論關注,暗含二者之中的不同地方觀及其學術建構,是導致這種理論后果的根本原因。現象學家凱西 (Edward Casey)對地方進行的長時段“知識考古”表明,相對于較晚出現的空間 (space)概念而言,地方具有超越歷史的先在性,而從鮮活的地方之中抽象出來幾何學空間,是在現代性的頌揚下才成為知識生產和社會建構的關鍵概念的。[1]這個理論見識對于審視上述問題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并有助于激發新的問題意識和人類學中國研究的理論拓展。
一
在諸如村莊這樣的小地方中獲取據以施展學術想象力的經驗素材,很長一段時間都構成了人類學中國研究的不二利器,至今未衰。這種潮流有著復雜的歷史與學術淵源,[2]而對民族志方法的運用是其關鍵因素。與此同時,民族志與生俱來的空間化地方觀及其影響,也隨之滲入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之中。
小地方與大社會之間的關系并非是人類學中國研究的特殊問題,它在總體人類學中同樣是一個核心主題。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認為,社會人類學的本質在于處理整體,但自從民族志方法發明以來,整體就逐漸以某個地方文化的形式出現,從而構成了一種“人類學的島嶼”。[3]作為現代人類學的一個重要標志,民族志方法的形成與馬凌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有著莫大的關系,正是他首先將其創造性地應用于自己的研究實踐之中,并對之做出了全面而細致的闡述,[4]從而確立了其在現代人類學中的基礎地位,使田野作業乃是人類學者的“成丁禮”成為一種基本的共識。這種經典民族志方法的本質在于,把意蘊豐厚的地方看作是現實生活的容器,以使致力于從生活中萃取抽象的社會與文化的人類學家展開實地的田野作業,具有理論上的合法性。把地方等同于進行田野作業的地理空間,體現出了人類學對地方一廂情愿的主觀建構,這種建構的思想源頭恰恰來自于凱西所言的由地方到空間的現代知識轉變。單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將地方加以空間化處理似乎無可厚非,然而,這卻對理論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地方自身理論價值的嚴重忽視。
盡管馬凌諾斯基發明的民族志方法后來受到了眾多批評,但其將地方空間化的理論傾向,非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愈加嚴重。例如,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在強調“深描”之于人類學的重要意義時指出,以為能夠從所謂“典型”村莊中發現社會、文明或宗教本質的觀念,顯然是一種謬見;他認為,“人類學家不研究村莊,他們在村莊里作研究”,人類學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研究不同的事物,但卻不能把地方作為研究對象。[5]又如,阿帕杜萊 (Arjun Appadurai)對經典民族志的批評指出,作為田野作業的地點,地方已經逐漸成為人類學特定理論的隱喻,構成了一個壓制“多種聲音”的圓形監獄,地方問題因此最終乃是一個關乎權力的問題;[6]他認為民族志的生產應該注重對多種聲音的呈現,并在任何一個地方充分挖掘研究主題的多樣性。[7]不管是格爾茲的“深描”還是阿帕杜萊的“多種聲音”,都試圖在小地方與大社會的題域中找到突破馬凌諾斯基經典民族志方法的可能途徑,但他們所運用的地方概念暗含的仍然是現代知識中空間化的地方觀,而正是對“多點民族志”的強調,使這種觀念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同時也于無形之中助長了忽略地方自身理論價值的理論勢頭。
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對地方自身理論價值的漠視,不僅與長時段的觀念史息息相關,而且與現代社會科學的興起與發展緊密相連。人文地理學家阿格紐 (John Agnew)對地方在社會科學中的“貶值”所進行的學術史考察表明:一方面,由于保守的社會科學把地方和共同體 (community)聯系起來,并將從共同體到社會看作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模式,所以導致地方研究胎死腹中,而作為“冷戰”中意識形態武器的現代化理論又在地方的棺木上加了一顆釘;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則將商品化的力量絕對化,并認為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必然會破壞地方的社會意義,因此看不到地方在現代社會與社會科學中存在的余地。[8]如果說保守的社會科學是在一種懷舊的憂郁中悲嘆地方的逝去,從而失去了拯救地方的學術勇氣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則是在一種怨憤的激情中歡呼地方的沒落,從而剝奪了地方研究的學術生命。雖然人類學更多地是以非西方社會為對象,并主要體現為對和現代社會相對應的共同體加以研究,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于整體社會科學的理論取向,但是,這種研究本身恰恰是以“共同體-社會”的理論模型為前提,并帶著一種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所說的“熱帶的憂郁”[9]投入到對現代社會的省思之中。正是在這種理論傾向的主導下,民族志方法在人類學的研究中獲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沿襲了地方是生活之容器的理論假設。
與整體人類學一樣,民族志方法也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其與生俱來的空間化地方觀同樣影響深遠。就本土人類學而言,空間化的地方概念最初是潛伏在由community翻譯過來的“社區”一詞背后,進入本土人類學的研究當中的,并在民族志方法的影響下成為理解社會的基本認識單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學派”的倡導者和領軍人物吳文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對社區方法進行的表述中強調,通過特定社區的研究可以了解抽象的社會,而“社區乃是一地人民實際生活的具體表詞,它有物質的基礎,是可以觀察到的”。[10]吳文藻開創的“中國社會學派”希望通過對社區研究的累積與比較來達到對抽象社會的整體認識,暗含其中的同樣是“共同體-社會”的理論模型,其背后的主導觀念也來自于現代知識,特別是其中空間化的地方觀。
盡管在社區方法的指導下,涌現出了諸多中國本土學者撰寫的具有廣泛影響的人類學著作,但是,對于社區方法在中國研究中的適用性,人類學者卻持有各不相同的見解。對社區研究方法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馬凌諾斯基表現出了模棱兩可的態度,在為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所作的序中,他一方面強調中國“有著最悠久的沒有斷過的傳統”,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漢學家的歷史工作應該“互為補充,且須同時使用”;另一方面又認為費孝通對一個小村落的研究使“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并揭示了“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基礎是多么結實可靠”。[11]利奇 (Edmund Leach)在評論中國本土學者的四本人類學著作時,也對《江村經濟》給予了肯定:“與所有社會人類學的優秀著述一樣,其核心內容是關于關系網絡如何在一個微型社區中運作的細致研究,”并認為這種研究沒有或者不應該自稱代表任何意義上的典型,其意義在于它們本身。[12]雖然利奇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費孝通的學術追求,但他顯然并不排斥社區方法在人類學中國研究中的應用。與馬凌諾斯基和利奇不同,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明確地提出了對社區方法的質疑,認為它對于研究復雜的文明社會并不適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應該借鑒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會結構的方法,在更大的空間和時間中探討社會運作的機制。[13]盡管弗里德曼對人類學中國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但他的忠告并未導致人類學家對民族志方法的放棄,相反,隨著人類學研究在香港與臺灣地區的展開以及中國大陸的開放,以小地方為單位的研究卻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而本土人類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則使小地方更多地出現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之中,并產生了大批的“村莊民族志”。在這個過程中,以小地方來反映復雜社會的方法問題進一步得到了深入的討論,[14]雖然依舊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卻大都不再停留于社區方法是否適用的爭論上,而是追問如何通過小地方來研究大社會。
不管怎樣,社區方法與經典民族志方法對地方的理解沒有什么本質不同,都是把地方等同于生活的容器,并且將之視為一種人類學的常識。由于二者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和整體人類學一樣,這種空間化地方觀的負面影響也深深地浸入到了人類學中國研究的理論傳統之中。
二
“中國社會學派”采用社區研究方法是為了認識中國社會,對社會整體以何種形態存在則似乎抱著一種開放的態度,其理論探討也暗含著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在西方學術話語的支配和影響下,這種彈性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壓縮了。當弗里德曼帶著人類學家從簡單社會中建構的理論成果進入文明中國的研究領域時,國家的存在無疑具有巨大的理論沖擊力,而他引入的國家與社會的理論框架也深刻地影響了很多人類學家的中國研究。在這些研究中,地方不僅作為生活的容器為人類學家提供了田野作業的地點,同時也作為一種文化觀念隱藏在society即“社會”一詞的背后,成為與國家相對的抽象存在。地方相對于國家存在的觀念并非人類學家的發明,而是本土社會與文化的歷史產物。中國社會中心與邊緣的政治結構形塑了中央與地方的觀念形態,并使之成為中國人認知社會的一種文化常識。國家與社會理論框架主導下的人類學中國研究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歷史,并以不同的方式對之加以重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空間的觀念成為不同論述的共同基礎,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地方自身的理論價值。
弗里德曼通過宗族組織的研究來呈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認為邊陲狀態、水利與稻作生產共同促成了中國東南宗族組織的發達,宗族組織的現實形態可以歸納為從A到Z的一系列理想類型,這些宗族組織不僅相互之間存在爭斗,同時也聯合秘密會社來對抗作為其共同敵人的國家。[15]在弗里德曼早期的宗族研究中,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地方隱含在宗族與國家的對立結構之中,并未得到直接的關注,但是,隨著宗族研究的深入,他意識到了應該對地方、地區和社會組織的社會地形學如何被納入到官方地圖中保持敏感,并認為行政地圖的權限規劃與社區及其群體的構造大致甚至完全吻合,而地方民兵系統的出現則把社會地圖引入了官方地圖。[16]這里所言之地方和地區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與國家相對應的“基層社會”,而與很多海外漢學家一樣,弗里德曼在國家與社會的結構關系中來看待地方的學術傾向,很明顯是受到了中國本土文化常識的影響。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對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認為“把中國疆域概念化為行政區劃的特點,阻礙了我們對另一種空間層次的認識”,并把這種空間結構稱為“由經濟中心地及其從屬地區構成的社會經濟層級”。[17]施堅雅對中國本土文化常識的學術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暗示著人類學中國研究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論可能。遺憾的是,他的“區系理論”在強調經濟力量對中國社會結構具有根本性支配的同時,認為非正式的市場區系與正式的行政區系之間存在著同構關系,二者并非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在社會空間上相互兼容,這實際上無非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關系中增加了對經濟因素強調,仍然沒有擺脫國家與社會理論框架的根本影響。弗里德曼和施堅雅都是在宏觀上來研究中國社會,前者把地方抽象為與國家對立的存在,后者則把地方置于經濟區系的網絡節點上,其核心觀念都是把地方等同于社會空間,從而使地方自身的理論價值埋沒在社會結構的宏大理論之中。
盡管弗里德曼和施堅雅之后的人類學家更多地是在小地方做研究,但是,這種微觀的社區分析同樣大都是以國家與社會的理論框架為根基,并通過小地方的研究來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仍然沒有充分意識到地方自身的理論意義。王銘銘在這些研究中辨識出“行政空間理論”和“宗教與象征理論”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18]行政空間理論強調地方的政治角色,從國家控制基層社會的角度來思考地方,視國家為一種政治的、全民的、軍事化的力量,國家對基層體系的建構,目的在于控制社會,基層社會因此處于消極的、被動的地位。宗教與象征理論則注重當地觀念,從基層社會回應國家的角度思考地方,認為,基層社會通過象征自主地建構地方。但是,這種自主建構同樣與國家緊密相關,比如,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認為基層社會的自我表述中潛藏著一種“帝國隱喻”的邏輯;[19]桑高仁(Steven Sangren)則認為,一方面,基層社會在通過進香儀式削弱了自身穩固感的同時,也突出了地區權威和王朝權威的功能,[20]另一方面,傳統陰陽宇宙觀的階序化使基層體系的階序化擁有了合法意義,國家因此有足夠能力在民眾意識中確立支配權。[21]在王銘銘看來,行政空間理論對特定地方的普通民眾如何看待地方關注不夠,而王斯福和桑高仁則在此處取得了成功,并發展出了可以用于理解民間文化觀念的理論模式,但是,在認為民間社會的文化觀念乃是模仿了官方關于基層社會階序化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界定方式的同時,他們仍然沒有回答民間社會模仿的究竟是官方行政空間還是別的什么東西這個更為根本的問題。[22]
在關于泉州的“鋪境”制度和“東西佛”械斗的經典研究中,王銘銘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鋪境的研究通過把行政空間理論和宗教與象征理論糅合起來,具體考察了行政空間與基層社會的文化認同究竟在何處契合、何處分野,認為鋪境既為官方提供了一種社會的空間設計方案,也提供了一種帝國的理想模式,而基層社會不僅通過民間傳說和慶典活動來反映和模仿這種理想模式,而且對之加以反饋,從而使帝國模式和民間模式之間在表面的妥協下形成一種矛盾關系,前者服務于帝國的政治目的,強調的是“秩序”,后者則表達了民間社會對在晚期帝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喪失的自主性的懷舊之情,突出的是基層社會的團結和“社區競爭”。[23]“東西佛”械斗的研究通過政治個體、時間與過程的歷史敘述,探討社會的地形學與官方的地圖之間互動的具體方式,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械斗本來是基層社會的一種節慶活動,這種活動以不同的文化意義自主地形塑了基層社會的階序模式,但是,在政治個體的手中,卻成為官方控制社會的策略,并在不同的官方策略中被賦予不同的政治意義。[24]王銘銘的研究同樣暗含著一種對本土文化常識加以反思的努力,然而,與施堅雅不同的是,他更強調文化象征與政治力量之間的互動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單純以政治或經濟因素來解釋基層社會的不足,同時也使文化與象征建構基層社會的具體方式得到了深入的探討。盡管如此,國家與社會的理論框架仍然構成了其濃妝重彩之下的底色,而在對歷史的重視中也在某種意義上帶有整體社會科學所秉持的從共同體“發展”到社會的基調。
很難說國家與社會理論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形成了庫恩 (Thomas Kuhn)所說的“范式”,[25]但它確實構成了一條清晰的主線,對諸如宗族與國家、經濟區系、行政空間、宗教與象征等理論主題的探討大都圍繞這條主線而展開。盡管這些探討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人類學中國研究的理論可能性,但國家與社會理論把地方等同于社會空間的理論傾向,也明顯限制了其更具彈性的理論延伸。
三
通過民族志方法的運用和國家與社會理論的建構,地方在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概念意涵。前者把地方等同于容納社會生活的地理空間,基于人類學常識在方法的層面上強調其作為社會與文化表演場所具有的民族志價值;后者則把地方抽象為相對于國家而存在的社會空間,基于中國本土常識在理論的層面上強調其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場域具有的分析價值。或許對于很多從事中國研究的人類學家來說,民族志方法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國家與社會理論也與中國的特征相契合,但是,從更普遍的歷史角度來看,地方并非是人類學建構出來的田野作業的地理空間,亦非相對于國家而存在的社會空間,作為人類生活中一種基本范疇,地方自身具有更根本的文化內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凱西的地方研究對于人類學的啟發意義,顯得彌足珍貴。這種啟發首先在于使我們認識到,對地方的空間化處理,并非是人類學家有意為之,而是現代知識的潛移默化所致;而經由人類學的自我反省,進一步的判斷在于,從地方到空間的歷史轉變本身也是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產物,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充滿了人類學據以擴展其理論領域的多種可能。
對于凱西的哲學論述,似乎并未得到人類學家足夠的重視,例如,王斯福認為,凱西在堅持地方的動態性方面值得肯定,但卻不解于他為什么把存在當作哲學沉思的原始對象,同時把身體作為衡量世界的起點,并以澳大利亞土著和漢人的宇宙觀為論據,得出了他的研究具有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morphism)缺陷的判斷。[26]實際上,凱西關于地方的知識考古和哲學思索,并非是意在探討地方的“動態性”,而是通過地方與空間的觀念史追溯,對二者加以區辨,以此來指出地方超越歷史的先在性。地方之所以超越了歷史,是因為它并不取決于人的存在與否或以何種方式存在,而正是這種先在性使人對地方的感知成為可能,通過和身體的相互作用,地方便具有了方向性。[27]凱西關于地方的哲學研究并非無懈可擊,但他對地方與空間觀念做出的區辨及其觀念史解析卻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斯福對凱西的批評就顯得有點南轅北轍了。雖然現象學還原體現出了鮮明的去文化和去社會的特征,但卻正是其獲得理論洞見的根本依憑。現象學還原看似具有反社會與反文化的傾向,實則是以去社會和去文化的方式“朝向事情本身”,并未否認社會與文化的歷史存在及其意義;而凱西的研究表明,空間觀念不過是歷史建構的產物,它是對人類經驗到的地方加以抽象的結果。雖然不同文化中的宇宙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空間的觀念,但同樣是地方進入歷史的具體表現。王斯福進行學術批評的嚴肅態度是毋須懷疑的,然而,對現象學的有限排斥卻也難掩人類學的些許“傲慢”,以致無法在常識的迷霧中看清地方的全貌,而他把地方營造(place-making)看作是一個中心化的過程,顯然受到了漢人社會中心與邊緣的政治結構及其造就的中央與地方的文化常識的影響。
盡管如此,但筆者并不認為直接面對現象學意義上的地方應該成為人類學的選擇,相反,在充分認識到地方觀念史之中必然包含了豐富的社會與文化內涵的基礎上展開理論探討,才應是人類學的分內之事。現象學研究并不在社會與文化的意義上關注地方文明化的具體過程,而以往人類學對地方的空間化理解,則通過對地方的無意識拆解,使具有豐盈之態的地方概念轉化為干癟的空間概念,從而無法意識到地方本身的理論價值。對于人類學研究而言,地方概念之所以具有理論價值,并不在于它的先在性,而是其由先在進入歷史的過程。換言之,如果說現象學是經由對社會與文化的去除來還原地方的原初意義,那么,人類學則應將原初意義上的地方回復到歷史之中。現象學洞見到了地方超越歷史的先在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存在于歷史之外,相反,對于人類社會來說,地方不可避免地會進入歷史。在進入歷史的過程中,地方被披上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外衣,成為人們展開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從而使自己獲得了社會生命,并在歷史的過程中處于不斷的營造之中。這不僅構成了地方在人類學研究中具有合法性的基本資質,而且構成了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地方超越歷史的先在性是毋庸置疑的,現象學把復數的歷史去除掉以朝向事情本身,把豐富的歷史還原為人與物,而人類學對社會與文化的倚重卻在此處語焉不詳,似乎社會與文化是自己生成的;只有認識到地方的先在性并將其重新納入到歷史之中,社會與文化的概念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性,因為是人與物的互動開啟了歷史,社會與文化的源頭在于地方的歷史化,二者不過是豐盈地方的一種方式,因此,如果說現象學探究的是“地方為何”的問題,那么,人類學關心的則是“地何以方”的問題。
基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盡管民族志方法和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但它們對地方的空間化處理卻在理論上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如果帶著地方概念及其問題意識,重新回到人類學中國研究之中,那么,無疑會有助于以往研究的反思和理論領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