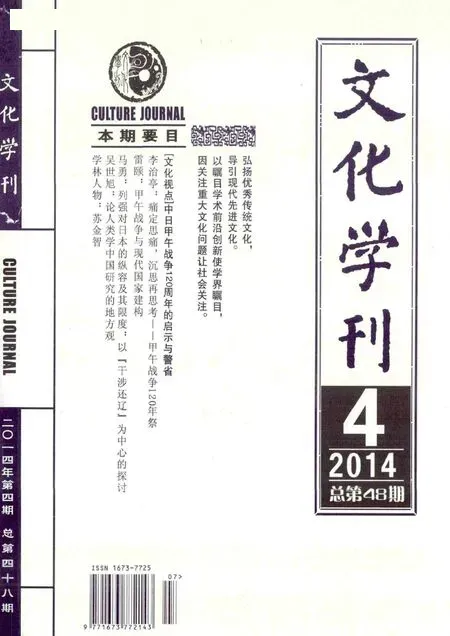《聊齋志異》的巫術文化與阿列克謝耶夫的俄譯闡釋
李逸津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4)
俄譯《聊齋志異》及“聊齋學”研究是現代俄羅斯漢學泰斗B·M·阿列克謝耶夫院士 (1881~1951)近半個世紀學術生涯中的一個亮點。1906至1909年,阿列克謝耶夫被派往中國學習,期間他隨法國漢學家沙畹在中國華北進行了4個月的旅行。這次中國之行使阿列克謝耶夫搜集到大量的民俗學材料,也就是在此期間他知道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并且產生了翻譯和研究興趣。這一方面是因為教他學漢語的“中國先生”拿《聊齋志異》給他作教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從《聊齋志異》中看到了中國17至18世紀的世俗生活和民間風情的描寫,而這恰恰可以為他當年中國之行的主要目的——搜集和研究反映中國人日常生活與信仰的民間繪畫,作文字的補充和說明。阿列克謝耶夫的女兒——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員M·B·班科夫斯卡婭女士在《聊齋的朋友與冤家》一文中曾經指出:“對中國民間創作,特別是版畫的關注加深了阿列克謝耶夫對于《聊齋志異》的興趣,因為在這部作品中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1]
將中國民間版畫與《聊齋志異》作為互相印證的民俗學材料,加之阿列克謝耶夫本人在中國民間的實地考察,使他不僅對《聊齋》文本作出了精湛的俄文翻譯,還對其中涉及的中國民間風俗信仰、婚喪禮儀等各方面民俗實況,作了細致的注釋和解說。這就使得他的《聊齋》譯本不只是文學作品的翻譯,還具有民俗學、文化學研究的性質。這里,我們擬介紹阿列克謝耶夫俄譯《聊齋》注釋中對中國民間巫術、占卜術的解說與評論。
巫術觀念是人類自史前時代起就具有的一種精神信仰。由于生產力和認識水平的低下,因此人類面對大自然的無窮威力感到由衷的恐懼和敬畏,但又幻想通過某種神秘的力量來控制和操縱大自然,于是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法術,這就是巫術。巫術是一種具有普世性的精神活動,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已的巫術體系,中國民間巫術更是源遠流長。在自詡“雅愛搜神”“喜人談鬼”的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就有不少巫師、道士運用巫術降妖除怪、驅災辟邪的情節,涉及諸多中國巫術的具體方法,為研究中國民間巫術提供了形象的史料。而阿列克謝耶夫俄譯《聊齋志異》注釋中對此所作的解說,又有向域外讀者傳播中國巫術文化的意義,值得我們梳理和研究。
中國民間巫術最常見的是畫符、貼符。“符”是中國道教創立的一種法術,指書寫于黃色紙、帛上的筆畫屈曲、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的符號或圖形,估計與古代中國人對文字本身的神秘崇拜有關。《嬰寧》篇中王子服的表兄吳生回憶自己的姑丈曾被狐所祟,并生有一女。姑丈死后,狐還常來,“后求天師符粘壁上,狐遂攜女去。”阿列克謝耶夫將這里的“天師符”譯作“天師辟邪的文字”,解釋說:“天師即張天師,他的封號之一是‘具有天的力量的老師’他的通常名稱是東方高峰 (泰山)的神靈,地點在山東。這個祭司是迷惑人們的卑微魔鬼的高級領導人。他書寫的文字、帶有印記的紙片,被認為確實能夠抵御一切邪惡。”[2]但我們說,張天師是對五斗米道創立者張陵及其后代世襲繼位者的通稱,他世居江西龍虎山,而位居泰山的神靈是東岳大帝,中國民間認為泰山是管轄鬼魂的地方,阿列克謝耶夫在這里是把兩種傳說混淆了。所謂天師符即用黃紙蓋以朱印,繪有張天師、鍾馗等圖像,粘于中門以避邪驅祟的符咒。當年阿列克謝耶夫在中國旅行期間,曾經大量搜羅和記錄一般歐洲漢學家所不屑的各種民間招貼、牌匾、廣告、符箓等有文字題銘的實物材料。他寫道:“中國是一個大村子,也是一件大古董。只有墻上、門上、門框上、頂子上、船上的題銘在描繪當今活生生的中國。”[3]在他身故后于1966年出版的《中國民間繪畫》一書中就收有他從中國帶來的各種符箓圖像。因此他對中國“符咒”的解說,是有實物依據的。《胡四姐》篇說尚生家人請來巫師作法降狐,“符咒良久”。阿列克謝耶夫釋曰:“辟邪的圖形咒語,它造成了用漢字寫的巨大文獻,乃是稀奇古怪的變化的象形字,還有決定人命運的星星象征。類似咒語的一般公式是:‘雷劈 (打死)鬼!’,有時這個句子又加上一個符頭‘敕令’,如‘奉天師敕令滅鬼,賜吾魔力’。”[4]從中可見他對中國“符咒”了解的詳細。
中國巫師道士在施行法術的時候,還有特定的步法動作,即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轉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稱“步罡踏斗”。因其相傳為大禹所創,故又稱“禹步”。《胡大姑》篇寫巫師降狐,“禹步庭中”,阿列克謝耶夫注“禹步”道:“神話的國君禹 (公元前23世紀)疏導國家的河流,很疲勞并且生病了。他的腿歪斜并干枯,他邁步走,但沒有一只腳能走在另一只腳前面。中國念咒者在這種步伐中看到了自己占卜的一種特別實際的手段。他們相信在這種時候,按照星座來走,最終會有幫助。”[5]戰國時人所撰《尸子》云:“禹于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手不爪,胚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此應為阿氏解說之所本。
中國巫師作法往往要用一些法器,最常用的是桃木劍。桃木辟邪的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淮南子·詮言訓》曰:“羿死于桃棓”。東漢許慎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畫皮》篇中描寫道士降妖“仗木劍,立庭心”,阿列克謝耶夫釋“木劍”曰:“有魔法的劍,念咒者的主要標志物。”在注釋《妖術》篇中“倚劍”一詞時,他說:“為了‘劈開’不潔力量,所有中國的念咒人都用劍。學會這個傳統的俗人不懷疑它對于理智來說是明確的、成功的符咒方法。”[6]在《畫皮》的注釋中,他還說:“有時這種‘寶劍’由刻有神秘花紋的錢幣做成。”[7]中國舊時有用絲線連綴古銅錢成劍形,據說是鎮宅辟邪消災最有力的法物。而阿列克謝耶夫也是研究中國古代錢幣的專家,他在1913年被聘為科學院亞洲博物館館員后,曾為博物館鑒定、整理過中國錢幣,并親手編寫了亞洲博物館和彼得堡大學館藏中國錢幣的大部分卡片和目錄。因此,他能在注釋“木劍”時提到錢幣劍,估計是他親眼見到過這樣的實物。
施行巫術還常用到圖形、偶像,這在巫術中屬于模擬巫術,即通過模擬某物的形貌或狀態來對該事物施加影響。《聊齋》故事中如《胡氏》篇提到“芻靈”,《妖術》篇提到“紙人”“土偶”。阿列克謝耶夫釋“芻靈”為“用于祈禱的紙質畫像”,[8]釋“紙人”為“中國交感巫術的方法,準確地說出相應的祈禱文或咒語并寫在希望變成現實的紙形上,紙形就會變成活人或者與其合一,在他身上產生未知的后果”,[9]釋“土偶”曰“非常便宜和有輕便特點的塑像”,并特別指出:“位于列寧格勒老村喇嘛寺里的佛像就是用的這種塑造方法。”[10]這里他對“芻靈”的解釋稍有不確,因為“芻靈”是用茅草扎成的人形馬形送葬物,而非紙質畫像,其他兩條的解釋還都是正確的。
巫師們用來降妖除怪的法器除木劍外,還可以用一些生活中的器物,如《畫皮》篇說道士“以蠅拂授生,令掛寢門”。阿列克謝耶夫注釋道:“為了詛咒和驅逐兇神及所有妖精,念咒人不只是在門上放一把具有降妖魔力的劍,還有一些無害的物品,如扇子、蠅拂等。這樣一來,人類活動的對象就被用來反對妖魔力量的不可見世界。”[11]當道士殺掉妖怪后,乃“出一葫蘆”,將其所化煙霧吸走。由于俄羅斯沒有“葫蘆”這種植物,因此阿列克謝耶夫將其譯作“瘦南瓜”,并解釋道:“是一種瘦長的、帶攀藤的細頸南瓜,曬干到充分變硬,可以用作盛藥的容器。在圣像畫上被描繪為仙人的標志物。”[12]這也是由于阿列克謝耶夫手中掌握中國繪有葫蘆形象的圖畫,因此才能做出這樣的解釋。
中國民間認為具有驅鬼辟邪作用的植物還有葵花,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記載:“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遞相宴賞。”[13]可知古代有以葵花辟邪的風俗。《小梅》篇中狐女小梅囑咐夫君:“家有死口時,當于晨雞初唱,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阿列克謝耶夫注釋“葵花燈”曰:“按照迷信的觀念,葵花可以驅逐鬼的魔力。”[14]但上述《聊齋》故事中說的是“葵花燈”,即葵花形狀的燈,而非葵花,阿列克謝耶夫單單拈出“葵花” (俄:подсолнечник,向日葵)來注釋,很可能與俄羅斯人以向日葵為國花的民族心理有關。這樣的解釋無疑拉近了俄國讀者與中國民俗文化的心理距離。
與巫術相關的還有占卜。占卜術也是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人類無法掌控自己的前途命運,但又渴望判斷未知事物或預測未來的一種精神性的實踐活動。漢字“占”意為觀察,“卜”是用火灼燒龜殼,以其出現的裂紋形狀預測吉兇福禍。后來發展出相面、測字、掣簽等多種占卜方式。《聊齋》故事中提到許多民間占卜方法,如《醫術》篇說一道士“善風鑒”,阿列克謝耶夫注釋曰:“根據臉部特點的一種占卜術,在中國非常普及。人面特征方面的文獻相當廣泛,但是同所有神秘主義文章一樣,全是用不可翻譯成一般語言的風格寫成的。”[15]《云蘿公主》篇云蘿公主借一婢女腹產子,嬰兒降生后說“此兒福相”。阿列克謝耶夫注釋“福相”曰:“根據面孔輪廓的預言,如其他占卜形式一樣,在中國具有眾多書籍。”[16]從中可知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相書有一定的了解。
中國民間預測未來最常用的方式是到廟宇中去求簽。《錢卜巫》中說巫婆把商人提供的錢“盡內木筩中,執跪座下,搖響如祈簽狀”。阿列克謝耶夫注“祈簽”曰:“手拿帶有刻著行列數字的小棍的罐子,跪在神龕前,自己祈禱以后,然后抖晃一下罐子,取出小棍簽。和尚或者寺廟里的仆役去看書,那上面寫著神靈對每一個簽上將要發生的情況,其中包括為跪求簽卦的人讀到的去病的藥方。不過,如果廟里有印刷好的神諭的文本,那么,所有的人都能憑某種酬金買到它,以便在家里讀這些預言。”[17]對照阿列克謝耶夫本人在其《1907年中國紀行》中對中國廟宇求簽方法的記載,可知他的這些解釋都是有親眼所見為依據的。[18]
祈簽之外,中國民間更便捷的占卜方法還有擲錢幣,以錢幣落下后的正反面來測吉兇否泰。《錢卜巫》篇說巫婆把錢放入簽筒搖晃后,“傾錢入手,而后于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為否,幕為亨。”阿列克謝耶夫注釋道:“中國錢幣從7世紀起就在正面刻有這樣的字:‘某朝通寶’,也就是被加給國君的年號,而避免使用他的名字。這些字先是手寫,然后做出粘土的模子,再澆鑄出錢幣。字都是由著名書法家寫的,而且按錢幣出品的時代有明顯的不同。錢幣的背面通常是沒有字的。”[19]這條注釋不是講占卜方法,而是介紹中國的錢幣,很明顯是運用了他到中國考察和在自己國內博物館從事中國錢幣鑒定整理工作,而積累起來的豐富的中國錢幣知識。
《聊齋》中提到的中國民間占卜方法還有“鏡聽”。此法相當古老,唐人《鏡聽詞》中就有句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 《聊齋志異》中的《鏡聽》篇即以此法為標題。文中說二媳婦盼丈夫考試得中,“竊于除夜以鏡聽卜”。阿列克謝耶夫注釋道:“由以下方法構成的占卜:取一精制古代銅鏡,獨自進入廚房,面向灶神 (灶王),許下咒語。然后走路偷聽談話,以確定未來的吉兇。再閉眼走七步,睜開眼,對準鏡子,其中照見的東西,合乎偷聽來的話……‘占卜沒有不符合實際的。’——在記載此事的文章中這樣說。”[20]考元人伊世珍《嫏嬛記》卷上云:“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神灶,雙手捧鏡,勿令人見。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兇。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估計即為阿列克謝耶夫注釋之所本,他的引文,也是由此而來的。
《聊齋》中被視為吉兆的占卜術還有聽喜鵲叫。此觀念也由來已久,據唐人張鷟《朝野僉載》所記:“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喂之。后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系南康獄,月余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也。”[21]可見喜鵲報喜的說法還不僅是因其名字中有“喜”字,故能象征喜悅,它還有幫人解困、預報人回家的功能。阿列克謝耶夫注釋《蕭七》篇中“晨占雀喜”一語曰:“喜鵲預兆喜悅,它的叫聲被認為是好的兆頭。它還部分地預兆出門人返回。”[22]可能就是由這個故事產生的聯想。
上述阿列克謝耶夫俄譯《聊齋志異》注釋中對中國民間巫術、占卜術的闡釋與解說,體現了他對中國民俗文化了解的全面和深入。同時相對于其他歐美漢學家來說更為可貴的是,阿列克謝耶夫的闡釋有他在中國親眼見到的實證材料和繪畫塑像等造型藝術實物的依據,因而他的解說就更為細致到位,更為生動可信。可以說,阿列克謝耶夫的俄譯《聊齋志異》注釋促進了中國民俗文化在域外的傳播,這是他對“聊齋學”研究的貢獻,也是對中國民俗文化研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