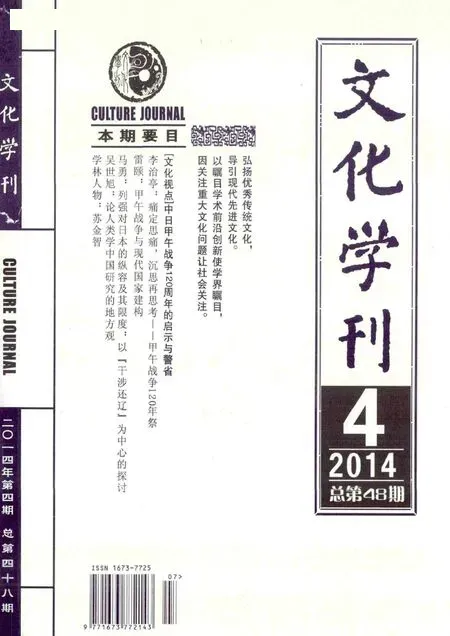劉昌詩《蘆浦筆記》之“蘆浦”考
——就劉昌詩“來任南監(jiān)說”與潘楊二先生商榷
萬 軍
(溫州大學圖書館,浙江 溫州 325035)
《蘆浦筆記》素來以“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變遷,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著稱[1],且因其知識廣博、治學態(tài)度嚴謹、頗多獨到之見,特別是書中保留了一些珍貴的史料和遺文佚事而備受推崇。《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收錄此書。中華書局將此書列入1986年出版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但關于劉昌詩此書的寫作地點、書名蘆浦究竟何指等問題,一直以來眾說紛紜、語焉不詳。
因為書名“蘆浦”二字與蒼南之“蘆浦”相關,且當?shù)貤钍献遄V中存有相關佚文,所以《蒼南歷史文化》2011年第03期發(fā)表了楊乃琦先生的文章 (以下稱楊文),文末引用溫州市圖書館研究員潘猛補先生的考證結論稱:劉昌詩《蘆浦筆記》中的蘆浦,當在今蒼南之蘆浦無疑。二者是否真的有聯(lián)系呢?劉昌詩真的來任天富南監(jiān)場鹽大使嗎?本文通過目前所能見到的相關文獻予以整理考證,也謹以此與潘楊二先生商榷。
一、劉昌詩生平簡述
《蘆浦筆記》作者劉昌詩,字興伯,為宋時臨江軍清江人氏,南宋開禧元年(1205)毛自知榜進士[2]。據(jù)《江西省志·行政區(qū)劃志》[3],宋時清江隸屬于臨江軍 (領清江、新淦、新喻三縣,治在清江),即今天江西樟樹一帶。劉昌詩名列明隆慶《臨江府志·選舉志》。
根據(jù)《蘆浦筆記·序》可知,劉昌詩稱自己“服役于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這是劉昌詩被認為有過鹽官任職經(jīng)歷的唯一根據(jù)。序文還稱撰寫此書的初衷是,“久懼遺忘,因并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余事,萃為十卷。”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蘆浦筆記》成于宋嘉定癸酉年 (1213)。
在此書既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在考中進士之后的第九個年頭即1214年,他前往江蘇六合縣擔任縣令,這也是他一生中有明確紀年的人生片段。六合縣,現(xiàn)為南京市六合區(qū),北接安徽天長市,西鄰安徽來安市,東為江蘇儀征市,南為長江,有南京市“北大門”之譽。六合還是雨花石的故鄉(xiāng),民歌《茉莉花》的發(fā)源地。劉昌詩在任期內有過修建縣署、縣學以及修造橋梁等舉措。光緒《六合縣志·官師志》[4]稱:“邑人尤稱其文教”。
二、評析關于“蘆浦”指向的幾種說法
學術界基本認定劉昌詩的《蘆浦筆記》成形于1213年,而此前的時間,劉昌詩當究竟處于何地過著何樣的生活環(huán)境呢?學界鮮有述及。“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僚往來。僻在村疃,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山,分不能挈累。兀坐篝火燈,惟翻書以自娛。”這位先人只用不過50個字,就將自己的職業(yè)、生活、情感等一段人生經(jīng)歷給濃縮了。位卑職輕,獨住僻壤,是導致他1213年以前的人生歷程被遺忘的原因嗎?夜半兀坐翻書自娛,是他這段經(jīng)歷被忽略的又一重原因嗎?一個難解的謎。
下面簡要評述一下學界目前對于“蘆浦”具體指向的幾種說法。
(一)華亭蘆瀝浦說
《蘆浦筆記》撰于何處、書名“蘆浦”落在哪里等疑問,長久以來,跟劉昌詩的生平一樣,眾說紛紜,沒有定論。
最早認為“蘆浦”是“華亭蘆瀝浦”的,是錢塘樊榭山民厲鶚于雍正十年十一月所作的考據(jù)結論,這也是確定“蘆浦”之所在的最初文本說法:劉昌詩乃清江人,開禧元年毛自知榜進士,“蘆浦”乃其寫作蘆浦筆記的處所,即華亭蘆瀝浦,昌詩蓋曾為鹽官者…… (據(jù)知不足齋本)。此說被《四庫全書提要》編者不加考據(jù)并附和,“蓋其監(jiān)華亭蘆瀝浦鹽課時作”[5]。
《江西文學史》[6]編者認為《蘆浦筆記》創(chuàng)作于劉昌詩在六合縣令任期內。從他的生平記載來看,他前往江蘇六合縣擔任縣令,是在1214年,更是在此書既成的第二年。此說難以成立。
據(jù)同治《清江縣志·文苑·劉昌詩》,認為蘆浦筆記的寫作地點在清江縣城江濱的廬州,“昌詩結屋于此,曰廬浦草堂,著書其中……曰《廬浦筆記》”。新編《清江縣志》(主編 柳培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明顯沿用了類似觀點。
由張榮錚、秦呈瑞點校的《蘆浦筆記》之“點校說明”(中華書局《蘆浦筆記·點校說明》撰寫于1983年11月)中否定了上述兩種觀點,認為此說“與劉昌詩的自敘相背的,不可取。”
此外,新編《清江縣志》所稱的“廬浦草堂”與《蘆浦筆記》中的“蘆浦”二字相去甚遠,更是不可靠。
(二)慈滋蘆浦說
清人祝堃并不認同華亭蘆瀝浦為蘆浦之說。事實上,浙江平湖也有“蘆瀝浦”,因此,“華亭蘆瀝浦”之說有望文生義之嫌。祝堃以為,“所謂蘆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qū),非今之蘆瀝浦”(“華亭蘆瀝浦”),因為“是書 (指《蘆浦筆記》)所載地理故跡,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及云間 (即上海)”。祝堃的看法雖然有所發(fā)展,但也僅限于質疑層面,結論不甚肯定。
由張榮錚、秦呈瑞點校的《蘆浦筆記》之“點校說明”中,發(fā)展了祝堃的說法,稱“在宋人四明志中發(fā)現(xiàn),慈溪縣有一驛鋪名蘆浦鋪,靠近海邊,而海邊又有鳴鶴鹽場”,于是認為劉昌詩任鹽官的地方就在慈溪蘆浦。點校者認為,《蘆浦筆記》就在這里所寫,時間為劉昌詩登進士第的1205年之后、任六合縣令的1214年之前。從上述幾處相關地名來看,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點,如上海“蘆瀝浦”、慈溪“蘆浦鋪”,均有與書名“蘆浦”相關元素或者近似的地名,這些地點均瀕海,也都有相應的鹽場。這些元素與劉昌詩“曾任鹽官”的經(jīng)歷都可能相吻合,或者說至少能為“劉昌詩任鹽官”提供時代背景或是就職空間。特別是《蘆浦筆記》中多處言及四明、奉化等地的一些人文歷史古跡等,更讓人相信與慈溪“蘆浦”有著莫大的關系。后人認為,其對某些古跡記載的細致程度,到了非親歷不可為的地步。
對于劉昌詩究竟是否在四明有過鹽官的任職,截至目前未見史料可資證明。四明三志 (宋寶慶志、宋開慶志、元至正志)、明天啟《慈溪縣志》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文獻,均無載劉昌詩在當?shù)氐幕顒盂欅E。如果是游學,不載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是任職,這些志書卻為何“口徑”如此統(tǒng)一,一概不予記載呢?不免令人生疑。
按常理,面對古跡形勝,文人墨客素來指點江山感慨人生,或抒情或言志,這個傳統(tǒng)也構成中國古代文學史重要的一個分支——“游記文學”。作為文科進士出身的劉昌詩面對四明的山水名勝、人文風情,他可曾激揚文字?《清代稿本百種匯刊·四明舊志詩文鈔》[7]中,未見有劉詩昌的作品。
《寧波地名詩》[8]是一冊當今寧波學人選編的本地古代才人詩集,選編時限上至盛唐下迄當代,收錄作者560余、詩作1260余首,作品內容涉及寧波山川關隘、州縣鄉(xiāng)村、名勝古跡、寺廟道觀、亭榭樓閣、街道里巷、風物人情、神話傳說等方面。但未見劉昌詩的蛛絲螞跡,當?shù)匾恍┼l(xiāng)土文化資料里也對劉昌詩“保持沉默”。可見當?shù)貙W人也并不認同劉昌詩曾在本地活動的說法。
(三)蒼南南監(jiān) (蘆浦)說
新增的蒼南南監(jiān)說,是因為在蘆浦(南監(jiān))楊姓族譜中保存的宋時佚文,述及劉昌詩及其任職南監(jiān)的經(jīng)歷,而且還明確提到他所撰寫的《蘆浦筆記》。于是,溫州市圖書館潘猛補先生根據(jù)當?shù)匚墨I進行考證而加以認定,認為蘆浦筆記中的蘆浦二字落在蒼南南監(jiān),即今天的蘆浦。所據(jù)文獻如下:
1.文獻一:《復楊少微廣文書》(宋張雋)
張雋在給楊少微的信中稱:“昨接《綠云居》大集,盥薇捧誦一通,具見宏詞古雅,學有淵源。惟第五十六篇,詆及劉昌詩作鹽課司于南監(jiān)場,撰《蘆浦筆記》十卷,謂其考辨疑義,類多閑記軼事,如蘆浦本乎回浦,無據(jù),殊非真切。其說甚韙,嘆服拜服!庸讀竟,鴻便歸趙。”此文現(xiàn)收入《浙南譜牒文獻匯編·第三輯》[9]一書。
南監(jiān)楊氏族譜中保存的佚文為《復楊少微廣文書》 (題目為后人所置),作者為宋時臨安人張雋,嘉定十年 (1217)登吳潛榜進士 (據(jù)《宋登科記》、宣統(tǒng)《臨安縣志》)。南監(jiān)楊氏先人楊謙度 (字少微),著有《綠云居詩文鈔》,入《江南文獻錄》。這里的江南,指的是昔時溫州府平陽縣,包括今天的平陽蒼南兩地轄域。昔日平陽名流方繼學曾為該《江南文獻錄》撰跋,稱“是編,于天下之大,雖未敢必其有所裨益,而一方之人文,實于是乎寄,他日考觀風俗者,亦可以概見。”遺憾的是,此書已佚。
據(jù)楊氏族裔楊乃琦先生稱,《綠云居》大集即為《綠云居詩文鈔》,其楊氏族譜在張文末注有“四庫全書有《蘆浦筆記》十卷,附識俟考”字樣。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后人所加。
2.文獻二:《臨安教授楊謙度墓志銘》(宋·孔景行)[9]
據(jù)同族譜另一篇名為《臨安教授楊謙度墓志銘》 (宋·孔景行)的文章來觀,同好對楊謙度的評價則為:“宜彬彬之英□,振家聲于蘆浦兮。”據(jù)此墓志銘,楊謙度在淳祐初以上舍登特奏名科,任臨安“教授”。遺憾的是,我們并未在《宋登科記》中見到楊謙度功名記載。
3.文獻三:《南監(jiān)地輿記》(宋·彭仲剛)
《南監(jiān)地輿記》中稱,“溫州為靜海軍,為應道軍,為瑞安府,橫陽仍平陽舊治。蘆浦為天富南監(jiān)場,仍設大使駐扎,數(shù)百年久安長治。”溫州市圖書館潘猛補先生綜合上述資料考證后撰文認為,“南監(jiān)鹽場屬地為蘆浦,今尚仍其名,劉昌詩當為南監(jiān)場鹽官,雖志書不載,然《南監(jiān)東門楊氏宗譜》記載甚明,故我們可得出《蘆浦筆記》蓋其監(jiān)天富南監(jiān)場時作,蘆浦乃平陽南監(jiān)之蘆浦鎮(zhèn) (今屬蒼南)。”
由此,《蘆浦筆記》中的蘆浦得以確認,劉昌詩《蘆浦筆記》的創(chuàng)作地得以揭曉,這似乎解決了一段了歷史懸疑。
三、關于南監(jiān)場鹽課司的爭議與考辨
(一)南監(jiān)鹽機構建置簡述
事實上,上述的這個結論,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另一段史實疑案,那就是天富南監(jiān)場的建置以及“鹽課司”的出現(xiàn)。同樣借用上述三個佚文,我們嘗試展開解讀,尋找些許有關劉昌詩謎一般身世的蛛絲螞跡。
昔日平陽南監(jiān)鹽場歷經(jīng)宋元明清、民國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鹽田隨著自然退化而大批被廢棄,2004年,蘆浦鹽場被正式終止其歷史使命,成為新蒼南建設工程中的臨港產(chǎn)業(yè)基地。
民國《平陽縣志》(符璋劉紹寬等纂修·民國十四年鉛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認為,宋時,溫州天富南、北監(jiān),皆合稱一監(jiān),其中天富北監(jiān)在玉環(huán)島上,濮陽李寬知監(jiān)事,此即鹽監(jiān)官。其監(jiān)官當設在北監(jiān),而平陽為其所統(tǒng)轄。編志者認為,平陽或不再設或另設一場官以佐之,今皆不可考。并稱惟《元豐九域志》(光緒八年五月金陵書局刊行)中“樂清下云天富一鹽監(jiān),平陽下云天富一鹽場,此略可見矣”。按宋史有關職官的記述,宋代的監(jiān)當官,即鹽監(jiān)官、鹽監(jiān)事,掌茶鹽酒稅、場務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光緒《樂清縣志》[10]則稱:宋時鹽監(jiān)未有鹽大使名。
于宋朝始建的“天富南監(jiān)”,稱“南天富場”。據(jù)《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南監(jiān)場》[11]的說法,南監(jiān)地輿落在今蘆浦之地無疑。民國《平陽縣志·食貨志》:明洪武元年,兩浙置都轉運鹽使司,所轄分司四,有溫臺分司于溫州,置鹽倉批驗所于天富南鹽,場置鹽課司大使。明洪武八年……置天富南監(jiān)場鹽課司。“鹽課司”這一鹽務機構的確切名稱首次見載官方史籍。相關稱謂,在《皇明一統(tǒng)紀要》中以“天富南場鹽課司”相稱,在嘉靖《溫州府志》中則稱“天富南監(jiān)場鹽課司”。也與《讀史方輿紀要》[12]“天富場,在平陽縣東南三十余里。明初,置天富南監(jiān)場鹽課司于此”相吻合。同樣可資佐證的是,平湖蘆瀝場鹽課大使署的設置——“明前無 (平湖)蘆瀝場鹽課大使署,設立蘆瀝場鹽課大使署是從明洪武元年 (1368)開始”。
(二)捉襟見肘的蒼南蘆浦說
以上這個宏大敘事背景,與宋時平陽先賢彭仲剛所撰寫的《南監(jiān)地輿記》等史籍相關記述,則更顯左沖右突:
1.“鹽課司”被提前記述
《南監(jiān)地輿記》中稱,“溫州為靜海軍,為應道軍,為瑞安府,橫陽仍平陽舊治。蘆浦為天富南監(jiān)場,仍設大使駐扎,數(shù)百年久安長治。”溫州為靜海軍、為應道軍、為瑞安府的初始年代,分別在宋朝的978年、1117年、1265年。
乾道二年 (1166)年,平陽縣金舟鄉(xiāng)人氏彭仲剛中進士第,他曾任金華縣主簿。其生卒年為1143年至1194年。溫州是在1265年由應道軍升瑞安府,這根本就在彭仲剛百年之后的事了。所以《南監(jiān)地輿記》中出現(xiàn)“為瑞安府”這一史實,值得商榷。這是其一。
既然光緒《樂清縣志》言“宋時鹽監(jiān)未有鹽大使名”,又何況南監(jiān)呢?明季始設“鹽課司”,而時為南宋的“劉昌詩作鹽課司于南監(jiān)場”的理由又從何而來呢?依據(jù)是什么?一個在幾十年后或者上百年后才設置的機構、職位,為什么可以被提前表述得如此精確呢?這是其二。
嘉定是南宋皇帝宋寧宗的最后一個年號,前后續(xù)存共計17年 (1208年-1224年)。這是距離彭仲剛仙逝之后10多年的事,彭文所持“仍設大使駐札 (蘆浦)”一說恐怕難有服人之理。
2.劉來任無記錄
假設嘉定17年間天富南監(jiān)職官被遺漏了,而這17年間,有可能會是劉昌詩來任嗎?從劉昌詩的個人簡歷來看,游歷桂林淮南姑蘇等地 (1181-1202)、中進士 (1205)、寫就《蘆浦筆記》 (1213)、任六合縣令 (1214)以及書末自跋所示捐俸刻刊于六峰縣的時間“嘉定乙亥(1215)”等。查《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 職 官》[13],歙 縣 人、嘉 定 辛 未(1211)進士呂午,“監(jiān)溫州天富北監(jiān)鹽場”,在此職官志中,有宋一朝僅此一人見任北監(jiān),更未提及天富南監(jiān)職官,這應該符合民國《平陽縣志》所言“宋時南監(jiān)鹽官幾乎無考”一說。
事實上,“監(jiān)溫州天富北監(jiān)鹽場”的進士呂午,是在嘉定辛未 (1211)中第之后赴任。而劉昌詩一生能與蒼南蘆浦形成交集、有著此書于蘆浦的可能年限,只在1205年中舉之后至1213年成書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僅有北監(jiān)官員的出場而無南監(jiān),恰恰說明南監(jiān)無相關職官在任。這與民國《平陽縣志》所持觀點是吻合的,“平陽或不再設或另設一場官以佐之,今皆不可考。”況且劉昌詩的《蘆浦筆記》中,根本沒有提及有關蘆浦豐富人文資源中的哪怕點滴信息,更可佐證劉此際并未出現(xiàn)在南監(jiān)。從民國《平陽縣志》稱“清初仍明舊額,置天富南監(jiān)場大使一員,駐扎蘆浦”一語來看,宋時南監(jiān)場“未設監(jiān)當官”的觀點是正恰當?shù)摹?/p>
3.“詆”字背后的信息
給合張雋給楊謙度的函件,我們再來仔細分析。張雋就楊謙度《綠云居》集中“惟第五十六篇,詆及劉昌詩作鹽課司于南監(jiān)場撰《蘆浦筆記》十卷”一事發(fā)表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對楊謙度關于劉昌詩《蘆浦筆記》“考辨疑義,類多閑記軼事”的作品特點及對“蘆浦本乎回浦,無據(jù),殊非真切”說法的點評予以認可,贊賞楊謙度“其說甚韙,嘆服拜服!”并在信中回復讀罷《綠云居集》后予以寄還。
可見,楊謙度對劉昌詩作鹽課司于南監(jiān)場一事,已有鮮明的立場——一個“詆”字,已經(jīng)告訴后人早在宋時就已有過關于此書與“蘆浦”的爭議;一個“詆”字,可見張雋對楊謙度反駁劉作立場的認可。事實上,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信息已非常明確,劉昌詩及其蘆浦筆記,與南監(jiān)無關!而潘楊二位前輩,僅憑“劉昌詩作鹽課司于南監(jiān)場,撰《蘆浦筆記》十卷”來說明此書與南監(jiān)或者蘆浦有關,由此確認劉昌詩生前任職蘆浦鹽場,或者認定他在此撰寫《蘆浦筆記》。這種觀點與張雋原文意旨明顯背道而馳,實乃誤矣!
如果憑著三篇有缺陷的文獻記載來認定在蒼南蘆浦,則顯然牽強。有清一代大儒阮元,曾撰寫《石渠隨筆》,其“石渠(里)”也曾是蒼南蘆浦的舊名,難道也可依此認定此書撰于蒼南蘆浦嗎?
四、“蘆浦”或為劉昌詩辦公場所的雅稱
劉昌詩《蘆浦筆記》中的“蘆浦”,就他自己所言,“乃廨宇之攸寓云”,即辦公場所的一處房子。再看同治《清江縣志·文苑·劉昌詩》一文,稱江濱有廬州,相傳唐廬肇讀書處。昌詩結屋于此,曰廬浦草堂,著書其中。如果當?shù)厥聦嵣洗嬖谶^“廬浦草堂”的話,那么由此“廬浦”到“蘆浦”的演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這也是此志以“廬浦筆記”一名見載的緣由,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蘆浦”僅是劉昌詩辦公場所或是起居之屋的雅稱而已。當然,這也只能存疑,畢竟劉昌詩在當年也僅是一名位卑職輕的小吏,并沒有太多的視線投向他的身世,因此也就難以有豐富的史料來證明,至少目前筆者還沒有找到更多的依據(jù),尚待以后做進一步的探查。在此,本文僅是以大膽而簡單的一點設想拋磚引玉,以求方家的不吝賜教。
最后做一點補記。筆者在查閱劉昌詩的生平經(jīng)歷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點意思的現(xiàn)象——光緒《六合縣志》有劉昌詩小傳。列劉傳之后,是一位叫陳容的長樂人(字公儲,自號所翁,端平二年進士),他任過臨江軍“通判”(“軍治”在清江,即劉的老家),也曾在六合縣任過知事。寶祐元年 (1253),他來任平陽縣令,頗有作為。在此前的淳祐七年 (1247),是一個叫朱時興 (或朱宋興)的平陽人,曾任六合縣令。此外,在與劉昌詩同年中毛自知榜的10余位溫州籍進士中,有后來升任禮部尚書的吳杜 (樂清人)與官至刑部尚書的趙立夫 (樂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