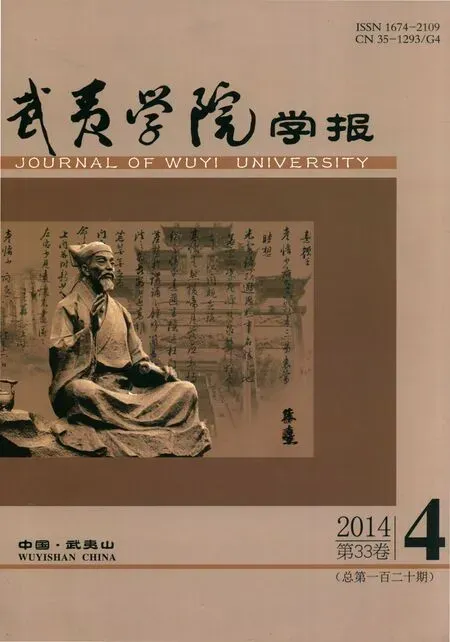才子風流與儒者氣象——柳永與朱熹文化人格比較
(武夷學院人文與教師教育學院,福建 武夷山354300)
有宋一代,武夷山人文薈萃,碧水丹山不僅孕育出風流才子柳永,還滋養出輝映當時、澤及后代的一代大儒朱熹。柳永(987-1057)出生于北宋盛世的崇安縣五夫里,在家鄉度過他的少年時代,青年時期離開崇安就再也沒有回來;朱熹(1130-1200)出生于南劍尤溪,14歲喪父,居五夫里,師事武夷三先生,中舉后除幾年外出做官,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武夷山度過。柳永和朱熹,一個是北宋盛世困頓科場的 “白衣卿相”,一個是南宋衰微之際傳道民間的學術素王,他們皆仕途偃蹇,而死后地位卻截然不同:朱熹被歷代統治者逐漸神化為圣人,朱子之學也被認定為官方學說;而柳永,由于歷代文人圍繞其詞雅俗之爭對其人品、詞品頗有微詞,一直是見棄于正統文化之外的浪子形象。
兩人在生命格調和精神風貌方面迥異其趣,代表了中國士人文化人格截然不同的兩方面,影響著歷代文人士大夫的行為方式、精神追求和生命底蘊。南懷瑾在《易經雜說》中認為:“人生最大的哲學是在‘存亡’、‘進退’、‘得失’這六個字。”[1]從出處行藏作為切入點可以很好地考察、比較其文化人格的不同。
一、薄于操行的風流浪子與克己自律的道學家
柳永和朱熹皆有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學背景,少年時皆穎悟好學,在理智上都信奉修齊治平、積極濟世的儒家思想。但柳永的儒家思想更多世俗功利色彩,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中,原始儒學已經蛻化為士人藉以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的敲門磚,成為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柳永也未脫樊籬,少年時即作《勸學文》自勉:“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2]其內心深處一直有無法割舍的仕宦情結,代表了封建社會一般讀書人的普遍愿望。
青年時代的柳永離開家鄉來到汴京,立刻被繁華的都市文化所吸引,接受了新興市民階層的享樂思想,“日與獧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3](宋.嚴有翼《藝苑雌黃》)并很快投入艷情詞創作,成為風靡詞壇的都市流行歌詞作者。柳永在歌壇上贏得了無限風光,卻也為以后的仕途埋下了隱患,第一次進士考試即被仁宗以“薄于操行”之由而黜落。世俗功利欲望受挫后必然產生強烈的逆反,自視甚高的柳永高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自稱“奉旨填詞”“詞足見柳永思想深處的矛盾:既不甘作一介平民久居人下,渴望高官厚祿,又怨恨統治者埋沒人才而自甘墮落。作為負氣帶性之人的一種反抗,柳永更加放縱地投身于綺羅香澤、聲色享樂之中,走向及時行樂和玩味感官刺激的享樂主義。從此,在他的處世心態和人生哲學里,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感的儒家積極入世精神消退成為潛在的思想,而彰顯一種佯狂、玩世不恭的叛逆行徑,一種非中庸的極端形態,通過自我墮落,以對通行價值觀的挑戰姿態來表現其對生存狀態的不滿,成為徘徊于正統文化之外的邊緣人。
柳永將生命的砝碼移向了男女私情,更無顧忌地投入詞的創作,表現出瀟灑自如的生命格調。與儒者比較,文人注重生命情調,詞人更重感性經驗,尤其是情感體驗,成為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詞更適于表現人性的真實存在,充滿世俗生活氣息,本來就志短情長,“不再以緊張的政治觀念或者沉重的理性原則壓抑自我的生命自由和感性享樂。”[4]詞放棄傳統寫作模式對于道德和教化的守護,抒寫的是感性生命的憂傷與歡樂,甚至可以寫正統文學不宜言說的男女色欲之大防。柳永為世所詬病皆因其“好為俳體,詞多媟黷”[5]。柳詞重感性,沉醉于感官的放縱和欲望的滿足中,展現的是真實、活潑的人性,帶有明顯的肯定自我、張揚個性的傾向。
柳永的人生態度和詞作具有明顯的離經叛道性質,帶有追求個人適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會、反權威、反主流價值的傾向,統治者發現傳統儒家道德戒律在柳永身上已失去約束力,進而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的綱常名教失去維系社會穩定的力量,因此封建統治階層和士大夫將柳永作為“小有才而無德”的鑒戒,視之為傳統道德的破壞者而深惡痛絕。可以說柳永是風流才子的典型,是正統儒家的叛臣逆子,具有有悖于士大夫傳統文化品格的另類人格。
不同于柳永的追求感官享樂和愛情體驗,儒者追求道德理想。朱熹對文學也很在行,但自命二程道學傳人、追求德性圓滿自足的儒者立場,常使他有感于作文害道,認為詩人的生活多崇尚感覺,作詩須有情感體驗,難免流為人欲之私,因此放棄了當文人的念頭,立志做讀書窮理的儒者。從朱熹開始文人與儒者之間逐漸形成很深的夙怨:“文人多視理學家為迂闊不通人情的腐儒,泥古不化而空談性理;儒者多認為文人是不拘禮節的輕薄之士,難免有蔑視權威而犯上作亂之嫌。”[6]在以醇儒自居的理學家看來,一切有悖于傳統倫理道德理性規范的言行都屬于 “玩物喪志”的表現,朱熹就曾批評歐陽修、蘇軾等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7]朱熹對柳永只字未提,或許是不屑一顧,因為朱熹是極力反對時文俗曲的,而柳永艷情詞是典型的時文俗曲。而朱熹的老師劉子翬對柳永卻評價極高:“屯田詞,考功詩,白水之白鐘此奇。鉤章棘句凌萬象,逸興高情俱一時”(《萊孫歌》)[8],認為柳永是武夷山后生俊秀效仿的榜樣。劉子翬是詩人中的理學家,其理學思想既有家學淵源,也有對名重一時的胡安國、楊時等理學家的師承,可見在劉子翬理學家和文人并非決然對立無法相融。朱熹參與了《屏山集》祖本的校編,還撰寫了《屏山集原跋》,不可能不知其師對柳永的評價,之所以不作評價大概出于朱熹向來對吟詩作詞的矛盾心理,或許是出于對其師劉子翬的尊重。
朱熹一生清貧,過著晦居山林的淡泊生活,清心寡欲,甘于讀書窮理和思想改造之苦,探求圣人之道,執著地把“立德”視為人生第一要義,立身嚴謹,其言行舉止不僅有不茍言笑、嚴于律己的嚴肅,也有嫉惡如仇、正義凜然的莊重。朱熹弟子黃幹在《朱子行狀》中說,朱熹常常終日儼然,端坐一室,晚睡早起,連走路都是整步徐行,“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事事表現出整齊嚴肅的態度,生活近乎刻板。朱熹在為自己畫像作的《寫照銘》這樣形容自己:“端爾躬,肅爾容。檢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共終。操有要,保無窮。”他確實做到了立身端正、自我檢點、堅持操守,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曾親自抄錄程頤所言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的“四箴”貼在墻上,作為修身養性的座右銘。
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反對親近女色,怕溺于情而傷害義理:“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從奏劾風流貪官唐仲友一案中可以看出朱熹對人欲泛濫的深惡痛絕和對端人正士品行和良好社會風化的崇尚。他是從事道德教化的布道者,貫穿朱子一生的正心誠意之說、知行統一精神和體現他教育思想的 《朱子家書》、白鹿洞書院學規等,無不體現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倫理精髓。
作為以“醇儒”自居的理學家,朱熹具有強烈的道學憂患意識,于南宋社會危機中發現了封建社會的精神危機和思想危機,認為國家的衰落、政治的腐敗與社會人心的道德墮落和信仰危機緊密相連,所以將二程理學作為拯救南宋衰敗的精神力量,試圖通過振興儒學教育來改變世道人心。朱熹為弘揚儒家失落的實踐理性,深入到文化思想的深層結構,由傳統儒學注重綱常倫理的政教意蘊轉移到如何做人的心性修養上,建立起一種實踐的儒家仁學,使傳統儒學成為士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內在道德需求,把儒學作為讀書人安身立命的根據,要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注重操持涵養心性,以培養嚴肅整齊的道德人格。他的五經學和四書學標志儒學思辨化歷史進程的完成,樹立了為適應大一統王權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統學說的思想權威。“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黃裳《朱子行狀》),是要有賴于內在的道德自律和養心存性。嚴肅、莊重的理性精神使朱熹具有持敬、克己工夫,于內始終保持道德的自律,于外事事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規范,往往克制自我情感欲望而入世苦行,因此必然帶有否定自我、壓抑個性的傾向。
柳永和朱熹,一個是薄于操行的風流浪子,一個是克己自律的道學家;一個偏重感性的情感體驗和審美超越,易流于淺薄輕浮;一個偏重于嚴肅、莊重的理性反思,易流于艱奧深沉。一個代表了人類文化中滿足欲望的享樂要求,一個代表了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他們的矛盾,既反映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兩種對立的典型文化人格,也反映了人類文化內部的深刻矛盾。
二、歌功頌德的干謁者與狷介剛直的道學諍臣
柳永和朱熹的文化人格可以從他們對功名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上進行比較。
柳永屢試不第,表面佯狂,骨子里卻放不下功名利祿,曾多次尋找機會干謁權貴以求引薦,可以說,柳永是北宋創作干謁詞第一人也是最多的一個。據《后山詩話》記載:“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骩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后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5](胡仔《苕溪漁隱詞話》)為得到賞識和重用,柳永可謂費盡心機,不僅向內官請求援引,也曾干謁當朝宰相晏殊,不料被晏殊數落了幾句,說他沒有作為官員應有的文化品格,只好尷尬地無言而退。柳永很多詞“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真實地再現了北宋繁華富庶的盛世圖景,但不可否認一些作品有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之嫌。如《玉樓春》有三首寫皇家慶典,皆是諛美應景之作。柳永還有意創作了不少投獻之作,如 《送征衣》、《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永遇樂》(薰風解慍),據薛瑞生《樂章集校注》考證,都是為宋仁宗祝壽而作。又有《早梅芳》詞是投獻給杭州知府孫沔的,《一寸金》(井絡天開)為投獻益州太守蔣堂所作,《永遇樂》(天閣英游)為投獻蘇州太守而作,大都刻意歌頌主人的事功人品,含蓄地表達了希望主人納賢好客、提攜自己的愿望。這些應酬文字都暴露了柳永強烈的功名意識、擺脫低微社會地位的渴望。及第被黜,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打擊,既憤憤不平,又不失時機到處干謁請托,進而形成依附人格和從眾心理,隨俗浮沉,足見其人格的矛盾性。
但柳永畢竟不同于功名利祿之徒,干謁求官主要是為了實現他少年時代的儒家理想,作為文人他還是有一定的操守。他不時在詞中表達對這種奔波競走生涯的冷靜反思和厭惡:“九衢塵里,衣冠冒炎暑”[9]黃氏在《蓼園詞評》里評說:“趨炎附熱、勢利薰灼、狗茍蠅營之輩,可以“九衢塵里,衣冠冒炎暑”二語盡之。耆卿好為詞曲,未第時,已傳播四方,……是耆卿雖才士,想亦不喜奔競者,故所言若此。此詞實令觸熱者讀之,如冷水澆背矣。意不過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針砭,而凌空結撰,成一篇奇文。”[5]在經受上層社會的冷眼、飽受羈旅奔波之苦后,柳永清醒地認識到“名韁利鎖”對生命的剝離,思想上還有作為文人獨立的人格和自尊,但傳統和現實的壓力迫使他無法割舍功名,因此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
由于柳永長期困頓科場、流連情場,景祐元年50歲進士及第后,至多只做了屯田員外郎這類小官,終其一生無政績可考。柳永只是北宋盛世一個風流才子的典型,在政治、學術上幾乎無所建樹。
與柳永人格的游離不同,朱熹具有一種順境退守、逆境進取的道學性格,難進易退,不肯唱頌歌,卻專好唱喪曲,天生有一副逞強好辯的性格。
這種狷介剛直的道學性格首先表現在對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上。南宋衰微之際,統治者戰和不定,由于隆興北伐的失敗,朝廷籠罩著茍安主和退守的氛圍。朱熹一變多年來上狀辭免的態度,慨然入京奏事,總結北伐失敗的原因,指出當時國家根本之憂不在邊境而在廟堂,對奸邪誤國、近習小人的結黨弄權進行嚴厲的批評。歷經人世憂患的朱熹稱得上是封建衰世以倡道救世為己任的匡世之才,他的三大政治主張是由安民——治官——正君構成的更革弊政體系,施仁政、寬民力、打擊貪官近習和要皇帝正心誠意的政治思想,無疑是對大病沉疴的南宋社會所下的一貼救世良方。朱熹不斷地犯顏直諫,其庚子封事、延和奏事對皇帝趙眘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戊申封事洋洋萬余言:“可以稱得上南渡以來第一篇奏疏文字,是朱熹生平對南宋社會的一次登峰造極的全面解剖,也是理學家用正心誠意之學解決社會迫切現實問題的著名的范例。……在憤激慷慨與理智冷靜交織的陳詞中,搏動著哲人的明智博大與庸人的昏聵渺小,帝王放臣的忠肝披露與道學錚骨的桀驁犯上,衰世大廈將傾的憂焚如火與拯民水火的真誠呼喊。”[9]“這些放肆無忌的攻擊是需要有極大的近于迂氣的膽量的。”[10]
朱熹是強毅威嚴、雷厲風行的治才,更是體恤民情、拯民水火的仁者。朱熹一生出仕的時間并不長,卻不斷在現實中實踐理學拯人心、挽世道的力量。綜觀朱熹一生政績,他治世剛決,敢于向腐敗的官僚制度開刀,打擊豪強、貪官、滑吏向來不手軟,有著非凡的政績。朱熹不僅有“法治”一手,還有“禮治”、“文治”的一手,不愧為革除弊政的改革家。由于各種邪惡勢力的阻撓,朱熹的改革大都付之東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移風易俗、振厲士風、震懾貪官酷吏的成效,表現出一代儒宗直面現實、積極進取的實踐精神。
昏君、庸相、叛臣、近習權幸、主和派,構成南宋小朝廷反道學的政治核心,對朱熹等道學家頻頻施以殘酷的打擊,但朱熹錚錚傲骨,從未屈服。他一次次觸怒最高統治者,一次次被迫請辭歸隱于武夷山。歸隱后朱熹毫不退縮,不斷反思和批判封建文化,埋頭鑄造理學之劍。垂暮之年,朱熹被新君趙擴召請入都成為帝王師,入侍經筵僅四十六日,因提出防止帝王獨斷與近習預權之法,招致這位表面上從善如流、有志行道的“賢君”的憎惡,趙擴借助外戚與近習剪除道學清議勢力,將朱熹打入偽籍并斥為逆黨之魁。晚年的朱熹在文化專制的煉獄中備受煎熬,但精神上沒有停止求索,轉而投入《楚辭集注》和文學創作、文學思想的新的探索中,將世上瘡痍化為筆底波瀾,最終懷著“吾道不孤”的信念在黨禁的陰影中去世。“這也許是他那個茍安腐朽的封建衰世社會在他身上逆反塑造出來的一種特殊進取心態和性格。”[10]
朱熹的道學性格還表現在對自己思想進行自我反省、在論辯中不斷辨析兼取他人思想的懷疑與求實精神。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同形形色色的人與學派進行無休止的講學論戰,其理學思想是在與各種不同論見不斷論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論戰成了進行傳統反思和現實批判的獨特方式。著名的有寒泉之會、鵝湖之會、三衢之會、白鹿洞之會、與浙東學派的角逐、與陳亮等人的義利王霸之辯、與陸九淵的太極論戰等,每一次論戰都給朱熹思想上帶來一次升華,先后完成了對生平學問的三次總結,建立了離經叛道的新經學體系和人本主義的四書學體系,最終集理學之大成。這種特殊的人格就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道學人格,是一種體道弘道的崇高人格。
有意味的是,柳永作為傳統儒學的叛臣逆子,卻經常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朱熹作為克己自律的曠世大儒,卻屢屢犯顏直諫,時時不忘革除弊政,極力挽救封建衰世。二人皆觸及最高統治者敏感的神經而不被接納。
三、進退失據的詞人與淡泊自守的晦翁
柳永和朱熹都飽經憂患,但化解人生憂患的方式迥然不同。
柳永熱衷功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奔波求仕,直到中年,在仕途上仍毫無進展,內心非常失望:“干名利祿終無益”[9](《輪臺子》)。失意時沮喪、憤激,得意時又忘乎所以,如進士及第后所作《透碧霄》言語夸飾,頗露志得意滿之情。入仕后久困選調,“游宦成羈旅”的困頓奔波生涯又使他陷入更大的仕宦與歸隱的矛盾沖突中,產生對功名的懷疑:“驅驅行役,冉冉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9](《鳳歸云》)并油然而生一種人生無常的感受。他認識到傳統價值觀對人性的剝離,在很多羈旅詞中表達對“名宦拘檢”的動蕩人生的厭倦,更傾向順應人的自然本性去生活。柳永幼時居住的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受道家影響很深,有記載稱其道骨仙風。精神上無所托庇的空虛迫使他對隱逸生活充滿向往:“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試圖遁入道家尋找精神避難所。
然而柳永抵擋不住繁華市井和歌妓舞女的誘惑,將人生的天平傾向了愛情和市井,以愛情的溫馨和市井的放縱對抗上流社會的拒斥,彌補功名無望的憾恨,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傳統大隱、中隱、小隱的歸隱之路,即以愛情為歸隱的方式,追求世俗物欲、情欲的感官享受成為他解脫人生苦悶的主要方式。
柳永在仕途與愛情的追求中表現出明顯的進退去就之間的矛盾,往往陷入軒冕與山林不可得兼、個體需求與人生責任不能統一的矛盾之中。這種思想矛盾與宋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標榜的“進則盡節,退則樂天”的人格理想不同,他受世俗束縛太多而無法做到進退自如。他所體會到的理性世界是有限的,始終無法解決思想深處厭倦現實與執著人生的矛盾,“他只是一個懂得愛情、珍惜愛情,懂得享受生活與溫情的世俗才子,不是超凡入圣的圣人,他的道行被滾滾紅塵、被和著胭脂的眼淚湮沒,不能‘以天地胸懷來處理人間事務’,達不到‘以道家精神來從事儒家的業績’的‘天地境界’(馮友蘭《新原人》)他還達不到哲人的層次,不能以哲人的思辨精神來看待人生,不能以圣賢的勇力和智慧獨立承擔人世的艱難。”[11]其道骨仙風只是一種外在的風度與表象,靈魂深處缺乏真正超然自適的精神。“他所追求的全是外向的,是‘有待’……所以,柳永的一生是兩邊都落空了。當年他聽歌看舞的這種感情生活落空了,用世的志意也落空了。”[12]由于局限于個人的榮辱得失和感官享樂,他的艷情詞和羈旅詞充分展示出升平時代失意士人既向往功名利祿又渴望官能享受而不可兼得的矛盾苦悶心態,進退失據,往往陷入求仕而事業無成、求愛而情感無依的兩難困境之中,始終無法戰勝自我,做自己心靈的主宰。因此,柳永是軟弱的,只能作為封建社會俗艷文化的代表而見斥于正統文化之外。
朱熹一生官多祿少,屢起屢撲,縱觀其一生,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了積極濟世的道學家淡泊自守的另一面。朱熹不僅有二程理學的頭腦,還有一個浸透佛老的靈魂,把佛老作為解決人生問題的一種方法和途徑。朱熹對道教和道家思想學說有十分深入的了解,有著長達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歷程。少年時代卜居潭溪就,青年時在建陽云谷隱居即自號“晦庵”,準備隱遁山林自晦終老,從壯年建筑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到晚年卜居考亭、滄州精舍,始終埋頭著述講學,過著寂寞清寒的生活,行為上是真正的隱士。曠世大儒的聲譽給朱熹帶來很多次做官的機會,但朱熹并不貪戀富貴顯達,多次受朝廷征召皆上書請辭。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過著晦居山林的淡然生活,清心寡欲,以著述講學為獨善其身的方式。
儒者的道骨仙風常常隱藏在其靈魂深處,時隱時現,難以捉摸,不象文人那樣任性直言、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來。朱熹學道不過是“在人生境界和精神修養方面吸收佛道的生存智慧以超越自我,使儒學重新起到全面指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成為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10]哲人的思辨精神使他超越于佛道而援佛道入儒,順應了宋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潮流而成為一代理學宗師,成為傳統文化的最大代表。與魏晉名士徜徉山水是為了逃避現實不同,朱熹對現實有著清醒的批判意識,敢于直面現實,與衰朽的上層統治者作艱苦的抗爭。“吾道付滄洲”(《水調歌頭》《文集》卷十)并不是去做功成名就的隱逸高士,而是要做傳道民間的學術素王,他不能身在朝廷建功濟世,卻可以退居山林倡道拯心。朱熹始終未嘗忘懷塵世蒼生,“退居山林講學著述不過是他歷來在現實中四處碰壁后的另一種更深遠的進取”[10],一旦時機成熟,便立刻出山,努力在實踐中“見儒者之效”和“反振民功”。
朱熹從容地進退于仕宦與歸隱之間,“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始終是自己的主宰,從未象柳永那樣心為形役,既享受了山水林泉的寧靜恬適、超然無礙,又無個體價值的失落感,用則進,廢則退,每次在現實中四處碰壁后更是收斂身心、韜光養晦,力戒躁進之病,做一個平和、沖淡、閑適的真正的“晦翁”。
朱熹是真正的“‘人中之龍’,一個身備陽剛正氣的一代儒宗,進退于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之間,有一個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云臺捉不住的傲魂,不為統治者所屈,不為衰世所用,也不為俗人所理解。”[10]正如他稱贊周敦頤那樣:“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濂溪象贊》),朱熹胸次浩然,具有一種“超然于個人名利富貴等私欲束縛而與天地合德的快樂……一種經過持敬存養的長期修煉后所具有的德性圓滿而內心充實的心境。”[10]這就是所謂能洞悉天地萬物本體而胸中灑落、天人合一的圣賢氣象,是千百年來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圣賢境界,惟有朱熹等極少數人達到了這一境界。
四、結論
柳永是北宋升平時代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崛起導致人欲膨脹并進而影響文人階層所產生的風流才子的代表,而朱熹是南宋封建衰世內外交困、文化道德全面衰退時期試圖以理學為武器對封建文化做一次全面總結和振興的曠世大儒。柳永重感性體驗,以審美活動為生命的最高形式,柳詞蘊含著封建社會見斥于正統文化之外的浪子才人對生活的體會和特殊的文化心理,放浪有余而嚴肅不足,因而政治上難有作為。柳永經歷了由儒家積極入世思想轉入享樂主義再轉入對道家出世思想的向往,且一直在矛盾中徘徊的過程,作為封建傳統文化的另類——風流才子形象為中下層文人和市民階層所喜愛,成為俗艷文化的代表。朱熹是讀書窮理的儒者,是道德教化的布道者,經歷的是一個出入佛老而歸宗于儒學的蛻變過程,重視的是理性,以道德人格的涵養作為拯救封建衰世精神危機和思想危機的利劍,嚴肅有余而豁達不足,他建立起的理學文化大廈成為封建社會后期的精神支柱,因而成為傳統文化的最大代表和后世景仰的圣人。柳永詞心放曠,追求個人價值和審美價值;朱熹道心為微,強調倫理價值和群體價值。兩人代表了中國士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追求,反映了傳統文化中個性價值和群體價值的深刻矛盾,在這矛盾不斷的對立統一和揚棄過程中影響了中國士人的文化人格。
[1]南懷瑾.易經雜說[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270.
[2]曾棗莊,劉琳.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卷580)[M].成都:巴蜀書社,1991:236.
[3]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M].北京:中華書局,1980:579.
[4]顏翔林.宋代詞話的美學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46.
[5] 唐圭璋.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6:3585,163,3061.
[6]張毅.蘇軾與朱熹[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26.
[7](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30[M].北京:中華書局,1994:3096.
[8]楊國學.屏山集校注與研究[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163.
[9] 束景南.朱子大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58,163,205.
[10] 薛瑞生.樂章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4:761,233,775.
[11]程榮.柳永的兩難處境與儒道思想[J].武夷學院學報(社科版),2010,29(6):8-13.
[12]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