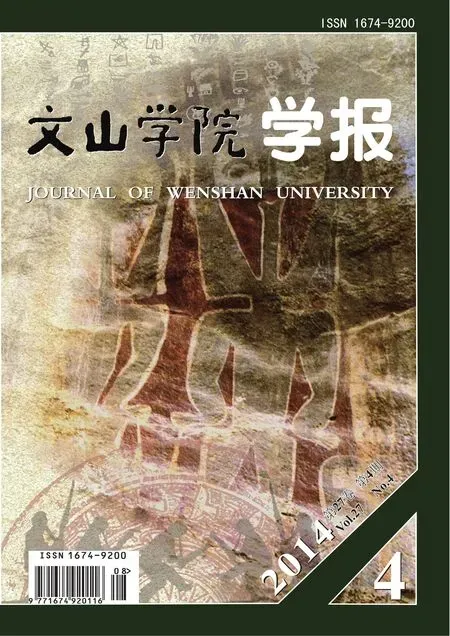我國傳統社會旱災應對機制特點探討
李相興,李玉軍
(1. 貴州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我國傳統社會旱災應對機制特點探討
李相興1,李玉軍2
(1. 貴州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文章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相結合的角度,探討了我國傳統社會應對旱災的機制,這一機制由預警、防范、應對和轉移等環節構成,并且幾乎每一機制中都有理性和非理性機制并用的特點。
旱災;應對機制;特點探討
干旱是一種頻發的自然災害現象,有人統計,我國從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發生了1035次旱災,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1]51。而且其波及面大,持續時間長,較之其他災害,無論從其波及的廣度還是對社會影響的深度,都可以算是各類災情中最為突出的。因此,歷史上無論是皇帝、官府還是普通百姓,無不受旱災的困擾。
以往學術界對歷史上旱災的研究,要么單獨講理性的抗災舉動,要么單獨討論非理性的防災抗旱之術,從沒有將理性與非理性的抗旱應對機制納入到一個系統中進行考慮,因此在分析我國傳統的抗旱文化現象時總有片面之嫌;同時,過去的研究多局限于歷時性的縱向研究上,基本沒有利用共時性的材料加以佐證的,更沒有將旱災現象納入共時性和歷時性相結合考察的先例。基于此,本文以 “旱災應對機制”為關鍵詞,以共時性的田野資料和歷時性的文獻資料相結合,抓住理性與非理性兩條主線,探討我國傳統社會應對旱災的機制問題。
千百年來人們針對旱災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應對機制。這些機制概括起來主要有:干旱理性與非理性預警機制、干旱理性與非理性防范機制、旱期的非理性與理性聯動應對機制、干旱后期的轉移機制等。以下是對這些機制的介紹分析。
一、傳統旱災預警機制
我國各民族歷史上經過不斷的觀察和驗證,總結出了許多干旱預警的經驗,這些經驗主要有季節氣象類、天體異常類、植物異常類、天人感應類等。
(一)理性預警機制
1.季節氣候干旱預警
我國傳統社會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這種經濟主要依靠自然界的調和來維持,如種的莊稼必須有一定肥力的土壤、必須有一定的光照時間、一定的濕度等。作物生長需要的土壤肥力來源于兩種途徑,其一為沖積平原的天然熟土,其二為農民們世代施加有機肥的土地;作物需要的水分一方面來源于溝渠,另一方面則來源于雨水,持續的干旱能使江河枯竭,使作物斷絕水分而枯死。因此農業生產甚至人畜生存都要依靠上天施舍的雨水來維護。人類對雨水的這種依賴迫使人們不斷觀察和總結經驗,以應對自然的不調。于是就有了一些判斷天氣陰晴的經驗,這些經驗在民間以“諺語”的方式存在著,如:“凍煞樟樹腦、曬煞沿山稻;今日日頭烏云托,明朝曬破烏龜殼;東電閃西電閃,曬煞泥鰍黃鱔;冬冷久,夏熱長;缸片云,曬死人;太陽東山烏云動,明天曬得腰背痛;上看初二三、下看十五六;立春不雨旱到清明;發盡桃花水,必是旱黃梅;螢火飛低,曬死鯉魚;雨落小暑頭,干死大水牛;大暑少雨吃水愁;夏至響雷三伏旱。”
這樣的農事或居家預警諺語,存在于我國各地,有些是預警幾天內天氣的,有些則是預警中長期的,人們常常根據這些氣候征示來合理地安排生產和生活,所以它形成了干旱預警機制中的一個部分。
2.天體異常類預警
我國古代認為,日月星等天體的異常變化,也是預示災害將至的標志。
《后漢書·丁鴻傳》“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晉書·天文志》“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這里,雖然沒有明示日食與災異現象的直接聯系,但示“有亡國”。考察古代朝代更替,有深層的政治經濟原因,但導火線大多與包括干旱在內的各種自然災害有關。在民間,人們一般認為日食必然會出現災異。現代科學也證明,日食可以引起地球赤道和兩級氣溫的改變,導致常態的大氣環流在日食時發生異常,進而引起旱澇等災害[2]。所以古代人民將日食作為氣候異常的預警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關月亮異常引起災異的有“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漢書·天文志》),意思是說當月亮擋住土星時,就會發生災難,使人民流離。“歲犯月星,在房。占曰:其國兵荒,人流亡”,“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饑,人流”(《晉書·天文志》),這里的“歲”,指的是木星。意思是月亮擋住了木星,會因國內欠收而使“民饑”,進而使人民流離失所。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其所言無非都是說月變引起包括旱災在內的災異,其最終結果是“人流亡”“民饑”“人流”。另外諺語中還有“月擔枷,旱死蝦”的說法。所以“月擔枷”也是一種旱災的預警征兆。
金星古代稱為“太白”,其失軌也會帶來災情:“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眾流亡”(《宋書·天文志》)。“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為饑,為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庭赦之,是后連歲水旱民饑”。所以金星異常也是導致水旱的災示之一。另外,古人認為流星大規模出現、彗星的出現都是災異現象的預警。
3.植物和動物異常類干旱預警
在我國民間,有許多植物的異常現象都被認為是干旱的預示,所以也倍受人們關注和重視。2010年4月底,貴州民族學院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組成了黔西南干旱專家學者考察隊,筆者也一并前往,在對彝、布依等民族關于旱情預示的采訪中,被訪者認為在當地,干旱的預警要數竹子,他們認為一般竹子都不開花,但如果秋冬季遇有竹子開花,那么下一年肯定會旱,而且少開旱情不大,如果很多人家的竹子都有開花,則預示將大旱。2009年,就有一些人家的竹子開了花,2010年果然大旱。諺語中也有“竹子開花,連月旱”的斷言。
民間還認為秋季地里結連瓣瓜,也預示將有不同程度的秋旱或冬旱;秋季野菌的頂上又長出菌也預示來年將旱。春季油菜花上蚜蟲太多預示旱情將持續;初夏松毛蟲太多吃盡桑葉、玉米葉要持續干旱;初夏不見螞蟻在平地上壘巢要干旱;見蛇從山上往山下趕要干旱……
在黔西南,這一類的預警是非常多的,然而這種種異常雖有警示作用,但人們的防范意識并不十分到位。或者在一定的社區內雖有經驗式的共識,但從無權威的人依據這類經驗警示來組織防范旱災。
(二)非理性類預警機制——天人感應
我國傳統上認為,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能相互感應的“道”,無論皇家失德、官府失德還是民間失德就是失去了“道”,由于天人之間的感應,失德者(包括失德者所在的區域)必受天譴。天譴手段主要就是降災于人類,這樣的災有水災、雪災、蟲災、震災、旱災等等。所以國內冤情太多、或皇帝等太失德,或過分地違背常理,就預示著天將有災異產生。
反映夏商周時期的《尚書》中就有許多“敬天保民”的思想。如《尚書·甘誓》中就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所以“天用剿絕其命”。《尚書·湯誓》也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之后歷代新王朝起兵時都認為是前朝違背天意,至使天怒降下大旱等災荒,因此正義之士秉承天意而伐之。
直到清朝,這樣的天人感應降災說仍大有影響,《清世祖實錄》中就記有順治皇帝的自責:“水旱連年,民生困苦,是朕負于上天作君之心”。[3]771
至于冤獄導致天降災難的情況也自古有說法,清時仍有史載此類之事,如順治十四年四月順治帝就說“今三年不雨,入夏尤旱,朕心甚切憂惶,常思雨澤愆期,多由刑獄冤滯”。[3]584
天人感應干旱預警系統應該說更有利于規范人間的行為,至于是否與天氣異常現象有關聯,應持否定態度,當然它作為傳統旱災文化預警機制中的一部分不容否認。
二、傳統旱災防范機制
(一)理性防范機制
1.興修水利
(1)歷代官方都重視水利以防水旱災害
我國最早有關水利方面的信息是傳說中的大禹,當時他“治水”主要是疏浚河道;《周禮》中也有了興修水渠、平息水害的記載:“掌稼下地,川潴蓄水,以防止水,以逐均水,川流舍水,發澮寫水”(《周禮·地官·稻人》);《管子》一書中也有“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足用……”(《管子·乘馬》);之后的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都有有關興修水利及其管理的記載。特別是從晉代開始,中央政權設有專管水利的機構(如晉及其后政府中設有水部曹郎,隋唐至宋各代,水部都是工部下面的四個主要部門之一),這為國家層面上的水利建設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歷史上的鄭國渠、各地的堰壩、堤壩、池沼的修建一方面利于防澇,同時也可以起到引灌抗旱之作用。隋朝修建的大運河,將南北水系貫通,對北方沿岸旱情的緩解以及振濟旱災物資的運輸都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2)民間水利方面的防范措施
官方水利畢竟無法兼顧國內的村村寨寨,所以,歷史上我國各地各民族民間都有防旱方面的一些水利應對措施;如修建小型的池塘堤壩、修理溝渠、打井修井、制石質或木質的水缸,或購買陶制的大水缸等等。旱情一來,這些都多少能解決一些用水方面的困難。
2.儲糧備荒
為了應對因旱而缺糧的狀況,我國歷史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有儲糧備災荒的規制或習慣機制。
從考古方面的資料來看,我國很早就有儲糧的窖穴,新石器時代的許多文化遺址中都有這類窖藏遺跡;甲骨文中多處有商王派人建設、巡視各地倉廩的文字;周代以后,倉儲糧食以備急需的制度不斷得到完善。西漢政治家晁錯提出了“廣積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漢書·食貨志》)的積極備糧備物主張。這樣的主張,歷代統治者不管出于何種政治目的,多少都參照著做了相應的一些工作。
從民間方面看,倉儲一直都是中國農民階級備糧的傳統。歷史上,我國民間一直重農輕商,同時也為了應各種災害之急,所以很少有把糧食拿到市場上交易的習慣,即便拿去賣,也是在保證留足下一季的前提之下進行的,所以在北方,幾乎各家各戶都有儲糧物的地窖;在南方,則專門在民戶民居樓上修有儲藏幾萬斤糧食的倉庫或能裝幾噸糧食的竹篾屯籮(在貴州六枝中寨一帶的布依族至今仍留有此類糧倉)。有些民族甚至修有單體的儲糧樓,如貴州開陽高寨鄉平寨的苗族就有這樣的糧樓。在中國各地除了給全家備糧的同時,還為家畜、家禽備足草料。
3.植樹護林防災
我國各民族自古就有植樹護林、保持水土的優良傳統,這樣的傳統一為官方提倡,二為民間將其作為一種自覺的利己利他行為。
從官方來說,周代時已有掌管山林的官職,如“山虞”“林衡”等(見《周禮》)。到春秋戰國時已有了“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的認知(參見《管子·權修》),后代也有官方詔令民間種樹植樹的信息:“開寶中,詔緣黃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為河防”(《宋史·太祖本紀》),這些記載,雖未明示為了防旱抗旱,但客觀上植樹對涵養水源是有非凡的作用的。
至于民間,無論哪里,中國人都喜歡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栽上樹,以利風水。或者在井邊種樹,以護龍神。在中國南方的很多地方,水井連同水井邊的古樹一起,都成為人們祭祀的對象。其用意無非就是祈其保水土,或祈其再利村舍,不因旱災而斷水。
在云南禮社江流域的漢、彝等民族地區,至今還留有在端午節那一天人人種下一棵樹的習俗。在貴州黔東南侗、苗民族地區,則有種植杉木的傳統,這在許多文獻中都有記載,而且明清以來的種樹等文契留世者多達幾萬份,成了今天人們關注的一大熱點。
對于護林,這在中國西南山區是一種傳統,“風水林”“井邊林”“廟樹”等都被賦予神圣的特性,這種特殊的“優待”,其實就是人防災害的一種攀高性策略,以“神”之尚方寶劍來堅守一方水土。而且在歲時年節里,加進一些祭祀貢品或神秘符咒以增強其“神性”。
中國民間風水學中,講求察砂觀水點穴,察砂就是看預地“穴”周邊之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各山是否有茂密之林木,觀水觀的就是“穴”前是否有能聚氣藏風的龍泉寶水。而一旦選定,對這一方風水寶地是要倍加呵護的,呵護之方不外一方面行教化,告訴當地居民惜風惜水,以免傷了風水之風氣;另一方面,則修觀建寺立塔作廟以“神”護佑其理想的風水。這樣的風水觀,對自然生態的維護力量有時也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二)非理性防范機制
1.年節時的祀神娛神
從皇帝到普通老百姓,都有在年節時向包括龍神在內的諸神貢獻犧牲,以祈求其保佑國家或一方五谷豐登之習俗;同時,人們在年節時還通過耍龍、賽龍舟等活動以娛神,讓其高興而少向人間施威。
2.立廟造像貢獻犧牲、上脊
給各種有超能力的神立廟、造像是人類出于自身的功利目的實施的結果,是人類對神有所求。就旱災來說,給相關的神建立住所、塑起金身、穿上衣服、貢獻上犧牲,這樣無非是讓神保佑風調雨順而已。
另外,中國民間一直有讓龍上房以防火的傳統,懸山還是硬山的屋脊上都會有龍,少則兩條,多則6條。宮觀、寺院的主屋脊上還有鴟吻、琉璃獸等,鴟吻就是為吐水防火之功效,琉璃九獸中也有吐水之獸。同時,在許多較高檔次住宅的柱上,也雕有龍等,其目的一者為主人一族騰達,再者也有護房佑族防火防旱之寓意于其間。因為,龍之功用總以水為主。
3.堅守道德操行
按照中國的傳統認識,認為干旱是“天”對人間失德的懲罰,因此,為了不觸怒天神,人們特別是皇帝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堅守著道德標準。
三、旱期的聯動應對機制
持續干旱一段時間以后,人們開始緊張、擔憂,看到了干旱帶給國家、地區或家庭的嚴重性災難,于是周而復始地生發出感性的儀式性祈雨、恤刑或生發出理性的從官府到百性的救災行為。儀式性祈雨和恤刑,其思想根源都是“天人感應”說,反映的都是災害來自“天”或其他神的心理,其共同的目的無非是想通過一定的儀式或措施以達到人和神之間的新的平衡。理性的救助則是主動的、積極的、實在的人類自助行為。通過研究發現,無論是感性的祈雨和恤刑,還是理性的自救,各自內部都有一個聯動的機制因素,都有皇帝、區域或社區聯動的聯合祈求行為和救助行動。同時,在感性與理性的行為之間,也存在一個聯動的機制,這個機制主要是祈神機制和人自助機制之間的聯動。
(一)非理性應對機制——祈雨與恤刑
1.祈雨
祈雨分為皇帝祈雨、地方官祈雨和民間自發祈雨三類,體現的是一種由上到下的聯動,或者說是由皇帝的點祈求到尋常百性的面上的祈求的聯動機制。
(1)皇帝祈雨
皇帝祈雨史書中都叫做“雩雨”或“雩祀”,而“雩”意思是“祭水旱也”(《禮記正義》卷十六),“雩者,為旱求者也”(《春秋谷梁傳注疏》卷十九)。“雩祀之設,本為求雨”[4]。
雩雨習俗源于何時,已很難考證,然而從考古資料來看,一些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中已有祭壇遺址,從人類主要目的之一是生存這一點來看,祭壇之設置主要就是為了設壇以求“天”或“神”佑人間以“泰”與“安”,以風調雨順,所以不排除新石器時代祭壇祈雨的可能,如果這種假設成立的話,那么“紅山文化”中的牛河梁祭壇祭雩雨已有6000年左右的時間了。《史記》中有“明鬼神而敬事之”之語,說的是史前時代的敬鬼祀神之事,其中也有“求風祈雨”的記載。夏代“祭樂于赤帝以求甘雨也”(許慎《說文解字·雩》),商“甲子卜,其求雨于東方”,之后,歷代都有相關記載。據山西師范大學張一平教授研究,唐代的皇帝雩雨有四個特點:其一,雩雨有大、中、小三類;其二,雩雨程序縝密;其三,設高壇以雩雨以敬畏天帝;其四,雩雨與祀帝相結合[5]。明清兩代,祈雨多在今北京天壇舉行,也有在宮內或其他地方進行祈雨的,有專家考證,清康熙在位61年,共祈雨50次。清乾隆在位60年,其中到天壇祈雨就達38次之多[6]。從這兩個皇帝的祈雨次數之頻繁來看,歷代祭天以祈雨的情況當也基本如此。
(2)官方祈雨
官方祈雨的思想根源主要有二。其一是受中國民間祀神授雨傳統的影響;其二是上行下效,皇帝都祭,旱區地方官更當效仿之。
有關官方祈雨的記載也有很多,如鄭樵《通志·略》卷十七:“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杜牧《祭木瓜山神文》中有“惟神聰明格天,能降云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后刺史,祈無不應”;李嵩《祭北岳報雨狀》有“臣受命之日,祈雨恒山。玉幣未呈,明靈已驗”;李商隱《為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鄭州剌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于水府真官”。宋代官方雩雨也很多,許多地方官(也是文人)都留有祭文,如曾鞏的《薤山祈雨文》、蘇軾的《祈雨吳山祝文》、韋驤的《龍教山祈雨文》《梨山祈雨文》《仰山祈雨文》等。[7]清代,江南地區官方祈雨仍很盛行,如1832年自夏至秋“恒風不雨”,巡撫林則徐率百姓迎請觀音到城中祈禱,“觀音顯靈,普降甘霖”(光緒《蘇州府志·卷三九·寺觀一》,光緒九年刊本)。
(3)民間祈雨
民間祈雨也分為非旱時娛神、旱時祭神等幾類。祭祀對象亦有諸多不同,有的禱佛、有的尋道、有的祀城隍土地、有的則祭龍神……總之各地都有娛祭的對象。
非旱時的娛神活動如春節舞龍、各地每年定點祭龍、掃寨、趕會、朝山、賽龍舟等,這些活動,既娛人也娛神,既酬神也期待神日后再效力。
在云南楚雄州境內的禮社江兩岸,當地彝族的祭龍娛龍活動一般在春節期間。首先是每家每戶在大年初一之晨要到水井邊說“好話”以求龍神在新的一年中保佑全家人一切平安,然后放一些生米于井中以酬龍神。正月初的幾天內,或聯合或單獨到山上有水井或山神的地方再去祭龍祭山。有些村寨則是年年均全寨聯合共祭一井之龍神,如南華縣馬街鎮后山村的下村彝族,該村每年都在正月的第一個虎日全村共祭位于村南頭的大井,“龍頭”以戶輪流,直至今日年年均祭,祭時多是男性參與,講喜慶祝頌詞、跳鍋莊唱轉龍經等。其目的主要是酬神和娛神,也有祈求龍神佑未來不旱不澇的用意。
旱時祭祀是求所祀之神直接出面以解當前之旱害。在山西大同一帶民間祈雨的步驟是唱戲、禱雨、取水、出馬。而且祭祀時往往是幾個村、堡聯合進行,規模大,財物用度多。[8]
在我國,前述的皇家雩雨、地方官祈雨多以儒家禮儀為主;一般民間祭龍等屬于原始信仰及其禮儀。但史籍中也有佛、道、襖等教祈雨的記載,信仰伊斯蘭教的云南回族也有祈雨的經歷,所以祈雨從宗教角度看是全面性的。
佛家祈雨的歷史信息如“歲嘗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酉陽雜俎》);《高僧傳》中也有宋孝武大明六年帝令僧祈雨的信息。
道家祈雨方面的信息如前文所引的“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于水府真官”就是一例。《三國演義》中赤壁戰前諸葛亮設壇“借東風”用的也是道家之祭儀。
襖教又稱瑣羅亞斯德教或拜火教,是古代波斯人的宗教,曾一度進入我國,并深入內地,在趙玉平、邰鵬飛合作的《唐代敦煌雩禮考述》一文(載《齊魯藝苑》2009年第2期)中,多有提及關于襖教歷史上在敦煌一帶參與或主持雩雨活動的情況。
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民族中,目前只有回族祈雨的信息。據昆明市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的馬穎生先生研究認為“祈雨是伊斯蘭教的一項‘圣行’”,有其獨特性。在馬先生的《云南回族祈雨文化探微》一文中,他介紹了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昆明及其附近尋甸的幾次回族人主持的祈雨文化現象。
我國民間的祈雨習俗遍及大江南北,這在歷史文獻、文學作品、各地各民族文化遺存中都有證據可尋。而且如前所述,它上及皇帝雩雨、中間為官宦祈雨、下為尋常百性求雨,盡管從科學上來講它沒有實證性,甚至就是一些迷信性質的行為,但它在歷史上是一種與理性抗旱活動并列的“抗旱”機制,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也是無法否認的。
2.恤刑機制
我國皇帝被喻為是天之子,認為皇帝是代天在人間行命,所以有了君權神授的思想。“天者,百神之君,王者之所最尊者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9]507,386,355人間君王既然是天之子,是受命于天,那天就可以感知君王的德行操守,這就是“天人感應”。由于有此感應之說,人間的君王如果在其任內遇有災異,都會認為是自己在治國方面出了差錯,所以天才降災于人間,也因此天子要自省和內斂。為補過錯,災時要進行恤刑,實行寬政。這樣的機制在中國行了幾千年。在干旱災害的各種應對機制中,皇帝的恤刑寬政也是一種被認為有效的機制之一。據學者對二十四史中因災異而大赦天下的統計,這種恤民恤刑的寬政行為在清代以前共29次,其中涉及旱災的為8次。[10]95-96
清朝道光朝及其以前的206年間(1644年~1850年),皇帝共進行了因災恤刑活動67次,其中因旱災的就高達58次之多[6],平均每三年多就有一次。從這種現象看,因旱恤民已成為清朝中前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常事了。清代恤刑的內容主要有清理積案要案、因災赦免、因災緩刑、停止詞訟等等。據文獻記載,恤刑的結果往往是“甘霖大沛,遠近沾足”。
因旱災恤刑,可以緩和階級矛盾或緩和社會矛盾,但絕非可以緩解旱情,我們從清朝中前期的頻繁恤政可知,如果恤刑可以得到上天的憐憫而不再降災,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就不會每幾年就要罪己一次了。不過,這樣多的恤刑寬政,使這種文化現象真正成了應對旱災的一大機制卻是成立的。
(二)理性聯合抗旱機制
理性指的是計劃的縝密性、手段的可行性、目標的可達成性或有效性。理性行為是指反復實證過的、從經驗上來說是旁人或自己親歷過、結果方面也是可預期的行為。理性的抗旱機制就是與前述的非理性的、不確定的祈雨、罪己恤刑相對應的直接解決問題的機制。我們說過,在應對旱災的歷史中,我國一直是理性與非理性兩條道并行的。一國如此,一村一寨也大體如此。
理性的聯合抗旱機制指的就是國家、旱區官府及受旱人共同聯動的抗旱機制。歷史上,在國家有效操控政權的時候,在離行政中心區較近的地區,這樣的機制一直是存在的。而且這樣的機制像一個有機的鏈,將國家君王、地方官和受災人民綁在了一起,成為了一個聯動的機制。當然我們也反復強調過,這樣的機制也是與非理性的感應性機制并行的。
首先,從國家的層面上看,我國古代的國家是屬于家族統治的國家,因此,歷代大多數頭腦清醒的皇帝主觀上是高度重視旱災的救助的,客觀上也有相關的得力措施,畢竟江山是自己的或是自己家族的,明智的皇帝總是會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從私來說恤民是為了自己的社稷江山。也因此他們會從國庫中支出銀糧,或責成地方官全力救助。
就地方官來說,無論官有多大,畢竟都是皇家的走卒,所以遇有旱災時,大多數明智的官宦也會為保全自身的既得利益為旱災盡些人事,如發放救濟、組織災民就食等,當然也不乏有發國難財的人。
歷史上,包括君王在內的官方主要采取一些措施進行救助,如漢代實行稟給衣糧、減免租賦、假民公田、假貸種子和農具、撫恤安葬等等。其他各代也不外就是賑濟、移民就食等措施。這些措施,多少都能緩解由旱情引起的生活壓力,多數時候也起到了維護社會基本穩定的效果。
民間自救是最為具體的救助行為,往往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為。從民族學人類學的經驗看,民間自救主要有戶內自救、家族互助、鄰里互助等類。家庭自救主要體現在對自己的家人、禽畜、農田負責,特別是率先滿足現實的人畜飲水問題。在2010年干旱的西南地區,有許多此類的報道。在組織考察的貴州紫云和黔西南州各縣大都如此。干旱初期農戶自己找水背水儲水,在屬于麻山區的紫云縣境公路沿線,當地苗族群眾旱情來臨后會用200元錢買一車水以備家用。而在普安三板橋鎮的一些彝族村寨,在政府介入前他們要到3公里外的溶洞中去排隊接水,來回一次得幾個小時。
傳統上,中國農村都是結家族而居,所以最小范圍的互救首先往往是家族內自救,族長們會領著家族成員一起打井或尋找新的水源,在發生因搶水導致的沖突時也往往是以家族的對立面出現,很少有非血緣的社區聯合搶水行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筆者也在自己的家鄉親歷過在水源地搶農田用水的事情,當時對立雙方也大抵是以家族為單位。
超出家族自救范圍的首先當數親戚互助,這樣的互助主要是糧食和種子方面的自助,也有有水的親戚幫無水的親戚照看牛羊等牲畜的。
2010年,筆者考察的貴州省冊亨縣和望謨縣的個別地方,也有相鄰民族之間互助的情況,互助的內容主要是山下有水的布依族主動幫山上無水的苗族同胞育秧苗。在各民族雜居的旱區,這樣的事例并不鮮見。
總之,理性抗旱君、臣、民之間是同時進行的,是一種聯動的機制。當然,工業化之前的時代由于受信息傳遞限制、交通不便等因素延誤,邊遠地區的抗旱聯動更多的是地方性的聯動,來自皇家的“恩典”非常少。
四、傳統旱災轉移機制
上文講的聯動機制,指的是災民各安其居地情況下實施的由理性機制和非理性機制組成的皇帝、地方官及災民之間的聯動。但如果災情持續嚴重,就得采取轉移機制,轉移機制有官方組織的轉移和民間被動的流徙轉移兩種情況,如果官方不組織轉移而災民又無法再生存下去或流徙過程中不順利,往往會產生極端的諸如起義、械斗等的對立機制。
(一)官方的災情轉移機制
歷史上,如果一個地方旱災太嚴重,民間自救、政府賑濟等行為均無法使災民在原居地堅持下去的話,官府往往采取“移民就食”,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役,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魏書·食貨志》)。《隋書·食貨志》中也有隋文帝時官府購買牲畜分發給關中旱災地區災民,讓他們到關東就食。《元史·世祖本紀》中也有“諸路旱蝗,告饑者令就食他所”的記載。
一些因災流徙后又回到居地的農民,“官方也假公田,貸種、食”(《漢書·宣帝紀》);因旱蝗、地震“詔:其山林饒利,陂池漁采,以贍元元,勿收假稅”(《漢書·和帝紀》);因京師饑荒,流民多,漢安帝命令“經鴻池假與貧民”,“上林、廣成苑可墾辟者,賦與貧民”(《漢書·安帝紀》)。
總之,歷史上,如果有英明的皇帝,又在官府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對災民還是采取了各種措施進行安置的,如同以上所列的移民就食及對流民的寬政政策,無疑是一種減災安民的轉移機制。
(二)災民被動流徙
在我國歷史上,因種種災害而使災民流徙的比比皆是,之所以選擇流徙,原因很簡單,肯定是自救和他救均失效后的無奈之舉。
因旱災而流徙的例子史不絕書,茲舉幾例。公元前17年至公元前15年,由于連年的“水旱為災”,至使“倉稟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役死者以萬數”(《漢書·薛宣傳》);《南史·梁本紀下·元帝本紀》“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魏書·食貨志》“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公私闕之”,“行者十五六”;公元880年,“農桑失業,……人戶逃亡”(《舊唐書·僖宗本紀》); 1315年“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盜起”(《元史·仁宗本紀》);明崇禎年間,或水或旱,“流殍載道”(《明史·五行志》);清光緒二年,江北旱災嚴重……前赴蘇常者千萬(轉引自《中國救荒史》)……
旱災引起的最極端行為就是起義,歷史上,因旱災引起的流民起義很多,如兩漢間的王匡、王鳳綠林起義,西晉時的李特領導的起義、北宋時期的方臘起義、明末的李自成起義等都與旱災有關,而且這些起義大多都是由旱災產生的流民為主體的起義,甚至起義的領導者都是旱區的流民,如王匡、王鳳、李自成等人。
災民流徙是旱災求助失效或無力求助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往往使問題更加嚴重,使一些流民走上了極端的反官府的道路。從這一角度講,歷史上旱災的應對機制很值得研究。
可見,我國傳統上應對干旱的機制依序為:預警—防范—旱期應對—轉移。轉移機制要視旱情的程度而定,普通的旱災由前三項組成一個機制圈,嚴重干旱時才加進轉移機制。
從以上分析我們還看到,在前三個彼此聯接的機制中,每一個環節都是理性與非理性機制并存,行的是雙軌機制,這樣的機制,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其特點都很鮮明。這樣的特點,使我國歷史上的應對旱災機制文化別具一格。它充分體現了我國傳統社會天人感應或人神共生、民胞物與的價值觀念。因此是值得重視也值得研究的。
在理性應對機制中,有許多方面至今都有借鑒意義。
另外,氣候、天體、植物類預警機制也值得重視,干旱與這些預警因素的聯系我們不得而知,但這些因素的變化與干旱之間肯定不是偶合,它們之間肯定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只是現代科學還無法詮釋罷了。如果能破譯這些“密碼”,那其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可估量了。
[1] 鄧云特.中國救荒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2] 趙得秀.論水旱災害的發生與日食效應的關系[J].中原地理研究,1983(1):18-22.
[3] 清世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 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張一平.唐王室雩雨考述[J].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68-69.
[6] 趙曉華.清代的因災恤刑制度[J].學術研究,2006(10):98-104,148.
[7] 全宋文[M].成都:巴蜀書社,1992.
[8] 張月琴.大同地區祈雨儀式與權威的建構[J].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29-32.
[9]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0] 徐式圭.中國大赦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
On the Features of Coping Mechanism Adop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LI Xiang-xing1, LI Yu-jun2
(1.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ping mechanism adop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which consist of early warning, prevention, response and transfer. Almost every mechanism has a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rought; coping mechanism; discussion of features
X432.74
A
1674-9200(2014)04-0042-07
(責任編輯 楊永福)
2013-12-25
李相興(1966-),男,彝族,云南南華人,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李玉軍(1981-),男,彝族,云南南華人,文山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云南民族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