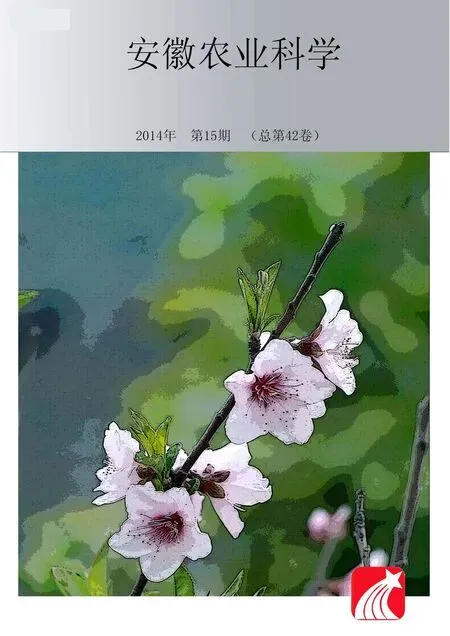生態人類學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例
張明波
(湖北民族學院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湖北恩施 445000)
生態人類學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例
張明波
(湖北民族學院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湖北恩施 445000)
生態人類學的主旨是探討人與環境的良性發展,這種價值訴求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即堅持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結合民族地區實際,大力發展生態經濟,實現民族地區生態與經濟和諧發展。
生態人類學;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事關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局。民族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自身發展能力弱,必須按照生態人類學的理念要求,強調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積極尋求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道路。
1 生態人類學的價值訴求
生態人類學緣于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思考,一般認為是斯圖爾德于20世紀50年代倡導的“文化生態學”是“生態人類學理論產生的直接源泉”[1]。而生態人類學”一詞則由美國學者維達(AndrewP.Vayada)和拉帕帕特(RoyA.Rappaport)于1968年首次提出。關于生態人類學的含義,學術界存在著爭議。其中,日本學者綾部恒雄認為,“生態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及其進化的人類學的一個領域”[2]。我國人類學家宋蜀華認為,“生態人類學著重研究人類群體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并把人類社會和文化視為特定環境條件下適應和改造的產物”[3]。宋先生還指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種生態環境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國家,如何處理好三者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課題,迫切地需要和發展生態人類學學科”[4]。
因此,可以說生態人類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人與環境的關系。在生態人類學的視角下審視經濟發展問題,應該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用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的話來講應該實現由“舊式現代性向新式現代性轉變”,前者片面強調人的力量和主宰,后者則強調“天人合一”。生態人類學強調發展要注重經濟、社會和生態的綜合效益,筆者認為,生態人類學理念對于指導民族地區探索發展道路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在我國的一些少數民族的發展中,他們也在不斷地就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思考,逐步積累了一些關于人與自然實現和諧發展的生存智慧。如學者李本書研究指出,“傣族對于‘龍山林’的敬畏,在文化層面是一種有益的生態意識觀念,在實踐層面上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5]。他還指出,生活在云南的彝族、白族、哈尼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對一些樹木和森林充滿了敬畏,并將它視為神圣的地方,這其實對于保護森林,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有著重要的意義。大多少數民族都有圖騰的植物或動物,有的民族把一定的動物視為他們的保護神,如白族人視雞為保護神,摩梭人把虎視為守護神等等,“一些社會的所謂土著或部落人民……保持著一種與自然環境親密和諧的傳統生活方式”[6]。
筆者認為,少數民族積累的這些生存智慧對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實施下,伴隨著西部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改善,民族地區必將加快現代化步伐。同時,這也會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的破壞,再加上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往往比較脆弱,對于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將產生很大影響。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例,該地區位于我國西部高原和東部低山丘陵的過渡地帶,地質結構十分復雜,山崩、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時常發生。該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旅游產業開發,都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產生著很大影響。因此,該地區發展必須高度注重生態環境保護,不能片面地追求GDP,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2 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
生態人類學的核心是正確地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這與今天要求踐行科學發展觀,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是一致的。就民族地區而言,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迫切需要加快發展。同時,必須考慮到民族地區實際,不能片面強調經濟發展,要注意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在我國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中,如不保護好生態環境,不按生態規律辦事,就會破壞生態平衡”[7]。當前,民族地區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還存在很大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地區許多領導還是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各級政府部門必須正視民族地區客觀上存著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現象,因為“我國土地資源生態環境質量較差、難以生存土地,占全國土地資源總面積的53%,主要分布于民族地區”[8]。正如有學者指出,“民族地區的發展面臨著其脆弱生態環境的嚴重制約,生態環境問題乃是民族地區發展的瓶頸”[9]。民族地區生產方式落后,工業主要以能源、煤炭、石化、采掘等為主,環境污染嚴重;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加快,污水處理系統、生活垃圾處理滯后,存在破壞生態環境問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資源,掠奪式開發,竭澤而漁,唯GDP依然比較嚴重。
筆者認為民族地區不能過于強調與發達地區相比,必須樹立正確的經濟發展理念,切實摒棄僅僅注重經濟發展的錯誤觀念,要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因地制宜地發展特色產業,注重綠色產品開發;要調整產業結構,注重發展低碳產業;要注重民族文化保護和開發,提高文化產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要制定和執行完善的環境保護和懲治機制,切實保護生態環境。“民族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必須摒棄單純工業化,片面追求產值的社會發展觀,樹立符合民族地區長期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保障本地區具有長期發展的能力”[10]。
3 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大力發展生態經濟
在生態人類學的理念下審視民族地區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筆者認為民族地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從實際出發,大力發展生態經濟,促進民族地區和諧發展。生態經濟要求“把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機結合起來,實現生態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1]。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將生態經濟的理念貫徹到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中去,結合區域特點,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和生態文化旅游,促進民族地區繁榮和發展。
3.1 發展生態農業 對民族地區而言,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是建設新農村,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狀況的一條有效途徑。民族地區在利用民族地區的資源優勢的同時又要注重環境保護,注意森林、草地、水源、特色資源的保護;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特色農業,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場競爭力。將生態農業的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實現民族地區加快發展。
恩施地區近年來在探索生態農業的道路上前進較快,第一,恩施州提出了“生態立州、產業興州、開放活州戰略”,十分注重特色農業建設,已經形成煙葉、茶葉、蔬菜、林果、藥材、畜牧等主導產業,并通過努力建成了全省最大的煙葉、茶葉、高山蔬菜基地。第二,成功地探索了“五改三建”生態家園文明新村建設模式,即改水、改路、改廚、改廁、改圈、建沼氣池、建高效經濟園、建現代文明家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第三,挖掘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村寨,發展觀光農業,扶持農家樂,大力發展農村休閑體驗和旅游,有力地推動農業發展、農村進步和農民增收。如恩施市成功打造的楓香坡侗族風情寨、柳州城休閑度假區、蓮花池旅游新村、望城坡—茅壩槽休閑旅游景區已經產生了很好的旅游效應和生態效應。
3.2 發展生態工業 西部民族地區工業比較落后,大多還是以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產出的增長方式,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污染嚴重。為此,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生態工業。
恩施的工業不夠發達,工業化程度不高,工業總量小。“十一·五”期間,恩施州規模工業增加值從28.9億元增加到101億元,年均增長22.7%。結合地區實際,恩施著力打造了食品、能源、煙草、藥化、建材、礦產等六大支柱工業的發展,“十二·五”期間恩施正努力打造綠色食品、潔凈能源、礦產加工、建材開發、現代煙草等“五大百億元產業工程”。筆者認為,恩施地區發展要充分考慮當地的資源、環境、文化優勢,高瞻遠矚,準確定位,長遠規劃,應該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不能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工業化發展思路,應該大力發展特色產業,注重清潔能源開發,培育生態工業,充分發揮生態和文化優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3.3 發展生態文化旅游 西部民族地區應該充分地利用民族地區的優勢,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民族地區旅游開發應以不損害生態環境為代價,要將旅游經濟與生態效益結合起來,在各環節都要強化生態意識。同時,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旅游潛力,“制訂生態旅游規劃,實施完善的生態調控與管理措施,尋找基于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措施”[12]。
近年來,恩施注重發揮生態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優勢,積極扶持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湖北省委省政府關于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重大戰略更是大大促進了恩施旅游的騰飛。“十一·五”期間恩施交通狀態大大地改善,高速公路、鐵路、航空的迅猛發展為恩施旅游強勁發展提供了堅強的保障。恩施目前有5A級景區1處,4A級景區3處,恩施市和利川市被評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通過舉辦中國·恩施生態文化旅游節等活動,進一步擴大了恩施旅游知名度,恩施州2013年獲“最佳中國城市旅游目的地”稱號。筆者認為,未來恩施生態文化旅游有更大的前景,但是,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恩施生態文化旅游一定要站在全省、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高度來進行準確定位和科學謀劃,要在特色上做文章,在特色上下大力氣;第二,要不斷打造恩施生態文化旅游的品牌,正如社會學家指出,中國已經逐步進入消費社會,人們的消費也是在消費符號。其實在筆者看來,旅游是一種消費,更是在消費符號。因此,恩施要充分發揮該地區民族的、歷史、生態的優勢,進一步挖掘文化內涵,提升恩施旅游品牌,擴大宣傳,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宣傳好、推介好恩施,使恩施家喻戶曉,將恩施打造成為一個全國知名,在世界上有一定影響的生態文化旅游勝地;第三,圍繞完善“吃、住、行、游、購、娛”旅游六要素,大力推進旅游配套設施建設。生態文化旅游是一個系統工程,要高品位、全方位、重細節地加大建設,全州廣大人民群眾要有長遠發展眼光,通過千方百計的努力使每一個在恩施旅游的人都能夠玩得開心、住的舒心、吃的放心,使他們成為宣傳恩施、推介恩施的重要力量。
4 結語
總之,生態人類學對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思考及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總結的一些生存智慧,對民族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民族地區應該堅持科學發展觀,結合自身實際,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注重生態經濟發展,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1] R·McC·內亭.文化生態學與生態人類學[J].民族譯叢,1985(3):23-29.
[2] 任國英.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J].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5):85-91.
[3] 宋蜀華.人類學研究與中國民族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4):62-67.
[4] 陳心林.生態人類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J].青海民族研究,2005(1):45-50.
[5] 李本書.善待自然:少數民族倫理的生態意蘊[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5(4):89-95.
[6]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M].王之佳,等,譯.長春:吉林出版社,1997:143.
[7] 宋蜀華.民族學的應用與中國民族地區現代化[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5):1-9.
[8] 馬林,楊玉文.民族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芻議[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42-46.
[9] 包慶德,王東. 西部開發與民族地區發展理論研究之進展[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10(2):94-98.
[10] 樸今海.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1):17-20.
[11] 程顯煜,陳釗.發展生態經濟 加快西部發展[J].天府新論,2000(2):28-33.
[12] 閆紅霞. 基于生態人類學的西藏原生態旅游研究[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145-149.
Eco-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ulti-national Areas—A Case Study on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ZHANG Ming-bo
(South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earch Center,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Eco-anthropology aims at discuss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nvironment, which direc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ulti-national areas, i.e., hold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hifting the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promoting eco-economics on the basis of multi-national areas realty, and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ecology and economic in multi-national areas.
Eco-anthropology; Multi-national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國家民委項目“和諧社會語境下的農村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研究”(08HB01)階段性成果。
張明波(1980- ),男,湖北鄖縣人,碩士,研究員,從事社會學研究。
2014-05-04
S 181.4
A
0517-6611(2014)15-0494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