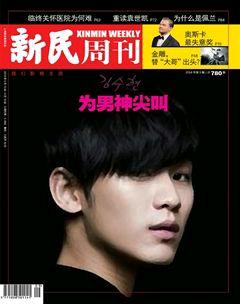羅敬頻:絢爛之后的窯變
2014-03-20 08:09:29沈嘉祿
新民周刊
2014年9期
沈嘉祿



申窯這把火還能燒多久?
申窯,一度成為上海文化人和陶瓷愛好者茶余飯后的談資,但在一番喧騰過后似乎陷入了沉寂。有朋友問羅敬頻:在上海產(chǎn)業(yè)轉型、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歷史大革局中,有沒有必要再搞一個可能產(chǎn)生環(huán)境污染的陶瓷產(chǎn)業(yè)?
羅敬頻這樣回答:這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產(chǎn)業(yè)問題,而是創(chuàng)新的問題。上海確實沒有必要搞大規(guī)模的陶瓷產(chǎn)業(yè),這個地方本來就缺少陶瓷材料。但作為藝術創(chuàng)新,卻很有必要。
十多年前申窯初建,羅敬頻與俞曉夫、黃阿忠、馬小娟、石禪等畫家簽約,再從景德鎮(zhèn)請來富有經(jīng)驗的窯工制作瓷坯。每個器型都是羅敬頻與畫家一起設計,從傳統(tǒng)器型蟬蛻而出,現(xiàn)代感很強。這里的瓶或碗無論多么龐大,都由手工拉坯而成,拒絕工業(yè)化的灌漿胎,從而保證畫家擁用很踏實的手工感。釉面處理也以釉中彩、釉下彩居多,極少釉上彩。
玩過陶藝的人都知道,燒窯最終靠的是“上帝之手”,在高達1300度的氣氛中,器型的完整、釉料的流淌與還原是最不確定的。但這就是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陶藝的魅力,對藝術家形成難以抵擋的誘惑,也對申窯形成一次次挑戰(zhàn)。
最終,申窯獲得了成功。這個成功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在藝術創(chuàng)新上,簽約畫家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具有現(xiàn)代審美理想的陶藝作品,使油畫國畫的表現(xiàn)技法在陶藝上獲得全新效果。第二層面在文化影響力上,申窯的作品一面世即令中國陶藝界耳目一新,連景德鎮(zhèn)的藝術家也從中獲得諸多啟發(fā)。……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