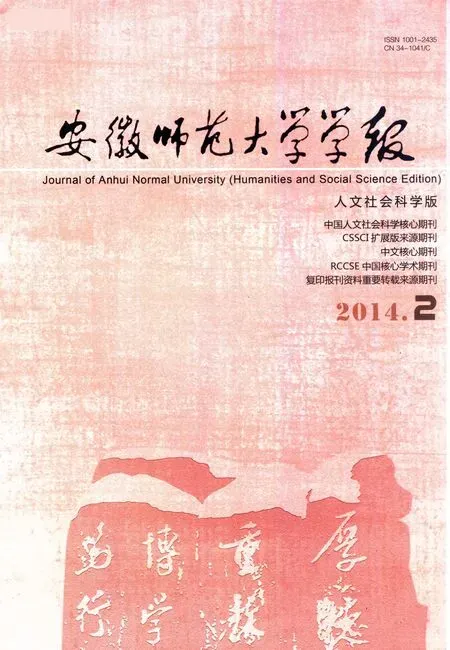主持人的話
按照學界的初步看法,所謂“思想咨商”就是以消解思想癥結、去除精神痛苦為旨要的思想關懷活動。在思想咨商研究者看來,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從動物界中脫穎出來,成為萬物之靈,也正是因為“思想”帶給了人們精神的愉悅,同時也帶來了精神的苦楚。按照悲觀意志主義者的說法,成功所帶來的精神愉悅總是短暫的,為了成功所付出的苦楚卻是長久的。因而,解決由“思想”困惑所帶來的精神苦楚便成為人們孜孜以求的事業,所謂的人生幸福論、道德境界論等,無不以消解精神痛苦為旨趣,以追求精神快樂為訴求。古往今來,無數智者因其在解決人們的思想困惑和精神痛苦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備受世人敬仰,比如古希臘蘇格拉底,再如古代中國孔子,等等。應該說,蘇格拉底和孔子的工作本質上就是在做“思想咨商”,他們是“思想咨商”的先驅踐行者。
雖然我們可以把蘇格拉底和孔子的工作看成是“思想咨商”活動,但他們未明確提出“思想咨商”概念,也不是在明確的“思想咨商”訴求下有目的地進行這種活動,因而,他們的思想咨商工作只是一種素樸的思想關懷活動。在明確的“思想咨商”概念之下有目的地進行思想關懷活動是現代人的事業。從廣義上說,在實驗心理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心理咨詢活動,乃至在心理咨詢基礎上衍生的理性認知療法、意義療法,以及在回歸蘇格拉底哲學風格中產生的哲學實踐活動,在思想政治教育經驗中總結的談心教育方法,等等,都載負著“思想咨商”的部分屬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在發揮著“思想咨商”的功能,踐行著“思想咨商”的旨趣。當代“思想咨商”雖然積極吸納了上述學科領域的有效做法,但是,從狹義上說,這些活動和方法并不就是“思想咨商”。因為“思想咨商”有自己的目標導向、學科依托、研究范式、工作原則和操作規程,有其獨特的內在規定性。比如,“思想咨商”的確要幫助案主澄清思想困惑,但它并不持“價值中立”的主張;“思想咨商”要以開放的心態積極吸收心理咨詢和哲學實踐的有效方法,但它并不只是為了解決案主的心理障礙,也不只是為了“做哲學”;“思想咨商”需要通過對話與案主進行溝通,但它并不是以案主為中心,而是主張發揮咨商師的主導和引領作用,如此等等,足以見得“思想咨商”是一個新概念,也是一個有待發掘、值得深究、前景廣闊的新領域。
本期刊發的四篇文章所體現的正是“思想咨商”的獨特主張。王習勝《“思想咨商”及其中國式問題論要》介紹了“思想咨商”概念創設的學科背景及其思想資源,同時將其與相關概念作了較為清晰的區辨。他在文章中剖析了在中國社會語境中生成的“思想癥結”所帶有的中國心理、中國思維、中國方法、中國價值和中國判斷等中國特質,指出在中國社會語境中有效地開展“思想咨商”活動所要夯實的理論基礎及其恰當的目標預設。楊希《國外“思想咨商”相關研究概要與檢視》梳理了國外“思想咨商”研究的主要節點、代表人物及其所創方法、國外“思想咨商”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別從工作重心、基本原則、學科范式和終極目標等方面作了可貴的檢視。蘇嫈雰《論先秦儒家人文療愈的雙回向系統》則從先秦儒家的思想寶庫中挖掘“思想咨商”的資源,揭示了“和”與“予”的人文療愈的雙面向價值,即以“予”掌握“知”﹝智﹞,在我與你的關系中實現“助人”;以“和”觀照“誠”,在我與己的關系中實現“自助”。薛曉陽《宗教治療倫理立場的哲學討論》探究了宗教的人文治療價值,指出宗教治療給病人帶來的不僅是健康更是人生的意義,本質上是對人生的治療,將宗教資源引入心理治療之中,有助于心理治療從關注“治療手段”走向關注“治療目的”,從而實現心理學意義的疾病觀發生根本的變革。四篇文章分別從中、外、古代和宗教的緯度體現了“思想咨商”研究的基本性狀,是以開放的視閾與多面的視角呈現了雛形中的“思想咨商”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