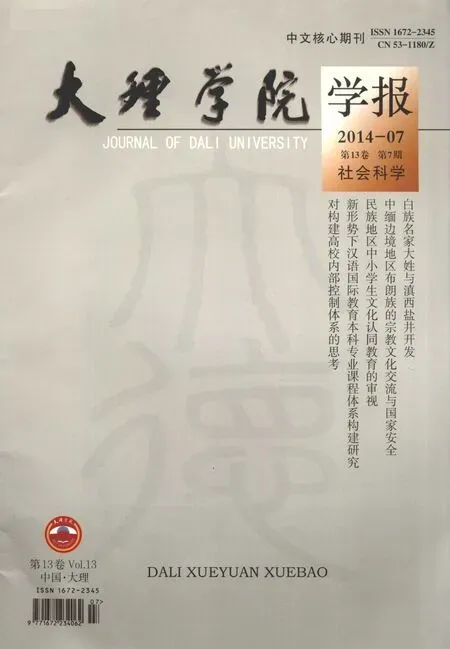《阿姆斯特丹》的人文主義解讀
鐘 妮
(大理學院外國語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伊恩·麥克尤恩是當代英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英國人文主義協(xié)會的支持者。他的作品常常從藝術與科學、道德與理性出發(fā),探討人生的價值與人性的理想,蘊涵了豐富的人文主義元素。
人文主義是一種生活姿態(tài),培養(yǎng)人的道德意志和創(chuàng)造性生存,以達到完善個人的目的。人文主義者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fā)點,堅信理性與自由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認為道德與社會的基礎源于自由和道德平等。他們認為文學必須體現(xiàn)道德價值,通過語言文字展現(xiàn)出人應有的秩序、節(jié)制和分寸。在這一點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麥克尤恩也不例外。
《阿姆斯特丹》是麥克尤恩1998年的布克獎獲獎作品。小說講述主人公克萊夫藝術創(chuàng)作的理想與失敗、道德抉擇的失誤與勝利幻覺,揭露主人公的創(chuàng)造性生存與道德意志的缺憾與理想。作品表現(xiàn)出豐富的人文主義思想。
一、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缺憾與理想
“創(chuàng)造性生存是在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中展開,是人類發(fā)展中理想的生存狀態(tài)。創(chuàng)造性生存是朝向人的全面發(fā)展目標的生存”〔1〕。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缺憾與理想在小說主人公克萊夫身上得到了具體化的表現(xiàn)。小說講述的是早年間,作曲家克萊夫因代表作《美之憶》而名聲大噪。1996年初,步入中年的他被政府委以重任,為4年后的千禧年創(chuàng)作一部交響曲,但進展緩慢,三番四次地催稿下才勉強完成。首排儀式后,過半的管弦樂手拒絕演奏千禧交響曲;意大利指揮家直言他厚顏無恥地剽竊了貝多芬的《歡樂頌》〔2〕176,整部交響曲簡直就是失敗;音樂評論家稱這部作品是后現(xiàn)代式的引用〔2〕164;英政府的千禧狂歡會計劃也只得作罷。克萊夫原本期望借助這部作品能重新登上事業(yè)的頂峰,捍衛(wèi)其樂壇地位和尊嚴、實現(xiàn)其人生價值和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理想,但事與愿違。
表面上看,是一次偶發(fā)事件終止了克萊夫修改樂章的計劃,他勉強交出一份不合格的樂稿,才引火燒身。但真正的原因是克萊夫正經(jīng)歷中年危機,在舊情人莫莉的葬禮后,危機加重。他變得郁郁寡歡,整日哀悼死亡;他疑神疑鬼,擔心自己罹患疾病。顯然,這并非是理想生存狀態(tài),這無益于藝術靈感的激發(fā),也無益于創(chuàng)造力的生長。對死亡的憂思讓克萊夫無法專注于藝術創(chuàng)作,他最終樂思枯竭,留下了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缺憾。原本用來紀念20世紀之終結的交響曲,卻成了克萊夫藝術生涯的哀樂,悲鳴當代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缺失和藝術大師的缺位,突顯出這一時代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缺憾。
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缺憾和理想在藝術大師和科學巨匠們的“推波助瀾”下顯得愈發(fā)醒目。麥克尤恩將莎士比亞、彌爾頓、布萊克、福樓拜,貝多芬、舒伯特、布里頓、普塞爾,達爾文、牛頓、梵高等大師的名字數(shù)次置放在小說的顯眼位置。而在《阿姆斯特丹》的小說世界里,唯一的藝術大師——克萊夫——卻是一個蹩足的音樂家。莎翁等巨匠的反復出現(xiàn)與蹩足音樂家克萊夫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反差投射出的正是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理想和缺失,暗示了當代藝術創(chuàng)造和自然科學領域人才的匱乏,揭示了作者對創(chuàng)造性生存理想的極度渴求。正如麥克尤恩在《審判日》一文中寫道:“自然選擇理論影響力很大,但是它依然翹首等待‘它的靈感四射的整合者,它的詩人,它的彌爾頓’”〔3〕。麥克尤恩崇尚自然科學,但也看重人文精神對現(xiàn)實的引導和救贖,他深信“作家能夠觸到科學所能企及的一切領域,卻絕不會被科學所替代。這是因為作家探究的是人的本性、現(xiàn)狀及特定環(huán)境里的表現(xiàn)”〔4〕。在這里,彌爾頓儼然超越了其時代,被抽象化為人文精神的代名詞,依此類推,《阿姆斯特丹》里的莎士比亞、布萊克、福樓拜、貝多芬、舒伯特、布里頓、普塞爾、梵高亦是彌爾頓,他們皆是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象征、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符號;而達爾文、牛頓亦是彌爾頓,他們是科學理性的象征、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標志。莎翁也好、達爾文也罷,在麥克尤恩的文本中,他們已被抽象為創(chuàng)造性生存缺憾的顯影劑與創(chuàng)造性生存理想的豐碑。
二、道德意志的缺憾與理想
道德倫理困境歷來都是麥克尤恩作品關注和探索的主線,其小說特殊的道德力量貫穿了他的全部作品〔5〕。《阿姆斯特丹》揭露了對社會責任的規(guī)避、倫理道德的墮落,懲治假丑惡、呼吁真善美。道德意志這一人文主義元素的缺憾生動地表現(xiàn)在克萊夫的兩次重要抉擇上,而正是選擇的失誤造成了他的最終毀滅。
第一次抉擇發(fā)生在湖區(qū),克萊夫不顧道義、推諉責任,對陌生婦女的險境漠然置之,以為他的命運與路人的命運是不同的道路,沒有交集,卻不知道人是社會性的,不能脫離社會和其他社會成員。正如利奧塔德所言“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島!人是處于復雜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之中、處于特定的政治體制與文化教育環(huán)境之中的,所以人并非是能動的構造者而是被構造的”〔6〕,在抉擇的瞬間克萊夫的命運已悄悄地發(fā)生了改變,失敗的首排正是他為自己已經(jīng)淪喪的道德意志而付出的代價。人文主義的理想是人們相互尊重、相互扶持,謀求全體人類的和諧與幸福。克萊夫的行為違背了社會道德準則。雖然人人享有自由,可是個人的自由必須與社會責任相結合,一個美好的世界將建立在社會成員相互關愛的基礎上。在社會責任和個人利益面前,克萊夫逃避責任,丟棄良知,自鑿道德的墳墓。
第二次抉擇發(fā)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克萊夫和好友弗農(nóng)假借友人間的安樂死之約,相互謀害,雙雙死在這座安樂死合法化的城市。作者以阿姆斯特丹為書名意味深刻。故事開篇描寫道,克萊夫的舊情人莫莉死得太可憐、太狼狽,像動物一樣。她的命運引起克萊夫的關切,出于對莫莉的尊重和關懷,他甚至聯(lián)想到應該為她實施安樂死,至少讓她死得安詳。從這一點來看,安樂死所解決的矛盾是“‘痛苦地死,還是安樂地死’,而不是‘生’,還是‘死’的問題”〔7〕,它是對病患的尊重和人文關懷,符合現(xiàn)代人道主義,是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科學來捍衛(wèi)人的尊嚴的理性選擇。莫莉的命運像一顆炸彈引爆了克萊夫和弗農(nóng)的不安和對死亡的道德思考,二人立下安樂死之約,但結果是君子協(xié)議成了復仇的借口,成了二人喪失理性和道德意志的佐證。兩人在首排酒會上相見,喝下對方為自己準備的毒酒。兩人的瘋狂舉動讓安樂死之約演變成一場陰謀與殺戮,不僅沒能捍衛(wèi)個人尊嚴,反而自損形象,留下了道德的缺憾。
書寫失望和缺憾的同時,人文主義者麥克尤恩也播下了道德救贖的希望之種。彌留之際,兩人陷入了某種勝利的幻覺。恍惚間,弗農(nóng)看見自己仍是報社主編,照常端坐在會議室里主持例會。克萊夫神志不清,把荷蘭醫(yī)生和護士錯當成樂評人和湖區(qū)的受害婦女。樂評人對他的音樂贊不絕口,而受害人正在傾聽他的懺悔,懺悔在湖區(qū)時沒有出手相助,幫助她脫離男子的攻擊。閉目辭世前,克萊夫從枕頭上抬起頭來,“謙恭地欠了欠身”〔2〕169。欠欠身,也許是為了致謝、為人生謝幕;也許是因為悔恨、因為良心發(fā)現(xiàn)。在小說的現(xiàn)實世界里,克萊夫與弗農(nóng)都因道德意志的淪喪而自食其果;而在二人的幻覺里,更確切地說,在作品所向往的人文主義理想境界里,克萊夫受到樂評人的贊賞,藝術創(chuàng)造力得到肯定;他重拾道德感,向湖區(qū)的受害人懺悔;他安詳?shù)仉x開,仿佛在喝彩中謝幕。弗農(nóng)威風凜凜、事業(yè)大展宏圖,實現(xiàn)了個人價值、捍衛(wèi)了尊嚴。顯然,在克萊夫和弗農(nóng)的勝利幻覺里隱匿著作品對人文主義理想的向往。創(chuàng)造性生存與道德意志的缺憾在作品的人文主義理想境界里一一得到了補償,個人得到完善,人文主義的終極目標得以實現(xiàn)。
三、結語
中國作家余華曾形容麥克尤恩的敘述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他說:“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溫暖、荒誕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邊界上,他的敘述兩者皆有。就像國王擁有幅員遼闊的疆土一樣,麥克尤恩的邊界敘述讓他擁有了廣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寫下希望的時候也寫下了失望,寫下恐怖的時候也寫下了安慰”〔8〕。在《阿姆斯特丹》里,麥克尤恩的寫作游離在缺憾與理想、真善美與假丑惡的邊界上,這里既有失敗的交響曲、蹩足的作曲家、羞愧的逃逸者、歇斯底里的復仇狂人,也有喝彩中的謝幕和悔過自新的逃逸者,作者在撥開現(xiàn)實缺憾外殼的同時也在其中注入了人文主義的理想。單純地揭露現(xiàn)實缺憾并非麥克尤恩這位人文主義者的意圖,通過鞭笞假丑惡,他呼喚真善美;通過暴露缺憾,他渴求希望。麥克尤恩樹起人文主義的豐碑,教育讀者要在人類文明文化的寶庫里汲取養(yǎng)料,發(fā)揮創(chuàng)造力和想像力,營造理想的創(chuàng)造性生存狀態(tài),邁出“完善個人”這一人文主義終極目標的第一步。他引發(fā)對生命的人文主義思考,呼吁讀者提升社會責任感,關切和尊重生命,培養(yǎng)道德意志,邁出人文主義終極目標的第二步。至此,道德意志和創(chuàng)造性生存得以培養(yǎng),個人得以完善,人文主義的終極目標得以實現(xiàn)。
〔1〕班保申,匡瑾璘.創(chuàng)造性生存的理論意蘊及邏輯特征分析〔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6):18-20.
〔2〕MCEWAN Ian.Amsterdam〔M〕.London:Vintage,2005.
〔3〕MCEWAN Ian.The Day of Judgment〔N〕.Guardian,2008-05-31(GB16).
〔4〕TONKIN Boyd.Ian McEwan:I hang on to hope in a tide off ear〔N〕.The Independent,2007-04-07(AA14).
〔5〕沈曉紅.伊恩·麥克尤恩主要小說中的倫理困境〔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0.
〔6〕陳嘉明.人文主義思潮的興盛及其思維邏輯:20世紀西方哲學的反思〔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42-48.
〔7〕楊湘紅.安樂死的倫理思考〔J〕.前沿,2002(12):134-136.
〔8〕余華.伊恩·麥克尤恩后遺癥〔J〕.青年教師,2010(6):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