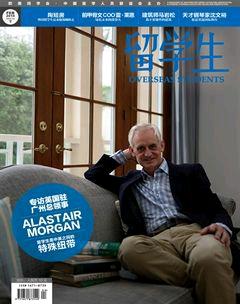專訪意大利語同傳第一人張密:坐上無法停止的列車
張艷

張密,曾用名張宓,我國意大利語教育界先驅,是最早將意大利文學大師卡爾維諾的著作引入中國的翻譯家之一,曾獲意大利共和國總統頒發的騎士勛章和爵士勛章。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意大利語教授、中國意大利語教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務
隨著馬可波羅和圖蘭朵計劃的日漸成熟,意大利的中國留學生數量正在急劇攀升,2005年,整個意大利不過500多名中國留學生,截至2013年底,這一項數字已刷新為1.5萬,僅在2013年,便有3700多名中國留學生前往意國求學。
時間回溯到32年前,有個年輕的女教師也曾踏上這條通往意國的求學道路。那時,她撇下一對年僅2歲的雙胞胎女兒,流淚遠赴異國,生命從此與意大利交織融合。
時光荏苒,當年的女教師已是中國意大利語界赫赫有名的張密教授,她的譯著《一個身子分成兩半的子爵》、《看不見的城市》、《命運交叉的城堡》等,為無數中國讀者開啟了一扇通往文學大師卡爾維諾的門窗。
除此之外,回國后的她還致力于中意兩國的交流活動,為兩國的友好發展搭建起座座橋梁,其本人在1999年和2005年被意大利共和國分別授予了騎士勛章和爵士勛章,在我國能被兩次授勛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這一切的開始,還得從32年前一個年輕女教師萌發的“出去學好意語,回來教好學生”的愿景說起。
出國進修 時不我待
2014年1月15日上午,《留學生》記者撥通了張密在對外經貿大學辦公室的電話,對方一聲“你好,我是張密”拉開了一個半小時的采訪序幕。
盡管已經64歲,卻聽不出絲毫“上了年紀的聲音”,張密發音字正腔圓,聲如洪鐘,思維連貫有序,盡管在記者突然拋出某些問題時稍有停頓,回答時卻能做到縝密周到,不愧是常年在三尺講臺和大型同傳現場廝殺出來的老將。
張密的一輩子和意大利密不可分,這段不解的緣分從1972年便結下了。該年,張密成為高校恢復招生后的首批工農兵學員,入讀北京外貿學院(對外經貿大學前身)的意大利語系,1976年畢業后便留校擔任老師。
1980年的一次短暫的意大利之行,讓張密做出了出國進修的決定。當時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開設的一家皮革廠向意大利引進設備,派遣了技術組前往該國學習,張密作為隨同翻譯,第一次踏上了意大利國土,聽到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語,在交流中捉襟見肘的張密百感交集:“我學的意大利語,完全不夠用,連正規教材都沒有,都是靠老師教,我就想出去學好意語,回來教好學生。”
就這樣,她萌生了出國進修的念頭,跟著技術組回國后,她立即遞交了申請,并在1981年得到批準。盡管當時一對雙胞胎女兒只有2歲,張密把她們送進托兒所“全托”,“走之前我去托兒所看她倆,她們對將有2年時間見不到媽媽這事完全不知情,我偷偷地看,流著眼淚離開,這是我最大的遺憾……”,說到傷心處,張密停頓了,雙方無言。
“那為何不考慮晚點去呢?”記者先打破無聲,這個問題立即讓張密跳過這短暫的低落,回答道:“我必須進修,時不我待,語言不足擺在那里,需要花時間去彌補,越快越好。至于家庭,我們那時候的思想就是工作第一,家庭第二。”
內心有陽光
進修時間為兩年,先后在貝魯賈外國人大學和羅馬大學,這是張密第二次踏上意國,與第一次相比,少了初來乍到的驚喜,多了揮之不去的孤獨。
身在異國他鄉,最令她魂牽夢縈的便是親人,尤其是年幼的女兒,可是沒有國際長途電話,與家人的聯系完全靠書信,從寄出一封信到收到回信,需要等上兩個月。除了了解家中的近況,她最想看到的是女兒們的照片,當看見回信的內容寫道,女兒對別人說,我不是沒有媽媽,我的媽媽在意大利,她很快就回來了時,張密心酸得直落淚。
她深知自己為這學習機會付出的代價有多重,所以更加如饑似渴地學習,食堂、宿舍和圖書館這三點之間的軌跡上循環往復,枯燥的生活中,寂寞感隨時侵襲而來。
“有時候,在宿舍獨自看著書,突然就感到可怕的孤獨,我打開門匆匆忙忙往人多的方向跑去,直到周圍來來往往的人群包圍著我,這種感覺才慢慢緩釋并消失”,多年之后,張密談起那時的孤獨感仍然心有余悸。
盡管留學如此艱辛,張密從未動過放棄的念頭。確實,這點困難對堅強的張密而言,不算什么,喪子、離異、癌癥她都經歷過,并挺過來了。張密說,讓她無所畏懼的,是內心的陽光,她樂于把這種陽光播撒給身邊的人,同時從身邊的人身上得到溫暖和支持。
除了學習意大利語,張密還在留學期間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由于學習任務很重,張密與一同進修的王軍(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意大利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在學習上“結對子”,一人主攻文學,另一人主攻歷史和藝術,然后交換學習心得,這種分享式學習讓二人在班上獲得了第一和第二的好成績,也被張密在后來的教學過程中不斷推廣。
進修到期后,張密迫不及待要踐行出國進修時的最初夢想——“出去學好意語,回來教好學生”。事實上,張密回國后全身心投入意語教學的全面建設中,規劃課程設置、編寫教材資料,連初露端倪的翻譯事業都被擱置一旁了。
翻譯是遺憾的事業
說起翻譯,張密是既愛又恨。
“做翻譯,要挨得住內心的寂寞,耐得住外界的誘惑,受得了稿費低廉的待遇,擔得起文責自負的責任”,她的一串順口溜讓記者忍俊不禁。
《一個身子分成兩半的子爵》是她翻譯的第一本卡爾維諾的作品,張密介紹說“我也是因為這本書才接觸到卡爾維諾的,拿到原稿我就被里面的情節深深吸引,翻譯時也是樂在其中,很享受。”
愉悅的感受并非翻譯帶給她的全部,張密感慨“更多時候的感覺是難!尤其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翻譯是特別辛苦的活計”。
由于教學工作上沖突,張密的翻譯工作總是放在寒暑期的時間進行,有時甚至足不出戶,即使在炎熱的暑期,也悶在屋內埋頭苦干,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翻譯,一氣呵成才肯“出關”。
但張密說這不算辛苦,找書比這辛苦多了,在翻譯《宇宙奇趣》時,自稱“科盲”的她為搜羅參考書到處跑圖書館、找熟人借,甚至請意大利的朋友寄回來,為了一本書累得人仰馬翻。
除了體力勞動外,腦力勞動量也不輕,遇到只能意會不知如何表達的長句時,在腦袋里推敲無數遍;倘若其中還夾雜著大作家使用的生僻字,除了反復查找字典尋出處外,還得找幾個文化修養高的意大利人請教去。
在與意大利文打交道的這幾十年里,張密翻譯的作品字數多達近千萬,翻譯事業橫跨文學、教育、科技、經濟、法律等多個專業領域,其中,不乏有獲得意大利使館文化處“最佳意大利文學翻譯獎”殊榮的《看不見的城市》、經典法律大部頭《意大利民法典》,但是談起究竟哪部是她最滿意的作品時,張密脫口而出道:“沒有滿意的,所以說翻譯是遺憾的事業。”
她繼續解釋道,翻譯《意大利民法典》前后花了三年的時間,即使是這樣“精心打磨”,出版后細細查看,還是出現了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更別說那些加班加點趕出來的“任務”了。
已經從對外經貿大學退休的張密,準備繼續堅守在她稱之為“遺憾的事業”上,“雖然年紀大了,該翻還得翻。”或許正是因為遺憾,才無法停止追求。
“同傳第一人”
盡管翻譯事業是張密人生的一座豐碑,但是她反對記者的“您是意大利語翻譯第一人”的說法,并為此糾正道:“我頂多算個‘同傳第一吧。”
作為中意兩國交往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者,張密常年活躍在經貿、金融、法學、科技、農業、環保、文物等方方面面的會議和活動中。她參加過中歐經濟部長會議、中歐農業部長會議,中意政府委員會和中意經貿混委會等官方重量級會議并擔任翻譯,來自非官方的會議和交流活動的邀請函更是不絕如縷。
意大利語同聲傳譯行業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第一人便是張密,談及她是如何率先從筆譯轉型到口譯時,張密說:“因為我臉皮厚,不怕說錯,說錯也不怕人笑話”,說完她自己笑開了。
張密坦言自己能從教室的講臺登上同傳的舞臺,還有一件趣事。大約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從意大利引進了《最美麗的妻子》等一批著名電影,當時國內觀眾對于電影的熱情空前,孰料這批意大利影片只有原聲對白,沒有中文字幕,張密便被請到放映現場當翻譯,她站在屏幕旁,拿著話筒,面對著人山人海的觀眾,逐句將片中對白口譯出來,十幾部片子放下來,著實讓張密“模擬”了一把同聲傳譯。
接下來的幾次中意雙方的會議,讓張密逐漸找到感覺,等到意大利語同聲傳譯行業開啟時,她淡定地踏入這扇門,邁著堅定的步伐,越走越遠。
20多年過去了,盡管學習意大利語的中國人數量呈幾何倍數增長,可是同聲傳譯人才缺口較大的狀況仍舊沒得到顯著改善,談及原因,作為意語教學者的張密誠懇進行了自我批評:“這首先反映了我們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需要改進”,其次,她認為,“更多同學是被這種即興的翻譯形式嚇退了,不敢嘗試,自己把自己擋在了門外。”
這個話題,勾起了張密對她的學生夏江的回憶,夏江畢業于對外經貿大學意大利語系,在張密的帶領下進入了同傳行業,是近年來意語界最優秀的人才之一,卻不幸于2012年患上胰腺重癥逝世,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就此隕落。
師生二人感情深厚,如同母子一般,在其治療期間,張密曾多次探望,并號召以意大利語界為主的社會人士為其籌措捐款180萬元,對于他的逝去,張密十分惋惜:“感到心痛,不僅為我失去一個好學生,也為意大利語界失去一個優秀的翻譯人才。”
LEARNING BY DOING
翻譯的這條道路上,有的人在思考“如何開始”,還有的人在糾結“如何結束”。
張密說,不少學生來向她討教,若打算以后從事翻譯工作,該做什么準備?張密的標準答案總是:“Learning by doing(從做中學)”。她認為,好的翻譯都是鍛煉出來的,語言底子、文學修養和專業知識都不是問題,統統能夠在實踐中彌補。
“若說我們當時是‘越野,現在頂多如同在大馬路上行駛了”,張密用開車來形容兩代人從事翻譯行業的難易程度,她認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翻譯工作消除了不少客觀障礙,所以“如何開始”的問題,根本不應該成為問題。
但是“如何結束”對她來說,卻是個難題。
人生猶如攀登,有的人在回頭望時,找到“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便不自覺地停下腳步,駐足欣賞起半坡的風光,張密說她很少回頭,望得更多的是前面更高的山峰,做一個匆忙的趕路人。
可以說,除了身體原因,沒什么能讓愛忙活的張密消停下來。2013年1月下旬,一向身體健康的張密,竟然在體檢中被發現胃部出現腫瘤,慶幸的是這個“癌寶寶”發現及時,在未擴散之前,利索的張密立即約好醫生在2月份進行了手術,結果連三個月的復查期都沒過,便在5月飛往意大利參加威尼斯文化節去了。
自從擔任歐美同學會留意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職務以來,張密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我如同坐上無法停止的列車,車轱轆在走,我怎能下車?”張密給記者形容她無法停止工作的感覺。
“那您是從沒想過要下車嗎?”記者追問道。
“有想過,拿同傳來說,我60歲的時候就決定不干了,結果怎么樣,到現在還干著。”張密笑著回答,“現在還不是下車的時候,希望長江后浪推前浪,意大利語界出現越來越多的人才來接班,我們才能安心卸下肩上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