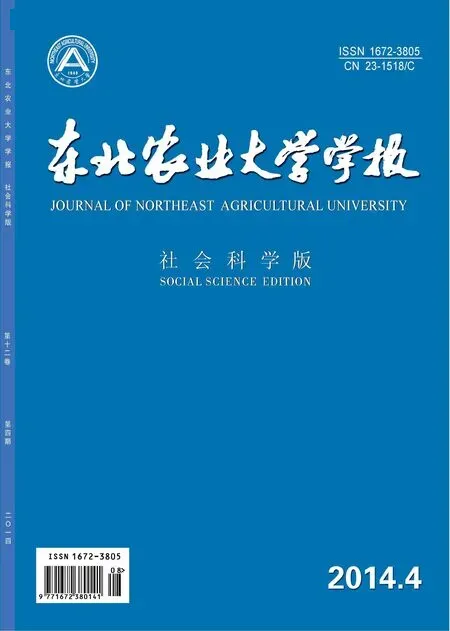合作與抵抗
——對《修辭作為語用的對應學科》的評介與思考
張雅卿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福州 350000)
合作與抵抗
——對《修辭作為語用的對應學科》的評介與思考
張雅卿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福州 350000)
《語用學學刊》2011年第43期《修辭作為語用的對應學科——在語言使用研究中開展競爭性合作》一文,對一直以來懸而未決的語用學和修辭學兩大學科關系之界定提出新見解,并以“不合作原則”首次對當代修辭學的觀念基礎做出系統的理論歸納。該文將交流初始聽話人是否與說話人合作作為區分標準,確定語用與修辭的分野。對這一新的理論視角進行介紹,進一步對其核心觀點,即修辭話語預設了聽話人的不合作(抵抗)以及由此產生的某種關系張力,進行思考與探索。
語用;修辭;合作;抵抗(不合作)
一、國內:語用與修辭
語用與修辭兩門學科的關系一直為學界關注,眾說紛紜而無定論。早自20世紀80年代,漢語界與外語界學者業已陸續開始討論二者關系[1-3]。除部分學者將二者等同以外,大多數討論集中在學科邊界劃線上,試圖厘清界線,合理定位二者關系。概言之,學界主要有三種說法:同心說、向心說與離心說。同心說表現為兩種情形:一是認為兩門學科重合[4-6];二是視二者為從屬關系,如池昌海與王希杰認為,語用學大于修辭學,修辭學歸屬于語用學[7]。向心說包括聯姻觀與借鑒觀:聯姻觀認為,應建立“語用修辭學”[8-9];借鑒觀則認為,二者在各自研究中應密切聯系、相互借鑒[10-12]。離心說認為,語用學與修辭學是對立關系,屬于截然不同的兩門學科[13-15],不能混為一談。
關于二者全同關系的說法,施發筆認為,這樣會產生“一門學科兩個術語的模糊認識”[16]。宗守云則反對將二者視為從屬關系,認為“修辭學和語用學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交叉,但并不存在誰包含誰的問題”[17]。對于聯姻觀的變體(即學科“圈地熱”),王建華批評道:“同當今社會的房地產熱相類似,修辭學界也有一種‘圈地熱’,在某片領域標上一個標簽:××修辭學,便標示建立了一門新的分支學科。至于它能否‘成學’,有無條件和依據是不大管的。”[18]宗世海與劉文輝則嚴厲批評了將修辭學與語用學“聯姻”、整合的風氣,力圖揭示兩門學科的差異。他們認為:“兩門學科所揭示的原則性質不同。”[15]這一見解為理清二者關系指明了方向,具有現實的學術意義。然而他們所謂的“不同”只是“修辭原則是規范的,語用原則是解釋的”這一建立在二元對立上的簡單化表述,顯然全面性不足。同時,他們對“principle”的漢譯持保留態度,指出“將英文的principle翻譯為‘原則’并不是很妥當的翻譯……修辭學所說的原則是強制性的、必須遵守的;而語用學中的principle有‘法則’、一般原理之意,不指必須遵守的原則”。然這一觀點亦含糊且語焉不詳。總的來說,持“語用與修辭相互借鑒”觀點的學者是主流,但往往未能說明二者差異究竟何在。
二、對《修辭作為語用的對應學科——在語言使用研究中開展競爭性合作》一文的評介
語用與修辭錯綜復雜的關系,對兩個學科的學者造成一定程度困擾。探究兩個學科的觀念基礎及其運作原則、厘清學科邊界,對于明確學術分工與合作、開展跨學科對話以及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健康發展均有重要意義。劉亞猛與朱純深發表于國際語用學會會刊《語用學學刊》(Journal of Pragmatics)2011年第43期的《修辭作為語用的對應學科——在語言使用研究中開展競爭性合作》(Rhetoric as the Antistrophos of pragmatics:Toward a“Competition of Cooperation”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下文簡稱《對應》),敏銳地把握這一學術修辭形勢,系統梳理修辭和語用的關系,深入考查語用與修辭觀念基礎與運作原則的實質差異[19]。文章明確指出,修辭的出發點亦即原則(principles)與語用不同,在肯定了語用的觀念基礎是合作原則(principle of cooperation)后,原創性地提出修辭的真正出發點是不合作原則(principle of non-cooperation)。二者共同致力于探討語言使用,彼此相輔相成卻又同中有異。本文就《對應》三個主要部分有關觀點作一介紹,以此為基礎進行思考與探討。
(一)語用與修辭關系淵源及現狀:密切而疏遠且充滿誤解的兩門學科
關于語用與修辭在作為彼此學科“他者”的學術實踐中分別是怎樣的情形與印象,《對應》指出,一部分語用學者征用了修辭的概念卻往往賦予其新的意義,從而對修辭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并致語用學界對修辭產生誤解。即便是Geoffrey Leech這樣的語用大家也不例外,其對“修辭”這一術語的使用不免使人聯想到“換心術”①Leech在《語用學原理》(Principles of Pragmatics)一書中宣稱他所用的修辭這一術語是傳統的,指的是在交際中對語言的有效使用。然而,他所指派給修辭的意義中實際上排除了它與“有技巧地使用語言用以說服、文學表達或公共演說”的那門藝術特定歷史傳統的聯系。當我們提到“修辭原則”時,通常是指那些指導修辭發明的總體綱領,諸如得體或認同等。然而,在Leech的新解釋框架里,它們卻是指對語言使用者施加限制及實現“良好交際行為”的“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等。此外,Leech的“修辭視角”只要求“說話人對聽話人的意識造成如此這般的結果”,這一點偏離了古典修辭理論中規定的演說家的職責,亦即教誨、愉悅、尤其是促成行動的職責。Leech的模式征用了修辭的概念卻賦予修辭以新的意義,將其作為整合現有語用范疇與原則以便形成新理論組態的一個焦點,其對“修辭”這一術語的使用不免使人聯想到“換心術”。。其他語用學者雖對自己極具修辭風格的語用研究心知肚明,卻往往對此諱莫如深。《對應》剖析了語用學中高頻率流通的若干核心概念,如順應(adaptation)、選擇(choices)與凸顯性(salience)等,指出它們其實是修辭學科中使用已久的固有詞匯。總體而言,語用學者對修辭的做法存在雙重脫節現象——“語用學家在使用修辭的時候很少坦然承認是動用了修辭,而當他們提到修辭時表述卻又往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修辭”(Where“rhetoric”is explicitly talked about in pragmatic discourse,it is often made to signify or implicate something that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what the term means traditionally.Where rhetorical thinking i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its presence is scarcely acknowledged.)②本文未注明出處的英文引文皆出自Rhetoric as the Antistrophos of pragmatics:Toward a“Competition of Cooperation”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
同時,《對應》指出,多數修辭學者對語用不以為然,表現出一種“集體漠然”(collective nonchalance),乃至視其為不值一提的話題。修辭學者對語用學的理論興趣,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皆與二者的關系不相稱。少數幾個例外卻又幾乎不約而同地把精力投向Austin與Grice,關注他們作為語言哲學家的一面。
(二)想象的對稱:將語用觀念基礎誤認為修辭運作模式
為拆除兩門學科間壁壘,Dascal與Gross對語用(以Grice構想的語言使用為代表)與修辭(以Aristotle說服傳統為代表)進行了細致對比。他們的近距離觀察使人們注意到一系列深刻差異。比如修辭的中心關注是情感(pathos)與人格(ethos),而語用作為以推理為基礎的認知理論(inferencebased cognitive theory)卻與二者均不相干。Grice會話交流排除了對聽眾有意誤導的可能性,而一個對有意誤導現象不具備解釋力的修辭理論是不可想象的。同時,Grice規定為交際使能條件(enabl-ing conditions)的合作原則在修辭互動中似乎也可有可無。然而,兩位學者對這些差異不以為然,主張Grice合作原則也統轄說服性話語互動,堅持以推理為中心的認知理論改造修辭。在他們看來,修辭只需輕巧地對其術語進行技術性調整,即可實現Grice版“語用化”。《對應》提到,盡管這種經過哲學修補后加盟語用學的修辭學聽起來很激動人心,但該論點在兩個學科內卻未能引發明顯“言后效應”。之所以普遍缺乏吸引力,主要緣于兩個原因:一是未能擺脫對兩門學科彼此關系的“雙重誤解”(double misunderstanding);二是由于一門心思撮合語用與修辭“聯姻”,造成其對兩門學科的差異視而不見。基于語用與修辭觀念基礎與運作原則的深刻分歧,要在兩者之間締結學科盟約,其結果恐怕只會進一步加深業已存在的學術隔閡。
《對應》接下來逐一批駁兩位學者關于“Grice合作原則也統轄說服性話語互動”之論據,同時對其研究中所遇觀念暗礁進行反思——用以表述“聯姻”雙方的術語存在匹配錯誤,是一種想當然的對稱。實際上,語用是以基礎原則(foundational principles),尤其是合作原則描繪自身;修辭則以操縱情感、訴諸人格或有意誤導等運作原理(modus operandi)進行自我定位。《對應》指出,沿Dascal與Gross思路,研究者找到了與合作原則有可比性又不兼容的修辭原則——不合作原則(Non-Cooperative Principle,下文簡稱NCP),認為這完全說得上是合作原則的對應原則。正是這一未被提出的基礎認定,統轄著Dascal與Gross提到的修辭活動的各個方面。
(三)CP、NCP及錯綜復雜的學科關系
《對應》一文將NCP定義為:在與對方交流或談話時,總是預設聽話人不會自愿與你合作以產生預期的效果或結果;在聽他人說話時,總是預設說話人不會主動與你合作,協助你從自己的角度看待當前的問題或按你自己的方式作出決定(When engaging and addressing another party,always proceed without assuming that the addressee would voluntarily cooperate with you in producing the effect orresultyoudesire.Whenbeingengagedand addressed,always respond without assuming that the addressor would voluntarily cooperate with you in your effort to see the matter concerned from your own perspective or to reach a decision about it on your own terms.)。
作為修辭基礎原則的NCP與作為語用基礎原則的CP(Cooperative Principle)在應用性與功能性上均有可比性。二者的對比將注意力引向作為兩門學科觀念基礎的“合作”這一概念,關注“合作”在兩門學科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對應》特別指出,CP與NCP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勢不兩立”。正如其定義揭示的,NCP雖然排除對話交流中為實現說服效果而自愿合作這一可能,但同時也意味著某種非自愿合作的極大可能性,即對話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迫與對方合作。其實,修辭學者從未否認這種意義上合作的可能性。他們盡管私底下遵循NCP,卻都公開承認合作是修辭過程的一個主要成分。肯尼斯·伯克甚至將修辭定義為“應用語言作為象征手段以誘使天生對象征敏感的人們彼此合作”(the use of language as a symbolic means of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beings that by nature respond to symbols)。要誘發(induce)合作正表明它的缺席,等于間接肯定了NCP。將修辭等同于誘發合作,亦指出修辭行為的運作邏輯:盡管修辭行為初始階段將“不合作”作為預設,它卻是以實現、維持并擴大合作為最終目標。修辭恰恰是要應對乃至最終克服結構上預先被決定的一種不合作傾向。《對應》回顧了顧曰國先生的“修辭性合作”觀,肯定了顧的部分觀點,即修辭目標的實現是“使然的”而非“自然的”(“achieved”rather than“assumed”)。同時對顧試圖將修辭語用化,亦即去掉傳統修辭中與語用不一致而難以從語用角度解釋的部分,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剝離了傳統修辭安身立命的關系張力與說服動力的修辭,很難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修辭。
《對應》還深入挖掘了“合作”在兩門學科中的微妙差異,認為“合作”盡管在語用學中指會話參與者遵守一套共同標準的總體協定,但在修辭學中卻暗含兩種不同的協定:說話人同意根據聽話人實際做出一切必要改變與調整,以產生說話人意欲達到的修辭效果,聽話人同意在說話人言之成理的情況下接受對方觀點。這一差別的根源是語言使用者交際目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預設:語用預設談話參與者共同享有一個或一系列共同目標,至少是雙方認可的大體方向,因此一套CP規定的準則通用于對話雙方;修辭則不然,它預設說話人與聽話人的目標存在分歧。如此看來,分別討論各方遵循的合作規范,尤其是這些規范在“不合作原則”中呈現的“負象”(ironical embodiment),顯得十分必要。繼續使用CP作為NCP出發點或參照點,以Grice處理CP的方式看待NCP,《對應》提出以下兩組說話人與聽話人分別遵循的準則:
其一是說話人準則:數量準則(Maxim of Quantity),指所言應包含不少于要對說話對象產生預期效果所需的信息(Say no less than is required for producing the intended effect on your addressee.)。質量準則(Maxim of Quality),指只說聽話人認為或能使他認為是真實或有價值的話(Say only what your addressee believes or could be made to believe is true or valuable.)。關系準則(Maxim of Relation),指只說聽話人認為或能使他認為具有相關性的話(Say only what your addressee deems or could be made to deem relevant.)。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指說話方式要順應聽話人及交際語境(Adapt your mode of presentation to both your addressee and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其二是聽話人準則:數量準則(Maxim of Quantity),指對說話人的認可不應超出你由衷信服的那些話(Concede no more to the addressor than you feel non-coercively compelled to.)。質量準則(Maxim of Quality),指(在說話者的言談中)只同意你對其真實性或價值不存疑義的話(grant the addressor’s point only when you are not in doubt of its truthfulness or value.)。關系準則(Maxim of Relation),指(在說話者的言談中)只考慮你覺得相關的那些話(consider only those of the addressor’s remarks which you find relevant.)。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指僅當你覺得說話者表達方式得體時才認真對待他的話(treat the addressor’s talk seriously only when you find its mode of presentation appropriate.)。
對比Grice合作原則,不難發現二者的鮮明反差:CP預設一種規定性語境,從而使“避免出現歧義”或“要簡明扼要”等準則聽上去順理成章;NCP則預設一種可變性語境,使對表達方式的預先規定毫無意義。Grice模式認為,對話參與者一方對交際情況的估量與對方有一致之處,從而使“統一度量衡”成為可能,即可對信息的質與量做出規定。與此相反,在NCP的框架內,由于說話人與聽話人各自對交際情境有不同定義,因此其關于質與量的利益及標準必定大相徑庭。隱藏在這些差別之下的,是關于語言使用者規范行為中兩種相互沖突的預設,指出語用與修辭兩門學科中不能簡化的觀念差異:語用思維中,合作可被想當然地作為構想語言使用規則的出發點與基礎認定;對修辭學家而言,合作更像是一種耗費心力去實現的目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說服目標產品。語用學者與修辭學者都很清楚,實際話語交際涉及作為同一話語關系的兩個不同側面,即合作與不合作的互動。對語用學者而言,表面的不合作行為歸根結底是一種合作行為,違反CP有時正是為觸發推理過程,以產生會話含義。對修辭學者而言,表面上的合作行為應被視為策略考量,是一種人為“設計”,本質上是不合作行為。說話人違反NCP,或在說話中表現出合作,通常是為了誘發聽話人尚未實現的合作。換言之,這是一種“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策略。違反不合作的預設而表現出合作,歸根結底是為了構建并維系一個說服過程,從而最終產生預期的施為(performative)或說服效果。
(四)在語言使用研究中開展“競爭性合作”
NCP開拓了比較兩個學科新的可能性。二者關系遠比一般的想象更加微妙與復雜:差異使彼此互相征用甚或合并不具可行性,同時又不乏共同目標與挑戰。顯然,兩門學科的實踐者若繼續將對方學科視作與自身研究領域不相關學科,將不利于學科健康發展。為搭建一個讓兩個學科實踐者定位自身、為共同利益與目標協調行動的總體框架或參照系,《對應》借鑒亞里士多德“修辭與辯證”的學科關系模式提出,不妨把修辭視為語用的對應③“對應物”指與另一事物非常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的事物。參見羅念生所譯亞里士多德《修辭學》。(disciplinary antistrophos)學科。兩門學科在對應關系指導下相互觀照,取長補短,為彼此自我創新與重新發明提供靈感。例如,語用既然一向只專注于有效信息交流,不妨借鑒修辭理論資源,更合理地解釋如何影響或指導他人的行動等。然人文學科普遍對方法的研究重視不足,不少修辭學者擔憂傳統修辭理論過于單薄,無法勝任對文本的闡釋性分析。鑒于語用學善于對形式與結構開展細致研究,并對范疇、規則等明確公開界定,對修辭學者而言,語用學很可能是一個不無啟發的例子。作為兩個獨立且密切相關的學科,二者應致力于構建以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為特征的關系。
《對應》的討論有三重意義。其一,對當代語用研究普遍認定的觀念基礎進行反思,指出這一基礎的構成成分中,除耳熟能詳的語言哲學原則外,還包含從修辭傳統中汲取的關鍵理論資源。語用學家“只用不說”的修辭觀念,對于語用研究居功甚偉,對促進語用研究覆蓋現實生活的各種話語現象,亦即使這一研究范圍超越“形式化及儀式化或典禮化的[日常語言應用]情景”,延及對除傳遞信息之外言說效用的解釋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二,文章以語用學為參照,通過提出“不合作原則”,凸顯并批評了當代修辭研究中存在的普遍傾向,即耽于現象層面而不注重對原理原則的挖掘、歸納及抽象,滿足于對古典修辭觀念的應用而不注重對修辭理論話語的更新提升。“不合作原則”的歸納,為克服這一傾向指明方向。其三,文章以語言應用研究這兩大學科的關系為例,說明鄰近學科既不能各自為戰,更不能相互“吞并”,而應互為參照、相互促動、互啟靈感、相輔相成。“對應學科”觀念提倡的是一個古為今用、對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學科間關系發揚光大的新規范。
三、思考與探索
滕慧群認為,“雖然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語用學和修辭學有各自的研究側重點,但鑒于兩者都以語言運用為研究的中心問題,而且兩者尤其是語用學的研究對象仍然處于不斷變化中,目前在語用學和修辭學之間劃分出明確的界限既不可能也無必要”[20]。筆者認為,《對應》一文正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并以交流初始聽話人是否與說話人合作作為區分標準,確定語用與修辭的分野。《對應》從語用學獲得靈感,不僅對當代修辭學的觀念基礎做出理論歸納,同時促使語用學對自身觀念基礎進行理論反思,以與修辭學開展更多學術對話。該文引發以下三點思考。
(一)“貌合神離”的合作
姜望琪認為,“合作”是指說話人和聽話人為實現同一目標而共同努力[21]。無獨有偶,陳志尚也將“合作”定義為“人們交往的一種基本形式,是指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某一共同目的,彼此以一定方式配合、協作的聯合行動”[22]。上述兩個定義的共識在于:合作者之間彼此有共同需要和利益,合作必須具有一致的目標。對照語用有關CP的論述可見,語用中預設交流雙方是一種不存在利益沖突的和諧關系,交流雙方享有共同利益(shared interest),齊心協力促成交際。修辭則不然,由于說服為其基本目標,遭遇抵抗④抵抗是指修辭者與受眾關系的內在張力。這種修辭的基本關系是說話人和聽話人在開始進行會話時的觀點差異,即說話人試圖勸說聽話人做出原本不會考慮的某種選擇,說出某些話或采取某些行動。在修辭的框架內,二者分別被分配了提議者和裁判的角色。根據制度性(institutional)安排,作為提議者的說話人與作為裁判的聽話人彼此針鋒相對:當說話人試圖用與聽話人有爭議的觀點說服對方,而對方又被賦予裁判權時,說話人的說服企圖必然遭到抵抗。這一觀點參考自Rhetoric as the Antistrophos of pragmatics:Toward a“Competition of Co?operation”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一文有關“不合作原則作為基本修辭原則”(NCP as a general rhetorical principle)部分。(resistance)亦即不合作態度,并在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存在一種關系張力是其必然特征,因而它往往預設交流雙方興趣分歧或利益沖突。根據顧曰國的研究,Sampson曾質疑Grice會話合作觀,認為這是對社會生活本質的錯誤表述(Sampson even concludes that Gricean View of conversational cooperation“implies a profoundly false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social life”.)。比照具體的社會生活,有理由相信交流雙方存在不同的興趣和利害(interests)更可能是現實寫照。徐盛桓在語用研究中提出:“人是利益的主體,自我滿足是人的第一尺度,交際雙方的利益和自我滿足的尺度都不會是對稱的。”[23]顧還提到,國外持這種“目標分歧說”的有Pratt與Kasher。Pratt認為:“只有一些情況下會話參與者享有共同目標。顯然,會話參與者目標與利益上的分歧至少是十分常見的。”(Only some speech situ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sharedobjectives among participants.Clearly it is at least as common for speakers to have divergent goals and interests in a situation.)[24]Kasher認為:“既然對話參與者在交談中享有共同目標并非常態,CP的有效性就很成問題,該原則預設“合作”而非“協調”,預設“目標一致”而非“目標分歧”,靈活性不足,因而與實際情況出入很大。”(Since it is not normal that conversationalists share some common purpose in talk exchange,the CP validity becomes questionable, the principle is too strong since it rests on an assumption of cooperation and shared purposes rather than on the weaker assumption of coordination and independent purposes.)[24]結合陳志尚[22]對“妥協”的界定⑤妥協是指合作者在特定條件下,為了各自利益在某些方面做出讓步,放棄對立,謀求暫時聯合、一致的交往形式。可見,修辭交流之初的合作實質是一種“妥協”。對此,劉亞猛在《追求象征的力量》一書中指出:“修辭者就盡可能多的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問題與對方‘求同’,為的是換取對方在某一有分歧的關鍵問題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異’,或者說爭取對方在那個有爭議的問題上認同自己所持的觀點。”[25]由是觀之,修辭交流中“合作”應一分為二,交流之初的“合作”是一種讓步與妥協,是為了達到社會行動的協調一致(coordination of social actions)這一終極意義上的合作而采取的以退為進策略,最終目的是消弭交流者間分歧,從而盡快形成共識,迅速協調行動。正如《對應》指出,語用的合作是一種預設要求,而修辭的合作則需要構建、強化并維持其運作,是“使然的”,而非“自然的”。簡言之,“合作”是語用的出發點,而實現“合作”卻是修辭的歸宿。既然兩個學科對“合作”的理解各異,認為修辭與語用原則相同顯然是一種過度概括,基于合作原則在語用與修辭兩個學科中的重大差別——“合”而不同,可以說,修辭和語用是被“合作”聯系起來同時又被其分隔的兩個學科。
(二)抵抗(不合作)作為語用與修辭的分界線
如前所述,學者未能明確提出語用與修辭的差異究竟何在,反而更加關注學科地緣政治,經常把對方當作征用對象,甚至執意“收編”對方,將其納入本學科版圖。宗守云提到,迷戀自己的專業是一個學者最基本的品質,但切不可因此失去理智[17]。因此,有必要正視兩門學科的內在差異,對其進行適度區分。《對應》提出,作為修辭學觀念基礎的NCP,預設了交流初始時說話人的說服目標與聽話人自有目標的分歧,聽話人有抵觸情緒是修辭性話語的題中應有之義。據此,不妨認為抵抗(不合作)是語用與修辭的分水嶺。從這個意義上看,并非所有語言使用皆可納入語用研究范圍⑥宗世海認為,“語用學”這一術語的字面意義易被誤解為研究所有語言運用的規律。他還指出,要防止把語用學流俗化的種種傾向,不應在不解學科內涵的情況下隨意亂用“語用”這個術語。隨意擴大語用學的涵義對科學的語用學建設毫無益處。,同時不能把所有語言使用都劃入修辭研究版圖。將語用視為語言使用的所有方面是一種顧名“失”義的錯誤,而將修辭等同于修飾言辭之類同樣不足為訓。從不同角度切入語言使用研究的語用與修辭,彼此既有共性,又可區分。這樣既可避免使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而事倍功半,也可提防復雜問題簡單化,低估問題難度。換言之,并非所有語言使用問題都要做修辭分析,只有在交流一方遭遇另外一方的抵抗(不合作)時,方將其視為修辭機制開始運行的標志。
(三)《對應》一文存在的缺憾
《對應》一文討論的話題面較廣,以至于重要話題未能深入探討,文章深度難免受到廣度影響。例如,《對應》第27號腳注從修辭視角重新審視關聯理論兩大觀念(“關聯的交際原則”及“關聯的認知原則”),事實上動搖了這一重要理論的根基,理應有卻未能提供進一步闡釋和論證。可能出于同樣原因,《對應》的討論停留在抽象層面,未能提供基于日常語用現象的充足例證,降低了可讀性。
四、結語
陳光磊認為,語用學和修辭學各有其學科價值[26]。語言的使用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應變創造過程,從不同角度探討和研究語言使用問題不可避免也十分必要。這種研究既互相有別,又互相聯系。《對應》一文以“不合作原則”對當代修辭學的觀念基礎第一次做出系統的理論歸納,以交流初始聽話人是否與說話人合作作為區分標準,確定語用與修辭的分野。本文進一步對其核心觀點,即修辭話語預設了聽話人的不合作(抵抗)以及由此產生的某種關系張力,進行了思考和探索,提出語言使用中抵抗(不合作)與修辭同延。
正如《對應》所言,語用和修辭是“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關系。這兩門學科遵循既有原則與方法,運用各自理論工具將會打開不同的學術視野。這樣的關系定位既能豐富對語言運用的認識,也會深化對語言復雜性的理解。
[1]戚雨村.修辭學與語用學[C]//復旦大學語言硏究室.《修辭學發凡》與中國修辭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
[2]陳晨.語用學和修辭[J].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2).
[3]溫鎖林.語用平面跟修辭學的區別[J].語文研究,2000(3).
[4]胡范鑄.從“修辭技巧”到“言語行為”——試論中國修辭學研究的語用學轉向[J].修辭學習,2003(1).
[5]叢萊庭,徐魯亞.西方修辭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7.
[6]曾文雄.語用學的多維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7]宗廷虎,吳禮權.20世紀中國修辭學(上、下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8]張會森.修辭學與語用學[J].修辭學習,2000(4).
[9]黎運漢.漢語語用修辭學建立的背景[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 2002(2).
[10]何自然.語用學對修辭研究的啟示[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6).
[11]戴仲平.語用學與中國現代修辭學的比較及其合作前景[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12]夏中華.關于修辭學和語用學學科滲透與借鑒問題的思考[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7(1).
[13]袁毓林.從語用學和修辭學的關系論修辭學的理論目標、對象范圍和研究角度[J].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87(3).
[14]高萬云.語用分析與修辭分析[J].韓山師范學院學報,1997(1).
[15]宗世海,劉文輝.論修辭學與語用學的關系及二者的發展方向[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
[16]施發筆.語用平面和修辭學的界限新論[J].南京社會科學,2002(6).
[17]宗守云.修辭學的多視角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18]王建華.語用研究的探索與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9]Yameng Liu,Chunshen Zhu.Rhetoric as the Antistrophos of pragmatics:Toward a“Competition of Cooperation”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1(43).
[20]滕慧群.語法修辭關系新論[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6.
[21]姜望琪.當代語用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2]陳志尚.人學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3]吳炳章,徐盛恒.認知語用學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24]Yueguo Gu.Pragmatics and Rhetoric: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Conversation[C]//In Parret,H.,ed.Pretending to Communication.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3.
[25]劉亞猛.追求象征的力量——關于西方修辭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26]陳光磊.修辭論稿[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
H030
A
1672-3805(2014)04-0055-07
2014-04-30
福建省教育廳B類科技、社科研究項目“語用與修辭學科關系研究”(JB12206S)
張雅卿(1977-),男,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閩江學院外語系講師,研究方向為西方修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