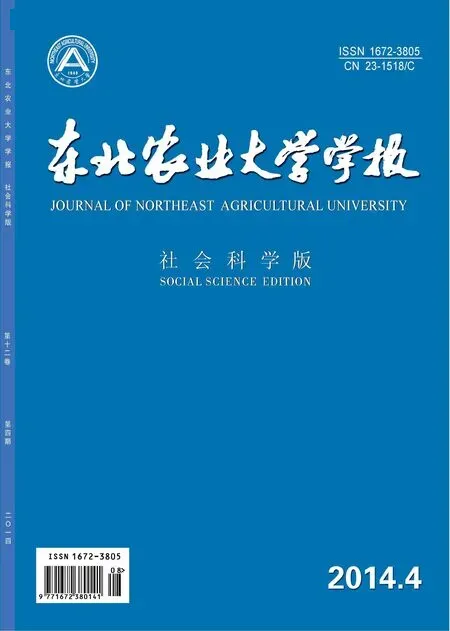《麗姬婭》中“復生”戲碼的“創傷理論”解讀
沈謝天
(上海海洋大學,上海 201306)
《麗姬婭》中“復生”戲碼的“創傷理論”解讀
沈謝天
(上海海洋大學,上海 201306)
以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創傷理論”為立足點,探討著名短篇小說《麗姬婭》中創傷的起因、診斷和治療過程。在回顧“創傷理論”歷史基礎上,通過對兩位女主人公死生交替進行剖析,說明小說文本“先診斷后治療”分段式創傷處理方式。強調“身體”應對創傷的突出作用,其與語言文字的協作使文學具有一定治愈力。
埃德加·愛倫·坡;《麗姬婭》;心理分析;創傷
一、引言
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引領19世紀美國文壇風潮的重要作家之一,主要從事詩歌和短篇小說創作。他命運多舛,一生神秘、離奇,特立獨行的做派令其成為多數人心中難解之謎。苦難的經歷和沉郁的個性,使偵探小說和恐怖小說成為其重點創作領域,并被譽為這兩類小說在美國的開山祖師。《麗姬婭》(Ligeia,1838)是坡式恐怖短篇小說的典范作品之一。作品采用第一人稱敘事。“我”的妻子麗姬婭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與“我”愛意濃濃,幸福美滿。死亡的突然降臨讓“我”與麗姬婭天人永隔。改換住地的“我”續娶羅維娜為妻,雖再難體會對麗姬婭的愛,卻也勉強活了下來。不久,羅維娜也罹患重病。“我”守在彌留中的羅維娜身旁照顧,光影綽綽的恐怖氛圍中,羅維娜死后又站起,原來她的肉身已被麗姬婭占據,“我”的愛妻“復活”了。
小說中的“復生”戲碼歷來是為讀者樂道的經典片段,也是國內學者的研究焦點。研究者從坡的美學思想、拉康心理學和性別敘事等角度對“復生”情節進行動機分析。何木英和朱振武分別指出“復生”是坡強調精神勝利的結果,喻指他用精神美克制死亡的努力[1-2]。李顯文從何、朱二人的論說中提煉出“精神美學”概念,以總括坡一生對永恒精神美的追索,闡明“復生”大戲幕后的美學動因[3]。心理動因方面,代表成果是杜予景《愛情與死亡背后的欲望書寫》一文,其在拉康心理分析理論觀照下,為羅維娜和麗姬婭各自在“復生”戲碼中的角色進行心理學意義的界說。羅維娜是“在場的能指”,是意識;麗姬婭是“缺席的所指”,是無意識。“復生”成為“能指”向“所指”的無止境滑動,反映敘事者永遠得不到滿足的無意識欲望[4]。這一闡釋實踐了拉康結構主義心理學的理論真諦,是無意識的語言結構在文本解說中的具體使用。除美學和心理動因外,周晶等在分析《麗姬婭》中單一男性敘事之后認為,男性話語權力的運作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復生”是在單一男性視角下進行的“有限全知敘述”,目的在于為男性實現以自我為中心的某種需求,周晶等將這種需求定性為男性通過對美女生死的窺視提升自我對悲傷之美的體驗[5]。此觀點與上文提及的美學動因暗合,二者皆以坡的美學訴求為立足點。
“復生”的意義在三種研究目光審視下呈現出較為清晰的圖景,但遠未達完美之境。如當代美國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所言,“偉大的文學作品會讓人感到陌生的熟悉”,這“熟悉”中的“陌生”意指新時代、新語境下的理論話語創新。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創傷理論”,作為極具生命力的新話語,能為“復生”大戲提供一種新的解讀范式。在肯定“復生”中飽含男性訴求的前提下,“創傷理論”可全面揭示這一訴求的結構和本質。作為心理分析學派的重要理論貢獻,創傷研究可將“復生”過程一分為二,分別揭示“死”“生”在創傷診斷和治療方面的具體意義以及女性“身體”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總的來說,坡將極度創傷化(traumatized)的內心世界投射于“復生”戲碼,而要透過文本看到坡已有多道裂縫的心靈實況并認識到他借助《麗姬婭》實施的創傷診療,必須從了解創傷相關理論的發展史開始。
二、“創傷研究”演進史
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創傷性神經官能癥”(traumatic neurosis)與“普通歇斯底里癥”(common hysteria)同源于“心理創傷”及有關回憶,并在與約瑟夫·布魯爾(Joseph Breuer)合作撰寫的論文《歇斯底里癥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1895)中首次提出“創傷性歇斯底里癥”(traumatic hysteria)的概念。一年后,在《歇斯底里癥的病原》(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一文中,弗洛伊德又提出“引誘說”(seduction theory),說明“創傷”的心理學構成。“引誘說”指出,每個歇斯底里癥病例背后,都隱藏了一起或多起患者在未成年時期的性經歷;這些經歷都發生在患者童年早期,且可在時隔多年之后,通過心理分析師的干預得以重現(reproduce)[6]。弗洛伊德提出“引誘說”的同時,在1887至1897年間寫給同事兼好友威爾海姆·弗雷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推出另一術語——“延遲性”①這一術語德文表述為Nachtr?glichkeit。通常被譯作英文單詞“belatedness”或詞組“deferred action”。。“我們毫無例外地發現,回憶總是被壓制的;它只有通過某種‘延遲行動’(deferred action)才會成為創傷。”[7]換言之,對一段經歷的記憶可以產生某種效應,但這種效應不會在事發時出現;當事人在一段時間之后,才對事件的效應獲得“事后認識”(a posteriori understanding)。這就說明,對一次經歷的記憶只有在當事人內心再度被激發(revivified)時,才能成為創傷。“延遲性”和“引誘說”中提到的“創傷”與“回憶”的復雜關系,使對“創傷”的“表征”(representation)成為首要問題,因為“表征”是開展一切“創傷”研究和診療的第一步。文學參與“創傷研究”的必然性,即在于其“表征”方面的優勢。
過去的20多年,極端事件頻發,由此引發的“創傷”結構和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對“創傷研究”的興趣也因此與日俱增。對“創傷研究”核心議題——“表征”的探索過程中,文學界推出一批創傷敘事作品(trauma narrative);相應地,作為新興批評理論,“創傷理論”也在20世紀90年代于美國應運而生。該批評學派代表人物凱西·卡魯思(Cathy Caruth)、肖莎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都曾是耶魯大學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理論家保羅·德·曼的弟子或同事。這從側面反映出“創傷理論”與后結構主義批評之間的內在關聯。在整合后結構主義與拉康學說的基礎上,“創傷理論”試圖探究一種新的“真實”(the real)——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及其在社會、歷史、政治、文化以及倫理領域內的意義和功能。
對“創傷真實”(traumatic real)的探究依然從“表征”開始。首先,法國心理學家拉康的學說給予研究者實現“創傷表征”(traumatic representation)的理論信心。“心理分析的經驗在無意識層面發現了完全的語言結構。”[8]進而將語言結構引入人類心靈構造之中,并指出:“正是這種語言結構讓我們確信,在‘無意識’這個術語之下,存在有一些可定性、可觸及以及可客體化的東西。”[9]無意識的語言結構僅為順利實現對“創傷”的表征提供了理論依據,“創傷表征”的具體操作路徑有待理論家們探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傷理論家”們皆強調,創傷問題的核心在于創傷經歷者(或者說幸存者)無法從創傷經驗內部對創傷進行檢視(witness)。這一問題意識與弗洛伊德提到的“延遲性”概念同出一脈。卡魯思同時指出:“瞬間回憶(flashback)的復現是一種中斷——一種具備干擾作用或影響的東西——這說明,人們不能簡單地將之視為一種表征。”[10]換言之,對“創傷”的表征超出了普通語言的直接指涉功能,而必須訴諸于“間接指涉”,但這“并不是否認或者取消指涉的可能性,而只是強調其發揮遲到影響力(belated impact)的必然性”[10]。在“創傷”里,指涉性(referentiality)是間接的和遲來的。
“創傷”的“間接指涉性”(indirect referentiality)要求間接的語言表征,即對語言進行藝術化處理,而這正是文學象征性語言的專長。因此,文學成為對一度無人問津的“創傷時刻”(moment of trauma)進行事后重演和檢視的場域。為說明“創傷”只有通過文學性或象征性語言才能為人識解,卡魯思使用一種創傷意象,它“喊叫出來,對我們說話,試圖告訴我們一個通過別的手段無法獲知的事實或者真相”[10]。進一步說,“由于創傷讓內省式檢視成為不可能,對創傷經驗的事后比喻性和文學性表征取代了(displace)指涉意義上的真實(referential truth)”[11]。埃德加·愛倫·坡在《麗姬婭》中對“創傷”的高度藝術化表征,在“創傷理論”成型一個半世紀前即充分證明了文學進入“創傷研究”之內在必然性。
三、《麗姬婭》中“創傷”的“源起”
生活的“創傷化”(traumatizing)本質是文學表征的必要前提和對象。創作《麗姬婭》前,坡已積累豐富而曲折的戀愛經驗。對其情史的回溯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麗姬婭》中創傷的由來,從而為理解坡使用文本診斷和治療創傷的努力奠定基礎。
“理想化”(idealization)是坡女性觀的關鍵詞,同時也是他本源性的“創傷體驗”之一。1824年,年方十五的坡愛上好友的母親斯塔那德(Stanard)太太[12]。這個愛詩、懂詩,長相酷似生母的女人,讓坡對女性的“理想化”推向極致,對麗姬婭內外之美的夢幻描摹正是此類女性觀的寫照。坡與斯塔那德太太相識的同年四月,剛過三十的她便溘然辭世[12]。少年坡未及談情說愛,便收獲人生第一次“創傷體驗”。事先毫無準備的他,因對女性“理想化”而被首次“創傷化”。
富家小姐莎拉·埃爾米拉·羅伊斯特(Sarah Elmira Royster)是坡生命中的真正初戀。二人在坡就讀大學之前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入學后不久,即因坡養父從中作梗而告吹[12]。剛走出初戀陰霾不久的坡,又因愛上年僅13歲的表妹弗吉尼亞·克萊姆(Virginia Clemm)再陷創傷漩渦。為挽留因求學而要離開的表妹,坡寫信給克萊姆姨媽,聲言自己將因悲痛而死,終于留住表妹,二人喜結連理[13]。這場“虛驚”的破壞力不遜于當年他與埃爾米拉愛情的“突然死亡”。
斯塔那德太太、埃爾米拉和弗吉尼亞是坡氏理想化愛情和女性的典型代表,三人皆以自己的方式,離開了或離開過坡。其中的“突然性”讓無準備狀態下的坡傷痕累累。直到1838年,坡利用短篇文本《麗姬婭》,對自身“創傷”進行了層次分明的“診治”。
四、“創傷”的“診斷”
“為什么要在這里糾纏,一再敘述那叫人毛骨悚然的死人復活的場面,一直講到灰色的黎明到來呢?”②文中的小說文本實例均引自埃德加·愛倫·坡:《愛倫·坡短篇小說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麗姬婭》中的敘事者——“我”有此一問。“在它最為寬泛的定義中,創傷描繪的是對一些突發或者災難性事件的深刻體驗;在這一體驗中,對事件的反應會是一種延遲的(delayed)、難以控制(uncontrolled)且重復發生的(repetitive)幻覺,以及其他的突發現象。”[10]“創傷”深埋于受害者內心,不同于外部環境突變對肉體造成的物理性傷害,它不可見,難量化,更沒有徹底被抹去的可能。只要記憶功能健全,人就會天然地對“創傷”進行回溯。對此,弗洛伊德和布魯爾一同指出:“心理創傷——或者更準確地說,對創傷的記憶——像一個異質體(a foreign body)一樣發揮作用,它在出現許久之后,應該繼續被當作一個仍然在發揮作用的實體(agent)。”[14]不論能否治愈“創傷”,人都會無意識地采取“重現”(repetition)和“追憶”(reminiscence)方式去認識“創傷”,且這樣的認識只能是一種“重識”,因為它不會在“創傷”產生當時完成。換言之,一旦貯存,“創傷經驗”一定會在此后某個時刻在個體心中被喚醒、被重演,因為這時,必有一起與“創傷經驗”類似的事件正起到提示物(reminder)的作用。在《麗姬婭》中,坡利用“我”的自述,展開一次符合“創傷”癥狀特點的、遲到但必然會發生的“重現”努力,其中,起提示作用的是“我”第二任妻子——羅維娜女士的死亡過程。
在此過程中,羅維娜女士的“身體”是“死亡復現”的核心元素。坡對“身體”的嫻熟使用極具藝術前瞻性,因為在當代“創傷理論”中有不少支撐此手法的理論觀點。凱思林·羅伯森(Kathryn Robson)和勞拉·迪·普雷特(Laura Di Prete)在各自著作中皆提到了“身體”。作為一個意象,“身體”應在表征創傷的文學媒介中扮演核心作用。羅伯森在批評凱西·卡魯思忽視創傷中“身體—心理”關系同時,還探討了在文學實踐和理論上都關涉心理創傷的身體意象③詳細觀點可參考:Robson,Kathryn:Writing Wounds:The Inscription of Trauma in post-1968 French Women’s Life-Writing[M].Amsterdam, NY:Rodopi,2004;Prete,Laura Di:“Foreign Bodies”:Trauma,Corporeality,and Textual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M].London:Routledge, 2006。。兩位學者的觀點可在拉康“三范疇”理論中找到佐證。“三范疇”分別指真實(the real)、象征(the symbolic)和想象(the imaginary)。“‘象征’范疇是指一組叫作‘能指’的相互之間有區別,且離散分布的元素。而‘真實’,以整體存在,不含區別;‘真實’處于語言之外,且不能被象征體系(symbolization)吸收。”[15]據此,作為人類最大符號或能指系統的語言,應屬于“象征”范疇,或者說“象征”從本質上是在語言維度(linguistic dimension)里運作。“真實”處于象征體系外圍,但主體只能通過“象征”試圖理解和看待“真實”。“雅克·拉康對經典心理分析理論的修改將‘創傷’置于‘真實’范疇。這一點在其著作《心理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第十一卷中被明確指出。”[16]戴倫·埃文斯(Dylan Evans)也總結說,“創傷”分享“真實”的一大特點就是“對象征的抵抗”,因為“它不可能被想象出來,也不可能融入象征體系”[15]。“創傷體驗”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使之成為“真實”范疇內的固定成員。“創傷體驗處于象征性交流的各項參數外圍;它是‘真實’的一種難以言表的突然闖入(irruption)。”[16]面對“突然闖入”的“真實”,作為象征體系的言語表述沒有做好充分、完全的準備,“創傷”和“語言”之間出現斷層。為“語言”加入文學性或者象征性,就是針對這一斷層的彌合劑。在《麗姬婭》中,坡讓“身體”加入,“語言”因此獲得文學性,他也得到了對“創傷”進行“近身處理”的機會。
羅維娜被安排演出的“戲份”即在故事尾聲,通過演繹“死亡”過程,重現最真實的“創傷體驗”,也為麗姬婭的“復生”做足準備。“我”首先對羅維娜軀體的消逝過程進行近距離逼視,眼睜睜地看著她在另一個世界的大門前徘徊。“眼皮和面頰上的顏色消失了,留下的顏色比大理石還蒼白。雙唇后縮,撅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死亡表情。”不久之后,已成為“尸體”的羅維娜,又有了一絲“活氣”,但經過“我”“盡責”搶救之后,“突然,那顏色又消失了,脈搏也停止了,嘴唇恢復了死人的表情”。直視著生命消逝前的生動反復,“我對麗姬婭的一千種回憶紛紛出現。夜漸深了,我凝望著羅維娜的尸體,心里滿是對我的最愛之痛苦懷念。”死神抓住了線繩,讓羅維娜這個“大玩偶”在“我”面前演出了愛人離世這一“我”早就經歷卻未曾用心靈去認識和處理的“創傷”全過程。“回憶紛紛出現”和“痛苦懷念”等字眼,已充分證明“我”的“身體”終于實現與“內心”的協調,以往沒有面對也不敢面對的“創傷”得以全方位展現在“身、心”面前。“死亡演繹”達成了單純語言表述沒有實現的效果。因此,“身體藝術是敘說‘創傷’的優勢媒介(privileged medium),這不僅是因為它讓‘內心’能接觸到原先只有‘身體’才知道的事實,還因為它強調了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交互。”[17]的確,在演繹“死亡”的過程中,羅維娜并不孤單,這位表演者身旁一直有“我”這位觀眾目擊整個演出過程。羅維娜和“我”構成了“‘創傷’的主體間維度”(intersubjective dimension of trauma)[10]。“我”對演員表演的反應就是“我”所能掌握到的最真實“創傷體驗”。總之,“演員和觀者之間的對話,既能總括心理分析意義上的‘遭遇’(encounter),也能重現‘創傷目擊’(traumatic witnessing)的時刻”[16]。
羅維娜的“死亡過程”實為“我”真正鐘情的先妻麗姬婭的“死亡復現”。坡利用文學語言獨特的表征優勢,為“我”,實則為自己,重現了“愛人死亡”的創傷母題,從而進入治療創傷的第一階段——診斷。從臨床上說,“診斷”階段中,“治療師幫助患者對創傷進行追憶和哀悼。有了安全感,有了信心和一定的自主能力,患者可以細致、深刻地講述創傷事件”[18]。簡言之,“診斷”是一次勇敢的回眸。愛倫·坡是“患者”,同時也是“治療師”。“我”自述的“死亡復現”讓坡接受“我有創傷,我是患者”的事實。這是他進入下一治療階段的前提和準備。
五、“創傷”的“治愈”
“創傷”的“治愈”絕不等于“抹除”。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專家朱迪思·劉易斯·赫爾曼(Judith Lewis Herman)指明創傷治療的真諦:“重述創傷的目標是整合(integration),而非祛除(exorcism)。”[19]創傷具有“永在性”,但人們可以端正對創傷的認識和態度,“整合創傷記憶,把創傷經歷變成人生閱歷,變成對人生價值體驗的素材而更好地管理人生”[18]。小說中,坡安排麗姬婭假借羅維娜的肉體獲得“重生”,就是他整合個體經驗,重建個人與他者及世界關系的別致嘗試,從而也是完成自我救贖、治愈創傷的方式。
“重生”即文學用來對抗“死亡”——坡愛情創傷的最大元兇,也是讓人最感無奈的現實——的有力武器。“在社會和歷史領域里的‘宣言’(testimony),和科學領域內的‘客觀性’與‘分析精確性’一樣,可以說是通過不斷進行精神上的抗爭(mental fight),來修繕(modify)‘死亡沖動’(death drive)。”[20]麗姬婭的“重生”,就是這一則“宣言”中的華麗一章。這一章節的書寫者——坡“通過清晰逼視(witnessing)全面的‘死亡表征’(death-manifestations),但卻并不向之屈服的方式,將對死亡的抗爭推向了否定現實(reality-denial)的境地”[20]。《麗姬婭》的故事尚未開始之前,坡就借他人之口,指明人們否定死亡現實的武器——意志(will)。文中提到約瑟夫·格蘭威爾④約瑟夫·格蘭威爾(Joseph Glanvill,1636—1680),英國作家、哲學家、牧師。“所言”,“其中就存在著意志,而意志是不死的。意志和它的生命力的奧秘誰又懂得?因為上帝不過是一種偉大的意志,他那堅定的天性滲透了萬物。人是不會向魔鬼屈服的,也完全不會向死亡屈服,除非由于他性格軟弱”。然而,格蘭威爾未曾說過這樣的話。坡此處的精心杜撰無疑是為麗姬婭注入足夠的精神驅動力,給她的“重生”鋪設理據。這一理據無奈而悲壯。面對“死亡”,包括坡在內的人文和科學精英都在尋求其背后真義,探求破解之道,但到頭來,“精神”對“現實”的否定似乎才是“縫合”這一最原始“創傷”的唯一手段。在《麗姬婭》中,“我”的兩任妻子麗姬婭和羅維娜聯袂上演的“死亡與重生”大戲,為坡伸張了人類“意志”;在思想領域,他實現了自己對“死亡”的掙脫。從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意義上說,坡通過小說中新奇的“死”“生”更迭,“凈化”(purge)了自身的“悲傷”(grief)和“恐懼”(fear),為“傷口”的“縫合”創造了必備條件。
“我很想安慰她,勸說她,但她是那么瘋狂地渴望著生命,一個勁地渴望著生命,安慰和勸說都同樣是最愚蠢的……對如此迅速逝去的生命懷著那么瘋狂迫切的渴望……一種瘋狂的欲望,強烈的生命之欲——只不過是對生命的渴望——那是我沒有力量刻畫也無法表達的。”對生命的渴望,對死亡的不屈服讓女主人公憑借“意志”從死神手中奪回失去多時的“肉身”,也讓愛倫·坡被“愛的創傷”肢解的人格重獲整一性。雖說以文學戰勝“死亡”不免虛妄,但坡借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憂懼,重回正常生活狀態,為他日后在與弗吉尼亞表妹的婚姻里重獲愛情甜蜜掃清障礙。從此意義上說,在《麗姬婭》結尾處,坡治愈了自己。
六、結語
“復生”是愛倫·坡為自己最得意的短篇小說精心設計的核心戲份。在這一設計背后悄然運作的復雜心理機制,因受到“創傷理論”的觀照而躍登前臺,這反過來也說明作為心理分析學說重要分支的“創傷理論”在釋讀文學文本方面的潛力,凸顯文學獨有的象征性語言表述在創傷診斷與治療方面的先天優勢。在《麗姬婭》中,坡將象征性的語言使用落實在引入“身體”,并令之巧妙“演繹”上。“身體演繹”讓坡層次鮮明地完成了應對“創傷”的努力:羅維娜身體的消逝過程讓坡直面“愛人早逝”的“創傷經驗”,診明了癥結;麗姬婭身體的“借殼回歸”則讓坡掌握對抗死神的利器,對自己受傷的心靈進行撫慰,完成了治愈。本文最大的隱憂在于將坡的生平事實引入對其創傷源頭的討論。這樣的研究路徑難免會將“現象性成因”(phenomenal cause or see-able)和“創傷”(not seeable)進行關聯(correspondence)。換言之,任何試圖將作者個人經歷與其“創傷”等同起來的努力都必須慎之又慎。這是因為“創傷”隱蹤于人的心靈暗箱之內,且人從出生到死亡,從來不會停止對“創傷化”(traumatizing)經歷的認識和處理。總之,“可見”對“不可見”的“祛魅”(demystify)過程本身也需得到“祛魅”。如此形成的“循環”,乃由“創傷”的根本性質使然,為使其不因發生“惡性”轉向而影響“創傷理論”的未來發展,后續研究務必對此問題詳考、深究。此外,坡的“創傷”創作實踐說明,戰爭、種族屠殺、恐怖襲擊等重大事件縱然是“創傷”的主要源頭,而本身具備“創傷化”(traumatizing)特性的普通生活才是“創傷”形成的根本。因此,以普通生活為生長土壤的文學必然與“創傷”同處持久的互動關系之中。“創傷”浸染文學——文學診斷和治愈“創傷”,這一持續往復的過程,為“創傷理論”提供了逐步擴大的闡釋空間。
[1]何木英.埃德加·愛倫·坡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朱振武.愛倫·坡小說全解[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3]李顯文.絕世美女麗姬婭的死亡與復活:評愛倫·坡的“精神美學”[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3(6).
[4]杜予景.愛情與死亡背后的欲望書寫[J].譯林,2011(3).
[5]周晶,李莉,肖瀟.性別與敘事:論《麗姬婭》中的男權話語[J].學理論,2010(32).
[6]Freud,Sigmund.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C]//Trans.James Strachey,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The Assault on Truth: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4.
[7]Freud,Sigmund.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C]//Trans. James Strachey.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Press,1981.
[8]Jacques Lacan.écrits: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M]. 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7.
[9]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
[10]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1996.
[11]Shoshana Felman,Dori Laub.Testimony: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M].New York:Routledge, 1992.
[12]Winwar,Francis.The Haunted Palace:A Life of Edgar Allen Poe [M].New York:Harper,1959.
[13]朱利安·西蒙斯.文壇怪杰:愛倫·坡傳:1811—1851[M].文剛,吳樾,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
[14]Freud,Sigmund,Joseph Breuer.Studies on Hysteria[C]//Trans. James Strachey.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Vintage,2001.
[15]Dylan Evans.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M].New York:Routledge,1996.
[16]Griffin,Brett Thomas.Can the Wound Be Taken at Its Word? Performed Trauma in Don DeLillo’s“The Body Artist”and“Falling Man”[D].Georgia:Georgia State University,2008.
[17]Prete,Laura Di.Don DeLillo’s“The Body Artist”:Performing the Body,Narrating Trauma[J].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05(3).
[18]李桂榮.創傷敘事——安東尼·伯吉斯創傷文學作品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19]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London:Perseus Books Group,1997.
[20]Hartman G H.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J]. New Literary History,1995(3).
I106.4
A
1672-3805(2014)04-0062-06
2014-04-15
沈謝天(1980-),男,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