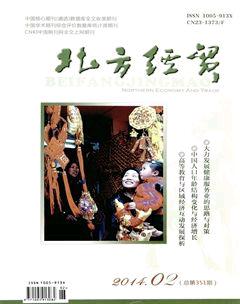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
劉月



摘要: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經歷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過程隨著中國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逐漸增加,勞動者所占比開始下降,勞動力市場的無限供給開始向有限供給方向發展,“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基于此背景,中國一直保持的高投資驅動高增長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戰。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債;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2-0015-02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現階段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現象,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帶來的問題主要是指人口負債,在醫療、財政支付和養老保險制度上。隨著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逐漸消失,社會老齡化的現象越來越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我們可以認為人口紅利是對往期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收入,那么人口老齡化就是人口變遷所呈現的經濟、社會負債。
一、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主要表現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長率和總負擔比、兒童撫養比以及老年撫養比兩個方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是在國家政策的實施下提前發生和進行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到90年代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始顯示,但是隨之2000年,全國65歲以上老人占全國人口總數達到了7%以上,也預示著中國人口老齡化也提前到來。
從下圖可以看出,中國人口出生率從1978年到1987年都處以一個上升時期,最高點在1987年達到23.33個百分點。但從該年以后出生率都處于一個下降趨勢,從最高點開始下降到2010年11.90個百分點;死亡率的變動情況一直處于一個變幅不大的水平區間,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死亡率開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種不變的速率,人口增長率的起伏與出生率正相關,在1987年是一個臨界點,該點之前,人口增長率表現出高增長水平,1987年以后,人口增長率開始下降。
從人口總負擔比、兒童撫養比和老人贍養比的情況來看,總撫養比與少兒撫養比正相關。自改革開放后,人口總負擔比與少兒撫養比開始下降,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1987年,在這一階段總負擔比和兒童負擔比迅速下降,可表現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兒童數量開始下降而勞動者開始增加;第二階段是1987年到1999年,總負擔比和兒童負擔比變化不大,處于平穩波動過程,可認為經過計劃生育政策后,出生率陡然下降,但是隨后出生率達到平穩下降水平,此時勞動力卻在之前兒童成長后開始增多,也達到勞動者數量略有增長的平穩過程;第三階段是2000年到現在,經過十多年人口變化后,十年前的勞動者開始走向老人階段,老齡化開始出現。因此,總負擔比中老人負擔比開始增加,兒童負擔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更加理性地對待“一個孩子“的問題,出生率下降。老人撫養比在三十多處于平穩增長階段,以2000年是一個臨界點,在2000年老人負擔比上漲到7.0%以上,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
中國經濟奇跡有很大因素是來源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國經濟增長中人口勞動力的貢獻超過了25%。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式微,對于勞動力的減少和老人撫養比的上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就是說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的發生改變,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不確定的影響。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15歲-59歲的勞動者在2008年出現下降,2012年出現負值,15歲-65歲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增長將會持續到2014年,達到9.97億人口。社會總供給勞動力數量開始遞減,勞動力出現短缺既能表現在總數量,也能表現在質量上面,中國對兒童成長教育的觀點是以讀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為榮,而對少年去參加技校,學一門技術的職業學校卻帶有鄙視心理,這種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國勞動者在藍領階層出現短缺,在大學生及以上學歷的水平上畢業生出現過剩的現象。
通過分析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動軌跡可以總結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總體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勞動人口在總人口比重逐漸上升,其中勞動人口中的就業人數也呈增長態勢;第二,相比勞動人口比重,少年和老人人數在總人數的比重呈現相反趨勢,兒童少年人數逐漸下降,老人人數比例逐漸增加;第三,與經濟增長速度相比,人口結構轉變速度要高與經濟增長速度,這種人口轉變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長速度,而是人口逐漸老齡化速度加快,與之相配套的經濟增長總體結構并不能與之相適應,會呈現養老福利基金缺口現象;第四,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特征和人口紅利的出現、消失以及老齡化的出現是在計劃性政策的干預和經濟發展共同驅動的結果;第五,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具有不均衡特征,表現在城鄉變動不均衡和地區變動不均衡。城鄉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不均衡是因為農村中存在無限勞動供給使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遷移,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不均衡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是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相東部地區遷移,隨著西部地區的大開發政策和中部地區的崛起政策,以及東部發達城市生存成本過高導致東部地區勞動者又開始向中西部地區流動。
二、人口負債分析
隨著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就是人口變遷所呈現的經濟、社會負債。老人的增加,勢必會增加財政支付和較少生產勞動力,降低社會總體收入,對于這一系列的影響,可認為是人口負債。
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人口負債上面。中國在2000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時期,但是中國經濟尚未達到應有的發達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還沒有得到質的提高,社會養老保險機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國現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贍養壓力增大,中國將會出現“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國由于在政策上對人口變動實行強制性的管理,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其他國家變動不一致,在中國經濟運行規律上也表現不一致,使中國在沒有達到富裕水平的時候人口就已經在開始老齡化,而這種“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會勞動力供給緊張的情況。
根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在2030年以前,中國0-14歲區間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15-64歲區間的人數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情況。勞動人口的絕對規模在2015年將會達到最高點。從而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信息,中國人口總體不僅出現老齡化,并且勞動力人口也在將來出現老齡化現象,這種現象對經濟增長將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也可以認為是提前到來的人口紅利對在未來進行經濟補償,也就是人口負債會在我國出現。
三、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分析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后其增長速度年平均達到了9.79%,這種高速增長狀況一直保持著持續性,被世界稱為“經濟奇跡”。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資為主要形式,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其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較高的資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但這與索洛模型所得出來的結論向左。索洛模型認為,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與人均產生水平成正相關,高的儲蓄投資轉化率可以促使人均產生的增加,但是這種穩定狀態不是穩定的,具有不可持續性。中國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因為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在勞動力市場供給方面有充足的勞動者。勞動者在各部門自由流動,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從農村向城市地區遷移,使得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
但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逐漸增加,勞動者所占比開始下降,勞動力市場的無限供給開始向有限供給方向發展,“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基于此背景,中國一直保持的高投資驅動高增長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戰。另外,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資擴散效應,他們對投資和儲蓄的需求會導致外資流入國內;但隨著人口偏向老年型轉移,這種投資擴散效應也開始消失,隨之對資本流入造成影響,甚至可能出現資本外流的情況。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勞動力無限供給規模,也體現在人口質量上。社會對教育的投入,使得勞動者中有一部分具有學歷成分,而且通過“邊干邊學”的模式增加了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沖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對經濟的負作用。但是,中國在20世紀末的大學擴招,是高等教育規模增長到了一個極限值,所帶來的結果是人力資本的增加速度也開始放緩。人口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達到一個極致水平。
通過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今后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所需要的因素將會發生改變:人口紅利的消失,無限的勞動供給轉向優先供給、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開始走向穩定數量,這些因素都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造成的負面影響。要是中國繼續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必須在人口年齡結構方面通過政策手段進行引導。建立完善的養老保險機制,發揮老齡人口的第二個人口紅利;防止人口過快老齡化。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使得其他對經濟增長的因素能夠順利運行,即使人口紅利消失,其他因素也可以相互配合,推動經濟繼續增長。對就業方面做充分的政策扶持,消除勞動者區域流動中所產生的制度障礙。
[責任編輯:王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