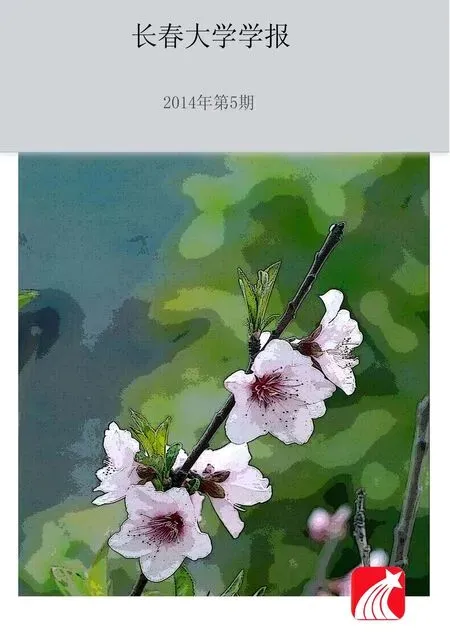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
黃德勝
(福建師范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福州 350007)
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
黃德勝
(福建師范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福州 350007)
金融危機(jī)以來(lái),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的呼聲越來(lái)越強(qiáng)烈,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大有一味被貶低、被妖魔化的趨勢(shì),但是目前我國(guó)仍是低技能勞動(dòng)力人口占據(jù)主體的發(fā)展中大國(guó),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仍大有可為之處。因此,必須從三次產(chǎn)業(yè)的協(xié)同發(fā)展來(lái)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的戰(zhàn)略實(shí)施中,必須在保增長(zhǎng)、穩(wěn)就業(yè)的基礎(chǔ)上持續(xù)、穩(wěn)定推進(jìn),必須重視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或環(huán)節(jié)與資金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或環(huán)節(jié)的融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穩(wěn)就業(yè);實(shí)體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
黨中央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必須從中國(guó)的最大實(shí)際出發(fā)。我國(guó)雖然已經(jīng)是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我國(guó)雖然已經(jīng)是世界工業(yè)大國(guó)、制造業(yè)大國(guó),但工業(yè)與制造業(yè)仍然只是“大而不強(qiáng)”。在我國(guó)勞動(dòng)年齡人口中還有超過(guò)一半以上是低技能的勞動(dòng)力。加快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升級(jí)當(dāng)然十分必要,但這是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guò)程,在當(dāng)前以及較長(zhǎng)遠(yuǎn)的未來(lái)時(shí)期內(nèi)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我國(guó)仍然具有發(fā)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而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必須在保增長(zhǎng)、穩(wěn)就業(yè)的基礎(chǔ)上穩(wěn)定、持續(xù)推進(jìn)。因此,必須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以更加科學(xué)、宏大的視野來(lái)認(rèn)識(shí)和引導(dǎo)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科學(xué)發(fā)展。
1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科學(xué)內(nèi)涵
首先,對(duì)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必須有一個(gè)科學(xué)、全面的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是與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相對(duì)的,是指在生產(chǎn)要素的配置比例中勞動(dòng)力投入比重較高的產(chǎn)業(yè)。其基本特點(diǎn)是物化勞動(dòng)消耗比重較低而活勞動(dòng)消耗比重較高,產(chǎn)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和資本有機(jī)構(gòu)成的提高,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將逐漸被資金、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所取代。這是對(duì)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經(jīng)典定義與傳統(tǒng)的認(rèn)識(shí),因而一提到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很多人就認(rèn)為是低端的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或低端制造業(yè);一提到產(chǎn)業(yè)升級(jí),就是通過(guò)減少、剔除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大力發(fā)展資本、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現(xiàn)在看來(lái),這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廣義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是指簡(jiǎn)單活勞動(dòng)占據(jù)主體的產(chǎn)業(yè)或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廣泛分布在三次產(chǎn)業(yè)之中。或者說(shuō),從最廣泛的意義來(lái)看,從整個(gè)國(guó)民經(jīng)濟(jì)來(lái)看,從社會(huì)勞動(dòng)分工與就業(yè)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是指“簡(jiǎn)單活勞動(dòng)”密集的生產(chǎn)領(lǐng)域、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
從工業(yè)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首先表現(xiàn)為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的擴(kuò)張,但是不能就此認(rèn)為,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僅僅是低端制造業(yè)。隨著工業(yè)化的演進(jìn),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內(nèi)涵、外延上也會(huì)發(fā)生轉(zhuǎn)型。當(dāng)前,我國(guó)工業(yè)化總體上仍然處于中期階段,勞動(dòng)年齡人口中還有超過(guò)一半屬于初中學(xué)歷以下的低技能勞動(dòng)力。
從農(nóng)業(yè)來(lái)看,黨中央提出要發(fā)展“兩型”農(nóng)業(yè)(即“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的農(nóng)業(yè)),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必須結(jié)合傳統(tǒng)精耕細(xì)作的優(yōu)點(diǎn)與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科技,實(shí)現(xiàn)適度的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顯然,在人多地少的硬約束下,為了保障口糧安全,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仍然需要大量的活勞動(dòng)。
從制造業(yè)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必須轉(zhuǎn)型升級(jí),但是即使是中高端的制造業(yè),也仍然有許多環(huán)節(jié)需要大量的活勞動(dòng),是簡(jiǎn)單勞動(dòng)與復(fù)雜勞動(dòng)的分工協(xié)作。制造業(yè)的升級(jí)需要增加高技能勞動(dòng)力的使用,表現(xiàn)為研發(fā)設(shè)計(jì)能力增強(qiáng)、技術(shù)工藝水平提高,但是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制造、組裝成品,仍然需要大量的活勞動(dòng)。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的產(chǎn)品絕大部分是日常必需品,因此,對(duì)內(nèi)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是穩(wěn)就業(yè)、促進(jìn)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徑,是穩(wěn)定與改善廣大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礎(chǔ);對(duì)外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也有存在的需求。雖然危機(jī)導(dǎo)致外部總體需求下降,但日常消費(fèi)品的需求具有剛性,歐美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居民的消費(fèi)減少主要是高端消費(fèi)的減少,日常必需品消費(fèi)總體上變化不大。目前,我國(guó)距離像美國(guó)這樣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如果我們過(guò)早地放棄制造業(yè),包括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將犯歷史性的錯(cuò)誤”[1]。
從服務(wù)業(yè)來(lái)看,城市化主要是城鎮(zhèn)居民人口的增長(zhǎng),是社會(huì)勞動(dòng)分工的深化、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表現(xiàn)為服務(wù)消費(fèi)需求的增加,尤其是生活服務(wù)業(yè)需求,其中有相當(dāng)部分是屬于勞動(dòng)密集型。2013年底,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huì)議提出,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jìn)城常住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落戶城鎮(zhèn)、約1億人口的城鎮(zhèn)棚戶區(qū)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顯然,沒(méi)有足夠的產(chǎn)業(yè)支撐,沒(méi)有足夠的就業(yè)崗位,很難實(shí)現(xiàn)這“3個(gè)1億”的任務(wù)。
傳統(tǒng)的工業(yè)化往往是用技術(shù)和資本代替勞動(dòng),而我國(guó)人口多、勞動(dòng)力成本低,充分發(fā)揮人力資源優(yōu)勢(shì)是正確選擇。而實(shí)現(xiàn)資金、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同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相結(jié)合,是當(dāng)前以及未來(lái)較長(zhǎng)時(shí)間內(nèi)我國(guó)新型工業(yè)化道路的特點(diǎn)之一。
2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是穩(wěn)就業(yè)、保增長(zhǎng)的重要基礎(chǔ)
從勞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來(lái)看,據(jù)《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動(dòng)態(tài)調(diào)查:2013年報(bào)告》顯示,我國(guó)勞動(dòng)力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9.76年,受教育程度以中等教育為主。2013年全國(guó)就業(yè)人員76977萬(wàn)人,其中初中及以下學(xué)歷的比重為70.3%,大約有5.41億人,而大學(xué)以上學(xué)歷僅為12.94%。說(shuō)明在16-60周歲的勞動(dòng)年齡人口中低技能勞動(dòng)力所占比例仍然很高。政府提出要把就業(yè)放在第一位,我國(guó)每年新增就業(yè)人口大概1300-1500萬(wàn)人,按已有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每年要實(shí)現(xiàn)1200萬(wàn)人的新增就業(yè),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控制在4%左右,GDP的增長(zhǎng)率就至少要在7%以上。
2013年,我國(guó)的GDP增長(zhǎng)7.7%,其中第一產(chǎn)業(yè)增長(zhǎng)4.0%,第二產(chǎn)業(yè)增長(zhǎng)7.8%,第三產(chǎn)業(yè)增長(zhǎng)8.3%。第二產(chǎn)業(yè)的增速總體與GDP增速基本持平,其中,紡織品、服裝等7大類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品出口4618.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20.9%,同比增長(zhǎng)了10.3%,比全國(guó)GDP增速多出2.6個(gè)百分點(diǎn)。顯然,我國(guó)在傳統(tǒng)加工貿(mào)易產(chǎn)品領(lǐng)域仍然占有很高的國(guó)際市場(chǎng)份額。嚴(yán)格來(lái)講,在出口貿(mào)易中勞動(dòng)密集型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還包括家電、一般機(jī)械等許多機(jī)電產(chǎn)品的勞動(dòng)密集型區(qū)段,若加總計(jì)算起來(lái),我國(guó)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品出口約占外貿(mào)出口總額的7成。
對(duì)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以及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固然必須大力發(fā)展,但并不意味著要替代傳統(tǒng)產(chǎn)品。“只有落后的技術(shù),沒(méi)有落后的產(chǎn)品”,當(dāng)前正確的做法是,推動(dòng)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產(chǎn)品不斷提高檔次和附加值,因?yàn)楸匦杵肥莿傂孕枨螅肋h(yuǎn)都有市場(chǎng)潛力可挖。雖然我國(guó)外貿(mào)出口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中,高科技產(chǎn)品比重已大大提升,但是我國(guó)企業(yè)參與生產(chǎn)的環(huán)節(jié)大部分仍然是勞動(dòng)密集型的加工、裝配環(huán)節(jié)。這說(shuō)明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仍然是我國(guó)穩(wěn)就業(yè)、保增長(zhǎng)的重要陣地。
從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分布來(lái)看,主要集中在小微企業(yè)。小微企業(yè)可以有效地實(shí)現(xiàn)以創(chuàng)業(yè)帶動(dòng)就業(yè),因?yàn)樗鼈兘^大部分是屬于勞動(dòng)密集型的行業(yè)或環(huán)節(jié),需要大量的勞動(dòng)力人口。據(jù)統(tǒng)計(jì),小微企業(yè)數(shù)量占我國(guó)企業(yè)總數(shù)的97%以上,廣泛分布在城市鄉(xiāng)村,基本涵蓋了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所有行業(yè)。其創(chuàng)造的最終產(chǎn)品和服務(wù)價(jià)值相當(dāng)于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60%,提供了85%的就業(yè)崗位,吸納了全國(guó)90%的新增勞動(dòng)力,創(chuàng)造了50%以上的出口收入和財(cái)政稅收。
顯然,在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yè)產(chǎn)能普遍過(guò)剩的情況下,要實(shí)現(xiàn)保增長(zhǎng)、穩(wěn)就業(yè)的目標(biāo),就必須繼續(xù)鞏固發(fā)展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加快服務(wù)業(yè)的發(fā)展。
3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是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重要基礎(chǔ)
從我國(guó)的勞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來(lái)看,勞動(dòng)密集型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仍然是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馬克思說(shuō)過(guò),“如果一個(gè)國(guó)家的工資和土地價(jià)格低廉,資本的利息卻很高,因?yàn)槟抢镔Y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總的說(shuō)來(lái)不發(fā)展,而另一個(gè)國(guó)家的工資和土地價(jià)格名義上很高,資本的利息卻很低,那么,資本家在一個(gè)國(guó)家就會(huì)使用較多的勞動(dòng)和土地,在另一個(gè)國(guó)家就會(huì)相對(duì)地使用較多的資本”[2]。我國(guó)地域大、人口多,各地發(fā)展程度不一,低技能勞動(dòng)力仍然占據(jù)主體,必須全面深入推進(jìn)對(duì)外開(kāi)放,繼續(xù)充分利用好“兩個(gè)市場(chǎng)”。不管是在當(dāng)前還是未來(lái)較長(zhǎng)的時(shí)期內(nèi),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都有其存在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是我國(guó)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
歐美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完成工業(yè)化向后工業(yè)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把大量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出去,即“去工業(yè)化”,結(jié)果在經(jīng)歷全球金融危機(jī)后,虛擬經(jīng)濟(jì)的虛假繁榮與房地產(chǎn)的泡沫破裂,導(dǎo)致了大量的失業(yè)人口,社會(huì)問(wèn)題叢生,危機(jī)四伏。因而危機(jī)爆發(fā)后,歐美等國(guó)相繼紛紛提出了“再工業(yè)化”的戰(zhàn)略。這說(shuō)明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才是社會(huì)的財(cái)富之源,是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繁榮的根基。“無(wú)糧不穩(wěn),無(wú)工不富”仍然是一個(gè)普遍、強(qiáng)有力的法則,因此只有在鞏固工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才能實(shí)現(xiàn)服務(wù)業(yè)的快速發(fā)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jí)不等于放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今后較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我國(guó)就業(yè)壓力仍然非常巨大,仍然需要大量簡(jiǎn)單活勞動(dòng)密集的就業(yè)崗位。
當(dāng)前,我國(guó)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環(huán)境有惡化的趨勢(shì),一方面與國(guó)際需求減少有關(guān),另一方面也說(shuō)明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失衡度偏大,有“脫實(shí)就虛”的傾向。現(xiàn)實(shí)的情況是,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與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仍然具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而大量的金融資源卻被錯(cuò)配,導(dǎo)致企業(yè)融資難、融資成本過(guò)高。地方政府片面發(fā)展重化工業(yè)、片面“造城”,過(guò)分依賴舉債投資與建設(shè),擠占了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要素資源,不僅惡化了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環(huán)境,而且高負(fù)債率、房地產(chǎn)泡沫化加劇,進(jìn)一步加大了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失衡。因此,必須鞏固好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根基,尤其是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
4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并非最大的“污染戶”
很多人一提到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就簡(jiǎn)單地貼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標(biāo)簽。當(dāng)然,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中有不少行業(yè)或領(lǐng)域或多或少存在著環(huán)境污染的問(wèn)題,比如紡織、造紙、印染等,如果加快對(duì)這些污染較為突出的行業(yè)的改造治理,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總體上看,污染程度相對(duì)較小。而真正的污染大戶是重化工業(yè),諸如火電、水泥、鋼鐵、化工、有色金屬、廢塑料加工、金屬表面酸洗、電鍍等行業(yè),都是空氣污染、水污染以及廢棄物排放的大戶。這與我國(guó)處于重化工業(yè)發(fā)展階段有必然聯(lián)系,也與我國(guó)整體的技術(shù)水平不高、資源利用率偏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失衡等方面有關(guān)。
目前,我國(guó)能源效率總體仍然偏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發(fā)展方式總體上仍未改變。我國(guó)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guó)的3.3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fā)展中國(guó)家。我國(guó)重化工業(yè),除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上游產(chǎn)業(yè)供給不足外,大多數(shù)行業(yè)的生產(chǎn)能力大于市場(chǎng)需求。2009年中央開(kāi)始實(shí)施“四萬(wàn)億投資”計(jì)劃,重點(diǎn)振興十大產(chǎn)業(yè),其中大部分是重化工業(yè)以及部分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從“四萬(wàn)億”流向來(lái)看,除了一部分流到房地產(chǎn)外,大部分都流向了重化工業(yè),尤其是“兩高一資”產(chǎn)業(yè),而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中的光伏產(chǎn)業(yè),大部分企業(yè)集中在低技術(shù)、高污染環(huán)節(jié)。近幾年由于重化工業(yè)的過(guò)度投資,在工業(yè)增加值的構(gòu)成中,2012年重化工業(yè)占比一度上升到71%,不僅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產(chǎn)能過(guò)剩,而且企業(yè)幾乎個(gè)個(gè)都是“污染大戶”。
在嚴(yán)重的供過(guò)于求的條件下,各地區(qū)企業(yè)進(jìn)行惡性價(jià)格競(jìng)爭(zhēng),為了壓低成本,節(jié)能減排上很多企業(yè)“偷工減料”,以至于全國(guó)有幾百個(gè)城市深受“霧霾”的肆虐。近幾年頻發(fā)的重大污染事件,基本上都是重化工業(yè)企業(yè)引發(fā)的。諸如火電、鋼鐵、石化、水泥、有色金屬、化工等重化工業(yè)產(chǎn)業(yè)均是PM2.5等污染物排放的大戶。像電解鋁、平板玻璃、水泥等產(chǎn)能嚴(yán)重過(guò)剩的重化工業(yè)也是污染大戶。汽車也是重工業(yè)之一,尾氣排放使其成為空氣污染大戶之一。顯然,我國(guó)“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的資源環(huán)境壓力,主要是重化工業(yè)造成的,這是由我國(guó)處于重化工業(yè)發(fā)展階段所決定的,也與地方政府片面推進(jìn)資本密集型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有關(guān)。因而,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首要的任務(wù)就是要加快推進(jìn)重化工業(yè)的轉(zhuǎn)型升級(jí),淘汰落后產(chǎn)能,向技術(shù)水平高的大企業(yè)集中,整合優(yōu)化、科學(xué)布局。
重化工業(yè)主要是生產(chǎn)資料產(chǎn)業(yè),主要為輕工業(yè)、高端耐用品的生產(chǎn)服務(wù),當(dāng)然也有一部分是直接為生活消費(fèi)服務(wù)的。要以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重化工業(yè)走向“高技術(shù),低排放”的綠色發(fā)展道路,強(qiáng)化源頭治理、全面推行清潔生產(chǎn)是節(jié)能減排的重點(diǎn)。同時(shí),要加強(qiáng)對(duì)可再生能源的開(kāi)發(fā)與利用,改善我國(guó)的能源結(jié)構(gòu),從而為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提供更加精良的技術(shù)裝備和更加環(huán)保的資源、能源。
5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并非全是“低端、低附加值”
近幾年很多人把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等同于“低端、低附加值”產(chǎn)業(yè),這種看法過(guò)于簡(jiǎn)單、片面。有人認(rèn)為,“高端不高端,關(guān)鍵看兩端”,從目前的國(guó)際分工格局來(lái)看,具有相當(dāng)解釋力。但是,我們要改變這種不平等、不利的分工格局,并非簡(jiǎn)單拋棄中間的制造環(huán)節(jié),把勞動(dòng)密集型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剔除就等于實(shí)現(xiàn)了轉(zhuǎn)型升級(jí)。而是要以技術(shù)、質(zhì)量、品牌來(lái)重塑產(chǎn)業(yè)鏈、價(jià)值鏈,提高產(chǎn)品的競(jìng)爭(zhēng)力。如果制造環(huán)節(jié)沒(méi)做好,所謂轉(zhuǎn)型升級(jí)就會(huì)缺乏根基,就會(huì)走向歧路。因而,轉(zhuǎn)型升級(jí)并不是簡(jiǎn)單地剝離中間的制造環(huán)節(jié)。當(dāng)然,具有品牌競(jìng)爭(zhēng)力的少數(shù)大企業(yè),可以把制造環(huán)節(jié)外包出去,轉(zhuǎn)移給國(guó)內(nèi)其他企業(yè)做,甚至轉(zhuǎn)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國(guó)家做。但是從目前我國(guó)的發(fā)展階段來(lái)看,大量簡(jiǎn)單勞動(dòng)密集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向國(guó)外轉(zhuǎn)移,不僅條件不允許,而且也沒(méi)必要。因?yàn)槲覈?guó)還有很多需要就業(yè)的低技能勞動(dòng)力,尤其是中西部地區(qū),總體上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還有相當(dāng)?shù)母?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
相當(dāng)多的人迷信“微笑曲線”,卻不知還有一個(gè)“武藏曲線”[3],忘了馬克思的勞動(dòng)價(jià)值論,好像產(chǎn)品價(jià)值主要地不是生產(chǎn)勞動(dòng)創(chuàng)造的。如果有一個(gè)自由進(jìn)入、公平競(jìng)爭(zhēng)的國(guó)際市場(chǎng)環(huán)境,那么我們很多產(chǎn)品的附加值(v+m)就能夠“按原樣實(shí)現(xiàn)”,至少獲得與外商同樣的平均利潤(rùn)率,產(chǎn)品價(jià)值中生產(chǎn)加工環(huán)節(jié)的勞動(dòng)價(jià)值就會(huì)從“被壓低、低估”的狀態(tài)回歸正常,就可以賣到好價(jià)格,實(shí)現(xiàn)更高的利潤(rùn)。因而,必須堅(jiān)持價(jià)值“為我創(chuàng)造、為我實(shí)現(xiàn)”的正確思路,重視技術(shù)與品牌,大膽“走出去”,打造自己的國(guó)際營(yíng)銷渠道,以質(zhì)量與品牌占據(jù)國(guó)際中高端產(chǎn)品市場(chǎng)。品牌是以技術(shù)、質(zhì)量為支撐的,在繼續(xù)做好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基礎(chǔ)上,做好兩端。繼續(xù)利用我國(guó)勞動(dòng)力低成本的優(yōu)勢(shì),在做好生產(chǎn)制造這一環(huán)節(jié)的同時(shí),充分利用我國(guó)中高端人力資源的總量?jī)?yōu)勢(shì),加大研發(fā)設(shè)計(jì)、營(yíng)銷與品牌打造的投入,在價(jià)廉的基礎(chǔ)上提升物美的層次,帶動(dòng)生產(chǎn)制造環(huán)節(jié)價(jià)值的回歸與實(shí)現(xiàn)。
6 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并非總是“低工資、不體面”
過(guò)去,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的發(fā)展片面依賴低要素成本,既不太重視資源的節(jié)約與環(huán)境保護(hù),也不夠重視自主創(chuàng)新與研發(fā)的投入。很多企業(yè)為了節(jié)約成本,竭力壓低工資,不重視勞動(dòng)條件與環(huán)境的改善。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zhǎng),競(jìng)相以低要素成本為吸引力大肆招商引資,導(dǎo)致工人勞動(dòng)時(shí)間延長(zhǎng),工作強(qiáng)度大,工資低。這樣的境況給80后、90后的農(nóng)民工留下了“低工資、不體面”的印象。
未來(lái),隨著服務(wù)業(yè)在三次產(chǎn)業(yè)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用工需求也將增加,低端服務(wù)業(yè)的用工將呈現(xiàn)更為緊缺的狀態(tài)。目前各大中城市的批發(fā)、零售、住宿、家政、保安、護(hù)理、洗車、保潔、餐飲、環(huán)衛(wèi)、倉(cāng)儲(chǔ)、搬運(yùn)、送貨、物流、快遞等低端服務(wù)業(yè)整體呈用工緊缺狀態(tài)。這些就業(yè)崗位一般需要大量低技能的勞動(dòng)力。很多城鎮(zhèn)居民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往往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這些低技能勞動(dòng)力,既需要他們,又歧視、排斥他們,這樣不僅會(huì)影響他們的服務(wù)態(tài)度、質(zhì)量,而且會(huì)激發(fā)各種社會(huì)矛盾。一個(gè)城市不僅需要高端制造業(yè)、高端服務(wù)業(yè),而且也需要低端服務(wù)業(yè),否則是很難正常運(yùn)轉(zhuǎn)的。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低端服務(wù)業(yè)的工資待遇也必然要提高,而且必須享受同等的社會(huì)福利保障與公共服務(wù),否則很難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與發(fā)展層次。
隨著我國(guó)收入倍增計(jì)劃的持續(xù)推進(jìn),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逐年大幅提升,而隨著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zhèn)化的推進(jìn),過(guò)去勞動(dòng)密集型崗位是“低工資、不體面”的面貌將會(huì)逐漸得以扭轉(zhuǎn)。具體表現(xiàn):一是提高工資待遇與福利水平。我國(guó)政府這幾年多次提高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二是大力抓安全生產(chǎn)。黨中央每年都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安全生產(chǎn),通過(guò)立法不斷改善勞動(dòng)環(huán)境。諸如引起員工“十幾連跳”的富士康、導(dǎo)致員工化學(xué)中毒的“蘋果供應(yīng)商”這樣的“血汗工廠”,廣大農(nóng)民工是不歡迎的,該搬走就讓它搬走。關(guān)于工廠制度下的勞動(dòng)環(huán)境,馬克思也曾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工廠勞動(dòng)可以像家務(wù)勞動(dòng)一樣潔凈、美妙,甚至更潔凈、更美妙”[4]。近幾年,隨著“用工荒、招工難”現(xiàn)象越來(lái)越普遍,很多企業(yè)為了招得到人、留得住人,不僅提高工資待遇,而且勞動(dòng)條件與環(huán)境也有明顯的改善。三是竭力消除“就業(yè)歧視、同工不同酬”的現(xiàn)象。尤其是國(guó)有企事業(yè)單位,通過(guò)“勞務(wù)派遣”、“編制外用工”,以廉價(jià)的工資把苦差、臟活外包給農(nóng)民工,這些崗位幾乎都是勞動(dòng)密集型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據(jù)統(tǒng)計(jì),全國(guó)大約有2000多萬(wàn)人處于這種不平等的用工關(guān)系。對(duì)此,中央已開(kāi)始著手進(jìn)行改革,以消除這種不平等就業(yè)的狀態(tài)。
縱觀這些年黨中央關(guān)于穩(wěn)就業(yè)、勞工保護(hù)等民生政策的推行,可以期待,我國(guó)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從業(yè)人員必將逐漸改變“低收入、不體面”的狀態(tài)。
7 結(jié)論
總之,從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優(yōu)化來(lái)看,重化工業(yè)的比重必然要有所降低,輕紡工業(yè)等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增加值比重應(yīng)該有所回升,同時(shí)在推進(jìn)城鎮(zhèn)化的過(guò)程中應(yīng)加快服務(wù)業(yè)的發(fā)展。穩(wěn)就業(yè)與保增長(zhǎng)相互促進(jìn),才能持續(xù)推進(jìn)居民收入增長(zhǎng),才能提高廣大居民的消費(fèi)能力,才能增強(qiáng)內(nèi)需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動(dòng)力,并以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升級(jí)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升級(jí)。因而,從國(guó)情、發(fā)展階段來(lái)看,在“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的戰(zhàn)略實(shí)施當(dāng)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我國(guó)經(jīng)濟(jì)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仍大有可為之處。政府、企業(yè)與社會(huì)必須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促進(jìn)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科學(xué)發(fā)展。
[1]龍永圖.放棄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將是歷史性錯(cuò)誤[J].進(jìn)出口經(jīng)理人,2011(8):18-19.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8.
[3]朱志礪.微笑曲線,還是武藏曲線?[J].董事會(huì),2005(7):96 -97.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7.
責(zé)任編輯:沈玲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ues
HUANG De-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F(xiàn)ujian Normal University,F(xiàn)uzhou 350007,China)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appeal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beenmore and more concerned,laborintensive industry has shown the trends of being depreciated and demonized.However,China i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in which low-skilled labors still occupy the dominant force,and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still have bright prospects.So,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scientifically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from the joint developmentof three industries,keep sustaining and stable promotion on the basis of preserving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of“adjusting structures and transferringmodes”and pay attention to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link and capital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aswell as links.
labor-intensive industry;steady employment;entity econom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062.9
A
1009-3907(2014)05-0592-04
2014-02-13
黃德勝(1981-),男,福建南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jì)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