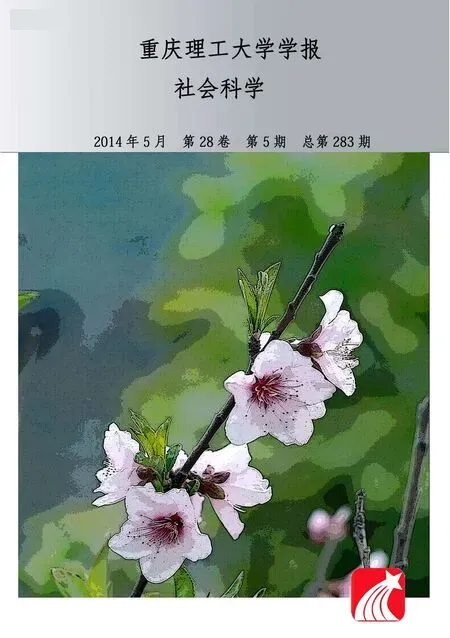社會互構論視角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機制探析
鄧海龍,王慧燕
(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濟南 250100)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是“五位一體”。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1]39。這是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升華的表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從社會互構論這一全新的視角審視建設生態文明的深層次原因,對于協調社會各主體間的互構關系,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視角
社會互構論(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 theory)是關于個人與社會這兩大社會行動主體間的互構共變關系的社會學理論。它是“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全球社會發展過程、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關系進行闡釋的一種社會學理論”[2]591。所謂互構,是我們對參與互構主體間的關系的本質刻畫,即指社會關系主體之間的相互建塑與型構的關系。所謂共變,是指社會關系主體在互構過程中的相應性變化狀態,相應性是共變狀態的基本特征。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類生活共同體的發展就是個人與社會的互構關系的演變過程。個人是社會的終極單位,社會則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具體而言,這種理論將個人和社會作為最基本的社會行動主體,將二者的關系問題作為社會學的元問題(meta-problem),從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這兩大行動主體的互構共變關系進行分析和闡釋,重點對當代社會轉型期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進行研究。
社會互構論將整個社會系統分為兩大子系統,即“社會自然”和“社會人文”。換言之,該理論將“自然”有規定地納入了“社會”這個最基本的社會行動主體中。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不同,這個理論中所說的“社會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因為與自然的關系,所以人與人要結成關系”[3]402。簡言之,社會就是由人與自然、人與人這兩大關系構成的統一體。
眾所周知,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濃縮的生態環境興衰史,也是人類文明隨著生態環境的興衰而興衰的歷史。現如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問題已成為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性越大,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報復性也越強烈。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4]559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已成為擺在人類面前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社會互構論對社會兩大子系統——自然系統與人文系統——交互構建的分析和研究,彌補了以往社會結構理論僅僅關注和分析人文社會結構的局限性,表達了社會學理論對以往理論和實踐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實踐的指導。
二、社會互構論視角下生態文明建設的必要性
從社會互構論的角度看,建設生態文明的深層次原因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主體間的不和諧關系,特別是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系,阻礙了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有重塑社會各主體間的和諧共變關系,建立和改善個人、社會、自然之間的互構共變關系,使各社會行動主體積極能動地互構,才能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人與自然正向諧變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的10年,我國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歷史性成就,“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1]6,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嚴峻;自然界的“反人化”表現日益突出,這些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要實現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實現人與自然的正向諧變。
社會互構論認為,“個人”、“社會”和“自然”是現代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自身的各種關系和紐帶的基礎。人與自然的正向諧變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性條件。“所謂正向諧變,是指參與互構各方,其行動關聯和關系相應地朝著共識互信、合作協調、互惠雙贏等和諧的向度與量級的發展、推進。”[3]530這就要求我們在改造世界的同時,“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1]39,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馬克思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161,恩格斯也特別告誡:“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4]560人與自然密不可分的關系啟示我們,在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改造客觀世界時,必須尊重自然的客觀規律,若違背自然規律,就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6]。在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曾發生過多次這樣的教訓,這些教訓也告誡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正向諧變[7]。
(二)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社會與自然正向諧變的迫切要求
社會互構論確信,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對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發揮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從歷史上看,社會與自然的不和諧關系主要表現在:工業文明所創造的物質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殖民掠奪和利用先進技術開采自然資源的基礎上,特別是建立在非可再生性或可耗盡資源的基礎上的。這種不負責任的、不可持續性的行為,勢必造成生產能力、消費欲望的無限擴張和生態環境的有限承載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破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最終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此外,這種不和諧關系還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問題上態度、立場和責任擔當的不同。發展中國家認為,全球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排放的累積效應所致,必須在追溯歷史責任的基礎上進行減排任務的分配;而發達國家則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承擔大幅度減排的義務。實際上,許多環境問題同各國發展階段的生產方式、人口規模、資源稟賦以及產業分工等因素密切相關。為此,要實現社會與自然的正向諧變,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演進的聯動性與可持續性,必須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具體問題上,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應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等要求,積極落實“巴厘路線圖”,最終實現社會與自然、人與自然的正向諧變,推動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構建。
(三)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其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和諧互構的內在要求
生態文明作為社會文明的重要內容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構成了當代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新框架。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8]。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于1986年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并在其著作《風險社會》(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中指出:“我們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風險威脅的潛在階段已經接近尾聲了,不可見的危險正在變得可見。對自然的危險和破壞——越來越清晰地沖擊著我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9]64而且進一步指出,生態的脆弱性超過了我們人類的想象,自然的新陳代謝和自我恢復的能力越來越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認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類活動愈是接近地球支撐這種活動的能力限度,對不能同時兼顧的因素的權衡就變得更加明顯和不能解決。”[10]18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國為應對嚴峻形勢所作出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包含著各文明之間的良性運行與和諧發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各文明之間的和諧互構。建設生態文明不是否定工業文明,而是強調先進的工業文明必須實現人與自然的正向諧變,使人們在享有現代物質文明成果的同時,又能保持和享有良好的生態文明成果。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反映著人類對自然、對社會和對自身的認識、利用和改造關系,反映著這些關系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它們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一方面,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為生態文明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科學的制度保證和強大的智力支持,分別體現著生態文明的物質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另一方面,生態文明所創造的生態環境、生態理念、生態道德和生態社會等,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態基礎,在人類文明的建設與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和諧互構、正向諧變的有機統一體。
三、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互構機制
機制就是“帶規律性的模式”[11]33。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互構機制,就是社會行動主體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構,這一過程包含著對社會主體的行動及意義具有推進、調節、創新功能的機制”[3]539。它是由情性調節機制、智性邏輯機制、意志驅動機制和實踐反思機制等所構成的綜合性創新機制。
(一)情性調節機制
情性調節機制,主要是對各社會參與主體的欲望、沖動以及由此所作出的行動進行合理而有效的調適,以期實現各主體間的正向諧變。在現代生活中,各種社會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由富有情感的人來驅動和運作的。然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正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所述,人的某一層次的需要相對滿足了,就會向更高層次發展。雖然這種理論存在一定的消極因素,但他提出的需要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趨勢是無可置疑的,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這就需要我們“對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和功利性思維及行動進行調適和節制使之合理化”[3]539。為此,我們人類對自然、對社會所作出的任何行動必須建立在社會良性運行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既要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求,也要考慮到滿足后代人的需求,要堅持走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之路,走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之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人類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作用,才能盡可能地避免遭到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從而實現社會的永續發展。
(二)智性邏輯機制
智性邏輯機制,就是使各社會行動主體“運用各種智性和邏輯的方式(如認知、判斷、推論以及歸納和演繹),展開理性的思考、構想等,對自我與其他行動者的關系、行動效益和代價,進行預先評估、度量、權衡,促成對行動過程的調適、修正、創新等”[3]539。這就要求我們在將計劃付諸行動時,不僅要注重對社會行動主體的利益和目標進行理性計算,而且要更加注重對社會行動后果的責任意識和公眾的直接感受,使各項行動都進一步規范化和理性化。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都必須樹立整體意識、責任意識和生態意識。建設生態文明就是要求我們把眼光放在國家和世界的高度,凡事從國家利益出發,增強節約和環保意識,合理規劃,勇于擔當,把解決環境問題與增強本國的可持續能力緊密結合起來,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三)意志驅動機制
意志驅動機制,就是指社會各主體在互構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達成正向諧變的既定目標,實現互構各方合作發展和互惠共贏。無論是個人、社會還是國家,都難免會發生各種利益糾紛,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應對,化解矛盾,加強合作,充分發揮各主體的自覺能動性。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人類的共同愿望,也是每一個公民和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生態文明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人類持續不斷地共同努力。只有我們轉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宣傳生態文明觀,大力倡導節能環保,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適度消費、綠色消費,從我做起,堅持不懈,勇于克服困難,切實把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要求落實到每位公民、每個國家中去,“和諧世界”的目標一定會實現。
(四)實踐反思機制
實踐反思機制,就是指互構各方要不間斷地對自我進行批判性思考,及時糾正實踐過程中各種不妥的行為方式,進而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眾所周知,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完善合理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是我們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保障,也是我們實踐反思的參照標準。“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1]41政府部門要充分發揮法律制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統籌兼顧,及時督查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源頭上解決生態問題。
從社會互構的視角來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實質上就是建塑和型構社會各主體間的和諧共變關系,建立和改善個人、社會、自然之間的互構共變關系,使社會各主體積極能動地互構,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這是一項系統工程,是情性調節機制、智性邏輯機制、意志驅動機制和實踐反思機制實現優化整合的過程,是往復調適、自我演進、無限更新和交互建塑的過程。
[1]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鄭杭生,楊敏.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王亞楠.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15-18.
[7]蔣俊明.生態文明建設視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優化[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13 -17.
[8]劉江翔.論生態文明建設的消費法治化視角[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3(6).
[9][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10][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長的極限[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 張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