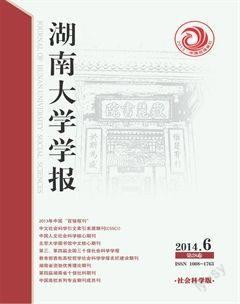孔子之“道”與儒學重構
[摘 要] “道統”是儒學的核心觀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傳承統緒。道統作為儒學的深層內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儒學的基本概貌和形態。朱熹以“心傳”、“心法”為其道統論的主要意涵,構筑了以“道心”與“人心”、“理”與“氣”、“天理”與“人欲”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學;牟宗三則以“心體即性體”、“即存有即活動”釋道統,建構了其道德形上學。在“后新儒學”的視域下反思宋明理學空談理氣心性,現代新儒學引向超越絕對的偏失,致力于當代儒學重構時,重歸孔子之“道”,確立儒學“新道統”或許應是基礎性的理論環節。
[關鍵詞] 道統;孔子;道;論語;儒學重構
[中圖分類號] B22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4)06—0134—06
Doctrine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Refactoring
Discussing from Chu Hsi and Mou Tsung-San
ZHENG Zhi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Abstract:Confucian orthodoxy is one of core notion in Confucianism for representing Confucian fundamental spirit. As the deep core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 orthodoxy decides general facts and forms in significant measure. Chu Hsi regarded Xin Chuan and Xin Fa as the mental implication of his Confucian orthodoxy theory, and built a dualistic world according to doctrine and individual, reason and spirit, heavenly principle and human desires; Mou TsungSan constructed his moral metaphysics by explaining Confucian orthodoxy with that in mind. We rethink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y prattling about reason, spirit, mind and nature under the view of NeoConfucianism and present NeoConfucianism to absoluteness. Refactoring, returning to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and establishing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should b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step.
Key words: Confucian orthodoxy;Confucius;Doctrine;the Analects;Confucianism refactoring
“道統”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一般說來,儒家的道統觀念以先秦孔孟為遠源,經中唐韓愈發揮
《論語·堯曰》、《孟子·盡心下》、韓愈《原道》。,并最終由宋儒推向成熟[1](P65-66)。“道統”是什么?不同的儒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有論者認為,儒家“道統”可在即“統”言“道”、即“道”言“統”兩種模式下得到詮釋和說明。所謂即“道”而言“統”,就是以“道”作為儒學之為儒學的真精神,并以此為要來判分和確立儒家的傳承譜系。如熊十力所言:“蓋一國之學術思想,雖極復雜,而不可無一中心。道統不過表現一中心思想而已。”[2](P342)就道統之寬泛意義來說,就是表征儒家之中心思想、根本精神、核心觀念的傳承統緒。確立一個什么樣的道統,往往也就意味著確立一個什么樣的儒學形態。不同時代的儒者圍繞著對“道統”之“道”的不同理解,建構了理論形態迥異、義理精神有別的儒學系統。作為宋明“新儒學”創設之關鍵人物,朱熹以“十六字心傳”和孔顏“克己復禮為仁”之“心法”作為道統之“道”的主要內涵,并由此整合圓融了呈現道心與人心、理與氣、天理與人欲、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二元架構的程朱理學系統。然超越精神的提升、理氣心性的圓融,宋明理學雖能成功回應佛老挑戰,扭轉“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之頹勢,卻也將儒學引上了形上超越的極端,淪為“空談心性”的玄學清談。與之有類,現代新儒家有感于儒學“花果飄零”之困局,矢志延續道統,復興儒學,他們遙接宋明,復活程朱陸王之思想睿慧,以形上超越的路徑保存、提升、重建儒學,牟宗三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牟氏以儒家內圣學“心體即性體”的圓教模型釋道統之“道”,判分先秦儒典,重組宋明儒學,援引西學,提出“內圣開新外王”的構想,完成了其道德形上學的建構。然這種形上保存的方式,雖在繼承、發揚、整合、創新中國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卻有以心性修養代道德實踐的偏執,難于“落實在整個歷史社會總體間”。對此,我們不免會有這樣一番思量:朱熹、牟宗三皆以回歸孔孟為追求,力圖彰明圣學本義,他們既以得悟儒門“道”之本旨,其孜孜以求,費盡心力所構創的所謂“新儒學”為何還有如此偏失?圣學要領究竟何在?事實上,我們今天在“后新儒學”的語境下對其進行總結反思,呼喚儒學重返生活世界,期待儒學活水流向民間,致力于儒學的生活化、民間化、大眾化、社會化開展及其當代重構時,如果能靜下心來細細品讀《論語》,回到孔子的生活世界,真真切切地體驗孔學精神,我們或許不難發現,儒門所傳之“道”既非朱子匠心獨運所提出的“心傳”、“心法”那般抽象神秘,亦非如牟氏所悟徹的所謂“心體即性體”那樣玄奧精深,孔子“道”之真義不過“仁禮和合”、“極高明而道中庸”二語,如此而已。倘能明此儒之為儒的真精神,對儒學的當代重建或可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指引。
一 朱熹的“心傳”、“心法”
及其“二世界”哲學
“道統”是儒學的核心觀念和中心思想所在。朱熹以“十六字心傳”與“克己復禮為仁”之“心法”作為其立學根基,可以說,其整個龐大的思想體系正是以此為起點,在此“道”的內核之上生發、展開的。“道統”一詞由朱子率先提出,其主要內涵在《中庸章句序》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達。他說:
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3](P14)
在此,朱熹徑直將堯、舜、禹圣賢一脈相傳的道統具體化為《尚書·大禹謨》中的“十六字心傳”。學界一般也都以之作為朱熹道統論的全面的經典性表述,其實不然。誠如有論者指出的:“蓋現有論述皆以‘十六字心傳’為朱子道統說之根本性、唯一性表述,而忽視了顏子及其所代表的‘克復心法’在構筑朱子道統學中的應有地位。……故孔顏克己復禮為仁的心法授受實為‘十六字心傳’的必要補充,其價值在于彰顯了儒家道統以工夫論為核心,由工夫貫穿本體的下學上達路線。”[4](P19-20)應該說,“心傳”與“心法”的結合方是朱子道統論之“道”的基本內涵所在,因為講“道心”、“人心”的“心傳”只體現了朱學本體與心性的統合,唯有輔以“克復心法”所彰顯的工夫學說,程朱理學才真正成其為一圓融本體、心性、工夫的完整體系。由是,朱學的整個義理架構可以道統中心,“心傳”、“心法”兩條主線進行分解說明。
就朱熹摘出的“十六字心傳”來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謂“道心”是指符合道體天理之心,故“微”;“人心”是指生于形氣之偏的私心,故“危”,而“允執厥中”就是要時時省察此“危而不安”的人心,持守“微而不顯”的道心,以合乎天理仁義之心為要求,“執中”,無過無不及。不難看出,朱子所傳之“道”正是二程“自家體貼出來”的“天理”,其對“十六字心傳”的解釋不過就是“存天理,滅人欲”一語。因此,以“十六字心傳”為突破口,正可以析分出程朱理學“理”與“氣”、“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天理”與“人欲”的“二世界”架局。朱熹以“理”、“氣”二元互動確立其形上根基,并以此論心性而言“一性二分”、“心統性情”,實現了本體與心性的合一。下引幾句話最能體現朱熹圓融理氣心性的意識,十分關鍵。他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氣,然后有形。[5](P2755)
論天地之性則是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5](P2688)
由此不難發現,在朱熹的思想世界里,理氣心性實已圓融為一,本體與心性合在了一起。這可以說是朱熹以“十六字心傳”為綱領所展開的義理建構。以“心傳”為根基的理氣心性的貫通,輔以“克復心法”所體現的工夫進路,完整確立了程朱理學之規模。這就是說,朱學明分“理”與“氣”、“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這種生命二元架局最終要落實于即物窮理、存理滅欲、涵養用敬、變化氣質的工夫,即要學做圣人、克己復禮、行仁踐義,堅守儒家道德價值理想,最終成圣成賢[6](P74-77)。他說: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7](P367)
“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朱子大談理氣心性,看似玄妙漫談,實則是要以真切工夫的開出為旨歸的。就工夫論而言,朱熹服膺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說法,以用敬與致知作為其工夫論的兩個重要方面。格物致知,即物窮理,雖被陸九淵譏為支離事業,但是如果從朱熹的整個哲學系統來看,這種“格物致知”的修養工夫,又分明能與其全系統相統一、相協和。
綜上可見,朱熹以“十六字心傳”和“克復心法”為綱,創構了以圓融本體、心性、工夫為基本特質,以形上超越著稱的“二世界”哲學,實現了儒學形態由“實存道德描述”向“道德形上學”的轉變。這極大地提升了儒家的哲學思辨水平、開拓了儒家形上超越的世界,由此也就成功回應了佛道的挑戰,重建了中華人文價值理想,實現了儒學的第二次復興。然而,程朱對“天理世界”的不斷拔舉和提升,尤其當朱子大言“理在事先”的時候卻也將儒學引上了形上超越的極端,所帶來的不僅是使儒學日益脫離“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而淪為“空談心性”的玄學清談;在絕對超驗的“天理世界”統治下,所造成的是道德本體之“超我”對自我的壓抑和束縛。朱熹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8](P3204)君臣父子夫婦之“理”既先于人而存在,人生而就只有被動地去接受這個“理”,即毫無懷疑地去遵循踐履儒家“三綱”之教了。正如楊國榮先生所說:“正統理學以性體為道德本體,并以此為前提,要求化心為性。在性體形式下,普遍的道德規范構成了涵攝個體的超驗原則,本體被理解為決定個體存在的先天本質,自我的在世成為一個不斷接受形而上之規范塑造、支配的過程。由此導致的,往往是先驗的超我對自我的壓抑。”[9](P12)由此可見,這種形上超越的追求和提升,也可能會使儒學蛻變為超然于世、藐視世俗、流于空談、乏于踐行的玄虛之學。
二 牟宗三的“心體即性體”及其新儒學
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學的系統建構者。他深研道德形上學,會通天臺圓融義,終悟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先以心體、性體的圓融為要,判釋先秦、宋明兩期儒學,重構儒學新道統,又以此為基石,構筑起以肯定“智的直覺”、“內圣開出新外王”、“三統并建”、“良知自我坎陷”為主體內容的儒家道德形上學體系。可以說,悟徹孔子成德之教,識得儒家內圣心性學“心體即性體”之要旨,實現道統重建,是牟宗三現代儒學創新的起點和關鍵。
其一,以“心體即性體”為要,厘定先秦儒家經典,分別宋明理學之系統,重構儒家道統[10](P15-21)。在牟宗三看來,儒家所謂“道統”乃是泛指儒家的內圣心性之學或內圣成德之教,“中國‘德性之學’之傳統即名之曰‘道統’”,此“德性之學”的精義,集中凝結為“心體即性體”這一哲理深邃的命題。“性體”是道德形上學的概念,指內在道德性之性,與“天”這一實體相聯系。“就其統天地萬物而為其體言,曰實體;就其具于個體之中而為其體言,曰性體”[10](P43)。這里,牟宗三發揮了《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說法,以為“于穆不已”的天體下貫到個體之中而成其為性體。此“性體”概念從形上超越的高度確認了道德實踐之可能,是儒家道德形上學可以成立的要害所在,正因為有此“法門”,儒家這里才能實現道德與形上學通而為一,確立其“即宗教即道德”的精神特質。與“性體”一樣,“心體”亦是儒家內圣學的重要范疇,可以說,性體與心體構成了內圣心性學的一體兩面。此“心”非生理之心、心理學之心,亦非所謂認知之心,而是超越自律,內在固有的道德本心,相應于性體而言“心體”。如果說,“性體”主要體現的是儒家內圣學“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第一義,而比較是一個本體論概念的話,那么,“心體”則多顯其“踐仁以知天”的第二義,而有工夫論之意味。當然,這里本體與工夫須是合而為一,“即心體即性體”,儒家貫通心體、性體的內圣學成為了道德實踐和道德形上學的完美體現,也即達到了其“大而化之”的第三義的最高踐履境界。確認了內圣學“即心體即性體”的要旨之后,牟宗三以之為主要依據重組先秦儒典、判分宋明理學,進而實現了儒家道統論的重構。牟宗三將先秦五部儒學經典《論語》、《孟子》、《中庸》、《易傳》、《大學》判分為兩系:《論》、《孟》、《易》、《庸》為一系,它們蘊涵著“心體即性體”的深刻義理,是孔子生命智慧與成德之教的“一根而發”,代表著先秦儒學的本質;《大學》單列為一系,它相對于儒家的內圣成德之教而言是“另端別起”、“似是從外插進來”,不合乎孔子生命智慧的方向,并不能代表先秦儒學的本質。論定《大學》之義理歸趣及其地位是牟宗三重建道統的重要一環,以此兩系“模式”為參照,牟氏將宋明理學也析分成了“兩宗三系四組”:第一組為“周張程(顥)”,大致說來,他們學宗《論》、《孟》、《易》、《庸》,由《易》、《庸》返歸《論》、《孟》,接續了儒家“即心體即性體”的一本圓融義。這一組作為理學先驅,至此宋明儒學尚未出現分系。第二組是“程(頤)朱”,從程頤開始出現了宋明儒學的分系,原因在于程伊川別取《大學》系統涵攝《論》、《孟》、《易》、《庸》的路向。其后,朱熹一脈相承,進一步拓展深化了這一“別樣”的路向。第三組為“胡(宏)劉(宗周)”,牟宗三較為推崇這組,認為五峰直承明道的圓教模型,其后由劉蕺山繼之而成為宋明儒學之殿軍。第四組是“陸王”,他們深契孟學精神,陽明雖也言《大學》,但那是在孟學系統統攝下來立說的。以上是“三系四組”的提法,至于“兩宗”就是將以《論》、《孟》、《易》、《庸》為中心的宋明諸儒作為“大宗”或“正宗”,這包括上述第一、三、四組;而把《大學》作為中心的程朱看作是所謂的“別子為宗”。言至此,牟宗三的道統觀也就大體明確了:“道統之道”應該是“即心體即性體”的內圣成德之教,其傳承統緒大致是孔孟、明道、胡劉、陸王等[11](P39)。所謂重續道統就要返歸《論》、《孟》、《易》、《庸》,“接著宋明講”,光大儒家圓融心體性體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
其二,以“新道統”為理論根基,創構現代新儒學體系。既以悟得了儒家“即心體即性體”的道統法門,牟宗三就是以此為內核展開其新儒學架構的。牟宗三接續宋明之“胡劉”、“陸王”而言良知本體,又以“心體”和“性體”作為其不同的表現形式,“心體”、“性體”合為一體,皆是指“良知”本體。他說:
心體是就此良知明覺即是吾人之“本心”說,此本心就是“體”。性體是就此知體、心體就是吾人所以為道德的存在之超越的根據,亦即吾人所以能引生德行之“純亦不已”之超越的根據而說。……此性體是通過知體、心體而被了解的。故性體是客觀地說的,知體、心體是主觀地說的。此兩者是一。[12](P66)
牟宗三講“良知”本體,進而也肯定人有“智的直覺”,其所謂“智的直覺”即是“自由無限心”、“知體明覺”或者就是“良知”。在牟宗三看來,正因為人也有“智的直覺”而不只屬于上帝,人不僅能認識現象世界,而且能呈現本體世界,不僅能踐履形而下的道德,而且能通過道德實踐實現自我轉化,從而實現超凡入圣。因此,“良知”、“智的直覺”是成就“道德的形上學”關鍵,正因為人有“智的直覺”、有和合心體與性體的“良知”,道德本體一方面可由內向上翻、將生命存在接通終極價值本源;另一方面又可自上向下“流布”、從至上的道德實體落實到具體萬物[13](P209)。顯然,牟宗三言“良知”本體、肯定“智的直覺”證成的道德的形上學主要只是“返本”,而對于儒家這套內圣成德之教如何實現現代開展進行全面系統地論證方是牟學之“開新”所在,這主要表現在其“內圣開出新外王”、“三統并建”、“良知自我坎陷”說的提出牟宗三先生《生命的學問》、《歷史哲學》、《時代與感受》、《政道與治道》等論著中有詳細論說,茲不贅述。。當然,其義理精神無論多么高明、新穎,皆是本于儒家的內圣成德之教立說,皆是在此“內核”上萌發的新思。也就是說,牟宗三仍是“接著朱熹講”,先將儒家內圣外王之道歸結為內圣之道,以內圣統外王;又將內圣之道歸結為形上的本體,以內圣的良知本體開出新的外王。換言之,牟宗三先是識得孔子的生命智慧和內圣成德之教,實現以“即心體即性體”為核心觀念的道統之重構,進而開出其道德形上學,提出“內圣開出新外王”等一系列創造性構想,最終完成其新儒學體系構建的。
以牟宗三為主要代表的新儒家在回應西學挑戰、實現儒學現代轉化等方面無疑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當其把“接著宋明講”的新儒學“提到一個超越絕對的地步”時,儒家之道德價值理想就很難“落實在整個歷史社會總體間”(林安梧語)而作為一現實道德實踐的開啟。如比之于程朱理學,我們或許會更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其實,新儒學發展至牟宗三,有類于宋明理學發展至朱熹立“形上絕對”、“超越至上”之“極”,理學遂日成超然于世、清高脫俗的清談玄學。與此相類,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學也有此特點,故林安梧稱其為“高狂俊逸的哲學家”,“在牟先生的系統中,卻把人提到上帝的層次,再從上帝下返到人間,就好像已經究竟地證道了,再作為菩薩下凡人間,而開啟現代化的可能性。這樣的理解方式,我以為可以用蔡仁厚先生所說的‘高狂俊逸’這句話來形容,牟先生是一高狂俊逸的哲學家,果然!”[14](P295)誠然,牟先生此“高狂俊逸”之哲學,難免也有疏離“生活世界”,以心性修養代替道德實踐的偏執。
正是因為有識之儒洞見了這種偏執,牟宗三之后所謂“批判的新儒學”所由出,遂成“護教的新儒學”與“批判的新儒學”之分野。所謂“批判的新儒學”,就是指對新儒學持一“批判繼承、創造發展”的態度,在批判繼承之基礎上創構一面向“生活世界”、面向“歷史社會總體之道德實踐”的“后新儒學”,從而開啟一個“后新儒學的時代”。在此“后新儒學”的時代,我們真切期望儒學能走出書齋,走出講堂,“來到我們身邊,活在我們中間”,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令婦孺皆知,如春風化雨般教化國民[6](P108)。由是,我們不得不去重新檢視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的道統觀,去覓求合乎時代精神的“新道統”,并以此“新道統”為綱領實現當代儒學的重建。為此,重讀《論語》,返本歸源,追尋孔子真正的生命智慧或許是我們首要的理論工作。
三 仁禮合一——回歸孔子之
“道”,重構當代儒學
細讀《論語》,回到孔子的生活世界,真切體驗孔學精神,我們或許不難發現,孔子“道”之真義不過“仁禮和合”、“極高明而道中庸”二語,如此而已。就主要內涵來說,孔子之“道”要在“仁禮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論,孔子之“道”要在“極高明而道中庸”,也即是說,孔子的“仁禮合一”之“道”本身彰顯著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
如所周知,孔子的思想起點是禮,其創立儒學源于補禮、糾禮的致思路向。周文疲敝,禮樂不興,孔子欲興亡繼絕,接替斯文,就必要對“禮”有一番因時制宜、損益革新的處理。孔子之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家體貼出了“禮”背后那個更為重要的根本——“仁”,為古老的禮樂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當然,“述”禮“作”仁雖是孔子創立儒學的基本線索,但這并不意味著仁、禮簡單拼湊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學,言禮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禮,亦非也;仁禮和合,真儒之謂。因此,孔子雖把“仁”界定為禮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廢禮,一方面以仁釋禮,另一方面又強調以禮來外化仁、落實仁。仁、禮不偏廢,內外合為一;“仁”是內化的“禮”,“禮”是外化的“仁”,兩者和諧互動、感通為一。如果仁不外化為禮而落實于日用常行間就不能實現其價值,此其所謂“克己復禮為仁”;同樣,如果外在的禮失去了內在之仁作支撐,那么禮就流于形式、虛文,此其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5](P24),“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15](P185)。可見,仁與禮構成孔子之“道”的一體兩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禮”合乎主體內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謂“吃人的禮教”;“禮”之要則在于將主體內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實于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仁”的內在情感與“禮”的外在行為合而為一,方是道德實踐之整個過程的完成。
由此,“仁禮合一”或許才是孔子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義所在,這也便是儒門所傳的“道”,此“道”所內蘊的正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高舉遠瞻,又平實切近;既是終極關懷,又不離人倫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論語》中論“道”多與“仁”相連,比如: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15](P36)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15](P6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而后矣,不亦遠乎?”[15](P80)
上引數語明白地指出了道與仁不可分割的關系,據此,以孔子之“道”為仁(須是合著禮的“仁”)道也似無不可。這個仁道,一方面是孔子的終極托付之所在,“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清楚地看到道作為人的“終極關懷”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分明地揭示了“道不遠人”的重要特點,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5](P74),“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5](P123),此之謂也。當作為“禮之本”的內在的“仁”顯發為用而成外在的“禮”時,又可化民成俗,落實于穿衣吃飯、日用常行之間。小至視聽言動、舉手投足、婚喪嫁娶、送往迎來,大至行軍作戰、為政治國皆要合乎“禮”。《論語》有言如是: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5](P123)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15](P13)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15](P38)
當我們一言一行、待人接物都依禮而行時,自可“求仁得仁”、“從容中道”,此即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其實,這也正是芬格萊特所說的禮的“神奇魅力”、“魔術效應”。他說:“人們純熟地實踐人類社會各種角色所要求的禮儀行為,最終便可以從容中道,使人生煥發出神奇的魅力。圣人境界就是人性在不離凡俗世界的禮儀實踐中所透射出的神圣光輝。”[16](P1-13)概而言之,“即凡而圣”四字恰切地表述了孔子仁禮合一之“道”的深層意涵,凡俗與神圣相即不離正是其最為顯著的特點。[17]
孔子的以上思路在《中庸》中得到了更加淋漓的體現。人與道的關系是《中庸》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而其立論的基點,則是道非超然于人,“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并不是與人隔絕的存在,離開了人的為道過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對象,難于呈現其真切實在性。而所謂為道,則具體展開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極其至也,察乎天地。”道固然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它唯有在人的在世過程中才能揚棄其超越性,并向人敞開。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庸》強調“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即無過無不及,“庸者,常也”。極高明意味著走向普遍之道,道中庸則表明這一過程即完成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18](P1)。“極高明而道中庸”一語雖非出自孔子之口,卻最能表述孔子“道”之本旨,可以說,這也正是儒學之真精神所在。儒家傳統一方面能“與時偕行”、“日新又新”(變),另一方面又“萬變不離其宗”,終不改其“極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這或許正是其窮變通達、可大可久的依據。恰如顏炳罡先生所言:“‘極高明而道中庸’體現了儒家的精義、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有別僧、道、耶、回處。”[19]如果我們把孔子“道”之“兩面”——“禮”和“仁”作進一步分解,就會析出“道德規范(克己復禮)與道德自覺(為仁由己)”、“規范建設與情感建設”、“社會存有與心性修養”、“超越理想與世俗價值”、“禮法規范與社會正義”等多重分疏,在這樣的分界中,我們更可以覺察到孔子“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取法乎中,無過無不及,遂避免了游走兩極的偏執,成就了仁禮合一的原始儒學這一陽剛勁健、元氣淋漓、生生和諧、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統。
回顧孔學精神,我們不難明白,儒家的道統之“道”應是此“仁禮合一”之“道”,應是此“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在“后新儒學”的時代語境下我們正需要接續、光大此“道”,確立合乎時代精神的“新道統”,并以此為綱領展開當代儒學的重構。誠如梁濤先生所指出的:“學習宋儒的做法,重新出入西學(黑格爾、康德、海德格爾、羅爾斯等)數十載,然后返之于‘六經’,以新道統說(仁禮合一)為統領,以‘新四書’(《論語》、《禮記》、《孟子》、《荀子》)為基本經典,‘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以完成當代儒學的開新與重建。”[20](P62)
對此,林存光先生有不同看法,參見其《也談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梁濤儒家道統論的“國學觀”》(《學術界》,2010年第2期)一文。這里我們比較認同梁濤先生的觀點。當然,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可以再做深入討論。總之,當我們回歸孔子之“道”,以之為指引重建當代儒學時,一定要守住儒家的“根”,切實把握儒家之為儒家的真精神,致力于建構一種“心性修養與道德實踐”、“德性倫理與規范倫理”、“美德與規則”[21](P27-28)、“形上超越與生活日用”、“理想與現實”、“神圣與凡俗”……平衡互動、通為一體的新儒學。
[參 考 文 獻]
[1] 朱葉楠.“道統”在近代學術體系中的失落與重生[J].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65-94.
[2]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 許家星.朱子道統說新論——以孔顏“克復心法”說為中心[J].人文雜志,2013,(6):19-27.
[5] 朱子全書(第23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 鄭治文.文明對話與中國文化[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3.
[7] 朱子全書(第14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 朱子全書(第17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楊國榮.心學的理論走向與內在緊張[J].文史哲,1997,(4):10-18.
[10]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臺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1]楊海文.略論牟宗三的儒家道統觀[J].學術研究,1996,(6):39-42.
[12]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M].臺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3]程志華.中國近現代儒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4]林安梧.儒學革命——從“新儒學”到“后新儒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5]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6][美]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國翔,張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17]李勇強.孔子人性論思想的新探討以先秦簡帛文獻為線索[J].求索,2013,(1):69-71.
[18]楊國榮.作為哲學的儒學[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3-16(06).
[19]顏炳罡.民間儒學何以可能[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f9ee10102drhp.html,2011-07-23.
[20]梁濤.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統論的檢討與重構[J].學術月刊,2009,(2):54-62.
[21]劉余莉.美德與規則的統一——兼評儒家倫理是美德倫理的觀點[J].齊魯學刊,2005,(3):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