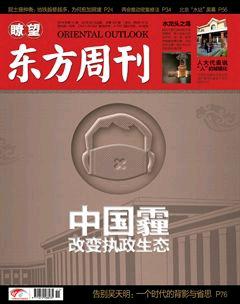以“權力清單”保障土地紅利公正分享
本刊評論員
具體落實“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地方政府,在強大的“財力”動機面前,會不會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慎重穩妥”等本意為控制改革風險的預防性約束條件上大做文章,甚至造成改革的停滯或倒退呢?
2014年是土地改革破題之年。
中央一號文件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做出了頂層部署,提出“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等措施。
這些措施都指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其本質是推進農村改革所產生的包括土地紅利在內的改革紅利更加公正合理地由農民等利益主體分享。
問題在于,在特定的時點上,其他條件不變時,農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很可能意味著其他部門不得不放棄或讓渡一部分權利。這些部門往往是手握實權,有責任對頂層設計實施分層對接的主體。它們的行為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頂層設計是否能順利執行。
例如,以往地方政府掌控著所有農地變為國有土地的渠道,通過壟斷這個市場賺取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才有充足的預算外財力落實包括“四萬億”刺激政策在內的投資目標。一旦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建設用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那么地方政府賺取土地差價的機會大大減少。這將極大限制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由度。
具體落實“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地方政府,在強大的“財力”動機面前,會不會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慎重穩妥”等本意為控制改革風險的預防性約束條件上大做文章,甚至造成改革的停滯或倒退呢?
對于這類可能直接影響到政策落實者利益的土地改革,如何讓農民在內的利益主體合理公平地分享土地紅利?關鍵在于以“權力清單”方式切實保障農民的財產性權利。
“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權力清單”制度,表示“確需設置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這為建構政府行政行為規范、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樹立了基本準則。
只有根據這一準則,把“規劃”與“管制”的負面清單擺出來,將政府在農村土地及農民財產權益等問題上的權力陽光化、制度化,農村改革的土壤中才能開出艷麗的創新之花。
除此之外,根本性的改革還在于,把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與其生產性的公共服務能力掛鉤,而非僅與其限制市場自由交易的能力相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要讓土地改革紅利充分涌流出來并實現公正合理的分配,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比如,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應予加快。無論是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還是土地承包權,要轉變為可用于轉讓、租賃、抵押、擔保的資產束,應當首先明確其權屬范圍及關系。在資本要素相對于土地要素更加緊缺的地方,更應該優先試點,并鼓勵土地承包權抵押貸款等有利于增加農村現代化經營能力的舉措。
與之相關的是,應加快推動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建立配套的抵押資產處置機制。
浙江、江蘇等地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暴露出來的問題,除了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民抵押物不足造成的融資困難外,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抵押資產的處理困難也讓銀行不愿意參與。處置抵押資產的市場基礎設施及規則的供給,是政府履行制度創新職能的應有之義。
總之,地方政府在農村土地改革紅利的釋放及分配中,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明確權力的界限和服務的職能,這是對其落實“市場起決定作用”要求及塑造現代化治理能力的鍛煉與考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