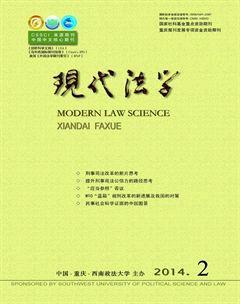再訪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情景化、類型化與限縮性適用

摘要:《侵權責任法》第59條出身于我國“醫藥不分家”的醫療體制,它過于注重醫療機構“銷售”醫療產品這一表征,而沒有對醫療服務區別于商品銷售的特性給予充分考慮。在醫藥尚未分離的時代,第59條具有存留價值。在醫療機構走向“醫藥分家”的進程中,與其狹隘地、機械地、不加區分地適用第59條從而將其演化為舊體制的“固化劑”,不如全面地、辯證地分析醫療機構的責任歸屬、使其細微地反映不同情形,將第59條演變為新體制產生和建立的“壓力閥”和“推動器”。可通過類型化處理方式,比如醫療機構的類型化、服務商品區分的類型化、產品缺陷的類型化、醫療產品的類型化和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責任類型化,來緩解第59條對醫療服務提供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醫療產品責任;《侵權責任法》;第59條
中圖分類號:DF526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2.16
在其他法域,醫療產品侵權責任一般屬于產品責任法的領地,它是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問題,在以醫療從業者為主體的醫療侵權法或醫療損害賠償法中很難尋到蹤影。醫療產品侵權責任出現在我國的醫療損害責任法(《侵權責任法》第7章)中,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政策考量,可謂別具一格。關于“產品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有專門一章,共計7條(第41條-第47條)。從法條上講,醫療產品(如藥品和醫療器械)完全可以適用其規定。但是,關于醫療產品侵權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在醫療損害責任一章中專門規定了第59條,稱之為“醫療產品責任”,成為一條頗具中國特色的條款。該條規定,“因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后,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追償。” 由此,醫療機構被拉入了醫療產品侵權損害賠償鎖鏈當中。對于第59條,作者曾將其置于美國法背景的比較之下[1]。本文則再訪第59條,旨在對其進行情景化、類型化處理和限縮適用。
本文從第59條產生的社會背景著手,探討了對它的解釋和適用,檢討其存留價值。其中貫穿著對域外法的觀察和比較。本文試圖向讀者傳遞的信息是:《侵權責任法》第59條脫胎于我國特有的醫療體制,尤其是舊有的市場主導型醫療體制,是一種偏向于患者救濟、輕醫療服務提供者利益、重“銷售”行為存在這一事實、輕醫療服務區別于商品銷售的特性之考慮的立法安排。它與國際做法并不一致。在《侵權責任法》的解釋適用時代,應尊重第59條產生的社會背景、利益權衡和政策考慮,緩解其對醫療服務提供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其成為舊體制的“固化劑”,努力使其成為當下政府主導型新醫療體制改革的“催化劑”。
一、第59條產生的社會背景我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肇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與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體制改革幾乎同步。受經濟體制改革思潮的影響,初始的醫療改革并沒有充分認識到醫療行業不同于其它產業的特殊性質,而是將諸多企業改革的理念和措施引入醫院管理領域,充滿著較多的市場經濟思維和操作模式[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寄希望于市場調控,政府也從改革開放之前的大包大攬的管理方式中退出,造成了醫療服務提供上政府投入、干預和責任承擔的缺位。醫院從單純強調社會效益,不重視經濟效益,轉變為在強調社會效益的同時,重視經濟效益。公立醫院的趨利性漸濃,公益性淡化。
市場化醫改模式造成的局面是,由于政府對公立醫院投入水平過低,醫院以創收來實現自我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大,曾經依靠國家財政補助的公立醫療機構轉變為商業利潤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醫療機構補償機制扭曲,醫療機構形成了“以醫療服務經營性收入補償為主,以公共財政投入補償為輔”的復合型格局,公共財政投入占醫療機構總收入比例不到10%[3]。醫療機構受市場利益驅動, 供方誘導需求的現象嚴重,過度檢查、“大處方”泛濫。醫療機構的業務與藥品收益影響到醫務人員的收入和醫院的發展,使其成為主要的利益驅動力。由此形成的過度供給不僅浪費了大量寶貴的醫療資源,而且影響到了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改革開放以來醫改最大的損失就是醫療行業發展方向的迷失和對宗旨靈魂的破壞以及醫患關系緊張[4] 。
現代法學趙西巨:再訪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情景化、類型化與限縮性適用 2005年,風向變動。市場化并非醫改的方向、醫改應以政府為主導、應堅持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共品屬性的聲音開始強大起來并占據了主導地位。2006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了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責任。2007年,衛生部開始實行以政府為主導、以省為單位的網上藥品集中采購辦法。2008年“新醫改方案”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2009年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表達了“推進醫藥分開,積極探索多種有效方式逐步改革以藥補醫機制”的決心。2012年國務院印發的《“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承諾要“落實政府辦醫責任”,“扭轉公立醫院逐利行為”,并且再次重申,“以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關鍵環節,推進醫藥分開,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將公立醫院補償由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醫院的藥品和高值醫用耗材實行集中采購。” 政府主導型醫改進入實質性階段。
目前,我國正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以資源配置和成本控制為核心內容”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正是意識到了有限的醫療資源供給與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之間的矛盾,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將資源的有效利用、優化配置和成本控制列為核心的追求目標。這表現在諸多方面,比如,設置基本的醫療保險藥品目錄、診療項目、醫療服務設施標準、鼓勵優先使用基本藥物和適宜技術、推行疾病臨床路徑、限制使用大型醫療設備檢查、限制使用高價藥品與新增診療項目和高費用新技術等。
我國的《侵權責任法》正是醞釀產生于市場化醫改模式向政府主導型醫改模式轉型之際。新的政府主導型醫改模式推出之后,舊有的市場化操作模式仍存在慣性。我國的《侵權責任法》“醫療損害責任”一章中的規定難免烙有市場化醫改模式的印記。比如,其第63條關于過度醫療之禁止顯然是回應了新醫改之前“按服務收費(fee-for-service)”體制下由不正當經濟利益正面驅動所導致的醫療資源的過度消費,而沒有注意到資源有限和成本控制型(cost-containment)醫療體制(如我國正在建立的基本社會醫療保險體制)下外在經濟壓力(如總額控制、優先考慮資源節約型醫療方案)負面驅動所引發的“醫療節制、不足或短缺”現象。另一例證便是本文所關注的第59條。第59條所反映的社會背景是:在醫療行業市場化運作模式之下,政府沒有完全承擔起醫療服務提供上的責任,因政府投入不足,醫療機構被迫、被容忍,甚至被鼓勵轉向市場通過藥品買賣來彌補政府財力支持的不足。它很難適用于醫療機構已脫身藥品買賣鏈條和事務,其功能已凈化為單純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新醫療體制設想之下。
通常認為,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起假藥致害事件——“齊二藥”案件2006年4月,位于廣州市天河區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中山三院”)發現該院先后出現多例急性腎衰竭癥狀患者,而這些患者均使用了齊齊哈爾第二制藥有限公司(“齊二藥”)生產的亮菌甲素注射劑。2006年7月19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認定這些假藥事件是一起因藥品生產企業“齊二藥”的采購和質量檢驗人員嚴重違規操作、使用假冒藥用輔料制成假藥投放市場并致人死亡的惡性案件。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通報,齊二藥違反有關規定,將“二甘醇”冒充輔料“丙二醇”用于“亮菌甲素注射液”的生產,而二甘醇在病人體內氧化成草酸,導致腎功能急性衰竭。僅中山三院使用的亮菌甲素注射劑已造成14人死亡,其中11名受害人將中山三院、銷售商“金蘅源”、“省醫保”、生產商“齊二藥”告上法庭,索賠總額達2000萬元左右。2008年7月15日,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判決賠償金額為350萬元,四被告承擔連帶責任。2008年12月10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維持原判的終審結果。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在其判決書中認定藥品“亮菌甲素注射液”為假藥,構成《產品質量法》上的缺陷產品。對《侵權責任法》第59條的出臺和行文有重要影響[5]。在該案中,兩審法院均據被告中山三院有償并加價向患者提供涉案藥品這一事實而認定其構成“銷售者”,從而與其他被告承擔連帶責任。比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中山三院屬于涉案假藥的銷售者。在目前我國‘以藥補醫、‘以藥養醫的機制下,醫療機構一方面通過藥品加價的方式獲取大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卻不欲作為藥品銷售者以劣藥、假藥等缺陷產品對患者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顯然于理不合,亦與權利與義務相統一之法律原則相悖。”法院同時認為,中山三院加價提供藥品的行為“與藥品經營企業通過賣藥獲得收入的銷售行為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并無本質區別”。由此可見,之所以讓醫療機構承擔產品損害賠償責任,我國司法看重的是醫療機構在產品銷售鏈條中的商業化身份(作為藥品銷售者的身份),并沒有對其提供醫療服務的特殊性質給予過多關注。對受害患者的救濟之考慮壓倒了醫療機構利益保護之需要,對“社會效果”的追逐壓倒了對應有法律規則的尊重。
二、第59條的解釋論關于醫療產品責任,我國有幾位學者曾提出立法建議。比如,由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科研項目提出:“在醫療活動中,因醫療機構使用的藥品、血液、血液制品或醫療設備的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適用關于產品侵權責任的規定。”同時規定,醫療機構、供血單位或者血液制品生產者能夠證明自己已盡到最大的注意義務仍然無法避損害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應當依據實際情況給予適當補償[6]。楊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建議道:“藥品、醫療設備、醫療器械及其他醫療用品存在缺陷,造成患者損害的,適用本法關于產品侵權責任的規定。”“用于植入或輸入的人體組織、器官存在缺陷,造成患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醫療機構或者供應單位能夠證明已采取必要檢驗技術并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應當依據實際情況給予適當補償。”[7]此類立法建議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將醫療產品責任視為產品責任的一部分,在行文上將醫療產品缺陷責任法與產品責任法聯結起來,沒有特別指明醫療機構為銷售者從而承擔醫療產品責任,而且特別指明在責任承擔上醫療機構只承擔過錯責任。此類建議具有較強的彈性、包容性和普適性。它既不妨礙在醫療機構兼具醫療服務提供者和醫療產品銷售者身份的體制下讓其以銷售者的身份去承擔產品缺陷責任(從而實現目前《侵權責任法》第59條的效果),也包容了醫療機構在擺脫掉醫療產品銷售者身份的情況下不再以銷售者的身份承擔醫療產品責任的可能。在不同醫療體制下醫療機構“銷售者”身份的有無決定了它是否承擔產品責任法中的“銷售者”責任。相比之下,《侵權責任法》第59條關于醫療產品責任的規定過于僵硬和直白。它直接將醫療機構置于醫療產品“銷售者”的責任之下。它很難適用于醫療機構不再是“銷售者”的情形。在后者情形出現時,它的有效性值得懷疑,可能遭受被廢棄的命運。
第59條簡單套用了產品責任法中生產者與銷售者的責任分配套路。參見: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五章“產品責任”部分第41條、第42條和第43條。比如,《侵權責任法》“產品責任”章第43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者請求賠償。產品缺陷由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第59條所做的工作僅是將其中的“銷售者”替換為“醫療機構”。這一機械替換導致的后果是,連真正的商業領域的銷售者(如醫療產品的批發商和零售商)都給替換掉了。對真正銷售商的追責,第59條已無法適用,不得不又需要回歸至第43條加以適用。這造成了第59條和第43條的并立。
立法者通過第59條所欲建立的效果尚不清晰。是將醫療機構置于真實的產品責任(無過錯責任)之下,還是僅提供一個方便患者救濟的機制?從歸責原則的歸類上看,第59條所展現的醫療產品侵權形態本身會讓人直觀地認為它對醫療機構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但是,細究一下,對于醫療機構,它適用的仍是過錯責任原則。就醫療產品來說,此條肯定的只是“生產者”對有缺陷的醫療產品的無過錯責任。從法條上看,醫療機構對有缺陷的醫療產品所造成的損害承擔的仍是過錯責任,而不是無過錯責任。血液提供機構和醫療機構對“不合格的血液”所造成的損害承擔的也均是過錯責任。而且,第59條只規定了醫療機構賠償后有權向負有責任的醫療產品生產者追償,而沒有對應地規定醫療產品生產者可以向有過錯的醫療機構追償。這種單向追償權的規定似乎向人們昭示醫療機構不同于通常的產品銷售者[8],而只是提供便利之人。
盡管第59條沒有就醫療機構適用無過錯責任,但這仍不能讓人釋然。該條所規定的醫療機構對有缺陷的醫療產品所造成的損害“最終”只承擔過錯責任(即“不真正”連帶責任)僅是就生產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內部關系而言的。就外部關系上而言,即就生產者和醫療機構與第三人(醫療產品使用者)的關系而言,醫療產品使用者(患者)可以選擇“生產者”或“醫療機構”作為賠償主體,醫療機構不能以其沒有過錯為免責事由。即使是患者一方只起訴醫療產品生產者或者醫療機構,人民法院也可能依被告的申請或必要時依職權,追加醫療機構或者醫療產品生產者為案件的當事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4條第2款。“生產者”和“醫療機構”被認為是承擔“連帶”責任。“醫療機構”被拉入了缺陷醫療產品損害賠償鏈條之中,且要承擔生產者賠償不能的風險。當醫療產品侵權導致損害時,醫療機構不再是無干系的一方,它極有可能被纏入訴訟,面臨著應訴成本、辯明自身“清白”的成本和生產者賠償不能時的賠償成本的支出。可以講,在醫療機構身上存在著切實的承擔產品責任和無過錯責任的可能和風險。這使得第59條所產生的后果變得凝重起來。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承繼了“齊二藥”案法院將“醫療機構”視為醫療產品“銷售者”的觀念。此種觀念之所以在我國存在巨大市場、沒有太多抵抗(包括來自醫療機構的),是因為我國舊有的、現在仍持續存在的醫療體制造成的。它回應了我國目前醫療機構“醫藥不分家”、醫療機構加價銷售醫療產品的現狀,盡管這種狀況是不正常的、需要改革的和正在改革的。可以說,它是我國現有醫療體制的產物,具有現實基礎。但是,比較來看,它難以堪稱為一種良好的法律設計。
三、域外法的觀察就我國法意義上的“銷售者”責任而言,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替代的是34年前的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它包括四章。其中,第一章規定了產品缺陷責任的規則。第一章又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可以一般性地適用于所有產品,第二個主題特別規定了適用于一些特殊產品(如藥品和食品)的規則。第二章規定了并非建立在產品銷售時的產品缺陷之上的產品損害責任,包括違反售后警示義務和違反售后召回義務所導致的損害責任。第四章規定的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些規則,如產品缺陷與損害間的因果關系、抗辯事由。將“從事商業性銷售或以其它方式分銷者(one who sells or otherwise distributes)”置于產品缺陷所導致的損害賠償責任之下。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商業性銷售者或分銷者”包括“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nonmanufacturing sellers or distributors)”(比如批發商和零售商),它是一個與“生產商(manufacturer)”相對應的概念。“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對產品缺陷也要承擔責任,即使他們自己并沒有使得產品產生缺陷,不管他們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風險的存在,也不管他們是否處于避免缺陷發生的位置。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o.一旦證明,在產品銷售之時或之前,處于銷售鏈條中的前手,應該能夠提供合理的替代設計或合理的警示,并且這些合理的替代設計或合理的警示能夠減少原告的損害,該產品的“非生產性的銷售者”就應承擔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責任,而不管他們是否行使了合理的注意。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o.這些都說明了嚴格責任的存在。
但是,對于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Prescription Drugs and Medical Devices),即那些只有經過健康服務提供者的處方才可合法銷售或以其它方式分發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情形有所不同。銷售或其它方式分發具有缺陷的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生產商(manufacturer)是缺陷所致損害責任的承擔主體。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a).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零售商和其它分發者(retail seller or other distributor)只有在存在以下兩種情形之一時才承擔產品缺陷責任:(1)在產品銷售或分售之時,產品具有制造缺陷;或者(2)在產品銷售或分售之時或之前,零售商和其它分發者因未行使合理的注意(fails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而對人身導致損害。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e).也就是說,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零售商和其它分銷者,只有在存在“過失”(即違反合理注意義務)時,才對此類產品的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承擔責任。之所以在此領域對其責任加以限制,是因為應允許他們信賴產品制造者的特殊專業知識、開方及治療的醫務人員以及政府的管理機構,且要考慮到病人方便地買到價格合理的處方類藥品之需要。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Comment h.這不同于一般產品的零售商和其它分銷者所承擔的產品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責任。
但是,美國許多州出現了一些立法,試圖全面免除“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的嚴格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將“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置入產品責任訴訟中會浪費法律成本和資源。但是,為了確保原告受害人的賠償不會因此而落空,這些立法一般規定只有在以下條件滿足時才免除“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的嚴格責任:(1)生產者處于原告住所地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內;(2)生產者沒有破產,也太不可能破產。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 Comment e.即要考慮到原告救濟得以實現的需要。此種立法存在二個問題。一是,如果在起訴時免除了“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的嚴格責任,原告可能會承擔在起訴時到判決時之間生產者破產的風險,導致原告的損害無法獲得賠償。對于此,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建議針對“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規定訴訟時效,以便在必要時將其拉入訴訟。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 Comment e.二是,如果產品的缺陷是由“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或分銷者”制造的,其應對產品的制造缺陷承擔產品嚴格責任,而不管其是否行使了合理的注意。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 Comment e.在學術界,也有學者主張,只要產品缺陷的制造者或者其保險者是可及的和能承擔判決結果的,處于銷售鏈條中的、沒有導致缺陷的非生產商不應承擔產品缺陷責任,也不應因成為訴訟一方而耗費大量的費用[9]。美國法中這種將“非生產性的銷售者”有條件地移出嚴格責任之射程的動向值得關注。
不管怎么樣,在美國法中,在醫療這個特殊領域,提供醫療服務時同時提供醫療產品的醫院和醫生并不被認為是產品的銷售者(sellers)[10-13],從而遠離了產品缺陷責任和嚴格責任。在美國法中,在是否適用嚴格責任上,有一種服務與商品二分(the sale-service dichotomy)的理論。在醫療服務過程中的醫療產品使用在整體上被定性為“服務”的一附屬部分,而非產品“銷售”,從而適用以過錯責任為原則的醫療損害賠償法,而不是以無過錯責任或嚴格責任為基礎的產品責任法。由于是基于過錯責任,在醫療服務當中,醫生行使的僅僅是“合理的注意和技能”,而不是就結果承擔擔保責任。
應該看到,在美國,對于讓醫療行業和醫療從業者免于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這一點,有些學者也頗有微詞。產生這些異議的主要原因是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商業化動向,他們看到了醫院從事商品銷售并獲得巨大贏利這一情況,并認為對醫療行業的豁免讓原告患者喪失了一個有利的救濟渠道[14]。 在早期有些法院也認定醫院的血液提供和產品使用是一種銷售行為[15-16],并得到了當時學者的支持。有學者認為將服務主導型中的商品交易不定性為一種銷售是法律上的虛構,它剝奪了對消費者的保護(Comment. Sale of Goods in Service-Predominated Transactions[J]. Fordham L. Rev., 1968, 37: 115-122)。但是,在美國,將醫療機構和醫療從業者排除在產品責任和嚴格責任之外是立法和司法的主流。許多法域不愿將產品嚴格責任賦加在醫院和醫生身上,比如加利福尼亞州[17]、紐約州[18]、賓夕法尼亞州[19]、新罕布什爾州[20]、密蘇里州[21]、佛羅里達州[22]、華盛頓州[23]、新澤西州[24]等。即使醫院在手術使用醫療器械時對醫療器械額外加價了,法院也不愿將醫院定性為醫療器械的銷售者,而是將其視為醫療服務的提供者[10]。再進一步講,即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定性為“銷售者”,但是,基于“政策(policy)”原因,法院也不會將醫療服務提供者置于產品嚴格責任之下[19] 。這些“政策”原因主要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獨特性質(peculiar characteristics),或者說醫療服務與商品銷售的區別有關[19]。有法官甚至言道,即使醫院在提供與某種醫療器械有關的服務中沒有使用醫療技能或知識,仍然可以講醫院是在盡其所能為患者的治療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也不能說其活動完全與醫療服務無關[10]。
在英國法中,產品缺陷所導致損害的責任主體是產品的“生產者或制造者(producer)”。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 (Eng), Section 2 (2). 產品的“提供者(supplier)”可能承擔產品責任,條件是:(1)遭受損害的人要求提供者指明產品的生產者(不管是否仍存在);(2)這種要求是在損害發生后的合理時間內提出的,而且要求遭受損害的人辨明生產者是不(合理地)符合實際的;(3)產品提供者未能在收到請求的合理時間內指明向其提供產品的人。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 (Eng), Section 2 (3).也就是說,產品的提供者是可以通過指明向其提供產品的人(比如生產者)來避免產品責任的。產品的“提供者”指的是銷售產品的人,或者,為履行法定義務而提供產品的人。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 (Eng), Section 46.就藥品或醫療器械來說,在英國的全民健康服務(NHS)體系當中,銷售很少發生,醫療服務提供者不會是“銷售”產品的人。但是,藥師、醫生、醫療服務提供者可能因為在全民健康服務體系中“提供”了醫療產品而成為產品的“提供者”而承擔產品責任。但是,這種責任可以通過指明產品提供鏈條中的前手(如生產者)而簡單地免除的,而且醫療服務提供者指明生產者的義務也并不是無條件的。
在英國法中,對于全民健康服務(NHS)體系之外的私人醫療來說,因醫療產品遭受損害的患者多了一條救濟,即他可以以違反合同為由起訴醫生。如果醫生提供的只是醫療服務,醫生只需在服務中行使“合理的注意和技能”,除非醫生對結果有過保證。如果醫生在提供醫療服務中使用了醫療產品(即出現了產品與服務的混合形態),醫生在診斷、提供醫療建議和治療的職業角色定位通常被認為是以交易為主導特征,而不是將其視為銷售合同[25]。這也避免了醫療服務提供者去承擔適用于商業領域的嚴格性質的責任。
在歐洲大陸,醫療侵權多是聚焦于醫生的診療和信息告知領域,很難尋到醫療服務提供者承擔醫療產品責任的影子[26]。在荷蘭法中,盡管有學者主張應由醫療服務提供者(尤其是醫院)承擔醫療產品缺陷責任、擔保所使用物品的質量,但這不是立法者的聲音[26] 185-186。 荷蘭《民法典》要求制造商對其產品缺陷所致傷害承擔嚴格責任。針對醫生或醫院而提起的產品缺陷責任訴訟可以被駁回,因為讓制造者承擔責任更合理[26] 185-186 。
四、對第59條的檢討我國《侵權責任法》出臺之后,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學者發出了一些對第59條進行反思和質疑的聲音[1,5,27]。第59條可能使過多的醫院陷入訴累,加劇醫患矛盾,而且醫療機構的追償權有時難以實現[5]。從我國司法和后來的立法反應來觀察,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將醫療機構拉入醫療產品責任法的主要現實基礎是醫療機構向患者“加價銷售”醫療產品,兼具了“銷售者”身份。但是,它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僅僅是一個非關鍵的方面。 它沒有意識到“(醫療)服務” 與“商品/產品銷售”之不同,沒有很好地區分產品責任法和醫療損害賠償法,沒有精心地權衡對醫療機構課以無過錯責任的利弊得失,也沒有正視我國“醫藥分家”的醫療改革趨向。
首先,從發展方向上來看,第59條與我國的醫療改革動向和實踐并不合拍。它是舊有的市場主導型醫療體制的反映。自2005年開始,我國已經進入了構建“政府主導型、以資源配置和成本控制為核心內容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時代。盡管這種改革的成功尚需時日,也不乏阻力和沖突,但是我國目前的注重政府主導、全民覆蓋、資源節約的新醫療改革符合國際上追求全民性醫療保障、注重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的醫改大趨勢[28],方向是正確的,也是不可逆轉的,應得到促進和被推動。
其次,從操作層面來看,作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我國已經全面實行“以政府為主導、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的網上藥品集中采購制度”。根據2009年衛生部、食品藥品監管局、中醫藥局等六部門聯合印發的《進一步規范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意見》和關于《進一步規范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意見》有關問題的說明,由政府搭建的非營利性采購交易平臺不僅適用于包括國家基本藥物在內的各種藥品之采購,而且要成為高值醫用耗材、省級管理的乙類大型醫用設備之采購平臺。這種集中采購采取公開招標、網上競價、專業分類、專家評議(考察安全性、療效、副作用、企業規模、品牌知名度、企業服務等指標)、集中議價、直接掛網(包括直接執行政府定價)的方法,形成統一價格,即醫藥企業向省(區、市)內所有參加藥品集中采購醫療機構的供應價格。縣及縣以上人民政府、國有企業(含國有控股企業)等所屬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必須全部參加藥品集中采購,而且鼓勵其他醫療機構參加藥品集中采購活動。除非有特殊情況且經過審批,各醫療機構只能購買中標(入圍)藥品,嚴禁標外采購、違價采購或從非規定渠道采購。藥品集中采購制度大大減少了醫療機構在藥品選擇、推薦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采用何種藥品和哪個廠家的藥品是政府主導的集體智慧的結果。醫療機構很難與通常和完全意義上的“購售商”同日而語。
再次,從宏觀角度看,在一個從藥品的研發、生產、上市都存在著政府嚴格監管,即制定并要求相關主體遵從藥物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L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和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GSP),藥品質量的把關者應是藥品研發、生產、銷售企業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醫療機構不應成為政府監管薄弱、企業自律不足和道德淪喪的“替罪羊”。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有理由期望進入市場的藥品具有合理的安全性。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對藥品的審查義務僅限于外觀審查,而不能苛求其對藥品的內在質量進行深入檢驗和解剖。即使藥品存在缺陷,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可能開啟或造成這種不合理危險,醫療機構也無法減少和消滅這種不合理危險。因此,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應承擔此種可能的不合理危險所帶來的法律后果。
我國的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已經走入實質性和實踐層面。隨著我國以“醫藥分家”為前進方向的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在醫療機構中藥品加價銷售這一做法會成為歷史,醫療機構充當藥品“銷售者”的角色將逐漸弱化和淡去,醫療服務機構的功能將逐漸由雙重趨于單一。產品責任法與醫療服務損害賠償法之間的界限將逐漸明朗和清晰。如果沒有了醫療機構“銷售”產品這一層現實基礎,患者為消費者從而適用產品質量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法律的論辯將相當脆弱。如果我國不動搖“醫藥分家”的改革方向,堅持醫療機構“去商業化”的努力,有理由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關于醫療產品責任的規則注定是短命的。
但是,需是指出的是,我國目前司法和立法將醫療機構置于產品缺陷責任之中主要是由醫療機構存在藥品銷售行為這一事實或直觀原因所驅動。其實,正如美國法所展現的,將醫療服務提供者剝離出醫療產品缺陷責任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對醫療機構醫療產品使用行為的定性和醫療服務的特性。也就是說,不管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產品使用行為是不是“銷售”行為,醫療服務不同于商品銷售的基本特性足以將醫療服務提供者擋在產品嚴格責任之外。我國法過度關注醫療機構“銷售”醫療產品這一表面事實,而忽略了對醫療服務之特性的考慮的狀況值得檢討。
五、第59條的存續價值和適用筆者注意到,我國“醫藥分家”的政策早在2000年就以公文的形式面世了。當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等部門《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0]16號),就提出了實行“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的目標。為了切斷醫療機構和藥品營銷之間的直接經濟利益聯系,當時還提出要在逐步規范財政補助方式和調整醫療服務價格的基礎上,把醫院的門診藥房改為藥品零售企業,獨立核算。但是,十多年過去了,早已成熟的國際經驗——“醫藥分離”做法在我國仍在摸索中前行,許多醫院仍沉浸在通過“賣藥”補貼家用的狀態當中。由此可見舊體制的頑固性、強大的慣性和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醫藥分家”牽動著政府、醫院和醫療保障部門的利益調整和重組。我國真正向國際做法看齊尚需時日。
如果不真正實現“醫藥分家”從而徹底讓醫療服務提供者從醫療產品銷售中脫身,至少從外觀上講,醫療服務提供者就很難擺脫承擔醫療產品責任的干系,《侵權責任法》第59條就存在著適用的借口、理由和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既讓法律的既有規定(第59條)得以適用,又忠實于不從事產品“銷售”就不應承擔產品責任這樣一條底線,將第59條對醫療機構的負面影響最小化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適用第59條時,有必要考慮到醫療服務的特殊性質和醫療機構在現有醫療體制中的兩難處境,在具體案件中做具體分析具體對待,不過分加重醫療機構的責任承擔。與此同時,有必要發揮第59條的威懾力和正面規范功能,使其成為醫療機構“醫藥分家”改革乃至國家整個醫療體制改革的“推動器”,而不是舊體制的“固化劑”。
首先,在患者使用醫療產品過程中,由于醫療產品的使用是醫療服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患者與醫療機構距離最近,且關系最直接,醫療機構當然處在了患者表達訴求和伸張正義的最前沿。但是,應當認識到,醫療產品的質量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不僅包括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積極參與(如不良反應報告制度),而且包括政府部門上市前和上市后的強有力的監管,當然更離不開醫療產品研發部門和生產企業的硬實力和責任心。我國應注重每個環節的建設,包括政府層面的環節在內,并要求其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不是通過簡單地將醫療機構置于醫療產品責任之下給本身已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醫患關系再添一把“助燃劑”。與此同時,通過監管,應強化醫療產品責任承擔主體——生產商和銷售商——的生產經營能力和責任承擔能力,以避免醫療機構在承擔賠償責任后追償權的落空。
其次,在解釋第59條時,立法者和司法者應釋放并強化醫療機構在醫療產品責任中只承擔過錯責任這樣一條信息。醫療產品責任的首要的而且主要的承擔主體是醫療產品生產商。醫療機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應是提供生產商信息、辨明生產商和代為賠償的作用。應降低患者和公眾在醫療產品責任歸屬和承擔上對醫療機構的過高期望,降低醫療機構在其中承擔的過重負擔。相較于美國法中的讓醫療服務提供者免于醫療產品責任和英國法中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只有條件地承擔“指明產品生產者”責任,不分情況地讓醫療機構與生產商承擔連帶責任,對醫療機構來說實屬負擔過重。
再次,在適用第59條時,應通過區別情形和類型化等技術手段,細膩地反映具體案情,將第59條適用于較為適宜的情境,盡量減少第59條對醫療服務提供的負面影響,讓其服務于并促進新醫療改革大局。在這方面,應考慮到醫療機構的類型、商品銷售在醫療機構中提供服務的必要程度、產品缺陷的類型、醫療產品的類型和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責任類型。醫療機構的類型不同、商品銷售在醫療機構中提供服務的必要程度不同,適用第59條的可能性是不同的。醫療產品“缺陷”責任和與醫療產品有關的“醫療損害責任”也是不同的。產品缺陷的種類不同,醫療產品的種類不同,缺陷判定的標準和所適用的歸責原則也是不同的,所傳遞的信息也是不同的。關于在醫療產品責任領域醫療機構的類型化和商品服務區分的類型化處理,我國學者已有涉及。有同仁主張在適用第59條時區分營利性醫療機構與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并考慮醫療產品與醫療服務聯系的緊密程度。(參見 楊立新, 岳業鵬. 醫療產品損害責任的法律適用規則及缺陷克服:“齊二藥”案的再思考及《侵權責任法》第59條的解釋論[J]. 政治與法律, 2012 (9): 120-121)本文在此略述。關于產品缺陷的類型化、醫療產品的類型化和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責任的類型化,我國鮮有系統的、詳細的論述,本文將多著些筆墨。
(一)醫療機構的類型化
在適用第59條時區分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反映了我國的這樣一個現實:我國的公立醫院以非營利為運營宗旨、是我國新醫療體制改革(包括“落實政府辦醫責任”、 “扭轉逐利行為”、 “推進醫藥分開,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的目標群體,而私立醫院營利性和市場化較強,尚未納入到以倡導公益性為主調的政府主導型醫療體制改革中來。但筆者認為,如果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均未實現醫藥分家和醫療產品零加價政策,僅從姓“公”姓“私”的名分上或從是否承載著基本醫療保障之重任上來區別對待公、私立醫院而適用第59條,說服力并不強,盡管從公共政策上考慮法律似乎更不應將肩負重任的公立醫院置于產品責任風險之下。但是,如果公立醫院通過新一輪醫療改革已擺脫了產品銷售者身份,而私立醫院仍以銷售醫療產品作為其獲取利潤的主要手段或手段之一,在適用第59條對二者進行區別對待的理由則較為充分。
不過,從長遠考慮,筆者對此處的公、私立醫院的區分提出點保留。盡管我國目前的醫療體制改革從政策文件表達上看只限于公立醫院,但應該看到,“醫藥分家”這一要求具有明顯的正面價值和普適性,它應是整個衛生事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它應波及到所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包括私立醫院。其實,基于醫療資源的有限性,私立醫院的發展會強奪有限的醫療資源,并加強貧富差距和不公平。如若想建立一個真正由政府主導的、以資源配置和成本控制為核心內容、以實現醫療服務提供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為目標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大力發展針對大眾的公立醫療服務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而不是針對富人的私立醫療服務和商業醫療保險才應是發展方向。令人警覺的是,我國目前已經出現了在醫療服務的提供方面窮人利用不足(通過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富人過度利用(通過購買和享受各種補充醫療和商業醫療保險)的沖突和矛盾[3]。這影響了醫療服務提供的公平性。因此,在我國的新醫療體制改革中,應注重樹立公立醫療服務的主導,甚至是絕對性主導地位,并通過第59條的適用使私立醫院加入到“醫藥分家”的行列中來。
就公立醫院來說,在適用第59條時,還應區分已經取消藥品加價、徹底實現“醫藥分家”的公立醫院和尚未擺脫“醫藥不分”、仍以“銷售者”身份面世的公立醫院。我國的“醫藥分家”改革是在試點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開的。公立醫院也不是千人一面,在法律負擔和待遇承受上也不應是鐵板一塊。就已實現“醫藥分家”的公立醫院來說,有必要讓其體驗到第59條得以免除適用的輕松和益處,從而堅定其對新體制的信心;而對那些尚未實現“醫藥分家”的公立醫院來講,也應讓其感受到因適用第59條而纏入醫療產品責任訴訟之累,從而產生“醫藥分家”的壓力和動力。
(二)商品、服務區分的類型化
在適用第59條時考慮商品銷售在醫療服務提供中的比重和必要程度有利于防止醫療機構濫用服務——商品區分理論,防止醫療機構以提供醫療服務為名行銷售醫療產品之實。人們有理由認為,醫療機構的醫療產品銷售在服務提供和商品銷售的復合行為中的比重越大,將醫療機構視為銷售者從而適用第59條的必要性越大,因為醫療機構有可能借助醫療服務大行醫療產品銷售之道。但是,商品銷售在醫療服務提供中的比重只能是考慮適用第59條的因素之一,不應是決定性因素。相較之下,司法者更應考慮醫療產品提供(銷售)在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中的必要性。如果產品提供是醫療服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有必要將醫療機構的行為定性為服務,從而排除第59條的適用。如果醫療產品的提供(銷售)并非醫療服務所必需,或者說醫療機構是在提供醫療服務名義下銷售醫療產品,那么醫療機構的行為便可定性為產品“銷售”行為,可以適用第59條。此種區分有利于促使醫療機構將中心放在醫療服務的提供上,克服“醫療”活動“服務于產品銷售”的趨向。
(三)產品缺陷的類型化
產品存在“缺陷”是產品責任,包括醫療產品責任的一個核心構成要件和責任追究的起始點。關于產品“缺陷”,我國《侵權責任法》并沒有對其給出定義。不過,我國《產品質量法》(2000年)第46條提供了“缺陷”的定義。它系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 具體到醫療器械缺陷,系指醫療器械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存在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合理的風險。參見《醫療器械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第4條。判定產品缺陷的主導性標準是“不合理的危險”標準。產品“缺陷”通常分為制造缺陷/生產缺陷、設計缺陷和警示/指示缺陷。我國學術界對于上述分類已基本認可,但是我國立法未加以規定,我國產品缺陷的判定標準是一個單一的標準,沒有區分產品缺陷的不同種類和產品的不同種類,沒有靈敏地反映不同種類缺陷和不同種類產品的特點和需求,是一種單一化、一刀切的處理方式,需要改進和精細化。在此方面,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很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一改原先的一體化和一元化處理方式原有的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實質上針對的只是制造缺陷,它不太適合于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領域。,將產品缺陷做了具體分類,并根據不同種類的缺陷給出了不同的認定標準。美國法對缺陷的分類和定義似乎對我國法學理論有重大借鑒價值比如,有學者在介紹產品缺陷的分類時,援引了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中的分類和定義。(參見:高圣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立法爭點、立法例及經典案例[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499-500.),有引鑒的必要。
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2條將產品缺陷分為制造缺陷(manufacturing defect)、設計缺陷(defective in design)和因為指示或警示不充分而產生的缺陷(defective because of inadequate instructions or warnings)。其中,“制造缺陷”是指“產品偏離了設計意圖,即使在該產品的制備和營銷過程中已經行使了所有可能的注意。”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a). 而如果一種產品所產生的可預見的損害風險(foreseeable risks of harm)可以通過一種合理的替代設計(a 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得以減少或避免,而這種替代設計的缺失使得產品不具有合理安全性(not reasonably safe)時,那么該產品則存在“設計缺陷”。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b).這推出了判定“設計缺陷”的“合理的替代設計”標準。同樣,如果一種產品所產生的可預見的損害風險可以通過提供合理的指示或警示(reasonable instructions or warnings)加以減少或避免,而這種指示或警示的缺失使得產品不具有合理安全性,那么該產品就存在“警示缺陷”。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這又簡稱為判定警示缺陷的“合理的指示或警示”標準。
制造缺陷是對產品設計標準或規格的背離,它通常會使“消費者的期望”落空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c.,因此使用傳統的“消費者期望(consumer expectations)”標準判定制造缺陷也不存在問題。但是,在判定產品缺陷方面,“消費者期望”標準并不是一個確定性的標準。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有自己不同的判定標準。
設計缺陷的判定啟用的是“合理性(reasonableness)”或“風險—益處權衡(risk-utility balancing)”標準。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d.它要看一個合理的替代設計是否能夠以合理的成本減少產品中可預見的損害風險,以及這樣一個替代設計的缺失是否使得產品成為不合理安全之物。這就需要將可替代設計和導致損害的設計做一比較,這一比較是以合理人的視角來進行的。這非常類似于過失侵權法中所啟用的傳統“合理性”標準。在決定是否存在一個合理的替代設計以及這樣一個合理的替代設計是否會使產品不具有合理安全性時,需要考慮一系列相關因素,比如:(1)可預見的損害風險的嚴重程度和可能程度;(2)產品上的警示或指示;(3)消費者期望的性質和強度;(4)現有產品設計與可替代產品設計各自的優勢和不足;(5)替代設計對生產成本、產品壽命、產品維持、產品維修和產品美觀的影響;(6)消費者的產品選擇范圍大小。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f.
美國侵權法重述中警示缺陷的定義同樣啟用的是“合理性”標準和“風險—益處或成本—益處權衡”。在判定產品警示的充分性時,法院需要考慮一系列因素,如產品的目標用戶群體的特性、語言表達的內容、可理解性和強度。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i.當存在一個“中間人(intermediary)”(即處于減少或避免損害風險之位置的人)時,關于產品的警示是通過中間人來轉述還是需要直接向最終產品使用者做出這一問題,法律上并沒有一般的規則,需要根據“合理性”標準來判斷。這需要考慮以下因素:(1)產品風險的嚴重程度;(2)中間人將產品信息傳送給最終用戶的可能性;(3)直接向最終用戶做出警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i.產品的警示既可以使消費者意識到產品風險的存在并通過妥善的使用或消費“減少”損害風險,也可以使消費者做出不購買或不使用產品的知情決定從而“避免”損害風險。在后一種情形中,可合理預見的產品用戶和消費者在決定是否使用或消費該產品時合理地認為具有“實質性(material)”或“重要性(significant)”的風險信息即是需要警示的信息。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i.
從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對產品缺陷的分類定義和相關評論來看,嚴格責任只無條件適用于制造缺陷,而不管生產者是否已盡了注意義務。對于設計和指示缺陷,生產者只對“可以預見的損害風險”負責,而這種風險是本可以通過采取“合理的替代設計”或“合理的指示”來避免的。三種缺陷中,只有“制造缺陷”徹底堅守了產品責任的“嚴格”性,它否定了生產者和銷售者在產品的制備和營銷過程中已經行使了所有可能的“注意”的相關性,是一個不考察當事人過錯(注意義務之違反)的概念。但是,“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定義中的邏輯則有所不同。“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問題往往出現在產品并沒有偏離“設計”(即沒有制造缺陷),但是“設計”本身,或者產品的營銷(沒有警示或指示)本身,使產品不具有合理安全性這樣一種場合。它的規則與適用于“制造缺陷”的規則是不一樣的。盡管許多法院堅持認為“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所適用的標準仍然是“嚴格”標準,這兩種缺陷的定義實際上借用的是過失侵權法中的“合理性”測試標準。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 Comment a.這表明,在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領域,法律在向過錯責任歸責原則靠攏。只有制造缺陷領域才是嚴格堅守無過錯責任原則或嚴格責任原則的一隅。
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之不同標準的建立是有原因的。相較于制造缺陷,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傳統的標準和嚴格責任適用于新領域也未必適宜。另外,在制造缺陷領域,消費者相對無助,適用嚴格責任較為妥當。但是,在設計和警示缺陷領域,消費者可以通過安全的使用和消費來降低產品風險,不同標準的建立有利于促進消費者安全地使用和消費產品。
實際上,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對產品缺陷的定義和對產品缺陷責任的規定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它沒有過分沉溺于對傳統侵權法類型和原則的依附和糾纏。比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2條試圖建立的是對不同產品缺陷類型的統一的、協調一致的定義。只要這些定義中的產品缺陷標準被滿足了,原告就可以在任何侵權類型(如過失責任或嚴格責任)下,甚至可在“對適銷性的默示擔保(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名目下提起訴訟。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2, Comment n.
美國法中將嚴格責任只限于制造缺陷領域,而將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置于過錯責任原則下考慮的景象會在其他法域重現。比如,歐盟的缺陷產品責任指令Council Directive of 25 July 1985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liability for defective products (85/374/EEC), Article 6.和英國的《消費者保護法案》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 (Eng), Section 3 (1).在定義“缺陷”時均采用了類似“消費者期望”的標準,即產品缺陷指的是產品的安全沒有達到人們通常有權期望的程度。但是,在判定產品缺陷時,會考慮到諸多情形,這包括:(1)產品投放市場的方式和目的;(2)產品的外包裝;(3)是否存在指示或警示;(4)產品的可合理期望的用途;(5)產品投放市場的時間。Council Directive of 25 July 1985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liability for defective products (85/374/EEC), Article 6;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 (Eng), Section 3 (2). 這些因素的考量很可能導致在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領域,法院會使用過失(negligence)侵權原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29]。比如,如果一個產品的風險可以通過不同的設計減少或避免,在判定產品的設計缺陷時,法院定會將產品的風險與其益處做一權衡,最終的問題轉換成了將含有某種設計的產品投放市場是否是“合理”的。這些導入的均是判定過失的規則。
在產品責任法(包括醫療產品責任法)精細化的過程中,我國有必要跟進這種區別不同缺陷類型適用不同判定標準的發展趨勢。產品責任法所處的已經不再是嚴格責任一統天下的年代。制造缺陷與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不同判定標準的設置,特別是過錯責任原則在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領域的浸入和滲透,對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利好。具體到我國現有的醫療產品責任法(第59條),這種產品缺陷種類上的區分以及區分的效果也會使得與產品生產者承擔連帶責任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責任相應減輕。由此,此種區分有利于減輕機械地適用第59條對醫療機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四)醫療產品的類型化
1醫療產品與血液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所建立的規則,雖然名義上或出于方便的目的稱之為“醫療產品責任”,但其實際上涵蓋兩類物品:一是醫療產品(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二是血液。血液提供機構和醫療機構就“不合格的血液”所承擔的侵權責任,是不是應該與醫療“產品”責任為伍,值得討論。兩者均為醫療所涉物品,但定性和規則并不相同。
美國法明確地將“人類血液和人類組織器官”(即使是屬于商業性提供的)排除在“產品”概念之外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9 (c).,從而遠離了產品責任法和嚴格責任。“血液”的提供被視為一種“服務”,從而將對血液提供者的責任追究限定在了是否違反合理注意義務上。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19, Comment c.在英國法中,盡管人體組織器官和人體血液似乎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案》中的“產品”構成要件要求,但是,在英國司法中,也存在著一種“服務/貨物兩分(service/goods dichotomy)”的概念,醫療機構的血液提供被認為是醫療和專業技能判斷的一部分,從而被認為是一種“服務”而不是貨物提供[30]。加拿大最高法院也傳遞出了人體組織不是商品的信息,認定醫療服務提供者實施人工授精的合同系一份醫療服務提供合同,而非精子銷售合同[31]。這些對人體組織和血液的特殊對待多是基于其對社會具有巨大用益以及屬于不可替代物和不可或缺物的考慮。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雖然觸及到了“不合格血液”所導致損害的責任承擔,但此條并沒有回答對于“合格”但仍存在污染的血液(比如因處于窗口期無法查出血液中所含病毒)所造成的患者損害如何賠償的問題,即該條沒有回應在血液提供機構和醫療機構均無過錯的情況下因“合格”血液導致感染的情形。在此問題上,全國人大法工委在其對《侵權責任法》的解釋中只談到了在此種情形之下如何承擔責任上學界與司法界的爭議。(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239-242.)因此,可以講,我國法并沒有在血液提供領域肯定無過錯責任的適用。就血液提供機構的責任而言,它是建立在考察血液提供機構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上的過錯責任。我國在侵權法中使用了“不合格”這個行政管理味道很濃的術語。“不合格”應指“不符合標準”。它是一個指向法律、法規、規范、質量標準和操作規程的概念,而不是看當事人是否違反合理注意義務。因“不合格血液”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指向的是血站和醫療機構在血液采集和臨床用血過程中“未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規范的要求操作”而導致輸血感染這一情形。(參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239-240.)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過錯認定中是絕對地以標準和操作規范為準,還是只將它們作為重要參考?也就是說,過失認定判準是“合理注意義務違反”標準還是“操作規范”標準?同樣,關于醫療機構就輸入“不合格的血液”所產生的民事侵權責任,也是圍繞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而展開的過錯責任討論。它們均不同于醫療產品責任以及嚴格責任或無過錯責任在其中的運用。這與域外將血液提供視為“服務”從而適用過錯責任的做法是一致的。這說明,人體的“血液”不同于通常的“醫療產品”。人體的“血液”上建立的侵權責任不同于產品責任,二者利益考量和歸責原則不同。
2非處方類醫療產品與處方類醫療產品
非處方類醫療產品與處方類醫療產品在缺陷判定標準上的區分也見于美國法。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2條的適用范圍是一般產品,包括非處方藥。但是,對于處方類醫療產品,美國《侵權法重述》將其挑出來單獨規定了不同的規則,即第6條。此時,對于處方類醫療產品,第2條將不再適用。對于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制造缺陷,在界定上與一般的產品制造缺陷定義并無二致,制造缺陷責任的承擔與其它產品也沒有不同,無需再述。但是,對于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擁有其自己的定義。
(1)處方類醫療產品的設計缺陷
根據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6(c)條,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設計缺陷”指的是,“如果藥品或醫療器械所產生的可預見的損害風險,相較于其可預見的療效,系足夠巨大,以致于合理的健康服務提供者在知道此種可預見的風險和療效后不會向任何一類患者開處該藥品或醫療器械,那么該處方藥品或醫療器械將因設計缺陷而不具有合理安全性”。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c).也就是說,除非處方醫療產品的設計達到了一位合理的醫師不會對“任何”種類的患者開處的程度,該類產品的設計不能認為具有缺陷。此定義推出的是測定處方醫療產品的設計缺陷的“合理的健康服務提供者”或“合理醫生”標準。相對來說,此標準是比較容易滿足的。
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的認定也是一個風險和療效權衡的過程。在此定義之下,生產者只需證明,對某一類患者來說,產品的益處大于損害,因此一位合理的醫生會開處此藥即可,而無需證明是否存在更好的替代設計使產品變得更合理地安全。因此,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的界定標準(益處大于損害風險)不同于一般產品(包括非處方藥)的設計缺陷的界定標準(是否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設計)。由此形成了非處方藥與處方藥分別適用不同的缺陷設定標準(即第2條和第6(c)條)的局面。
第6(c)條背后體現的政策考量是,應該保證一種處方藥向那些在醫生看來屬于受益群體的某類患者群體的供應。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c) Comment f.只要某種處方藥對某一類患者具有凈益處,就應該向這些患者維持該藥的可及性。應依靠醫生(專業中間人)的判斷來保證合適的藥到達合適的患者人群當中。但是,如果在合理的專業中間人(醫生)看來,某種處方藥不會給任何群體的患者帶來凈受益,該種處方藥就存在設計缺陷。
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6(c)條的前身是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評論K——關于“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產品(unavoidably unsafe products)”的評述。Restatement (2d) of Torts, § 402A, Comment K.“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產品”主要是指在現有人類知識狀態下就其用途來看不可能變得安全的產品。這類產品包括藥品,特別是處方藥、新藥和試驗性藥物。根據評論K,對于此類產品,只要制備適當、警示適當,考慮到其帶來的社會益處,不能僅因為存在風險(已知的但不可避免的風險)就認定其存在缺陷。“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應免于嚴格責任。評論K有鼓勵創新之意。
在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之下,認定一件產品是否存在設計缺陷的標準有兩個:一是消費者期望標準。在美國的侵權法重述(第二次)中,“缺陷產品”是指具有“不合理危險的(unreasonably dangerous)”產品 (Restatement (2d) of Torts, Section 402A),而“不合理危險”則是指“危險程度超出了一位對產品特性擁有通常知識(ordinary knowledge)并購買產品的通常消費者(ordinary consumer)所料想的范圍” (Restatement (2d) of Torts, Section 402A Comment i.)。即一個產品是否達到了一位通常的消費者所期望的安全程度。二是風險—益處(risk-utility)標準,即權衡產品的設計風險與益處。與上述兩個標準相對,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評論K給處方藥的缺陷認定提供了不同的標準,并形成了一種保護。為了促進藥物創新,評論K實際上為處方藥提供了免責(免于嚴格責任)機制。
盡管二者的政策考量相近,在處方藥的設計缺陷認定方面,相較于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402A條評論K,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6(c)條有以下改進:一是,在進行風險益處平衡時,它面向的不是所有種類的患者(all classes of patients),而是某一種類的患者(any class of patients)。這就避免了盡管某一種藥對某一類患者有益,但因對所有患者不一定是益處大于風險而被認定為具有缺陷從而被逐出市場這樣一種局面的產生,從而保證了某種藥物對某類患者的可及性。二是,在第6(c)條下,這種風險益處平衡的主體是合理醫生,而不是陪審團或法官。在判定是否存在設計缺陷時,第6(c)條依賴的是“合理醫生(reasonable physician)”的判斷。第6(c)條考察的中心內容是一位“合理醫生”在知曉藥物的風險和益處后是否會向任何一類患者開處此藥。如果它會開處此藥,則說明該藥具有可以受益的患者群體,說明此藥對該類患者來說比其它替代藥物更為有益,就不應被認定為具有缺陷從而遭受被逐出市場之運。三是,在決定是否有比所涉藥品設計更安全的替代設計上,評論K可能會允許陪審團或法院將所涉藥品的設計與尚未得到藥監部門許可、尚未上市的、試驗性的、所謂“更安全的”替代設計相比較,從而認定藥品存在缺陷,但是第6(c)條不允許做這種比較。第6(c)條聚焦的是一位合理醫生是否會開處所涉醫療產品。醫生在做決定時,當然會考慮到替代設計的風險和益處,但是含有這些替代設計的醫療產品須是已獲藥監部門許可的,因而是可以開處的。總之,相對于評論K,第6(c)條是一種對新藥研發和上市更為有利的條款設計。
盡管遭遇到了一些批評,稱其對既定規則的偏離過大,第6(c)條并沒有形成對評論K嚴重的偏離,而是對其進行了改善以更好地實現評論K之主旨。首先,第6(c)條并沒有拋棄傳統的風險—益處分析方法,這種風險—益處分析被揉進了合理健康服務提供者對是否開處所涉藥品的分析判斷當中。第6(c)條所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客觀來看,合理的健康服務提供者,在知道某一藥品或醫療器械的可預見的風險和益處后,是否會向某一類患者開處此醫療產品”。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c) Comment f.其次,第6(c)條也沒有拒絕“更安全的替代設計”標準。第6(c)條所涉及的風險—益處分析不是獨立進行的,它要考慮有無其他更安全的替代醫療產品。第6(c)條更加明確了處方醫療產品的設計缺陷判定是個案認定,而不是地毯式的一概豁免。第6(c)條的好處在于它有利于鼓勵對人類健康帶來益處的處方產品的供應,保證其可及性。正如一位法官所言,“如果某一處方藥因對某類患者有益而不被認定為缺陷產品從而被保留在了市場,這使得,在拒絕將此藥提供給可能受害的患者的同時,讓從中可獲益的患者可以獲得該處方藥。”[32]關鍵的問題是,需要醫生行使專業判斷和把關讓正確的藥到達正確的人手中。
(2)處方醫療產品的警示缺陷
根據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6d條的規定,處方類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警示缺陷”指的是,“如果有關可預見的損害風險的合理指示或警示未向下列人員提供,一處方藥或醫療器械將因指示或警示不充分而被認為是不合理安全之物:(1)處方醫療人員和其他健康服務提供者,當他們處于根據指示或警示減少損害風險的位置時;或 (2)患者,當生產商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健康服務提供者不處于依據指示或警示減少損害風險的位置時。”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d).根據對第6條的評論,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orts: Products Liability, § 6 (d), Comment a.6(d)(1)規定了傳統的“習得中間人或專業中間人(learned intermediary)”還有翻譯為“博學的中間人”者。 (參見:美國法律研究院. 侵權法重述第三版:產品責任[M]. 肖永平,龔樂凡, 汪雪飛. 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07-208.)原則,即只有當生產商未能向健康照護的提供者警示產品的風險,它才對未盡產品風險警示義務負責。 根據該評論,6(d)(2)對該傳統規則設置了有限的例外,要求生產商在特定情況下向患者盡警示義務。至于“習得中間人”的規則是否適用于處方藥品的直接市場營銷(direct marketing)或者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廣告宣傳(direct-to-consumer (DTC) advertising)場合,重述則無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有法院認為,在藥品生產商面向消費者的直接促銷和營銷活動對消費者的藥品選擇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以致于處方醫師作為風險評估和藥物使用決定者的角色減弱或喪失殆盡時,“習得中間人”規則不再適用,藥品生產商需要對消費者直接盡藥品的危險警示義務。在Perez v. Wyeth Laboratories Inc., 161 N.J. 1, 734 A.2d 1245 (N.J. Aug 09, 1999)案中,新澤西州最高法院認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藥品廣告改變了“習得中間人”原則的變量。適用“習得中間人”原則的理論根據和前提在向消費者的直接廣告中幾乎不存在。在生產商的市場營銷旨在影響患者對藥品的選擇時,直接向消費者做藥效承諾的藥品生產商不應不受限制地免除其對產品的危險和副作用提供適當警示的義務。法院認為,在此種場合,醫師選擇決定處方藥的角色已經變化,由于生產商面向消費者的直接廣告的攻勢以及其提供的信息的影響,患者對治療方法的事先期望增強,有時醫師不得不屈從于患者的選擇和意志。因此,在適用“習得中間人”規則時,患者是否對專家(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專業判斷存在依賴是一重要考量因素。
習得中間人/專業中間人可能是開處方藥的醫師、指導患者用藥的護士,或配方的藥劑師,但通常是處方醫師。法律之所以設置“習得中間人”規則,是因為:“處方藥有可能是復雜的藥物,在組方上使人難以理解,在效果上也千差萬別。作為一位醫療方面的專家,處方醫生可以考慮藥物的特性和患者的過敏狀況。這需要將藥物的益處與潛在危險做權衡。他所做出的選擇是知情下的選擇,是一個個體化的醫學判斷,此判斷是以對患者和療法的認知為基礎的。”[33]適用“習得中間人”原則的理論根據和前提在于:(1)法院不愿侵入醫患關系,(2)醫師在向患者傳送有意義信息從而確保知情同意方面具有優勢地位,(3)藥品生產商在與患者直接交流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4)處方藥風險信息具有復雜性。
一般認為“習得中間人”規則是藥品生產者向用戶盡警示義務這一般性原則的例外。它豁免的僅是藥品生產商對最終消費者的警示義務,而不是對習得中間人的警示義務。“習得中間人”必須是“習得”的。因此,處方藥的制造商有義務向處方醫師盡藥品危險的充分警示義務。 “習得中間人”規則在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三次·產品責任編》第6d條中是原則,在一般法中是例外。“原則”和“例外”的定性,只系因其所處的情景不同而已,規則本身并沒有不同。
有理由相信,“習得中間人或專業中間人”規則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會得到青睞和推廣,因為它是古老的普通法原則——“中間審查(intermediate examination)”原則[34]——的邏輯延伸。這一規則一般適用于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因而只能在專家指導下才可使用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主要會依賴“專業中間人”的判斷。這一規則已經在加拿大司法中被加拿大最高法院所采用[35]。它也受到了英國學者[25] 1617和新西蘭學者[29] 292的垂青。
總之,由于處方類醫療產品相較于非處方類醫療產品風險較大、風險益處較為復雜,且需要醫療服務人員的專業判斷的介入和干預,因此在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定上將二者加以區分是有正當性基礎的,也是必要的和值得借鑒的。從美國法重述的文字表述看,特別是從“可預見”的損害風險、權衡“可預見”的“風險和療效”、有關“可預見”的損害風險的“合理”指示或警示、“合理”的健康服務提供者等術語的啟用來看,處方類醫療產品的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定運用的也是“過失”侵權法的思維,顯現的也是向過錯責任原則的回歸。但是,相較于非處方類醫療產品,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定更多地邀請了處方者——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生)——的參與。醫療服務提供者及其專業判斷在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定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具體講,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的判定有賴于醫療服務提供者對醫療產品風險益處和具體患者病情的判斷和權衡,而在處方類醫療產品警示缺陷的判定中,由于醫療服務提供者往往處于從事風險和益處評估減少風險的專家位置和受信賴的位置,醫療服務提供者便成為了生產商警示義務的對象。總體來看,盡管具有一體性和相通性,相較于非處方類醫療產品,處方類醫療產品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定標準對產品的生產商和銷售商更為有利。它充分考慮了處方類醫療產品的可及性、特性和復雜性。同樣,這種醫療產品類型上的區分也會產生緩解在我國醫療產品責任法(第59條)下與生產商承擔連帶責任的醫療機構之責任的效果。
(五)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責任類型化
我國應區分醫療產品缺陷責任法和醫療損害責任法。此處的醫療損害責任法指的狹義上的(不包括醫療產品責任)、主要專注于診療領域和信息告知領域、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主導原則的醫療損害責任法。醫療產品缺陷責任法和醫療損害責任法的區分可以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在某些情形之下免于產品缺陷責任的困擾。有三種情形,應當適用診療和信息告知領域的醫療損害責任法,而不是醫療產品責任法:
一是醫療產品的選擇不當和濫用。在醫療服務中,醫生應對,由于專業技術或專業判斷欠佳,或出于經濟利益驅動,所導致的醫療產品的選擇不當和濫用承擔責任。不過,這種責任不是產品缺陷責任,而主要是在診療領域醫生因違反注意義務所產生的責任,是一種醫療服務提供方面的過錯責任,可以適用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4條(過錯責任原則)、第57條(過錯判定和醫療水平論)和第63條(過度診療之禁止),而不是第59條。
二是醫療器械置入和操作使用不當。患者遭受醫療產品所害,既可能是產品缺陷的原因,也可能是醫生的醫療技術失誤,如醫療器械置入和操作使用不當。這里就要區分產品缺陷責任和醫生因違反注意義務而產生的在診療中的過錯責任。前者適用醫療產品責任法(第59條),后者可以適用《侵權責任法》第54條(過錯責任原則)和第57條(過錯判定和醫療水平論)。
三是未盡醫療產品風險警示義務。醫生對醫療產品的風險還有一個信息告知或警示的義務,此項注意義務的違反所導致的也是一個過錯責任,只不過發生在信息告知領域,可以適用《侵權責任法》第54條(過錯責任原則)和第55條(信息告知義務),而不是第59條。此項醫療機構違反告知義務的責任(過錯責任)不同于藥品生產商的警示缺陷責任(適用產品責任法,比過錯責任嚴格)。即使存在“習得中間人”這樣一個規則,也并不意味著醫療服務提供人員應在處方藥上承擔警示缺陷責任。在“習得中間人”這一規則之下,醫生是否開處了藥品以及是否告知了藥品的信息是在醫生的“過失侵權”法律構架下討論的[25] 1617。 “習得中間人”規則僅是藥品生產商警示義務的一種例外。由于“習得中間人”的存在,藥品生產商向“習得中間人”盡藥品風險的警示義務即可。它處理的是藥品生產商與“習得中間人”在警示義務上的一種關系。它并沒有處理醫療服務提供者與患者之間的關系。醫師針對患者的藥品風險警示更宜在醫師的告知義務或知情同意法則之下進行考察。對醫師告知義務或信息披露義務之違反的考察適用的是同診療領域一樣的過錯責任原則。要判定醫師是否違反了醫療服務提供領域的信息告知義務,要考慮醫師是否有過錯,既要考慮合理醫生之所為和行業做法,更要考慮個體患者的信息需求。這是傳統的知情同意法則的一部分。
醫療產品責任規則的精細化發展與第59條的限縮適用
類型化和精細化處理 是否適用第59條?醫療機構的類型化 實現“醫藥分家”的醫療機構未實現“醫藥分家”的醫療機構
(商品服務區分的類型化→) 醫療產品提供系醫療服務之必要部分醫療產品的提供(銷售)并非醫療服務所必需 醫療產品不存在缺陷醫療產品存在缺陷 第59條不適用第59條不適用第59條不適用產品缺陷
類型化 醫療產品類型化非處方類醫療產品 處方類醫療產品制造缺陷 “偏離設計”標準(“消費者期望”標準)(嚴格或無過錯責任) “偏離設計”標準(嚴格或無過錯責任)設計缺陷 “合理的替代設計”標準(合理性標準或風險-益處權衡)(過錯責任) “合理的健康服務提供者(醫師)”標準(過錯責任)警示缺陷 “合理的指示或警示”標準(合理性標準或風險-益處權衡)(過錯責任) “習得中間人”規則(過錯責任)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責任類型化 醫療機構非因醫療服務之必需而“銷售”“缺陷”“醫療產品”(醫療產品缺陷責任)醫療產品的選擇不當和濫用(醫療損害責任(診療領域),過錯責任)醫療器械置入和操作使用不當(醫療損害責任(診療領域),過錯責任)醫療服務提供者未盡醫療產品風險警示義務(醫療損害責任(信息告知領域),過錯責任) 第59條適用第59條不適用第59條不適用第59條不適用六、結語《侵權責任法》第59條反映了我國“醫藥分家”尚未到位的實然狀態,它體現了立法者對醫療產品雙重性的考慮以及對被認為是“弱勢”消費者(患者)和占信息和專業優勢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利益的權衡。但是,它對應然狀態的反映不足。它過于注重醫療機構在“銷售”醫療產品這一表征,而沒有對醫療服務區別于商品銷售的特性給予充分考慮。我國的“醫藥分家”改革具有艱巨性和長期性。在醫藥尚未分離的時代,第59條具有存留價值和現實正當性。在醫療機構走向“醫藥分家”的進程中,與其狹隘地、機械地、不加區分地適用第59條從而將其演化為舊體制的“固化劑”,不如全面地、辯證地、區分地分析醫療機構的責任歸屬、使第59條細微地反映不同情形,將其轉化為新體制產生和建立的“壓力閥”和“推動器”。
既然第59條產生于“醫藥不分家”的體制,并在利益取舍中充滿了對醫療機構“銷售者”身份的考量,它的適用范圍就應限定在仍以醫療服務提供者和“銷售者”雙重身份面對患者和公眾的醫療機構,不管其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特別是適用于那種并非為醫療服務所必需的產品“銷售”行為。對于已經實現“醫藥分家”的醫療機構和產品提供確系醫療服務必要組成部分的醫療活動,第59條不宜再適用。這種適用上的限制有利于重塑第59條,使其接近“服務—商品區分”理論意欲達到的效果。
此外,即使醫療機構被置于第59條之下也并不意味著醫療機構將面臨承擔無過錯責任或嚴格責任的厄運。這有賴于我國產品責任法的精細化發展和類型化處理。在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領域(不管是處方類醫療產品還是非處方類醫療產品)過錯責任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在處方類醫療產品的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判定方面對該類產品特性的特殊照顧都改變了嚴格責任歸責原則一統產品責任領域的局面。將設計缺陷和警示缺陷與制造缺陷區分開來,將處方類醫療產品與非處方類醫療產品區分開來,將醫療產品缺陷責任與醫療產品相關的、診療和信息告知領域的損害責任區別開來,不僅是法律規則細微化發展的需要,而且會在客觀上拓展過錯責任原則適用的范圍,大大壓縮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進而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被置于無過錯責任的可能和空間。ML
參考文獻:
[1] 趙西巨. 我國《侵權責任法》中的醫療產品責任立法之反思:以商品與服務二分法為視角[J]. 東方法學, 2013,(2).
[2] 衛生部, 財政部, 國家勞動總局. 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意見的通知[(79)衛計字第579號][EB].1979.
[3] 梁鴻, 趙德余. 中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解析[J]. 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7,(1): 128.
[4] 周幼曼. 對我國“新醫療改革”的幾點思考[J]. 宏觀經濟, 2010,(1):3.
[5] 楊立新, 岳業鵬. 醫療產品損害責任的法律適用規則及缺陷克服:“齊二藥”案的再思考及《侵權責任法》第59條的解釋論[J]. 政治與法律, 2012,(9): 112-113.
[6] 王利明. 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侵權行為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69-272.
[7] 楊立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270-271.
[8] 王竹. 論醫療產品責任規則及其準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59條為中心[J]. 法商研究, 2013,(3): 61.
[9] Robert A. Sachs. Product Liability Reform and Seller Liability: A Proposal for Change [J]. Baylor Law Review, 2004,(55): 1032-1136.
[10] Hector v. Cedars-Sinai Med. Ctr., 225 Cal. Rptr. 595, 599–600 (Cal. Ct. App. 1986).
[11] Porter v. Rosenberg, 650 So. 2d 79, 82–83 (Fla. Dist. Ct. App. 1995).
[12] Goldfarb v. Teitelbaum, 540 N.Y.S.2d 263, 264 (N.Y. App. Div. 1989).
[13] Cafazzo v. Cent. Med. Health Servs., Inc., 635 A.2d 151, 154–55 (Pa. Super. Ct. 1993).
[14] James W. Poppell. When Is A Sale, and A Product A Product? Missouri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Strict Product Liability Claims [J]. UMKC Law Review, 1994,(63): 283.
[15] Jackson v. Mulenberg Hospital, 96 N.J. Super. 314, 232 A.2d 879 (1967).
[16] Cheshire v. South-hampton Hospital Association, 53 Misc. 2d 355, 278 N.Y.S.2d 531 (Sup. Ct. 1967).
[17] Carmichael v. Reitz, (1971) 17 Cal. App. 3d 958.
[18] Perlmutter v. Beth David Hospital, (1954) 308 N. Y. 100.
[19] Cafazzo v. Central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Inc., (1995) 668 A.2d 521.
[20] Royer v. Catholic Medical Center, (1999) 741 A. 2d 74.
[21] Budding v. SSM Healthcare System, (2000) 19 S. W. 3d 678.
[22] Russell v. Community Blood Bank, (1966) 185 So. 2d 749.
[23] McKenna v. Harrison Memorial Hospital, (1998) 960 P. 2d 486.
[24] Margin v. Krasnica, (1967) 227 A. 2d 593.
[25] Kennedy & Grubb. Medical Law[M].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13.
[26]富爾,考茨歐. 醫療事故侵權案例比較研究[M]. 丁道勤, 楊秀英, 譯.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27] 廖煥國. 醫療機構連帶承擔藥品缺陷責任之質疑[J]. 法學評論, 2011,(4).
[28] 顧昕. 全球性醫療體制改革的大趨勢[J]. 中國社會科學, 2005,(6): 121-128.
[29] Stephen Todd. The Law of Torts in New Zealand [M]. 5th ed. Wellington: Thomson Reuters, 2009: 301.
[30] Dodd v. Wilson [1946] 2 All ER 691.
[31] Ter Neuzen v. Korn (1995) 127 DLR (4th) 577.
[32] Bryant v. Hoffman-La Roche, Inc., 585 S.E.2d 723 (Ga. App.2003), 734, Judge Andrews.
[33] Reyes v. Wyeth Laboratories, 498 F 2d 1264 (5th Cir 1974), 1276, Wisdom J.
[34] 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AC 562.
[35] Hollis v. Dow Corning Corp (1995) 129 DLR (4th) 609 (Can Sup Ct).
Revisiting Article 59 of Chinas Tort Liability Law:
Contextualization, Categorization and Restrictive Application
ZHAO Xij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Article 59 of Tort Liability Law was born in a context where provision of health service is not separated from sale of medical products. It gives too much emphasis to the fact that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involved in the affair of selling goods, lacking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distinct nature of health care. In an era when provision of health service is still integrated with sale of medical products, there is room for Article 59. There is a need to view Article 59 in a context, to differentiate circumstances, and to transform Article 59 into a vehicle of promoting new health care reform, rather than applying it mechanically and uncritically and making it become an obstacle to new reform.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categorize several key factors, such as medical institutions, servicegoods dichotomy, defects of products, medical products and liabilities relating to medical product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that Article 59 has exerted on medic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medical products liability; Tort Liability Act of China; Article 59
本文責任編輯:林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