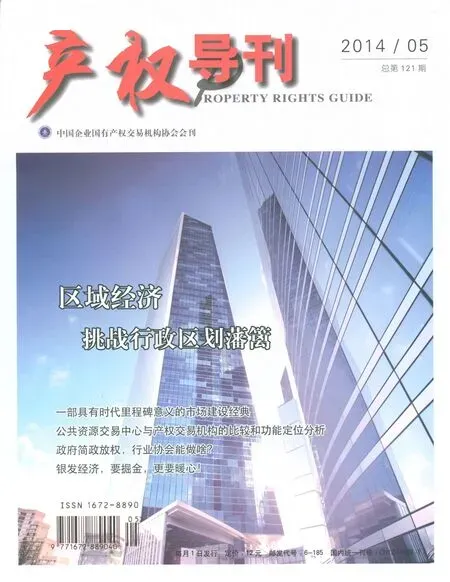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吸引民間資本的關鍵在改革
◎ 郭文靖
新型城鎮化吸引民間資本的關鍵在改革
◎ 郭文靖
3 月5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在“2014 年工作總體部署”中提到9 項重點工作,其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位列第五。但橫亙在新型城鎮化面前的最大難題,就是錢從何來的問題,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經濟,還是進城農民融入城市所面臨的就業、社保、住房等,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據國開行預測,2020 年前,新型城鎮化至少需要50 萬億元新投資以滿足新增城市居民的需求。
我們已經走過的城市化之路,資金需求往往依賴政府投入。而政府投入在財政不足時,基本的路徑就是“投資靠土地財政,融資靠貸款舉債,償債靠土地擔保”的循環。結果,一方面就是土地財政的風險與地方債務的風險交織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地方的“人為造城”淪為了“鬼城”。可見,傳統城市化的老路已在新型城鎮化中行不通了。實際上,巨大資金需求政府也無力獨自承擔。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特別要求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
在多元資金中最主流、最有潛力的顯然就是民間資本,一方面因為我國民間資本確實很富余,截至2013 年11 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高達102.7 萬億元,僅個人存款就高達45.2 萬億元;另一方面,我國民間資本投資渠道不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直接導致民間借貸高漲、跟風炒作盛行。如果能夠真正釋放民間資本的強大活力,新型城鎮化的資金難題就會迎刃而解。但問題是,資本都是趨利的,不僅要保值,而且要追求盈利。如果不能解決民間資本的回報問題,無論怎么提倡和鼓勵,可能作用都非常有限。
目前,民間資本之所以不愿積極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新型城鎮化本身的集聚力問題。無論新型城鎮化怎么“新”,如果不能積聚產業和人口,民間投資的回報就沒有基礎保障。然而,目前因為各種資源,大機關、大總部、大學、大醫院、大企業以及大的文化體育項目和基礎設施,都依然集中在大城市,這就直接導致了無論是產業還是人口,都依然處在向大城市積聚的過程中。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的話,不僅無法增強新興城鎮的集聚能力,而且會導致更多的城鎮出現“空心化”危機。不從根本上解決城鎮的集聚力問題,即使放開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民間資本也不會去。
二是以土地財政為代表的政府逐利問題,導致民間資本盈利空間太小。官員出于政績的焦慮,雄心往往比財力跑得快。怎么解決資金缺口?我國各級政府已經形成了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除了賣地收入和土地融資之外,似乎別無他法。所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就利用國家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政策,以至于相當一部分地方出現人為并村、強迫農民上樓的現象。這樣的結果,不僅沒有解決農民城市化的問題,反而擴大了地產和金融泡沫,讓城鎮化的成本直線上升,導致對產業和人口的吸引力進一步下降。這種情況下,民間資本對暴利的房地產都要三思,更不必說其它了。
政府投資可以不計效益,民間投資就要盤算投下去是否能賺錢。因此,吸引民間資本積極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列出新型城鎮化對民間資本的商機、放寬市場準入門檻、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運用政策的鼓勵扶持作用、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等很有必要,但可能還不夠激發民間資本的創業投資熱情,還難以形成政府與社會力量共同推動城鎮化的發展機制。要真正激發民間資本投身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積極性,關鍵就在于改革,一個是從宏觀上明確中國今后城市化的重點,并在公共資源配置上體現出來;二是從微觀上徹底退出拿地賣地的土地財政,不再“人為造城”,而要靠市場規律自然成城。
從宏觀的角度,雖然近年來城鎮化發展可能是歷史上最快的時期,但“八五”、“九五”期間才是城鎮化發展堅實的時期,這直接為現在的“城市群”建設打下了基礎。“十五”以來,國家把城市化發展戰略由“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調整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結果一線城市都往“國際性大都市”發展,二、三線城市都往“大城市”發展,城鎮就只能簡單“人為造城”了。因此,新型城鎮化要吸引民間資本,國家就要明確我國今后城市化的城鎮化方向,并改變目前大城市在不釋放資源的基礎上而靠“限購”、“入戶”來提高門檻的作法,而要通過實實在在的釋放資源,產業下鄉、資源下鄉,引導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動。
從微觀的角度,就是要學習日韓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城市化的經驗,用土地開發的財務平衡替代土地財政。政府不能想著靠土地拍賣賺錢,政府所征的地,除了解決底線基礎建設和解決人的城市化之外,都不能拍賣,而是要用來建保障房,用來扶持實體經濟。資本“逐利”而生,擠掉了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避免了“造城、擴城陷阱”,才可能提高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投資的積極性。也只有這樣,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轉變,才能自然實現,人們在城市里才進得來、留得下、過得好,新型城鎮化才有活力、才可以持續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將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并稱為“影響21 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實際上是給了我們很多啟示的,核心的就是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政府必須定好位,不能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場規律。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具體進程和方向,也必須順應市場規律。民間資本本身就是市場要素,要吸引民間資本積極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就更應該尊重和順應市場規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在新型城鎮化吸引民間資本的問題上,政府必須率先改革,由過去的主導資源配置和直接逐利,變為引導和服務資源配置,并為民間資本創造盈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