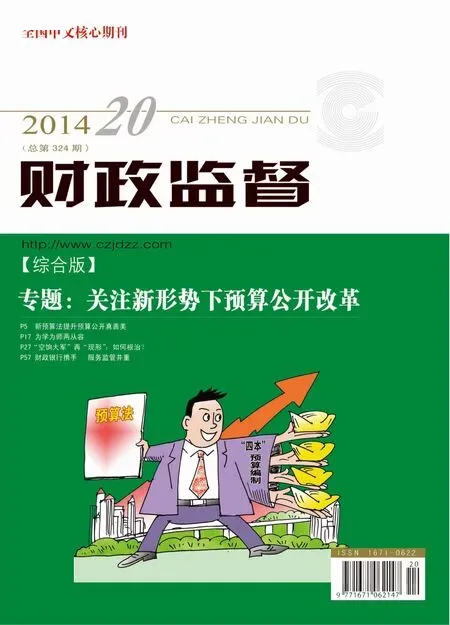對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的思考
●李 博
對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的思考
●李 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吹響了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進軍號。《總體方案》對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方面,提出要“研究清理規范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本文試就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的原因、引致的問題,對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的益處,以及如何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提出筆者的思考。
一、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的原因
重點支出掛鉤,是指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掛鉤或生產總值掛鉤,即某項重點支出要達到財政支出或GDP的百分比。之所以將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掛鉤或生產總值掛鉤有以下原因:
(一)地方政府的生產性投資偏好導致教育等重點支出不被優先考慮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提出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占有較高的比重,公共部門為經濟發展提供道路、交通等社會基礎設施,這些投資,對于處于經濟與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的國家經濟“起飛”,以至進入發展的中期階段是必不可少的。地方政府由于任期制的政績壓力,有短期內通過大量生產性投資來獲得當地高GDP增長率的動機,有持續擴大生產性投資與持續縮小公共性投資的激勵。地方政府這種獨立的市場化利益取向,加之公共服務需求無限性與財政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教育支出等重點項目投入長期不足,經濟欠發達地區擠占個別亟需的公共事業資金等情況。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為了教育、農業等重點支出得到保障,將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政策的出臺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掛鉤事項的公共品屬性及其外溢性
公共品的外溢性,即是指轄區之外的居民也能從公共品中受益,但成本則由轄區政府或居民承擔,這就導致“搭便車(free-rider problem)”問題的出現,直接投資者享有的收益小,自然降低了轄區政府投資公共品的積極性,導致其投資動力不足,進而縮減此類公共服務開支。由于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能通過價格機制的調節自行實現,需要政府參與協調與管理。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糾正市場失靈,政府應當履行公共品提供者的職能,但因公共品的供給缺乏有效的利潤考核機制和社會評價機制,最終將導致教育等準公共品提供的低效率,因此將教育等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作為公共品提供的保障性條款就應運而生。
二、重點支出掛鉤事項引致的問題
(一)肢解了預算分配權,不利用財政宏觀統籌
目前與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的重點支出,涉及農業、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社保、計劃生育等7類、15項規定,2013年該類資金占到了全國財政支出的47.4%。重點支出掛鉤事項追求的是部門利益最大化,與現代財政體制的內在要求相背離。政府的預算分配權受到極大限制,既不能充分發揮預算的調控功能,也無法突出當年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重點,特別是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可支配財力原本即已捉襟見肘,若再有項目要求地方配套,就更加大了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
(二)預算支出結構僵化,不利于提高資金績效
每項重點支出都很重要,既不能顧此失彼,同時也應體現不同時期的支出重點,若某項重點支出僅依據一個固定比例執行下去,就不能很好兼顧各個時期的需要。某項重點支出應當達到什么水平,并不依賴于當地GDP有多大的量,而應當取決于該地區對該項重點支出的實際需求。“一刀切”式統一將某項重點支出掛鉤比例,可能脫離地方實際,為了達到指標,反而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速與財政收入增速雙換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地方政府不但需要厲行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支出,還應將每一分錢都用到刀刃上,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根據當地經濟發展實際,壓縮并非亟需的重點支出,騰出資金用于未掛鉤的民生項目就勢在必行了。
三、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帶來的益處
(一)使政府預算更好地切實當地實際,服務地方發展
以往重點支出之所以與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目的是保障當時階段性重大問題的解決,確保重點支出。修訂前的《預算法》第三十條“各級預算支出的編制,應當統籌兼顧、確保重點,在保證政府公共支出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其他各類預算支出”,明確規定要“確保重點”,這就是剛性指標、硬性任務,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決定》已將其修改為“各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編制,應當統籌兼顧,在保證基本公共服務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優先安排國家確定的重點支出”,不再硬性規定“確保重點”,而是“優先安排國家確定的重點支出”,即是要求今后預算支出要更加公平規范,使預算安排能更好地服務于地方實際,突出當年經濟社會政策重點。
(二)順應經濟規律,更好地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經濟發展階段論”提出,經濟達到成熟階段后,公共支出將從基礎設施支出轉向不斷增加的教育、醫療和福利服務方面支出,同時其支出增長將遠遠高于其他支出增長,也會快于GDP的增長速度。目前我國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根據“經濟發展階段論”,政府公共支出會轉向教育、醫療和福利服務方面,其中自然而然會包括教育等重點支出掛鉤事項,這種公共支出方向轉變有其內在動因,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對發揮 “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增強地方自主權、靈活性都有重要意義,地方政府保障民生類重點支出的執行力會更高,同時也破解了錢由誰來花更合理的問題。
四、如何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事項
(一)明確預算法在預算分配方面的主導地位,理順預算法與部門法的關系
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決定》新增條款“預算、決算的編制、審查、批準、監督,以及預算的執行和調整,依照本法規定執行”,體現了修訂后的預算法是規范預算全過程的一般法。教育、農業、科技、文化等其他部門法中涉及的重點支出掛鉤事項屬于預算分配范疇,其效力應當低于預算法、服從于預算法。建議人大釋法時明確預算法在預算分配方面的主導地位,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之與預算法銜接配套。
(二)明確事權,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合理調整并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與支出責任,既要橫向解決預算管理問題,又要縱向解決事權、財力問題。當前,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權、財力、事權“倒掛”的形態還未得到緩解和改善。有數據顯示,地方政府以45%的財力承擔75%的事務。不同政府層級間的事權劃分,要充分考慮公共品屬性及其外溢性等因素。屬于全國性的公共品,理應由中央政府牽頭提供;區域性公共品,由地方政府牽頭提供效率更高。支出責任宜與之對應,分別劃歸中央與地方。由于地方政府更加了解當地居民需要,需求信息獲取上優勢更大,所以在中央和地方均能提供某種公共服務的情況下,基于供給效率的考慮,更傾向于由地方政府提供。
(三)將預算控制的重點由控制投入向控制產出轉變
《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決定》明確要求各級預算應當“講求績效”。重點支出掛鉤事項有相關法律、法規保障,一些有重點支出項目的部門在編制部門預算時,對項目可行性研究不足,預算編制不細化,致使預算執行過程中不得不頻繁調整,造成相當多的重點支出掛鉤項目要跨年完成。這屬于“投入預算”,以投入為導向,重點是如何控制資源的投入和使用,而不考慮其支出的經濟效果。然而在產出控制的模式下,資金投入必須保證有績效,從而將財政資金投入成本與績效結合在一起,用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從而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從制度上杜絕部門單位只爭取財政資金而不考慮績效的情況。這也要求政府進行細致的預算分析,大力推進績效預算管理,要求相關部門根據年度計劃編制項目的績效目標,并將項目績效目標細化,同時項目實施過程中,財政部門將進行全程監督,對項目績效進行評價,并將評價結果與下一年度預算編制掛鉤,從而切實提升重點支出資金使用效益,增強財政投入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作者單位:四川省財政廳監督檢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