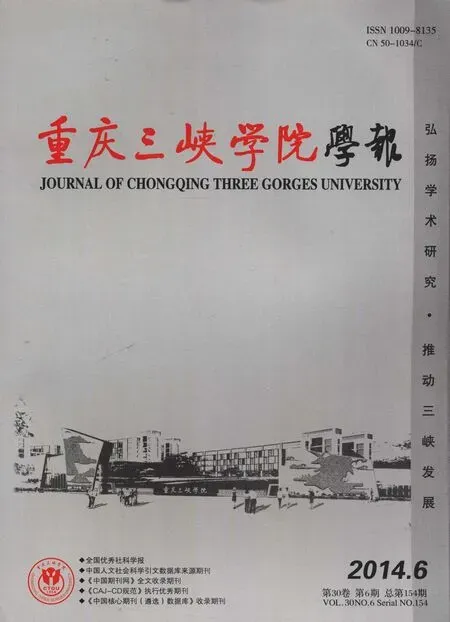以佛救心
——蘇東坡與禪學的辯證延伸
劉紅星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湖北黃岡 438002)
以佛救心
——蘇東坡與禪學的辯證延伸
劉紅星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湖北黃岡 438002)
蘇軾早年得志開始其從政生涯,但終其一生卻仕途失意,其人生軌跡亦飄零輾轉,多災多難。然雖遭巨變,其深受禪學思想影響,能夠超然于物外,在悲苦的人生境遇中,以佛救心,實現其自我心靈的救贖及文學創作實績的轉變。
蘇軾;禪學;辯證延伸;以佛救心
蘇東坡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天才之一,也是文學家中少有的人生經歷最為坎坷、生命軌跡最為豐富的傳奇人物。縈繞于新舊黨爭,卻被新舊兩黨所棄絕;雖早有才名,為帝王賞識,宋神宗曾評價:“李白雖有蘇軾之才,但無蘇軾之學!”但蘇軾仍難以避免官場失意,屢經磨難。在起起伏伏的人生境遇當中,蘇軾卻能邁過坎坷,以平常之心“回首向來蕭瑟處”,以禪學思想為營養,極力拓展自己的人生境界,以佛家的看破以及禪學中“人生悲苦為空”的思想體悟實現其生命價值的升華。
一、北宋禪宗的興盛及與文人主流思想意識的契合
在佛教發展史上,禪宗的興起大大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宗派紛呈,義理幽深的情況漸漸被“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所代替,在入宋后禪宗逐漸成為佛教各宗派的主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活動的日益繁榮,以“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為核心的禪宗,也為文人群體所接受,并在兩宋時期迅猛發展。
佛教自東漢便隨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然而由于其最初形態的理論架構及觀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存在較為廣泛的差異,在禪宗之前其發展仍然是較為緩慢的。然而,隨著佛教中國化程度的加深,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在相互摩擦、碰撞、妥協之中,逐漸完成了其中國化改造,而禪宗便是這一過程的產物。
禪宗意蘊對中國文學空靈的審美追求具有深遠影響。而空靈的文學審美作品,又延伸了禪宗思想作為文學審美思想的藝術性和歷史的深度,兩者的互動形成了相互影響的發展態勢。在兩宋文人的創造實績中,許多作品就其思想意識和審美追求上,在很多方面都體現了禪宗的審美情趣的影響。
自六祖慧能傳道以來,禪宗也經歷了由阡陌到廟堂的發展過程。在北宋,盡管此時的禪宗較以前相比無甚大變化,但同時仍具有自己獨特的魅力。不僅宗門耆宿,教內大德,推崇禪宗,調合宗教,還有一些士大夫紛紛皈依禪宗。在文人群體當中,佛學信仰不但影響其在文學的創作實績,并且在他們的引領下,禪宗也逐漸形成其哲學理論體系的架構。
首先,這一時期禪宗佛學典籍開始大量出現,這在此前是沒有的,以普濟和尚的《五燈會元》為例,其開始大量記載禪宗宗門軼事語錄,梳理了禪宗的脈絡,為禪宗的傳承做出了貢獻。第二,文人士大夫群體中,禪宗受眾的人數激增,學禪蔚然成風。據歸元本和尚《叢林辨佞篇》所載,宋代上層官僚士大夫如富弼,楊億,李遵勖,楊杰、張育英,張九成、李邴,呂本中等都曾熱衷于禪學,棲心于禪寂,與禪學結了不解之緣。而下層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當中禪宗的信眾也較此前大大增多。第三,僧群尤其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僧人社會活動非常活躍,其對社會政治的參與度、文學活動的參與度等都達到相當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僧人為主體的文學創作主體的出現,也為佛教文學開拓了更為廣闊的世界。
二、蘇軾的禪宗因子及結交的僧人
禪宗作為較為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在北宋的影響力非常大。一方面,自五代十國戰亂之后,人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這與佛教宣揚的慈悲精神十分契合;另一方面,禪宗理論體系架構已經建立起來,這一時期作為佛教代表的禪宗一脈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其在整個社會當中都極具廣泛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社會的主流思想意識對蘇軾也有很大的影響。就蘇軾的文化基因來看,其求學過程中,難免會受到整體社會思潮的影響。對于蘇軾而言,其文化基因當中的禪宗因子首先來自于其家庭教育[2]。究其文化淵源,蘇軾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體系與其父蘇洵有著非常大的關聯性。而蘇洵對佛學尤其是禪宗思想有著相當深的造詣。而蘇軾也曾說“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舍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此,而志則無盡。”可見,從家庭的信仰氛圍和教育氛圍來看,其自小便深受父母佛學信仰的影響。
考究其人生軌跡,其與諸多僧人有著不淺的交情。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蘇軾最早結識的僧人是成都大慈寺的惟慶(文雅)、惟簡(寶月)兩位法師。據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載,蘇軾20歲“游成都,謁張安道”;又與弟蘇轍同游大慈寺,見惟慶、惟簡法師。其在《中和勝相院記》中寫道:“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法師惟慶,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史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游,甚熟。惟簡則共同門友也:共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齋眾,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其與當時的名僧參寥子持續一生的友誼,更是在其人生歷程當中,禪學對其影響的佐證。
如果說早期的家庭教育影響與日后其僧人朋友的交往互動,為其思想種下最初的種子,那么其對佛學尤其是禪宗理論體系的自覺學習,則是對自我思想體系進行整理重新架構的實踐。其在被貶黃州之后,歸誠于佛教,開始大量閱讀佛教經典并系統學習禪宗思想理論體系。為排遣其憤懣之情,其更是定期到寺院打坐參禪,希冀以禪學徹悟來實現自我境遇的解脫和解除內心世界的痛苦。而在黃州期間,其更是自號為東坡居士,表明其皈依佛門。
三、蘇軾的人生境遇及佛學的心靈撫慰
在蘇軾的人生歷程當中,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高中進士至烏臺詩案前,第二個時期為烏臺詩案至司馬光為相重新以禮部郎中入朝,第三個時期為不被舊黨所容直至再度被貶儋州。其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如是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此詩之中悲憤之情躍然紙上。
少年成名的蘇軾才情頗高,而文名亦是名滿天下。而當時的皇帝宋神宗、高太后等最高決策層也對其才情贊不絕口,而其在士大夫階層也有著較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按照官場邏輯,其在仕途上即使不是一路順遂也不至于如履薄冰。但實際上,蘇軾的仕途卻步步驚心。烏臺詩案禍起《湖州謝表》,其在上書宋神宗的文章中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在新舊黨爭的大背景下,這幾句牢騷語卻被新黨上綱上線,說其“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而針對其詩文,新黨羅織成罪,將其扳倒使其被貶黃州。而在此次文字官司當中,若非廣為救援,蘇軾甚至有被殺的危險。
烏臺詩案后,蘇軾遇到人生的第二次打擊是被貶儋州(即現在的海南)。蘇軾元祐六年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圣元年(1094年)六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紹圣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縱觀蘇軾一生,其糾結于新舊兩黨的黨爭之中,作為中間派人士,非但不能置身事外,反而里外不討好,在夾縫中艱難生存。
可以說,蘇軾的一生充滿波折與艱難。這種人生困境的存在,使得蘇東坡的精神世界充滿著挫敗感和幻滅感。而世事無常那種并非人力可以掌控的力量,令人生充滿種種苦難。他在其詩中寫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種對人生徹底絕望的體驗和對個人遭遇不公平的控訴,卻無法改變其悲慘的人生命運。
禪宗注重內省的觀照意識和消解執著,導向空淡無我的處世態度,而這種精神世界的構建,正與文人在現世當中亟需的精神撫慰機制相契合。而所謂“以佛救心”,便是這種精神撫慰機制的體現。從當前的文獻資料來看,蘇東坡開始系統學習佛家經典并以居士自居的時間節點恰恰是在其被貶黃州期間。烏臺詩案是蘇東坡人生的轉折點,幾近經歷生死險境,蘇東坡不得不選擇佛家的思想去尋求精神解脫。
一方面,禪宗重視對自我內心世界的觀照和洞悉,從自我精神世界當中去尋求皈依。禪宗的觀照即以智慧觀事、理諸法,而照見明了之意。又“觀照般若”則指能觀照事、理等諸法實相之理之智慧。而在這種思想理論空間的架構中,對人生世相是澄明和淡然的。另一方面,佛家宣揚的“彼岸”“極樂”與“放下解脫”等思想,又給苦悶無奈當中的蘇東坡指明一條可以得到解脫的人生道路。即使這條道路似乎是玄之又玄的,但他仍然以此為突破口,實現自我的突圍。
禪宗在理論構建最大的貢獻就是性起緣空說的提出,禪宗理論認為通過頓悟人人皆可成佛。盡管緣起性空的提出者龍樹菩薩遠遠早于禪宗,但是六祖慧能之后,該理論卻與中國本土的思想源流匯合,形成符合中國人思維模式的“性空”理論。在禪宗的視野當中,諸法既是因緣所生,自然空無自性,無自性便無法自我主宰,所以說“無我”。放棄我執之后,便形成以無我為核心觀念的理論構建。而在其倡導的修行觀中,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則成為其信眾廣泛傳播。而陷于人生兩難境界的蘇東坡,在感受到“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電亦如露”的幻滅時,便試圖以悟與放下去實現自我人生境界的拓展。“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在一切浮躁繁華歸于涅槃的寂靜當中,蘇東坡亦在這種頗具撫慰功能的思想理論下得到些許庇護。
四、蘇軾作品的禪意及蘊含的空靈美學
經歷了禪學洗禮之后的蘇東坡,一方面實現了其心境的轉換,令其從苦悶、不滿的現狀當中走出,令其能夠以更為豁達勇敢的人生態度,去實現自我人生境界的拓展;另一方面,其作品也受禪學影響,更具思辨性和哲學性。
其代表作《赤壁賦》,便將禪學當中的無常與永恒抒發得淋漓盡致:“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這幾句話將水月人生天地物我等意象組合在一起,通過哲學上的思辨與求索,闡述的道理恰恰便是禪宗中所謂的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電亦如露的世界觀。而其在西江月的詞作中,更是直言世事一場大夢。其作品當中,對人生體悟的幻滅感和對世事無常的無力感,正好與禪學相契合。
直指本心,明心見性,是禪學給予蘇東坡自我觀照的法門。從體悟當中去參照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個人生命體驗與整個世界的相互關系,為其豁達豪邁人生境界的開啟注入了不竭動力。在蘇東坡的文學創作實績中,其不但試圖在義理上去表現抒發自我的見解進行禪學上思考,對人生進行深層次感悟;并且在文學創作審美意蘊的追求上,也存在著濃重的禪學意味。在禪宗與中國文學的結構關系當中,以禪宗意蘊為主線,形成的具有空靈審美追求與美學意義的文學審美形態,其貫穿于整個中國文學史。而蘇東坡的作品中,這種具有空靈境界的文學作品也并不罕見。其代表作《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中,“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惟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的意境勾勒出空靈唯美的境界。
五、結 語
蘇軾的思想深受禪學思想的影響,其人生經歷與人生體驗當中的苦難構成其人生當中的無常,勾起其對于世事的幻滅感。而其以禪學為救贖,實現心靈境界由小我到更為廣闊世界的提升,使得這種人生體驗更具深度,體現在其作品中則是獨具特色的思辨性和哲理性的理性思考與極具空靈意味的審美情境。
參考文獻:
[1]趙文斌.蘇黃詩歌與禪門公案[D].廣州:暨南大學,2010.
[2]王東濤.禪宗美學思想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影響[J].齊魯藝苑,1996(2):40-44.
[3]李明華.蘇軾詩歌與佛禪關系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1.
[4]孫小迪.參禪操琴 修心明性[D].西安:西安音樂學院,2011.
[5]方漢文.當代詩學話語中的中國詩學理論體系——兼及中國詩學的印象式批評之說[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8.
[6]黃金華.宋代文論“理趣”范疇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學院,2013.
[7]鄧心強,梁黎麗.論佛教思想對古代文論中“虛實”范疇的影響[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87-93.
(責任編輯:鄭宗榮)
Salvation by Zen: a Dialectical Expansion of the Relation of Su Dongpo to Zen
LIU Hongxing
(Hubei Huangg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Su Dongpo’s early success saw his commence of his official career, but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he was frustrated and his life course featured wandering and misfortunes. Though his life was never smooth, he can live transcendentally, salvage himself with Zen in misfortune-filled life and never cease his literary creation.
Su Shi; Zen; dialectical extension; salvation by Zen
I206.2
A
1009-8135(2014)06-0075-04
2014-06-02
劉紅星(1972-),女,湖北英山人,黃岡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文學、高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