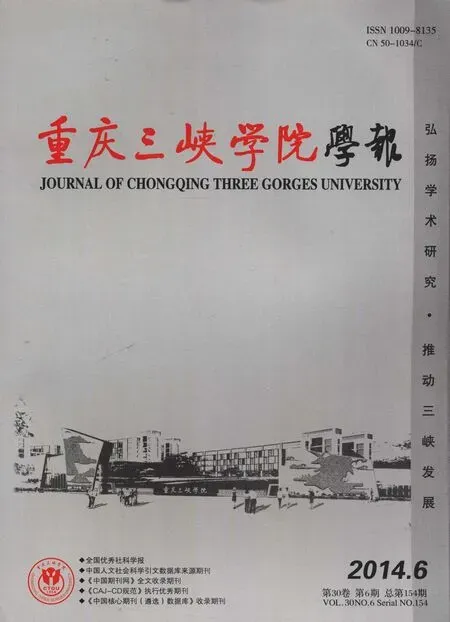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
——以冰心、廬隱、王統照、葉紹鈞等為例
崔 璨
(安徽大學文典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
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
——以冰心、廬隱、王統照、葉紹鈞等為例
崔 璨
(安徽大學文典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
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的重要一環。在五四運動從高潮到落潮的這段時間,以冰心、廬隱、葉紹鈞、王統照等為代表的“問題小說”作家通過其小說創作,表達了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深切思考。以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為切入點,將小說中的家長形象進行了類型劃分。在細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長形象在五四“問題小說”中的獨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蘊。透過這一新的視角能夠更好地理解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內涵和價值。
“問題小說”;家長形象;類型劃分;五四運動
“問題小說”是典型的五四啟蒙運動的產物,它(問題小說)探問人生的終極意義,觀照每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生存真諦。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問題小說”這一概念由周作人提出。在1918至1919年之間,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和《中國小說中的男女問題》等文章中借肯定日本近代“問題小說”的價值來提倡中國的“問題小說”創作,指出“教訓小說”所宣傳的必是已成立的、過去的道德。“問題小說”所提倡的,必是尚未成立的,卻不可不有的將來的道德。一個重申說,一個特創新例,大不相同,并明確提出“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1]299。同一時期,沈雁冰則在《文學與人生》、《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等評論性文章中寫道:“現在熱心于新文學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們注意社會問題,同情于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大力提倡“為人生”的“問題小說”。[2]周沈二人對于“問題小說”的提倡促進了此類小說的創作和發展。1919年初,北大學生團體新潮社創辦了《新潮》雜志,羅家倫、俞平伯、王志熙、楊振聲、歐陽予倩、葉紹鈞等人相繼在雜志上發表小說作品,其中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花匠》、《這也是一個人?》等作品已開始顯示出“問題小說”的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斯人獨憔悴》,正式開創了“問題小說”的風氣[3]47。“問題小說”也伴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和高潮,成為了當時最為流行的文學創作潮流。
一、家長形象在五四“問題小說”中的研究價值
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將“問題小說”的主旨內容歸納為反思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唐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中是這樣描寫“問題小說”的:“文學研究會成員從‘為人生’出發,創作的小說也大多以現實人生問題為題材,出現不少所謂‘問題小說’”。[4]164傅子玖《中國新文學》中將“問題小說”定義為“探索人生問題的小說”。[5]229錢理群、溫儒敏等人則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也認為“問題小說”和“問題小說”作家是五四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除舊布新的巨大力量而引出的,他們的創作顯示出明顯的“為人生”的寫實小說的傾向。[3]47毫無疑問,五四“問題小說”自其誕生之始便帶著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其關注的范圍自然涵蓋了家庭問題以及由家庭問題所引發出的一系列家長和子女的沖突與矛盾。
近些年來,學術界的一些文學研究者開始更進一步地重視“問題小說”的價值,并有將其看作重要的文學流派的趨勢。如郭仁懷認為:在評介“問題小說”時,要重視它的題材特點和藝術效果,不能一味去談它探索了什么問題,解決了什么問題,這樣有可能把讀者導入庸俗社會的泥淖。[6]初清華認為“問題小說”作為文學革命后較早的小說創作實驗,已涵蓋了現代小說創造的思維模式,在文本形式上呈現出散文化傾向。[7]龍泉明也認為“問題小說”是我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創作潮流,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在小說創作領域最初的社會性成果。[8]“問題小說”處理“問題”和“小說”的關系上已部分超越了中國傳統小說和近代小說。其他一些學者則從社會學、心理學等角度來探討“問題小說”,在“問題小說”的“公共性”等方面得出了新的學術研究成果。[9]可以看出,對于五四“問題小說”而言,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研究價值,從不同的方面來研究“問題小說”可以獲得不同的研究結果。從家長形象這一新的角度來切入“問題小說”的研究,在內在思路上繼承了五四“問題小說”為人生的人文關懷精神。在實際的文本分析中,家長形象的存在能夠為讀者提供更為清晰的閱讀參照,使讀者能夠更為精準地把握五四那個變革時代的精神內涵。
在分析家長形象在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價值時,自然不能離開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大的時代背景。美籍學者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一書中稱五四運動是一個復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10]6這場運動最為顯著特征就是重估一切價值,用新的價值體系來取代舊的價值體系。以此便不難理解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作家在寫作過程中的焦慮和掙扎。在五四這樣一場劇烈的文化變動中,社會大眾在新舊價值的接受與轉換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和矛盾。而這種文化交替的內生性撕裂感給當時的年輕人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力和困惑感,使得他們帶著嚴峻的眼光來審視現實社會和文化傳統中的問題。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問題小說”中的所謂“問題”涉及到了人生問題、家庭問題、婚戀問題、勞工問題、女權問題、兒童問題、教育問題等諸多在當時困擾人們的問題,可以說幾乎囊括了當時社會上的主要問題紛爭和流行思潮。
雖然五四“問題小說”所表現的“問題”有很多,但幾乎所有的“問題”小說都涉及到了家庭問題。而在這些表現家庭問題的小說中,作者對于家長形象的刻畫是較為豐富與深刻的。在一些作品中,作者是以顯性的方式將寫作的視角主動地投向家庭,批判了傳統中國和那個時代的家庭中所暴露的各類問題,以啟蒙者的姿態向那些蠻橫無理的家長們做出了挑戰。如冰心的《斯人獨憔悴》和《兩個家庭》、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王統照的《湖畔兒語》、廬隱的《一封信》等。而一些作品則是將家庭問題視為其他社會問題的附帶品,借由其他社會問題的描寫來被動地反思家庭問題。在這些小說中,家長們既是家庭悲劇的制造者,又是家庭悲劇的受害者。如廬隱的處女作《一個著作家》和后來發表的《海濱故人》、王統照的《沉船》、葉紹鈞的《隔膜》、以及俞平伯為數不多的小說《花匠》等。無論是主動地暴露還是被動地反思,家庭問題是五四“問題小說”中最為顯著的問題之一。而寫家庭問題的“問題小說”作家中,又尤以冰心、廬隱、葉紹鈞、王統照等人為甚。
五四運動已過去近一百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問題小說”中所反映出的一些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卻依然存在著。五四“問題小說”所表現出的家長形象更是憑借著他們強烈的文化思維模式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于五四運動時期的“問題小說”來說,無論是小說本身還是其背后所反映的問題都還有許多可以挖掘的內涵和意義。
二、家長形象在五四“問題小說”中的類型劃分
在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中,作者筆下的父母形象是多元的。他們(指“問題小說”中的父母)并不是完全以負面的封建衛道士的形象出現,相反,有的父母卻顯示出明顯的進步思想意識。如果以是否是城市人、是否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是否能夠接受新思想等因素作為區分條件的話,那么可以將“問題小說”中的父母形象大致分為三類。在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中,首先一類父母形象就是那些擁有較高社會地位,但拒絕接受新思想的城市保守派形象。這類人物形象在冰心的“問題小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雖然冰心的散文創作在文學史的地位要高于其小說創作,然而作為現代文學史上最早進行“問題小說”創作的作家之一,對于其“問題小說”的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1919年下半年的《晨報副刊》上,年僅19歲的(當時還是北京高等師范女子學校的大一學生)的冰心便發表了《兩個家庭》。在隨后的幾年,冰心又相繼發表了《斯人獨憔悴》、《超人》等“問題小說”。在冰心的這幾部“問題小說”中,其對父母形象的刻畫是較為一致的。無論是《兩個家庭》里的陳太太還是《斯人獨憔悴》中的化卿先生,他們都是那種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城市人。從作者對于他們的描寫來看,他們都是接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如在《兩個家庭》中,陳先生向他人傾訴自己的家庭悲劇,“我屢次地勸她,她總是不聽,并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我也曾決意不去難為她,只自己獨立地整理改良。”[11]19而化卿先生在干涉其兩個兒子參加進步運動時也說:“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里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地得罪了?眼看著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11]26從表面上來看,他們(指“問題小說”中的父母,下同)在處理家庭問題的時候并不似傳統社會里的家長,開口之乎者也、仁義禮智(雖然化卿先生也有類似的話語,但考慮到通篇的對話,還是不將其作為主要話語方式),也是在用新式的話語體系和思維邏輯來說服自己的丈夫和子女。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們依然沒有逃脫出傳統社會的家長制的窠臼。他們始終將未成年的子女當做是絕對服從自己的附屬品,而沒有將其作為平等的人格獨立體來對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只是賈政似的封建家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翻版。雖然我們承認他們對于子女也是充滿愛意的,但是這種愛意卻裹挾著子女對父母的順從和對家庭權威的恐懼。在《斯人獨憔悴》的結尾處,化卿先生在終止了穎銘、穎石兄弟的學業后,頗為得意地說自己已經為兒子們安排好了出路。他用犧牲子女自由的權利來獲得自我的滿足,用自以為是的道理來強迫子女接受自己的觀點和思維,并且在實際行動上宣告了子女自由生活的滅亡。
雖然冰心的寫作年代是在民國時期,但是以化卿先生為代表的父母們還是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新思想。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從階級分析法的角度來解釋化卿先生這個人物形象,將其定性為阻礙社會革命的封建保守主義者。可是在小說的敘述中,化卿先生是在新的民國政府里任職的大官。若是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者,這不免有失偏頗。筆者認為,冰心對于化卿先生的形象塑造其實和魯迅關于諷刺辛亥革命的小說(如《阿Q正傳》、《祝福》等)有相同的理路。聯系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的社會僅是從制度名稱上進行了改變,但潛藏在民族文化心靈深處的糟粕卻沒有發生改變。如果以人的現代性這一價值標準作為衡量尺度,那么“問題小說”中以化卿先生為代表的父母則無疑是穿著現代的衣服、卻裹著一副封建傳統心腸的人物。他們只是把“之乎者也、忠孝禮義”等詞語變成了“不懂國情、難解民意”等在當時較為“現代”的說辭罷了。
“問題小說”中的第二類父母形象是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的鄉下人或城市邊緣分子,他們苦命地掙扎在生活之中,對于所謂的新思想則是完全沒有自覺意識。對于這類家長形象,我們又可按照作者的褒貶取向進一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五四時期家庭問題的受難者,一類是五四時期家庭問題的制造者。
就五四時期家庭問題的受難者來說,首先要提的便是廬隱在小說《一封信》中的人物——蕭媽。廬隱的這篇小說主要是通過對于天真姑娘梅生不幸遭遇的描寫,揭示了萬惡的舊制度對于貧苦家庭的摧殘。小說中,蕭媽為了葬自己的母親,只得將自己的女兒賣給了當地的財主惡霸陳老爺。[12]11在作者的描寫中,蕭媽并不是以一個負面的形象示人的,可對于梅生的不幸遭遇,蕭媽卻也難逃其責。廬隱通過這篇小說,表達了自己對于貧苦人家的同情之情。此外,在王統照的小說《湖畔兒語》中,作者也借小順這個孩子的遭遇,表達了對于貧苦家庭不幸命運的悲憫。在《湖畔兒語》中,小順的父親成了躺在席上不起的煙鬼子、后媽則為了生計成了在家接客的妓女。[13]36成人世界的骯臟與齷齪對于還是個孩子的小順來說是莫大的傷害,而其父母則無疑要對這份傷害承擔一定的責任。無論是《一封信》中的蕭媽,還是《湖畔兒語》中小順的父母,他們本身就是家庭問題的受難者。而隨著他們的受難,他們的子女也連帶著承擔了苦難。可無論是蕭媽還是小順的父母,他們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反抗意識,只是苦痛地承擔著,或者是采取自我毀滅的方式來逃避生活的不易(如《湖畔兒語》中小順的父親)。在“問題小說”中,作者對于這種現象明顯是以一種啟蒙者的姿態來描寫的。廬隱和王統照等“問題小說”作家已經開始明白這苦難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他們自身造成的,但礙于時代的局限,他們對于問題根源的揭示顯得不那么明顯和清晰。
而葉紹鈞“問題小說”中的父母形象則表現出十足的罪惡之態。在葉紹鈞“問題小說”的代表作《這也是一個人》中,主人公伊的生身父母、公公婆婆、丈夫等所有人都把她當成是一個物件。她在父母眼里,是一個可以賣錢的東西;在公公婆婆眼里,她是一個可以傳統接代的生育工具;在她丈夫眼里,她則是一個可以發泄性欲的玩偶。[14]99伊在家庭里,完全沒有自己的自尊和自由可言,她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我的意識,故而葉紹鈞在描寫這個人物時發出了“這也是一個人!”的悲鳴。在葉紹鈞而后的小說《隔膜》中,雖沒有直接描寫家庭生活,但卻借相逢、飲宴、閑聊三個場景的描寫,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冷漠。[14]156
“問題小說”中第三類較為典型的父母形象是社會水平處于中等的城市一般市民階層,他們能以平等的姿態來面對子女,也能夠接受新思想,但對于新思想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廬隱的小說《兩個小學生》中,國樞和堅生的父母就是這類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廬隱的小說《兩個小學生》講的是還處在小學階段的國樞和堅生參加政府請愿的故事。在面對新潮與變革等問題的態度上,國樞和堅生的父母顯得和前兩類父母不太一樣。他們不似化卿先生那般強烈抵觸新生事物,也不似蕭媽那樣對于革命新潮處于完全無知的狀態,更不像伊的父母那樣完全將子女當做是可以賤賣的商品。在小說中的一些對白能夠很明顯地反映出這些特征,如國樞的母親在聽說自己的孩子將要去參加請愿運動時,便表現出了十足的為難之情,她說:“這么點小孩子,也學管那些事。請什么愿?倘若闖出禍來,豈不是白吃虧了嗎?沒的嚇得啊爹媽的心都碎了!”而國樞的爸爸則說:“他們學生去請愿,按理說只有有效沒效罷了。斷不至有什么意外的禍事,他既是一定要去,也就讓他去,小孩子們也應該使他們鍛煉鍛煉。”此番爭論之后,國樞的父母也都同意讓他上街去請愿,但反復叮囑其要小心。[12]15對于這類父母來說,他們了解新潮思想,也在心底支持學生們的愛國進步運動,但當面對危險叢生的街頭運動可能帶來的風險時,他們就顯得有些遲疑了。他們希望社會的變革能夠發生,但是卻不希望為這場變革流血的人是自己的孩子。
縱觀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對父母形象的刻畫是非常豐富的。而對于父母形象進行刻畫之后,其背后所蘊含的家庭問題也就顯得十分明顯了。無論是以蠻橫姿態來阻止子女接受新潮思想的父母、或者是無視子女尊嚴、將其當做商品進行買賣的父母來說,其最核心的問題都是在于是否把子女當做是一個平等自由的人來看待。平等和自由是現代文明最為基礎的價值尺度。因此,“問題小說”中所謂的家庭問題其實也就是人的自由的問題。在小說的語境中,這種家庭問題又具體地表現成了子女有意無意地對于人身自由的追求,對于個性自由的追求、對于婚姻自由的追求等眾多子問題。
三、家長形象在五四“問題小說”中的文化內涵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新舊思想交鋒碰撞的時期。處于時代變革中的青年知識分子自然也會敏銳地感受到這種變化之于其個人和其家庭的影響。這一時期,有許多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男女逃離封建家庭的束縛,選擇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但也有很多青年男女在封建家庭與現代家庭之間徘徊不前。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作家多是一些青年學生和年輕教員,借由對家長形象的描寫表達了自己的家庭觀念。“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是作者抨擊封建傳統社會的一個窗口,而家長形象本身則在小說構建中承擔了描述歷史的敘事功能。
從時代發展的橫向來說,“問題小說”作家對于家庭問題的暴露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
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生活問題劇就大量反映家庭問題,而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更是在其著作《安娜卡列尼娜》開篇即說:“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15]3對于家庭的理解是東西方都必須面對的實實在在的問題。因此,五四“問題小說”作家也緊抓時代的脈搏,并借由他們的小說創作表達了對于現代家庭的向往與熱愛。
從歷史發展的縱向來說,五四“問題小說”中對于家長形象的描寫在無形中表明了作者逃離封建傳統社會的決心。在傳統中國,以家族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社會長期存在于古代社會中。傳統中國視域下的“家”的概念是多元的,它不僅承擔著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還起著維護社會倫理、調節社會矛盾的類似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功能。在一些封建皇權管制衰弱的地區,以宗族倫理為載體的家權輻射范圍和實際影響力要超過封建皇權。馬克思·韋伯就在《儒教與中國》中宣稱:“事實上,正式的皇權統轄只局限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統轄威權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16]110這一說法在后來被溫鐵軍進一步地表述為“國權不下鄉,鄉下唯宗族,宗族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7]3雖然學術界對于家權在傳統社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還存在著一定爭議,但是大家都無法否認家族文化對于傳統中國人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處在時代變革中的“問題小說”作家已經具有了覺醒意識,他們不愿意在傳統家庭中壓抑個性、接受封建倫理對自己個性自由的摧殘。所以,部分“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正是代表了那個腐朽與衰敗中的封建社會,而作者則通過對其的描寫來間接地控訴封建傳統社會對人的迫害。
在“問題小說”中,作者是以啟蒙者的姿態來進行寫作的。他們多以當時社會中的青少年為其小說創作的主人公,透過其遭遇的種種故事來反思各種問題。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很多時候是帶著先行的姿態納入到作者的寫作中的,因而在人物的飽滿度上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呈現出一定的臉譜化傾向。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五四“問題小說”作家的思想動向,他們雖未在作品中直接提倡該用哪種主義,卻也在時代的洪流巨變中開始懷疑過去、思考未來,對于所處的時代表現出一種極為不滿的憂傷情緒。
從五四“問題小說”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內涵上來說,小說中的部分家長形象確實代表了封建傳統的思想文化。然而,“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又并不總是以負面形象示人,有的時候他們是站在進步思想的對立面,而有的時候則是將信將疑地去試圖接近進步思想。在“問題小說”中,家長們和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處在變革與焦慮之中,對于家長形象的描寫其實是作者在借家長之口來表達自我對于五四那個時代的復雜情感。而這一切又無疑給了讀者們一種較為復雜的閱讀觀感,使得讀者能夠更為真切地理解“問題小說”及其所反映的各類問題。這種復雜的情感抒寫反映出以“問題小說”作者為代表的五四啟蒙主義者在傳統與現代、變革與守舊之間的糾結與躊躇。透過“問題小說”,我們可以看出處在時代變革中的人們在心靈深處處于掙扎和搖擺不定的焦慮傾向。
“問題小說”中的父母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那個時代父母形象的縮影,他們自身的思想以及對待子女的教育方式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雖然“問題小說”對于家庭問題的描寫不似后來的文學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那樣來得猛烈與深刻,但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初創之作,其精神與意義也是值得尊重的。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還在無形中起到了啟示未來的預測功能,這不得不引起文學研究者更近一步的重視。
不可否認,五四時期“問題小說”中的父母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已經漸漸或已經離我們遠去,那種板著面孔說教的封建式大家長也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變得越來越少。可是,“問題小說”中家長們的部分思維模式卻堅硬地保留到了現在。在面對自我所做出的一些惡的行為時,越來越多的人們會選擇用一種去正義化的思維來使自己釋然,用社會上的大惡來原諒自己的小惡,通過這種方式來模糊真與假、善于惡之間的分野。在面對一些歷史變革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了謹慎而又狡猾的態度來巧妙地規避自己的風險。在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中,有這些思想的還是父母,我們無法在五四年輕一代的身上找到這種影子。相反,我們從很多的文學作品中看到的是年輕人對社會的深切憂慮和頗具理想主義情懷的聲聲吶喊。但到了現在,當時的“年輕人”變成了“后來的父母”,“后來的父母”則又成了這代年輕人“父母的父母”……幾代人過去了,這些思維模式卻如同民族性格中的基因密碼一般一代接一代地流傳著。若是說到當今知識分子的犬儒心態,“問題小說”中的父母形象是否早就已經為我們埋下了伏筆。
四、結 語
從1919年到1924年間,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經歷了短暫的創作熱潮。毫無疑問,作為我國現代小說發軔期的作品,其小說創作在文學性上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家并沒有給那個時代開出明確的藥方,只是暴露了那個時代的家庭中所存在的問題,多數作者借由這些問題來抒發作者的傷感之情,并以此來啟發社會大眾的深層思考。這一度也成為部分學者詬病“問題小說”價值不高的因素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較為純粹地憤慨似寫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文學的獨特性和純潔性,使之沒有被諸如政治因素等外力綁架。
五四“問題小說”中的的父母形象是多元的。對其進行不同的類型劃分可以使讀者更為清晰地把握“問題小說”所反映的家庭問題及其背后所蘊含的時代隱憂。而“問題小說”中的家長形象本身又在小說中承擔著敘述歷史、刻畫當下與啟示未來的三重功能,這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問題小說”的文學價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讀者重新去閱讀五四時期涉及家庭問題的“問題小說”時,依然會覺得很真切。時間的流逝并沒有成為讀者的閱讀障礙,反而成了激發讀者沉淀和思索的觸媒。五四時期“問題小說”作家留給我們的難題依然值得我們理解和消化。
[1]周作人.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M]//陳子善,張鐵榮.周作人集外集(上).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
[2]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影印本)[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3]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弢唐.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傅子玖.中國新文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6]郭仁懷.五四問題小說中的問題[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4):117-112.
[7]初清華.再探“問題小說”——兼論小說現代思維模式的形成[J].蘇州大學學報,2005(4):63-68.
[8]劉勇,龍泉明.中國小說現代轉型的歷史性出場——“問題小說”新論[J].江蘇大學學報,2005(3):69-73.
[9]官志紅,歐陽鋒.論中國現代問題小說的生成及其公共性鏡像[J].求索,2013(11):126-128.
[10]周策縱.五四運動史[M].長沙:岳麓書社,1999.
[11]冰心.冰心全集:第一卷[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
[12]廬隱.廬隱小說全集[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
[13]王統照.中國現代作家選集——王統照[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14]葉圣陶.葉圣陶集:第一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15]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
[16]馬克思·韋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17]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鄭宗榮)
The Parental Image in the “Problem Nove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ing Xin, Lu Yin, Ye Shaojun and Wang Tongzhao
CUI CAN
(Wendian Colleg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The “problem novel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n it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climax to the ebb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uch authors as Bing Xin, Lu Yin,Ye Shaojun and Wang Tongzhao, etc expressed their deep reflection on life and social issues through their “problem novels”cre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arental image in the “problem novel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classifies the images into several specific types, and then carefully analyzes the parental image’s unique rol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behind the “problem novels”.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in the “problem novel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problem novels”;parental image;classification of specific types; the May 4th Movement
I206.6
A
1009-8135(2014)06-0083-06
2014-06-20
崔 璨(1992-),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學文典學院人文科學實驗班學生,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