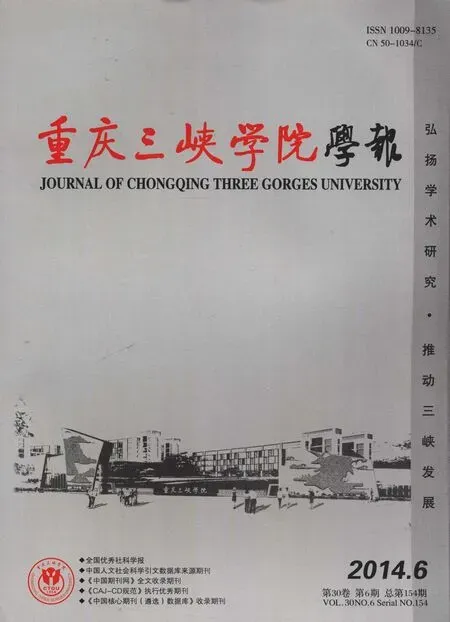揚雄《方言》詞匯與漢代社會體系管窺
鄭 漫 賴慧玲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 637009)
揚雄《方言》詞匯與漢代社會體系管窺
鄭 漫 賴慧玲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 637009)
揚雄《方言》記載了眾多的漢代方言詞匯,這些寶貴的歷史語料不僅反映了漢代各地方言分布情況,還為管窺整個漢代社會體系提供了相對詳盡的資料。通過整理發現,《方言》一書中囊括了有關漢代政治和經濟體系、社會階級關系、生產力水平以及戰事物質配備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且這些都是社會體系中至關重要的組成要素。希望從以上幾個方面著手,立足《方言》詞匯,盡可能窺見漢代社會體系的輪廓。
《方言》;詞匯;社會體系;史料
一、引 言
揚雄《方言》是我國第一部方言學著作,不僅開創了我國方言學研究的先河,還第一次以個人力量對全國大部分方言進行比較詳盡的描寫與比較,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占有卓越非凡的地位。羅常培先生在《方言校箋及通檢·序》中,將揚雄的《方言》譽為“中國語言史上一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1],這不僅僅因為其在語言學、文字學、訓詁學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還歸功于它對漢代社會體系包括政治和經濟體系、社會階級關系、生產力水平以及戰事物質配備等方面的寶貴記錄。撒皮爾曾說過:“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并且,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2]通過對《方言》中詞匯的整理,洞悉其語言后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可以為我們管窺整個漢代社會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與平臺。
二、揚雄《方言》中展示的漢代社會
了解一個社會最直接、最確切的信息來源,就是與當時人們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常用詞語。揚雄《方言》一書共耗時二十七年,“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這正如羅常培先生所說的:“《方言》是開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語言作對象而不以有文字記載的語言作對象的。”[3]這種街頭方言調查方式為我們研究漢代社會體系提供了豐富、可信的歷史資料。
(一)《方言》中的漢代政治、經濟制度與階級關系
漢朝是我國封建王朝發展進程中不容忽視的一瞥,漢代社會、政治制度大都承襲秦制,并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較秦而言,漢初統治者重視發展農業經濟,推行輕徭薄賦的賦稅制度。同時,漢朝依舊崇尚重農抑商政策,對各階級之間的等級制度也有嚴格的控制。《方言》是作者揚雄花時27年搜集整理而成的方言詞書,其所收字詞大都是對漢代社會面貌真實反映。正如布龍菲爾德所言:“每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4]探析揚子《方言》一書中所記載的字詞,反思其背后的來由,對我們了解整個漢代社會是很有幫助的。
1.《方言》詞匯與漢代政治制度
古來統治者就崇尚帝王之風,不止反映在絕對的政治統治秩序上,同時還要求其日常生活都具有皇室典范,其中高屋建瓴的宮室建筑就是一種體現。揚雄《方言》卷二中:“娃,嫷,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嫷……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木桼]娥之臺。”郭璞注:“皆戰國時諸侯所立也。”“娃”是吳人對美女的一種稱呼,《資治通鑒》卷4胡三省注:“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御覽》卷46引《越絕書》:“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其中,“館娃宮”原為吳宮名,為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寵幸美女西施而興建。據《吳越春秋》載:宮內“銅勾玉檻,飾以珠玉”,樓閣玲瓏,金碧輝煌。這些從某種程度都反映了古代帝王為博美人一笑的驕奢之風。
除此之外,《方言》中還有關于漢代官職的介紹,如“亭父”一職。《方言》卷三:“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璞注:“亭公,亭民也。弩父,主擔幔弩導憺因名云。”戰國時,曾在臨接他國之處設亭,并設置亭長,主擔防御之責,出土于云夢的秦簡上有“市南街亭”等語。《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記載:“十里為一亭,亭有亭長,掌治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漢高祖劉邦就曾擔任亭長一職。又《史記·高祖本紀》裴骃集解引應劭曰:“舊時亭有二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捉捕盜賊。”這里認為一亭長官由兩人分別擔任,亭父的主要工作是“開閉掃除”,治安警衛則為他職。
2.《方言》詞匯與漢代階級意識
縱觀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人際社會關系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分,漢王朝也不例外。在這種等級深嚴的社會制度中,以地位低下的人為禮物相贈的舊俗,在古代并不鮮見。《方言》卷三中:“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官婢女廝謂之娠。”郭璞注:“女廝婦人給使者,亦名娠。”所謂“女廝”,是指送給使者的婦人,即“娠”,這種制度在漢代及漢以前都存在。《說文解字》:“娠,宮婢女隸謂之娠。”其中“娠”也就是女奴,也可作養馬的人。女廝,《玉篇》:“使也,賤也。”《集韻》:“析薪養馬者。”
漢代的階級意識是比較強烈的,除了貴族不與平民、奴隸通婚之外,平民與奴隸通婚也有嚴格限制。同樣在《方言》卷三中:“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我們可以看到凡平民與奴隸通婚,其社會地位也會隨之降低。由此可看出漢朝對各階級之間的通婚是有嚴格的控制的。
此外,漢代社會對農夫和商人是很輕視的。我們可以從對農夫和商人的稱呼窺見一斑。例如:《方言》卷三:“儓,農夫之丑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辟。辟,商人丑稱也。”“儓”是古代對低級奴隸的稱呼,在漢代也作古代對農民的蔑稱,這就說明漢代農民的地位是很低的,近乎奴隸。“辟,商人丑稱也。”郭璞注:“僻僻便黠貌也。”“辟”,會意字,從卩,從辛,從口。“卩”,甲骨文象人曲膝而跪的樣子。“辛”,甲骨文象古代酷刑用的一種刀具。稱商人為“辟”,是對商人的一種歧視。
3.《方言》詞匯與漢代經濟制度
漢初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訓,采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方言》卷七:“平均,賦也。燕之北鄙東齊北郊凡相賦斂謂之平均。”《廣雅》:“平,均賦。”“均”,形聲字。從土,勻聲。勻者,帀也,“勻”亦兼表字義,合起來指土地分配均勻。《說文解字》:“均,平也”。《周禮·序官·均人》:“均,土均。”“均”特指古代的一種重量單位,古代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到漢代,一均等于二千五百石。《漢書》:“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據上所述,“平”、“均”都和“賦斂”有了聯系。隨著詞匯意義和賦稅制度的發展,語言對社會變化也適時做出反應,到了唐代,“平”、“均”發展為“均田”、“均平賦役”。明清時期,關于“均平”指稱均賦稅的情形就更多了。
關于漢初的賦稅制度,有從漢高祖時起,實行“十五稅一”的政策;及至漢文帝時期,又有“田租減半”之詔,也就是采取“三十稅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稅”。除此之外,漢初還有所謂“口賦”,也就是“人頭稅”,以及后來的“算賦”。但這些賦稅制度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商人與奴婢則加倍征收,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出漢代對商人的歧視,以及等級制度的深嚴。
(二)《方言》中的漢代的勞作工具
農耕文化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一直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重視農業生產,在以農耕為主的漢代社會,勞作工具種類相對多樣化。正如閔宗殿在《兩漢農具及其在中國農具史上的地位》中所言:“兩漢時期,是我國農具獲得飛速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不論在材料上、動力上,還是在種類上、結構上,兩漢農具都有突破性的發展,在我國農具發展史上,寫下了十分輝煌的篇章。”[5]漢初的強盛與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勞作工具的多樣化是不可分割的。揚雄在《方言》中對此也有大花筆墨的介紹,其中包括糧食收割工具、收攏工具、加工工具以及織布的工具等,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漢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
《方言》中記載了一種收割莊稼的勞作工具,即現如今的“鐮刀”。卷五:“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鉊,或謂之鐹。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鍥。”“刈鉤”是指鐮刀一類的工具,多用于收割莊稼和割草。《說文解字》:“鉤,曲也。”《玉篇》:“鉤,曲也,所以鉤懸物也。”從形狀上來看,“刈鉤”是彎曲的,所以也可稱為“鉤”。《說文解字》:“鍥,鐮也。”《六書故》:“刎鐮,一曰小鐮,南方用以乂谷。”由此看來,“刈鉤”、“鉊”、“鉤”、“鎌”和“鍥”都是漢代各地對“鐮刀”這一收割工具的不同的稱呼而已。
有收攏糧食的“杷”。《方言》卷五:“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郭璞注:“無齒為朳。”《說文解字》:“杷,收麥器。”“杷”是指一種有齒和長柄的農具,多用竹、木或鐵等制成,用以把谷物等耙梳或聚攏起來。據此說來,王智群將“杷”歸為“收割工具”[6]是有欠妥當的,我們竊以為應單獨歸為收攏糧食工具。
此外,還有對糧食進行加工的工具“臿”和“僉”。《方言》卷五:“臿……宋魏之間謂之鏵,或謂之鍏。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臿”本意是指舂去麥皮,引申為舂搗。《說文解字》:“臿,舂出麥皮也。”同樣在卷五:“僉,宋魏之間謂之欇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柫。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柍,或謂之桲。”郭璞注:“僉,今連架,所以打穀者。”僉,亦作“連耞”,或作“連枷”,是農民的手工脫粒農具,由竹柄及敲桿組成。原為農村手工脫粒農具,工作時上下揮動竹柄,使敲桿繞軸轉動,敲打麥穗使表皮脫落。同理,我們以為王智群將“僉”也歸入收割工具是不恰當的。
也有用來織布的工具。《方言》卷六:“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杼”本義是指織布機的梭子。《說文解字》:“杼,機之持緯者。”注:今以梭為之。《后漢書·列女傳》:“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機杼,后泛指織布的工具。杼柚也作“杼軸”,后作織布機上的兩個部件,即用來持緯(橫線)的梭子和用來承經(直線)的筘。亦代指織機。朱熹《集傳》:“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劉君惠曾說過:“文化中最容易被人注意到的是一個社會中的物質設備。”[7]生產工具作為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物質生產設備,其種類的多樣化和廣泛分布一方面體現了我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
(三)《方言》中的漢代武器、戰車、船等
漢初政權建立之后,強大的中央集權尚未形成,漢代統治者尤其以漢武帝為甚,都力圖開疆擴土、征伐四方。劉軍在《漢代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一文中指出:“漢代是中國古代軍事發展史上的豐碑,開創了古典軍事作戰的典范。”[8]我們認為這不僅要得益于強大的后勤物質儲備,還要歸功于統治階層對軍事武器設備發展的重視和大力扶持。《方言》中第九卷介紹了種類繁多的軍事武器、車輛和船只,這也是漢代戰事準備的一個寫照。
1.《方言》中的軍事武器
“戟”這種作戰工具在漢代是很常見的,并且總類較多,連大小、曲直不同稱呼也會隨著改變。《方言》卷九:“戟,楚謂之[釒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釒孑],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卷九:“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郭璞:“今戟中有小孑刺者,所謂雄戟也。”《廣雅》:“匽謂之雄戟。”三刃枝,這種兵器也是戟的一種。我國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戟出現于商代,戟是在戈和矛的基礎上演進而成的。由于戟吸取了戈和矛的長處,在戰場上也就更處于優勢地位。西漢以后,戟由平直變為弧曲上翹,進一步增強了前刺的殺傷力,成為當時軍隊中的常備兵器。
“矛”,是古代用來刺殺敵人的進攻型格斗兵器,主要用于直刺和扎挑,是古代軍隊中大量裝備和使用時間最長的冷兵器之一。《方言》卷九:“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說文解字》:“矛,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鍦”,《集韻》:“短矛也。”《左思·吳都賦》:“藏鍦于人。”注:鍦,矛也。“鋋”是指古代一種鐵柄短矛,也泛指短矛。《說文解字》:“鋋,小矛也。”《史記·匈奴列傳》:“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鏦”,古代一種小矛,也指古代一種有方形柄孔的斧子。《說文解字》:“鏦,矛也。”
除了進攻型格斗兵器,漢代軍事戰爭中還有一種廣泛應用的防御型武器“盾”。《方言》卷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瞂”,《說文》:“盾也。”《張衡·西京賦》:“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又通作伐。”“干”按其甲骨文字形,其形像叉子一類的獵具、武器,其本義是盾牌。《禮記·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注:“朱干,赤盾。”《禮記·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2.《方言》中的運輸工具
漢代戰車的結構構造比較成熟,關于漢代對車的組成部分的稱呼,《方言》第九卷也有詳細的記載。例如:“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畢”的本意是指打獵用的有長柄的網。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畢,田網也。”卷九“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竹恢]……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篷”古時一般指遮蔽風雨和陽光的設備,后也指帆。“輪,韓楚之間謂之轪,或謂之軝。”郭璞注:“輪,車輅也。”“轪”,按許慎《說文解字》:“轪,車輨也。”揚雄《甘泉賦》:“肆玉轪而下馳。”注:“車轄也。”
漢代的水上運輸是比較發達的,舟因大小、長短、深淺不同而稱呼各異,揚子《方言》中對這種情況的描述也極為細致,《方言》卷九:“舟……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艇長而薄者謂之艜,短而深者謂之[舟符],小而深者謂之[楺,矛換鞏]。”“舸”在楚方言多用來指大船。后來也可指小船,泛指一般的船。這些繁多復雜而又近乎詳盡的區分,從側面反映出漢朝船運之廣泛,也為漢朝擴土開疆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三、小 結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方言》作為“中國語言史上一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不僅記錄了相當數量的方言詞匯,并指明各方言分布狀況;還超出語言學的范疇,為后人研究漢代社會體系包括政治和經濟體系、社會階級關系、生產力水平以及戰事物質配備等方面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華學誠曾指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言》研究將面臨著總結、加深、開拓三個方面的任務。”[9]從社會體系的角度來重新看待《方言》,也可以為我們研究《方言》提供一個別樣的視角。
[1]周祖謨,吳曉鈴.方言校箋及通檢·序[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2]撒皮爾.語言論[M].陸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3]周祖謨.方言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1993.
[4][美]布龍菲爾德.語言論[M].袁家驊,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5]閔宗殿.兩漢農具及其在中國農具史上的地位[J].中國農史,1996(2):29-33.
[6]王智群.揚雄《方言》詞匯與漢代農牧業[J].臺州學院學報,2011(2):41-43.
[7]劉君惠,李恕豪,楊鋼,等.揚雄方言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1992.
[8]劉軍.漢代軍事后勤思想述要[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4):115-118.
[9]華學誠.近15年來的揚雄《方言》研究與我們對《方言》的整理[J].南開語言學刊,2001(1):59-69.
(責任編輯:張新玲)
Dialectal Words in Yang Xiong’s Dialect and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Reflected
ZHENG Man LAI Hui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Yang Xiong’s Dialect had recorded numerous dialectal words of Han Dynasty. Those precious recording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dialectal atlas of Han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 detailed data to obtain a rough view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A sorting out reveals that Dialect includes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ystem, class relation, level of productivity and war equipment storage, which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ialectal words in Dialect, and from the aspects just mentioned, we attempt to obtain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Dialect; words; social system; historical data
H172.3
A
1009-8135(2014)06-0117-04
2014-07-29
鄭 漫(1989-),女,湖北天門人,西華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對外漢語方向。賴慧玲(1980-),女,四川成都人,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蘇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