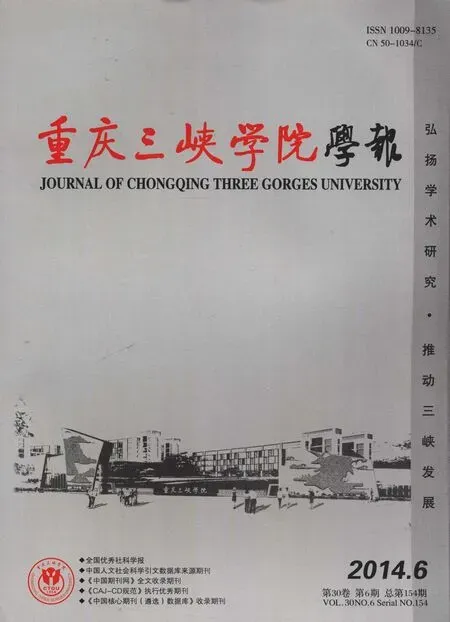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影像資源的效用及限度
劉志華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北碚 400715)
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影像資源的效用及限度
劉志華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北碚 400715)
圖像時代文學作品的影像化傾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提供了可茲利用的豐富資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對文學文本意義豐富性的消解與遮蔽。明確影像的效用及其限度,把握好相關影像資源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系,化解圖文的矛盾,才能把影像資源作為文學教學有益的補充。
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影像;效用
早在20世紀30年代,海德格爾就提醒人們,世界正在“被把握為圖像”[1]72。隨著信息和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世俗化生存的加劇,今天的世界已全面進入圖像時代。文學文本也開始大量向影像轉化,文學與影像的關系變得復雜而密切。文學存在樣態及傳播渠道的變化,勢必影響到文學的閱讀與接受,給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提出了新要求。
一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學生普遍是受閱讀文學作品的影響而走進電影院的,或是基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而對作品改編的電視劇產生興趣。那時,人們往往把影像作為文學的延伸閱讀或印證式鑒賞,影視更多要借助文學經典來抬高自己。今天,這種情況已發生根本性逆轉。學生普遍對閱讀文學文本缺乏濃厚興趣,往往通過影像了解作品概要,更喜歡影像的直觀、時尚與“生動”,不再迷戀文字作為“冷媒介”的“深度”和對想象力的激發。面對影視文本,覺得津津有味,面對文字文本,卻提不起閱讀興趣。即使是那些時尚化的配合影視作品播出的影視同期書,多數也是書店櫥窗的擺設,隨著影視作品熱播的結束而壽終正寢,很少有人真正閱讀。
今天,互聯網的便利,進一步助推人們讀圖傾向的同時,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提供了更多可茲選擇的影像資料。現代文學中經典作品大多有影視改編,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傷逝》,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腐蝕》、《春蠶》,巴金的《家》、《寒夜》,許地山的《春桃》,沈從文的《邊城》、《蕭蕭》,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老舍的《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月牙兒》、《茶館》,張愛玲的《金鎖記》、《半生緣》、《紅玫瑰白玫瑰》、《色·戒》等,都被搬上了銀幕,部分作品還被多次改編;錢鐘書的《圍城》、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等還被演繹成電視連續劇。當代作家杜鵬程、柳青、楊沫、王蒙、張賢亮、王安憶、余華、劉震云、劉恒、賈平凹、王朔、莫言、陳忠實、畢飛宇、趙本夫等的作品都有影視劇改編。當代文學中大量的作品是通過影視走進人們視野的。王朔被稱為“觸電”最頻繁的作家,十余篇小說的影視改編為他賺得了知名度;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主要靠電影《紅高粱》家喻戶曉;對海巖文學作品的了解,多數讀者也是從影視開始的。
另外,作家的人生故事也開始大量以影像的方式呈現。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新浪網、鳳凰網等制作了大量的訪談節目和傳記片。中央電視臺的“人物”、“藝術人生”、“見證”、“子午書簡”等節目頗具影響。如“那一場風花雪月的往事”系列節目就把魯迅、郭沫若、沈從文、丁玲、徐志摩、蕭紅、郁達夫等的情愛故事搬上熒屏,對了解作家性情與創作觀念,是難得的資料。互聯網的便利使我們不必走進電影院,甚至無需耐心等待電視臺的節目播出,這為我們帶來了資料的豐富和讀取時間上的便利。就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而言,借助新媒體和互聯網,可以大量利用相關影像進行輔助教學。多媒體教學技術的廣泛運用,可以把以前單純的教師講解的平面化教學變為視頻、聲音、圖像的立體化課堂,大大增加了課堂教學中的信息量和直觀性,使課堂教學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在今天,通過影像來集約作家作品信息,不失為教學與時俱進的需要。
二
影像資料在給現當代文學教學帶來內容的豐富與形式多樣的同時,影像閱讀也可能給大學文學教育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一是影像與文字在表意方式上存在差異,影像作品對文學作品的詮釋可能存在大量意義貶損或者附贅情況,有可能干擾甚至扭曲受眾對文學作品的認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屬于“冷”媒介,“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度卷入、積極參與、填補信息”[2]7,因此文學閱讀需要想象力與語言難度的雙重克服。而影視依靠的主要是表演、臺詞、音響、氛圍烘托和蒙太奇等剪輯手段,是技術化和群體創意的產物,依托的是導演、明星的人氣效應。影視作為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其與文學表現在“語言”和方式上存在差異,這會帶來二者在內涵詮釋深度上的區別。文學的本體是語言以及對語言的創造,而影像主要依賴的是對技術的運用。文學的語言內部張力更豐富,讀者二度創造的空間更大;影像的直觀性,在調動讀者想象力方面比之文學來說有所欠缺。所以,文學作品常常在影視改編中造成意義的流失,甚至為了迎合觀眾而進行情節演繹和附贅。特別是今天的很多影視作品,走明星路線,對文學作品意義的闡釋往往迎合世俗和時尚趣味。如電視劇《京華煙云》、《啼笑因緣》,與小說相比,都存在過分煽情的傾向。而對小說《白鹿原》的電影改編,導演所重的是小說中的情欲糾葛,白靈等重要人物都未出場,很難見出深刻的社會文化批判內涵。當然,也不乏《芙蓉鎮》那樣改編成功的案例,其豐富的人文和人性內涵,似乎比原作的意義更為豐富,但這樣的作品需要高超的導演和出色的演員,類似的影視作品鳳毛麟角。就整體而言,文學作品的影像改編,基于影視受眾的大眾化和表現方式的具象化,大多都很難企及文學文本意義和內涵的豐富性。王安憶就批評說:“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印象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3]88
二是影像的直觀容易導致人們感覺的遲鈍與心靈的粗鄙化,這與文學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文學是探討人類可能性的藝術,是偉大心靈在不同時空中的幽思感嘆,文學可以抵達鏡頭無法觸及的地方,抵達人的精神高處和內心深處。讀者通過和偉大心靈的交流,從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影像主要依賴于視覺印象的直觀,故是人類童年期的最愛。讀圖較少深度情感的摻和,尤其缺乏心靈的共振與搖蕩,容易造成心靈的惰性和情感上的從眾,使人沉迷于世俗趣味。人自由敏銳的心靈往往容易被影像的平面化直觀性所俘獲。心理學研究證實,長期置身圖像環境的人對世界的感受能力會有所下降,而且圖像往往帶著物的痕跡,容易造成人的詩性感悟力的衰退,從而影響到人的想象力和創造欲望。“影視表現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眾化要求,造成了文學文本想象空間被擠壓,掏空了文學的詩性和美感,使文學本性中的崇高越發不能承受影視化接受之輕。”[4]現代人喜歡影像直觀帶來的視覺快感,常常忽略了對思想和心靈的深度開掘,從而造成對世界詩意把握能力的退化,這是需要加倍警惕的。
三是影像的時尚追求與文學的精神性之間存在矛盾。影像以吸引人的注意力為第一要旨,往往追慕時尚,打著時代的烙印和追逐商業利潤的痕跡。即使是改編于上世紀的影視作品,時代印痕也非常明顯。當今的電視媒體,被稱為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受眾的寬泛,他們必須盡量調和滿足多數人的口味,追求審美的社會平均數。影視的大眾文化特征,其對世俗欲望的渲染、炒作,煽情就成為慣用的招數;媒體的行為往往帶著明顯的商業目的,那些用“文化”或者“藝術”精心包裝的東西,其背后多為利益所限,往往與藝術無關。如2004年北京電視臺播出的28集電視劇《林海雪原》,就給楊子榮、少劍波增加了許多三角感情戲,以至于被網絡戲稱為“林海情緣”。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借王琦瑤與幾個男性間的情感糾葛,重點是對城市與人生命運的思考,表現上海的市民化和對日常生活的偏愛。而被關錦鵬改編成電影,則變成了“一女四男”的情愛戲,小說被置換成了一個舊上海的情欲故事。文學追求的主要是精神價值,是盡量遠離現實的理想高蹈。雖然受消費文化濫觴的影響,文壇也出現了大量的時尚化讀物,但文學的世界主流還是其對高貴精神的捍衛和對人性豐富可能的透視,尤其是對人類詩性的堅持。作為文學教育者,我們不排斥影像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但我們更應堅守文學的精神礦藏,尤其是不能通過影像讀圖來替代文學文本的閱讀體驗。
四是文學作品在影像改編中容易出現時代性的誤讀現象。影像比之文學而言,具有更強的社會文化特征,這也造成一些影像對文學作品意義的理解帶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阿Q正傳》經過1958年和1981年兩次電影改編,前者明顯是在附和政治革命,后者又過分夸大人物的喜劇元素,尤其是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啟蒙意識的迎合,體現為另一種形式的教化。而到1999年改編成《阿Q的故事》電視劇的時候,后現代的戲說背離了原著的精神,惡搞與戲謔一起上陣,阿Q被打扮成一個后現代的“英雄”。一些當代文學作品的改編,更是被大眾趣味或者社會潮流牽著鼻子走。電影《白鹿原》走的是感情戲的路線,而電影《高興》把農民離鄉進城的艱難與悲情打上時代的亮色,把悲劇演成了正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影視劇改編,比較重視悲劇情愫與啟蒙情懷,而當下則過于強調欲望敘事與迎合社會主旋律。如果僅僅通過影像資料來理解文學作品,或者把影像等同文學作品,勢必導致對文學作品的誤讀。影像對文學作品的故事性詮釋較為容易,但對文學的美感和更深層次的內涵,尤其是詩性韻味的表現,卻有相當難度。面對影像質量的參差不齊,我們應披沙揀金,發現那些好的作品,但絕不可以把影像讀圖視為一條代替文字閱讀的捷徑。
三
如何利用新媒介時代影像資源獲取的便利,同時克服其負面效應來指導學生進行文學閱讀呢?我們不妨做以下一些嘗試。
首先,把影像作為一種資料補充,重點在激發學生對文學文本的審美閱讀興趣。教師的課堂不能是枯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閱讀”殿堂,尤其是對那些出身在新媒體時代的指上一族青年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但也不能成為“看戲”的劇場,更不能把講臺變成資料剪輯和展示的操作臺。好戲連臺,看似熱鬧,其實并不能帶來好的教學效果。教師應有主體的介入,以自己的方式引導學生對文學文本進行審美感知和閱讀,尤其是強調把對文學作品的技術性閱讀和感悟性閱讀結合起來,激發學生對文學閱讀的興趣,將文學作品作為藝術交還到學生手中。文學的閱讀既需要一定的知識,更需要生命和情感的參與和體會,借助影像的目的是把學生引入文學博大的殿堂,而絕不是把學生從文學豐富的文本世界引向一個直觀的圖像世界。
其次,教師對相關的影像資料要熟悉,能夠引導學生對影像文本與文學文本進行比較性閱讀,明確影像文本的成功和局限之處。教師要能夠讓學生在圖像與文字的雙重閱讀中游刃有余而不至失之偏頗。我們強調文學文本閱讀的同時,并非排斥對影像的閱讀和借用。二者應互為補充,互為印證,互相激發藝術的想象與體驗。因為當代很多文學創作與影視關系密切。王朔坦言在1988年以后的創作幾乎無一不受影視的影響。他的小說《我是你爸爸》最初就是馮小剛一個電視劇的設想;小說《千萬別把我當人》實際上是張藝謀、楊鳳良、謝園、顧長衛等的一次集體創作的結果[5]。文學與影視的互動催生在當下文學創作中并非特例,這也啟發我們對文學的接受與觀照方式有進行調整的必要,純粹學院式的文學教育在新媒體時代的今天看來難免有些理想主義,也可能存在諸多盲點。
第三,教師要引導學生進行正確的文學和影像閱讀。教師要對學生進行文學閱讀和影像閱讀的知識教育,讓他們能夠在各自的知識規范中進行閱讀,明確彼此的界限和特點,做到不互相僭越,彼此替代。讀不懂本身,一方面可能是作品的難度所致,但也很可能是閱讀方式的問題,尤其是相關背景知識的欠缺。影像本身切合了新媒體時代的特點,也契合這個時代人的存在本質,是人的審美欲求與技術的合謀。而文學本身,雖有希利斯·米勒等終結論的說辭,但在深刻性方面依然體現出難以替代的優勢。相信隨著影像技術的提高和美學觀念的進步,影視對文學作品意義的詮釋空間也會大大拓展,影視反芻文學不是沒有可能。張藝謀曾說電影永遠離不開文學這根拐杖[6]10,其實,反之亦然。在今天,如果文學對影像的力量視而不見,難免給人文學有自欺和自負的嫌疑。
[1][德]馬丁·海德格爾.世界圖像的時代[M]//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2][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王安憶.小說家的十三堂課[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4]儲兆文.影視化接受:文學不能承受之輕[J].唐都學刊,2004(5):103-105.
[5]王朔.我看王朔[N].北京青年報,2001-01-11.
[6]李爾葳.張藝謀說[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張新玲)
Ut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Image Resources in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U Zhi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The tendency of video material of literature in image times provides rich resources for the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has reduced and obstructed the richness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nly by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ut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video material, a good mastery of the re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video material and a sound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of illustration and text can we effectively use video material in literature teaching.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ideo; utilities;
G642
A
1009-8135(2014)06-0141-04
2014-07-10
劉志華(1972-),重慶銅梁人,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美學。
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影像資源的效用研究:以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為例”(2012-GX-037);西南大學教改課題(2010JY06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