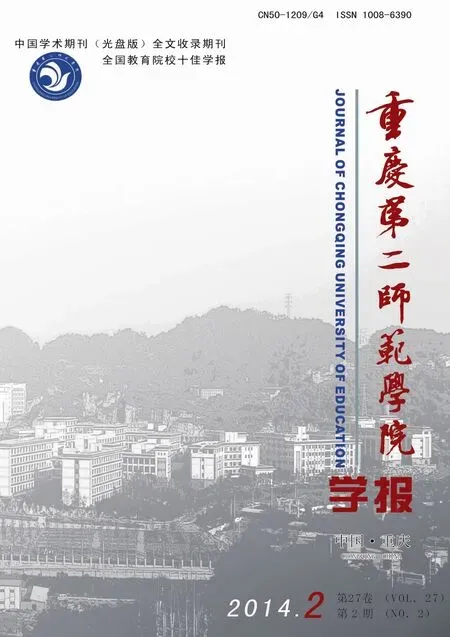論王小波與卡爾維諾小說創作的異同
——以《白銀時代》系列為例
毛 琴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伊塔洛· 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歐洲當代文學的曠世奇才”[1]。王小波被譽為“最具后現代色彩的作家”。他們二位都致力于“小說藝術有無限種可能性”[2],在王小波的閱讀生涯中,卡爾維諾是他最推崇的一位作家,他曾說:“我喜歡奧威爾和卡爾維諾,這可能因為,我在寫作時,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3]王小波在讀卡爾維諾的論著《美國講稿》時這樣說:“我一直喜歡卡爾維諾,看了這本書,就更加喜歡他了。”[4]可見,卡爾維諾對王小波的創作生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王小波的創作也多少呈現卡爾維諾的痕跡。筆者將從故事內容、敘事技法和思想內涵三個方面來探討王小波與卡爾維諾小說創作的異同之處。
一、故事內容的異同
王小波和卡爾維諾的創作都體現了康德“藝術即是自由”的觀點,他們暢游于各自創設的小說世界中,以頑童的心態“玩弄”文字,創作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始于自由,終于自由,他們對故事內容的設置都十分離奇,通過離奇的想象力和創作力來實現他們的自由人生。卡爾維諾“喜歡自由發揮——他的一篇小說叫《我們的祖先》,就是自由發揮,可以算作是一種寫法。其實也不叫‘歷史小說’,就叫‘小說’好了。它常常在一個虛擬的時空里自由發揮,寫出來相當好看,更容易進入一種文學的狀態,不受現實的約束,和紀實文學也徹底劃清了界限”[5]。《分成兩半的子爵》講中世紀后期梅達爾多子爵因戰爭而身體一分為二,又合為一體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樹上的男爵》寫17世紀意大利貴族少年柯希莫因反抗專制家庭而上樹終其一生;《不存在的騎士》以中世紀為背景,講述身體不存在的騎士阿季盧爾福為了證明自身存在而不斷探索,最終失敗而消失于樹林中。卡爾維諾生活在20世紀,這些故事都發生在他虛構的過去時空。梅達爾多的身體被炸成兩半還能存活,柯希莫在樹上終其一生,阿季盧爾福空有一身鎧甲還能驍勇善戰,這些故事如此離奇但并不虛無縹緲,所蘊含的意旨十分深刻。卡爾維諾大學畢業后曾為意大利共產黨工作,對二戰后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相當熟稔,《我們的祖先》就是他對社會的極度不滿及對自由的無限向往。
關于想象,王小波認為:“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6]正是想象力的驅使,使得王小波一反常規,馳騁于自由時空,任意書寫現實生活,看似荒誕不經,實則呼出了他的心聲。在《白銀時代》系列小說中,“作品都是以未來時間為舞臺,以我們這個時代的烏托邦邏輯為經緯,推展演變。電腦時代的網絡空間、藝術家、知識分子的趣味和他們受到鉗制,變得滑稽可笑的情形出現在小說中”[7]。《白銀時代》將“我”放置于2020年這一時空中,通過回憶“我”的大學生活來展示“我”現在的生存狀態;《未來世界》將“我”置身于未來世界,“我”為死去的舅舅寫傳記而犯錯誤,進而導致我現實的災難。王小波將“我”放置在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空來講述“我”和舅舅的生活處境,時空跨越非常大。在《未來世界》中,“我”將舅舅的真實生活公之于眾卻犯直露和映射錯誤,并遭公司的安置,一切財產被沒收,所有身份也被取消,“我”的自由完全被剝離。王小波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對人間的陰暗面了解較深,他設置如此離奇的故事內容更能揭示出他因反烏托邦的思想和對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系統極盡顛覆之能事,王小波放逐了社會。王小波將自己對現實社會的真實感受以不可思議的態勢映射到作品中,可見他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王小波和卡爾維諾都具備豐富的想象力,對故事內容的安排別具一格。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以過去時空為舞臺,主人公的生活空間都設定在過去,作品通過寓言故事的形式揭示現實生活哲理。《樹上的男爵》講述17世紀意大利貴族少年柯希莫為了自由而反抗專制的父親,實質上是卡爾維諾對專制的痛恨和自由的向往。卡爾維諾所設想的故事內容都發生于過去,并且無論多么離奇,總是充滿現實社會氣息并有一定的社會效應,作品極具感染力和說服力。而王小波的《白銀時代》系列小說是以未來時空為舞臺,以過去的生活為輔助物,通過過去的離奇故事來揭示他對現實的失望與憎惡。王小波所設置的故事內容跨越比較大,主人公的身份不斷穿梭于過去與未來。相較而言,卡爾維諾小說的時空跨度較小,而王小波的小說時空跨度較大,時空的跳躍性特別強。
二、敘事技法的異同
王小波和卡爾維諾是極具后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家,他們的小說籠罩著一股濃厚的后現代主義氣息。在《白銀時代》系列小說和《我們的祖先》中,他們二位都將嚴肅的哲理與插科打諢混為一體,還將其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情緒通過一些可笑的或不可思議的言行發泄出來,不僅諷刺意味濃厚,還染上了后現代主義特色。他們的小說創作超越了傳統,實現了現代化,但敘事技法還是與傳統一脈相承。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采取連貫敘述與插敘相結合的手法,《分成兩半的子爵》以連貫的敘述手法講述梅達爾多子爵的故事,在連貫敘述的同時,又采用插敘的手法介紹人物的身世。梅達爾多善良的一半出現并幫助帕梅拉姑娘時,插入他的經歷,“原來炮彈并沒有把他的身體炸碎,而是劈成了兩半:一半被軍隊的收容人員收走了,另一半被埋在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尸體之下”,這就將善良和邪惡子爵的不同形象公之于眾。卡爾維諾采取這種手法使文章既不晦澀難懂,又條理清晰、格局妥當。他還采取限制敘事視角來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我們的祖先》都采用第一人稱的手法展開故事情節,“我”主要講述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講述他人的故事。通過第一人稱敘事手法的使用,文章的內涵更加真實,卡爾維諾本人的精神機制也一目了然。在《我們的祖先》中,卡爾維諾不追求跌宕起伏的情節,為讀者設置良好的情節來琢磨文本的精神實質。卡爾維諾終其一生對小說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大膽的探索與革新,“他的每一部作品風格迥然,但無不閃耀著對藝術異常嚴肅而又無比大膽的探索精神的奇妙之光”[8]。他在追求現代化精神內涵的同時,對小說敘事技法的安排回歸了傳統,這體現他對藝術大膽而執著的探索精神。
王小波追隨了卡爾維諾對傳統性的回歸,他的《白銀時代》系列小說也采用了連貫敘述與插敘相結合的手法和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情節的安排清晰明了。在《未來世界》中,“我”因為替死去的舅舅寫傳記而犯錯誤,并因此為自己招致了禍害。不管是“我”的遭遇還是舅舅的故事,展現的是王小波本人的傷痛與困惑。王小波在《未來世界》中采取連貫的敘述講述“我”為舅舅寫傳記而遭受一連串迫害的故事,同時在“我”寫傳記的過程中大量插入了舅舅過去的感情生活。這種連貫敘述與插敘相結合的手法也使得文本的情節發展有一條清晰的脈絡,提高了文本的吸引力。
王小波和卡爾維諾對敘事技法傳統性的安排,為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領悟文本的真諦。但二位對敘事技法的細節處理有所不同,王小波小說故事時間的跳躍性較大,他將主人公放置在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空,而卡爾維諾將主人公放置過去與現在兩個時空中,同時王小波對插敘的使用頻率也很高。在采取第一人稱限制敘事的手法上,卡爾維諾將“我”與“他”的故事放置在同一時空下,而王小波打破了單一的時空,將未來的“我”與過去的“他”雜糅在同一背景下,通過“我”的磨難來揭示王小波的困惑與寂寞。在故事情節的處理上,二位都極力追求情節發展的清晰,但王小波小說的情節顯然要比卡爾維諾復雜。《我們的祖先》主要講述梅達爾多、柯希莫和阿季盧爾福的故事,“我”雖不時參與其中卻只是他們的代言人,故事情節是圍繞他們展開的。而《白銀時代》系列小說講述過去的“我”、舅舅或小舅的故事,突顯更多的是“我”的現實處境,故事情節不時在“我”與“他”之間交替展開。
三、思想內涵的異同
小說的重心“主要在于呈現敘述者對人生的主觀感受和體驗,以及由這種感受和體驗所引發的一種特定情緒”[9]。無論是故事內容還是敘事技法的設置,最終都要落腳到思想內涵上。小說必須具備深刻的思想內涵,正如孫紹振所說:“現代讀者的主體性很強,作家提供必要的信息,然后讀者去補充,留下的空間大,想象的空間大,那是對讀者的尊重,作家把什么都講得清清楚楚,描寫得那么細致,沒有讀者介入的余地,也就是沒有感染力。”[10]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通過寓言故事揭示了不同的人生真理,《樹上的男爵》中柯希莫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我才不在乎您的列祖列宗哩,父親大人”,可見他叛逆的天性。他自從反抗父親的專制爬到樹上后,與樹相依為命一直到死。他在樹上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和人間誘惑,通過自己的舉止感化作惡多端的人。樹上的柯希莫就是理想、高尚、自由的象征;地上的父親則是專制、邪惡、虛偽的象征。“樹上的柯希莫”是卡爾維諾一味追求的理想境界,可現實卻與“地上的父親”是一丘之貉,讓人難以忍耐。《樹上的男爵》揭示了卡爾維諾對戰后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的批判與反抗精神,也表達了他對自由的無限向往。
在王小波的《白銀時代》中,“我”在寫作公司寫作《師生戀》這部小說,正是《師生戀》的寫作導致“我”的不幸遭遇。《師生戀》回憶的是“我”的大學生活,“我”與大學老師之間的往事穿插在現在的工作環境中。“我”的真實生活遭到領導的槍斃,只能按照領導的指示來虛構生活。“我”對現在的生活深惡痛絕,只想回到過去的美好回憶中,這體現了王小波對現實社會的嘲諷與戲謔。王小波師承英美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學派,對卡爾維諾和羅素批判與思考的精神十分推崇,他的作品顯示的就是對現實社會權力至上、人際關系的冷淡和虛偽、集體道德的理性缺失等的批判。
王小波和卡爾維諾小說的思想內涵有很多相似之處,如他們對自由的無限向往、社會的批判以及自己現實處境的無奈與憤懣等等,但是他們的傳達方式不同。卡爾維諾將主人公放置于一定的生活空間之外來觀察生活,更能看清社會現實。《樹上的男爵》中柯希莫自從反叛傳統、專制的父親爬上樹后,一直與大地分離但又密切地關住人間的一切。柯希莫看清了社會現實,憑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些冥頑不化的人。卡爾維諾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相當失望與憎惡,但他并沒有置之不理,通過作品感化更多的人。王小波的《白銀時代》系列小說將主人公安置于過去、現在、未來的空間中,但是主人公與生活近距離接觸,通過主人公對生活的體驗和主觀感受來直接展示他最真實的感受。《2015》中“我”因為脫離主流社會而經歷種種磨難,“我”一直在尋藝術真諦,這也是王小波對生活真諦的探索。
王小波相當推崇卡爾維諾“輕逸”的小說藝術價值,他認為小說不應當負載不堪忍受的義務。他們都相信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充分發揮作者的主觀能動性才能顯出藝術的真諦。不論他們對小說創作的故事內容、敘事技法和思想內涵如何安排,最終目的都是表達對現實生存處境的感慨。“王小波嗜讀卡爾維諾,認同他那種探索無限的寫作,并明確承認主要是以卡爾維諾的小說為摹本。”[11]卡爾維諾對王小波創作生涯的影響毋庸置疑,但他們的小說創作也都獨具風格,為后來的中外文學研究開創了廣闊的道路。
參考文獻:
[1]袁華清譯.白天的貓頭鷹——意大利當代中篇小說選[M].北京出版社,1989.2.
[2]王小波.卡爾維諾與未來的一千年[A].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上)[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2.
[3]王小波.王小波小說全集·《未來世界》自序[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57.
[4]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316.
[5]黃集偉.王小波:最初的與最終的[A].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上)[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90-91.
[6]王小波.關于幽閉型小說[A].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上)[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67.
[7]艾曉明.不虛此生——紀念王小波[A].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上)[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79.
[8]呂同六.多元化,多聲部:意大利二十世紀文學掃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112.
[9]馮光廉.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168.
[10]孫紹振.文學性講演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69.
[11]張懿紅.王小波小說藝術的淵源與創化[A].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下)[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