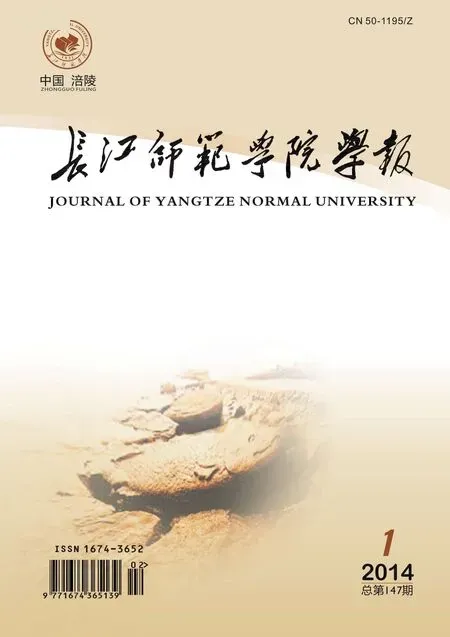試論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張 銘,李娟娟
(1.西南師范大學 出版社,重慶 400715;2.巴川中學校,重慶 402560)
試論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張 銘1,李娟娟2
(1.西南師范大學 出版社,重慶 400715;2.巴川中學校,重慶 402560)
隋唐時期,由于 “揚一益二”的經濟格局,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特別是作為帝王、文人等關中、河南民眾逃避戰亂的戰略后方,巴蜀地區被隋唐中央政府倚為根本,在兩朝中央政府的關注之下,巴蜀地區各項事業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巴蜀先民承接先秦至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開發態勢,對巴蜀地區的生物資源再次進行了深入的開發。較之前一階段的開發,這一時期巴蜀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更為深刻、更為廣泛、更為專業。無論地域、規模還是專業化程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高度。這里試圖將這一時期巴蜀生物資源開發進行分類整理分析,以期揭示這一時期巴蜀生物資源的開發進程與特色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生物資源;開發;交流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在長期相對安定的社會條件及優越的自然環境之下,承接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開發態勢,其經濟地位在全國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雖然司馬光稱為 “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 ‘揚一益二’”[1]。但是唐王朝卻倚巴蜀為根本,國家有難,皇帝便逃亡巴蜀,如唐玄宗與唐僖宗奔蜀[2]。成都能成為唐王朝倚重的根本與長江上游最重要的商業大都市除了其工商業的繁榮外,在傳統農業社會里,農業是其發展的根本,而農業的發展與巴蜀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密不可分。這里即通過對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流的探討為契機,從一個側面展示隋唐時期巴蜀地區資源開發的盛況。
生物資源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人類可以利用與可能利用的生物,包括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和微生物資源等,這三類資源是不同的,互不隸屬。在隋唐時期,先民們生物資源的開發主要集中在植物資源和動物資源上面,有關微生物資源的史料較少,以靈芝為代表,主要作為祥瑞或者災異的征兆。如 “武徳四年 (621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占曰:“王徳將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草亦木類也。”[3]為論述清晰起見,本文將植物資源的開發主要分為木材類生物資源的開發,糧食作物類生物資源的開發,經濟作物類生物資源的開發,瓜果、蔬菜、香料類生物資源的開發。將動物資源的開發主要分為養殖業類型的動物資源開發、捕獵類型的動物資源開發和水產業類型的動物資源開發。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木材類生物資源的開發主要體現在這一時期巴蜀居民營建房舍、衙署、寺廟等建筑、車船等交通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上面。隨著外來移民的增加和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巴蜀地區人口密度大幅度的提高,圍繞成都的益、漢、蜀、彭四州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200多人,是唐代相同大小區域內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4]。如當時巴蜀地區居民房屋多為木構架,眾多的人口需要相應數量的房屋,如此眾多的人口使得巴蜀地區生產生活用的木材數量也逐漸增加,城鎮周邊的林木被砍伐殆盡,逐漸地向邊遠地區采伐。隨著巴蜀地區經濟的發展,在巴蜀地區用于運輸各種物資或商品的船舶建造更加昌盛。隋初巴蜀地區就能建造容納八百名戰士的大型單體船,單體船建造技術發展很快,而舫船建造似乎沒有明顯的進步。唐代亦是延續隋代造船格局,即以單體船為主,舫船為輔[5]。這一時期巴蜀地區造船場主要分布在長江、岷江和嘉陵江沿線,主要有成都府、邛州、眉州、雅州、夔州、南州、黎州、嘉州、渝州等,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成都府、夔州、嘉州、渝州[6]。隨著這些地區造船業的興起,其周邊適于造船的林木材料逐漸被砍伐殆盡,如成都府就因建筑材料缺乏及航道逐漸湮沒,其造船業也逐漸衰落。當時巴蜀地區造船用木的上好材料是楠木,隨著城鎮周邊地區楠木的砍伐殆盡,巴蜀地區也開始廣泛種植楠木,當時以四川地區楠木種植最為廣泛[7]。巴蜀地區在隋唐時期佛、道等宗教逐漸興盛,這些宗教的興盛帶動了巴蜀地區佛寺、道觀等宗教建筑的興建,當時成都城內的佛寺和道觀建筑是僅次于官廳的龐大壯觀建筑,這使得巴蜀及其周邊地區適于建筑的大量木材又一次遭到砍伐。而巴蜀地區為保證交通順暢而大量修建的棧道也使得沿線木材得到開發利用。當時巴蜀地區采鹽業的興起也使得巴蜀地區的竹木資源得到了廣泛應用。當時竹類資源在采鹽業中的應用主要是:巨竹固井;竹筒采鹵,主要采用斑竹、壽竹、楠竹;竹制井篾,用于鑿井;竹篾索,用于汲鹵;此外還有竹把手、竹拭篾等,可見竹類資源在當時的應用之廣泛[8]。除這些大型建筑用材外,巴蜀地區的眾多生活器具也加速了這一地區木材類生物資源的開發,如當時彭州蒙陽郡的交梭、卭州臨卭郡的酒杓、合州巴川郡的竹箸、書筒還作為貢品貢入中央[9]。這些生活用具,能作為貢品貢入中央,足見其質量的上乘與工藝的精湛,也只有在其大規模生產并名聲在外后才能作為貢品貢入中央。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糧食作物類生物資源的開發主要表現為糧食種類的增加與糧食種植范圍的擴大。隋唐時期隨著巴蜀地區水利事業的發展,水稻的種植范圍逐漸由成都平原向北擴大到地處涪江沖積平原的綿州,向南擴大到位于岷江沖積平原的眉州,在沱江、嘉陵江、長江等河流形成的沖積平原上也都有水稻的種植,但是這一時期水稻種植始終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鄰的涪江沖積平原和岷江沖積平原[10]。而巴蜀邊遠地區的水稻種植業發展則很不均衡。如位于巴蜀邊遠地區的嶲州,唐代設置了8處屯田,約有屯田400頃。這些屯田多分布于清溪古道沿線的安寧河谷地帶。南詔占領嶲州以后,將部分從事農耕生產的白蠻遷入今西昌、會理盆地等處從事水稻種植等,不過唐代嶲州需從內地轉運糧食接濟,估計當時安寧河谷水稻糧食作物種植規模較小,尚不足以供給當地消費[11]。而同樣位于巴蜀邊地的夔州城外則 “東城稻谷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豐都出現了新品種稻谷的培育,重恩稻 “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精耕細作,使三峽居民向平壩、寬谷以外的淺丘、山地進軍,形成了三峽地區的畬田農耕運動[12]。不僅三峽地區如此,巴蜀內地也多緩山和丘陵,除在沖積平原種植水稻外,緩丘和山地則主要將水稻種植在梯田中,通過向山和向丘陵要田的方式擴大耕地面積,杜甫和張九齡都在其各自的作品中描寫過當時巴蜀地區梯田盛行的景象[13]。黍和粟是巴蜀地區種植最為古老的旱地作物,這一時期的主要種植地區有所縮減,主要集中在今四川盆地內的丘陵低山和盆周山區,其中畬田種植黍和粟比較廣泛[14]。如 “忠州刺史已下悉以畬田粟給祿食”[15]。由于巴蜀地區糧食生產的興盛,以糧食為原料的釀酒業也開始興盛。成都府蜀郡土貢的“生春酒”就極負盛名[16]。《舊唐書·德宗本紀》載:“劍南歲貢春酒十斛”中的 “春酒”,亦是 “生春酒”或者 “燒春酒”。岑參詩云:“成都春酒香”,雍陶詩稱:“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更身入長安”,都是對巴蜀地區所產高品質酒的贊美。由于前往關中地區的道路較為困難,往關中直接運糧較少,多以價值較高的酒類商品作為運往關中的物資。而巴蜀地區順長江及其支流向東運糧則較多,如德宗時由于 “四鎮”之亂,巴蜀糧食即 “方舟而下”轉運至洛陽。
經濟作物類生物資源的開發主要是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絲織品、麻織品、茶葉等生物資源的開發。在蠶絲生產方面,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的絲織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蜀錦在唐代與 “齊紈”、“楚練”齊名,僅四川一地就有28州產絹,占當時全國87個產絹州的三分之一[17]。這一時期重慶地區的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有研究認為唐代重慶的絲織品至少有7種,但與當時成都及其附近地區以及四川盆地中部一些絲綢中心區 (如閬、果、渠州)的絲織品相比,則顯得品種少,質量差。唐代重慶絲織品產地和品種在唐代后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產地主要是后期新增了昌州和夔州。這時重慶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是與今日四川緊密相連,地處嘉陵江流域的遂州的遂寧、青石二縣和普州的崇龕縣;其次是合州以及長江沿岸的忠州、開州、夔州等地[18]。實際上忠州的絲織業也較為發達,其產品黃絹不僅為刺史以下的官吏充俸,還作為貢品貢奉中央[19]。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的紡織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當時巴蜀地區各州郡幾乎都有各自的高品質紡織品或紡織原料進貢中央,分別是:夔州云安郡的纻錫布,忠州南賓郡的綿綢,涪州涪陵郡的獠布,興元府漢中郡的縠,洋州洋川郡的火麻布、野苧麻等,利州益昌郡的金絲布,鳳州河池郡的布,文州陰平郡的紬、綿等,壁州始寧郡的綢、綿等,蓬州蓬山郡的綿綢,通州通川郡的紬、綿等,開州盛山郡的白纻布、閬州閬中郡的綾、綿、絹、紬、縠等,果州南充郡的絹絲布、渠州潾山郡的紬、綿等[20]。以及成都府蜀郡的錦、單絲、羅、髙杼布、麻等,彭州蒙陽郡的叚、羅等,蜀州的錦單、絲、羅花紗等,漢州徳陽郡的雙紃、彌牟、纻布衫、叚、綾等,卭州臨卭郡的葛絲布、簡州陽安郡的葛、綿、紬等,嶲州越嶲郡的絲布、花布等,戎州南溪郡的葛纖,梓州梓潼郡的紅綾、絲布等,遂州遂寧郡的綾絲布,綿州巴西郡的輕容、雙紃、綾、錦等,劍州普安郡的絲布等,普州安岳郡的雙紃、葛布等,渝州南平郡的葛,陵州仁壽郡的鵝溪絹、細葛等,榮州和義郡的綢、班布、葛等,瀘州瀘川郡的葛布、斑布等[21]。巴蜀地區如此眾多的州郡向中央貢奉高品質紡織品或紡織原料,足以證明這一地區紡織業的發達。隋唐時期巴蜀的絲織品在巴蜀對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唐代四川每年賜給黎州淺蠻衣3000匹使其觀察南詔,唐朝官兵在戰爭中被南詔俘虜后,往往許以30匹絹才能贖回[22]。這一時期南詔還直接從巴蜀地區獲取絲織品成品,通過各種手段獲取成都的紡織技術和技工,如大和三年 (829年),南詔引兵抵成都,陷西郭,“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23]這些 “子女、百工”多是紡織界的能工巧匠,他們的遷入直接促進了南詔紡織技術的發展。在巴蜀紡織人才和技術的幫助下,南詔所織錦絹 “密致奇采”,成為緬甸婦女的披錦緞,南詔還利用緬甸不產錦緞的情況迅速利用自身通巴蜀紡織技術的優勢搶占了緬甸市場[24]。而除因政治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巴蜀絲織品對外交流外,隋唐時期巴蜀絲織品也作為大宗商品遠銷海內外。雖然這一時期有南詔阻隔了巴蜀地區對東南亞、南亞的絲織品貿易,但是通過邕州道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巴蜀絲綢也能轉運并行銷印緬。
這一時期另外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茶也開始大規模生產。由于西周時期巴蜀地區的茶葉即是其重要貢品[25],如此悠久的茶葉生產歷史造就了隋唐時期巴蜀茶葉的優良品質。唐朝北方與西北方向少數民族飲茶風俗的興起也大大促進了巴蜀等南方地區茶葉資源的開發。由于這一時期長江中部的今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各省的茶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使得巴蜀地區的茶葉地位相對有所下降,但巴蜀地區的茶葉品質依然很高,自身相對于前代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當時四川的茶業,已經基本上與糧食生產分開,成為一個單獨的產業部門,極大地促進了其商品化進程,使得當時 “惟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以后,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其為功德也如此。”[26]如此優秀的品質與盛名使得巴蜀眾多地區的茶葉成為唐王朝貢品,當時巴蜀地區茶葉能作為貢品的州郡有夔州云安郡、興元府漢中郡等[27],以及雅州盧山郡等[28]。隨著巴蜀地區漢代開始種植甘蔗,巴蜀地區的甘蔗種植地域逐漸擴大,到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甘蔗的主要產地已經擴大到益州、蜀州、資州、梓州、綿州、遂州、巂州等州郡。這一時期甘蔗的種類主要有兩種,一類是果蔗,只能生吃,不能制糖;一類是糖蔗,雖可生吃,但主要用于制糖。制糖工藝也有很大的進步,能夠生產沙塘、乳糖、蔗霜等茶品[29]。隨著巴蜀甘蔗種植業的發展,巴蜀地區甘蔗及其產品逐漸成為貢奉中央的貢品,如成都府蜀郡的蔗糖、梓州梓潼郡的蔗糖、綿州巴西郡的蔗等即是作為貢品與關中地區進行交流的[30]。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產紙區域,出現了大批造紙作坊和造紙戶,提高了造紙的專業性,專業化的生產使得巴蜀的造紙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時的蜀紙特別是麻紙已聞名天下,造紙原料主要有桑、麻、藤、竹、褚、麥稈、芙蓉皮等草類植物纖維,其時用竹造紙屬于新工藝,而巴蜀已有大量竹紙生產了[31]。當時寫成的 “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32],“其后,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33]。蜀紙能夠成為唐王朝中央的御用紙張足見其技藝之高超,而如此大量的紙張供應也可見當時巴蜀紙張專業化生產的規模與產量。中唐人李肇在 《國史補》中也提到 “紙之妙者,則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等,這更是對蜀紙技藝的直接贊美[34]。其時蜀中佳紙,制以為箋,早有盛名,杜甫已有 “蜀箋染翰光”的詩句。韋莊 《乞彩箋歌》之一:“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閣深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即描述了薛濤在浣花溪制箋的過程。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瓜果、蔬菜、作料類生物資源的開發主要體現在下述幾種產品上面。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水果莫過于杜牧在 《過華清宮》中描述的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茘枝來”中的荔枝了。楊貴妃所吃的荔枝即來自巴蜀地區的涪州,這一時期涪州所產的荔枝品質上乘,荔枝在涪州以南地區已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35]。這一時期也是巴蜀其他地區荔枝種植史上的鼎盛時期,其中宜賓地區 “僰道縣出荔枝,一樹可收百五十斗。”南溪縣“多荔枝”[36]。樂山地區在這一時期也是重要的荔枝產地,故薛濤 《憶荔枝》贊曰:“近有青衣連楚水,素漿還得類瓊漿。”這一時期滬州荔枝異軍突起,僅列于宜賓之后居四川荔枝第一等第二位。杜甫嘗到瀘州荔枝后,作 《解悶》贊曰:“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巴蜀地區東部的萬州、忠州一帶也出產荔枝,白居易作 《荔枝圖序》贊道:“荔枝生巴峽間,形園如帷蓋。”總之,這一時期的巴蜀地區在北緯31度以南的成都、重慶、宜賓、瀘州、涪陵、樂山、萬縣、雅安等地河谷地帶都有荔枝種植,其中北緯30度以南的樂山、宜賓、瀘州、涪陵四地品質最佳[37]。由于當時的保鮮技術限制,除向楊貴妃供奉的特例外,鮮荔枝的長途外運較少。當時能夠貢奉中央鮮荔枝的主要是距離長安較近的涪陵地區,故其他地區了解巴蜀地區荔枝盛況主要是通過鮮荔枝的相關詩文及荔枝加工而成的副產品得知,如當時戎州南溪郡的土貢中即有“荔枝煎”。 “荔枝煎”即是用荔枝制作而成的蜜餞,適于長途販運,故巴蜀周邊地區都能獲得這一美味[38]。柑橘也是這一時期巴蜀地區的重要瓜果之一,種植廣泛且質量上乘,當時能將柑橘作為貢品供奉中央的州郡就有:夔州云安郡、興元府漢中郡、文州陰平郡、巴州清化郡、開州盛山郡等[39],以及眉州通義郡、簡州陽安郡、資州資陽郡、悉州歸誠郡、梓州梓潼郡、綿州巴西郡、普州安岳郡、榮州和義郡等[40]。梅子也是隋唐時期巴蜀地區重要的水果之一。由于梅子的廣泛種植,鮮梅子制成的 “梅煎”也是巴蜀地區的重要零食之一,更是對外交流販運的重要商品之一。當時成都府蜀郡 “梅煎”更是作為貢品貢奉中央,這種特供也提升了巴蜀 “梅煎”的知名度,從而加大了巴蜀地區梅子這一水果的開發力度。蔬菜類生物資源的開發,這一時期巴蜀地區蘿卜大量種植,以蘿卜莖、葉等為原料制作的 “諸葛菜”在巴蜀地區廣泛流行;元修菜在這一時期也被廣泛開發成各種菜肴,在巴蜀民間廣泛食用;其他如大巢菜、苦菜、蕺菜、冬葵、薤、棕筍、苦竹筍、蕓苔菜、韭菜、芹菜、溫食瓜、秋泉瓜、生瓜菜、菠菜、莼菜、落葵等常見蔬菜做成的菜肴也在巴蜀民間廣泛食用。巴蜀人民早有食用野菜的習慣,這一時期巴蜀地區廣泛食用的野菜主要有野蕨菜、野生木耳、芥菜等[41]。當時巴蜀地區蔬菜中適于長途運輸的蔬菜上品也有貢奉中央的,如興元府漢中郡冬筍、糟瓜[42],以及綿州巴西郡的白藕就曾成為貢品貢入中央[43]。蔬菜類生物資源的開發必然伴隨著大量作料類生物資源的開發,否則大量菜品則無從成為美食。當時巴蜀地區廣泛使用的作料主要有蒟醬、姜、茱萸、花椒、桂子、食麻等[44]。由于作料便于保質和運輸,也是巴蜀對外貿易的重要產品,其中的上品也是巴蜀貢奉中央的貢品,如興元府漢中郡即以夏蒜作為貢品貢入中央[45];黎州洪源郡則以椒作為貢品貢入中央[46]。
藥用生物資源的開發方面,由于唐代醫藥發展相當完善,除傳統的私人傳授外,國家也采取措施,在太醫署設醫學,招收學生,廣泛普及醫藥知識[47]。在唐代醫學繁榮的背景下,巴蜀地區的藥用生物資源也得到了廣泛的開發,巴蜀眾多州郡中均有其上乘中藥材貢奉中央,主要有:萬州南浦郡的藥子,利州益昌郡的天門冬、芎藭等,扶州同昌郡的芎藭,集州符陽郡的藥子,通州通川郡的楓香、白藥等,開州盛山郡的芣苢,渠州潾山郡的藥實等[48],以及雅州盧山郡的菖蒲、落雁木等,茂州通化郡的羌活、當歸等,維州維川郡的羌活、當歸等,松州交川郡的當歸、羌活等,當州江源郡的當歸、羌活等,悉州歸誠郡的當歸,柘州蓬山郡的當歸、羌活等,恭州恭化郡的當歸、升麻、羌活等,真州昭徳郡的大黃,遂州遂寧郡的天門冬,合州巴川郡的藥實,龍州應靈郡的厚樸、附子、天雄、側子、烏頭等,普州安岳郡的天門冬,渝州南平郡的藥實,陵州仁壽郡的續髓、苦藥等[49]。如此眾多的州郡能將其土產藥材貢入中央,足見當時巴蜀地區藥物的豐富與開發的深入。
捕獵類型的動物資源開發主要表現在當時野生動物的獲取,除獲取野生動物的皮肉外,麝香也是捕獵野生動物資源的重要目標。麝香是當時阿拉伯商人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販運的主要藥材,因為產于益州等巴蜀西部地區的麝香質量上乘,阿拉伯商人認為 “療效極好”,這也加速了巴蜀地區麝香這類野生動物資源的開發[50]。當時巴蜀地區諸多州郡都有麝香進貢,主要有洋州洋川郡、利州益昌郡、鳳州河池郡、文州陰平郡、扶州同昌郡、通州通川郡[51],以及嘉州犍為郡、嶲州越嶲郡、黎州洪源郡、茂州通化郡、翼州臨翼郡、維州維川郡、姚州云南郡、松州交川郡、當州江源郡、悉州歸誠郡、柘州蓬山郡、恭州恭化郡、保州天保郡、真州昭徳郡、昌州下都督府等,如此眾多的州郡貢奉麝香,證明了巴蜀地區麝香的豐產,也證明了巴蜀地區麝這一鹿科動物分布之廣泛及其捕獵程度之高。據《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隋唐時期中國人用犀牛角做成的腰帶非常昂貴,當時野生犀牛主要分布在印緬交趾等地,但 “益、寧”也出產犀角[52],當地居民也捕獵本地野生犀牛以獲取犀牛角作為加工原料,杜甫 《冬狩行》即記載廣德元年 (763年)冬猛士三千在梓州行獵,“生致九青兕”的行動[53]。但是大多數犀角原料是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從印緬等地輸入巴蜀地區,經過當地工匠的深加工后再轉銷全國[54]。同時,隋唐時期巴蜀地區華南虎也分布廣泛,“唐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開元 (713—741年)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55]“開元(713—741年)末,渝州多虎暴。”[56]由于虎患漸烈,必然引起當地居民組織捕殺華南虎,主要為除掉虎害,當然也不乏獲取虎皮、虎骨等雙重的目的。熊羆也是當時巴蜀地區的捕獵對象之一,如夔州云安郡即以捕獵而來的熊羆作為貢品貢奉中央[57]。在小型動物捕獵方面,由于此時期巴蜀地區生態環境較好,野兔、山雞、狐貍、野生魚較多,都能成為人們的捕獵對象,天寶十四年 (755年)“劍南道獲白兔一,獻之”[58]。夔州云安郡也以捕獵的山雞作為貢品貢奉中央[59],松州交川郡即以捕獵而得的狐尾作為貢品貢入中央[60]。唐代沱江 “多魚鱉”,峽江地區 “頓頓食黃魚”,證明當時巴蜀地區捕魚的興盛[61]。
隋唐時期巴蜀地區畜牧養殖業類型的動物資源開發的格局主要是巴蜀邊地特別是以西部邊地出產的馬、牦牛、羊為主,而巴蜀內地則由于農耕的需要,主要出產水牛、黃牛作為耕作工具。這一時期巴蜀地區養馬業已發展成為國家馬匹資源供給地之一。蜀馬體型小,善攀爬,能適應山區托運和行走,為茶馬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運載基礎[62]。這一地區所產蜀馬的上品還要進貢中央,漢州徳陽郡、嶲州越嶲郡土貢中即有蜀馬[63]。養牛除獲取勞動力外還可提供皮、乳制品、肉等,如茂州通化郡即以干酪作為貢品進貢中央;翼州臨翼郡、維州維川郡、悉州歸誠郡、保州天保郡則以牦牛尾作為貢品貢入中央[64]。蜜蜂養殖也是這一時期巴蜀養殖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養蜂除獲取蜂蜜外,還要獲取蜂蠟。蜂蜜主要作為食物,也可用于釀制蜜酒,孟冼在 《食療本草》中指出蜜酒有食療的作用。隋唐時期還發明了蠟燭,唐代學者賈公彥記載了以蜂蠟制燭的方法,蠟燭己廣泛用于王侯家,永泰公主和章懷太子墓道壁畫上即繪有手持蠟燭的宮女,唐詩中亦有大量描寫蠟燭的詩句。除廣泛用于制蠟外,蜂蠟也廣泛用于印染、制作丸衣,加工成蠟丸(或蜜丸)傳遞重要文書[65]。如此廣泛的市場,注定了當時巴蜀地區養蜂業的繁榮。當時巴蜀地區諸多州郡有養蜂產品進貢中央,主要有夔州云安郡的蜜、蠟等,涪州涪陵郡的蠟,洋州洋川郡的蠟,利州益昌郡的蠟燭,鳳州河池郡的蠟燭,興州順政郡的蜜,文州陰平郡的白蜜、蠟燭等,集州符陽郡的蠟燭,巴州清化郡的石蜜,通州通川郡的蜜、蠟等[66]。以及眉州通義郡的石蜜、翼州臨翼郡的白蜜等[67]。
隋唐時期,由于 “揚一益二”的經濟格局,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皇帝、文人逃避戰亂的戰略后方,巴蜀地區被倚為朝廷根本,在兩朝中央政府的關注之下,巴蜀地區各項事業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與先秦到南北朝時期相比,這一時期巴蜀地區的生物資源開發更加廣泛和深入。如這一時期隨著巴蜀地區人口的增加與經濟發展的需要,林木采伐向遠離城鎮的更為邊遠的地區推進,林木的采伐量也大幅度增加;糧食生產的范圍突破河流沖積平原和較為寬廣的壩子,向開發難度更大的坡地推進,形成了壯觀的畬田景觀;由于北向路途較為艱難,巴蜀糧食外運以長江及其支流所代表的東向外運為主要路線;隨著紡織業的發展,巴蜀地區紡織產品在全國的地位顯得更加重要,能將其紡織產品作為貢品的州郡較前一時期更加眾多,而且這一時期巴蜀地區的紡織品更是行銷海內外;雖然這一時期巴蜀地區茶葉生產在全國的地位相對下降,但是其品質依舊上乘,仍有眾多州郡能將茶作為貢品貢入中央;在巴蜀舒適的社會生活環境中,蔬菜、作料的種類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上又有了增加,烹飪出了無數著名菜品;隋唐時期醫學事業的發展也使得巴蜀地區本身蘊藏豐富的中藥材資源得到了廣泛的開發;雖然這一時期漁獵經濟在巴蜀地區僅作為補充經濟,但是在巴蜀周邊地區漁獵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周邊州郡的貢品中不乏捕獵而來的珍禽異獸等漁獵產品;養殖業與前一階段相比較為明顯的變化是這一時期巴蜀地區養蜂業逐漸興盛起來,眾多州郡養蜂業的副產品作為貢品貢入中央,作為商品行銷全國。
在巴蜀地區對外交流方面,北向交流顯現出明顯的貢奉特色,即其貢奉物產占了巴蜀地區北向交流的主要部分,這主要是因為隋唐兩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均在關中地區。但是其間也有往復,如東都的興起,使得巴蜀地區對外生物資源東向交流也呈現出一定的貢奉特色。在東向交流方面商業特色較為濃厚,因為隨著經濟重心的東移南遷,揚州等東南地區的城鎮逐漸發展起來,在 “揚一益二”的經濟格局下,傳統農業社會中東向商品交流多與生物資源開發相關。南向交流的政治和商業特色都有一定呈現,因為南詔的興起,使得巴蜀地區與南詔處于首當其沖的地位,這使得巴蜀地區生物資源開發在南向交流方面,受中央與南詔關系的影響較大,如南詔入侵成都擄走當地技工,使得南詔的生物資源開發進程得以大幅度提高,而巴蜀地區由于人才資源的大量損失使得本地區生物資源開發進程受到一定的影響;當與南詔和平相處時,與南詔交流則呈現出商業貿易的繁榮局面。在西向交流方面,隨著唐代巴蜀與吐蕃地區茶馬貿易的興起,茶馬貿易在巴蜀地區生物資源開發西向交流方面占據著主要地位。在巴蜀地區四個主要方向的生物資源的交流中,西向交流因茶馬古道剛興起且與吐蕃和戰不定而影響較弱,東向交流因為長江及其支流、南向交流因為南方絲綢之路都較為方便,但是影響不及北向交流;北向交流因為先秦以來即已形成的交通格局且政治中心在關中的緣故,其影響最為重要,也是巴蜀生物資源貢品的主要流向。
[1][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M].四庫全書本.
[2]江玉祥.唐代劍南道春酒史實考[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
[3][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志)[M].四庫全書本.
[4]路 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421.
[5][10][14][29]李敬洵.四川通史(第三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98-399、285-286、286、404-406.
[6]夏自金.隋唐時期西南地區的造船場[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4).
[7]藍 勇.歷史時期中國楠木地理分布變遷研究[J].中國歷史地理理論叢,1995(4).
[8]杜紹慶.竹在井鹽生產中的應用[J].鹽業史研究,1988(3).
[9][16][19][20][21][27][28][30][38][39][40][42][43][45] [46][48][49][51][57][59][60][63][64][66][67][宋]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十二志第三十二地理志)[M].四庫全書本.
[11]朱圣鐘.歷史時期四川涼山地區森林植被的變遷[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2).
[12]藍 勇.長江三峽歷史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3.
[13]裴安平,熊建華.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269.
[15][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十一感傷三古體詞)[M].四庫全書本.
[17][22]黎小龍,藍 勇,趙 毅.交通貿易與西南開發[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42.
[18]盧華語.唐代重慶紡織產品芻議[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2).
[23][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四唐紀六十)[M].四庫全書本.
[24]孫仲文.隋唐時期的西南絲路及貨幣[J].云南金融,1997(11).
[25][東晉]常 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M].四庫全書本. [26]陳 虹.四川茶葉生產的歷史考證[J].農業考古,2000(4).
[31]鄧劍嗚.薛濤箋在中唐時期對四川造紙業的影響與貢獻[J].中國造紙,1993(6).
[32][五代]劉 呴.舊唐書(卷四十七經籍志第二十七經籍下)[M].四庫全書本.
[33][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第四十七)[M].四庫全書本.
[34][北宋]倪 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九歷代書論三十九器用之三紙譜)[M].四庫全書本.
[35][37]藍 勇.四川荔枝種植分布的歷史考證[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4).
[36][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二劍南道)[M].四庫全書本.
[41][44][61]藍 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70-274、275、274.
[47]計光輔.唐代的醫藥機構與醫科大學[J].中醫藥文化,2007(4).
[50]藍 勇.唐宋川滇滇緬通道上的貿易[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1).
[52][唐]魏 征,等.隋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二梁睿傳)[M].四庫全書本.
[53][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二)[M].四庫全書本.
[54]藍 勇.南方絲綢之路[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2:99.
[55][宋]李 昉,等.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虎一)[M].四庫全書本.
[56][宋]李 昉,等.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虎二)[M].四庫全書本.
[58][宋]王欽若,[宋]楊 億,等.冊府元龜(卷二十四帝王部符瑞第三)[M].四庫全書本.
[62]李永桂.四川畜牧史略[J].四川畜牧獸醫,1995 (3).
[65]楊淑培,吳正愷.中國養蜂史大事記[J].古今農業,1994(3).
[責任編輯:丹 涪]
F329.4.7
A
1674-3652(2014)01-0017-07
2013-12-27
張 銘,男,四川德昌人,主要從事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李娟娟,女,重慶城口人,主要從事社會生活史研究。